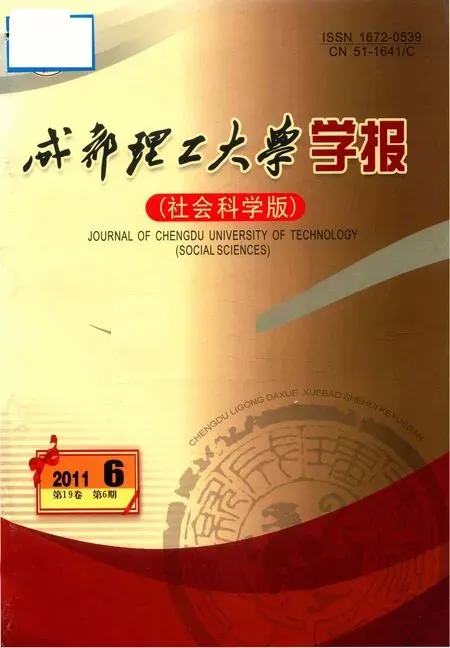论民事二审程序中原告撤诉权的司法适用——兼与李海涛法官商榷
2011-03-31曾令抄
石 珍, 曾令抄
(1.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重庆 408000;2.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 518000)
论民事二审程序中原告撤诉权的司法适用
——兼与李海涛法官商榷
石 珍1, 曾令抄2
(1.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重庆 408000;2.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圳 518000)
私权自治并不能证成二审撤诉权的自由行使,《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57条也不能成为二审撤诉权的规范依据。二审撤诉权必须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的规定》第191条为适用依据。在原告申请撤诉、被告同意撤诉且生效判决尚未确定等要件之下,方可允许原告撤回起诉,且应通过禁止再诉防止原告滥用诉讼权利。
撤诉;撤回起诉;禁止再诉;诉讼和解;私权自治
《法律适用》2011年第2期发表了李海涛法官的《论民事二审程序中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几个问题》一文,李海涛法官以法律体系解释的方法论证了二审程序中原告撤诉权之存在的合法性,此一思路笔者甚为赞同。在各方诉讼当事人达成了和解的前提下,原告有权申请撤回起诉。但是李海涛法官在论证“‘二审撤诉之审查标准的具体认定’以及‘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方式’”这两个问题时却未以一贯之的坚持前述之结论,反而抛弃了“达成和解”方可撤诉之前提条件。(1)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此,本文将对民事二审程序中原告撤诉权的司法适用重新加以阐释,以明晰司法实务中的疑惑。
一、私权界限:二审撤诉权之容许性考量
撤诉又称诉之撤回,是原告向受诉法院表示对其所提之诉不为审判的表示[1],即原告撤回诉讼上请求审理和判决的申请而向法院进行的意思表示。[2]2原告在其以诉讼的形式向法院呈交了要求给予他权利保护的申请之后,如果他不再希望以此方式来解决权利争议,则可以收回他请求法院给予司法救济的申请,这就需要通过诉之撤回而实现。在诉之撤回中,原告并不对他诉求的权利存在与否加以表态,尤其是他并没有否认该权利之存在,这就是其与诉之舍弃的本质区别。[3]153而欲达致诉讼请求被撤销的法律后果,必须以该诉讼启动之人明确提出撤诉申请为要见。其中,诉讼启动之人提出撤诉申请的权利,即为撤诉权。一般而言,撤诉权是诉权的一种具体存在形态,它属于私权的范畴。从当事人的视角来看,这种以当事人自己意思使诉讼程序不依终局判决而终结的权能构成了私法自治之下处分权主义的一个内容。[4]238因此,有人主张,只要撤诉权的行使未损及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其他人的合法权益,则在法院所做出的判决尚未发生既判力的约束力量之前,原告可随时撤回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即便是在二审诉讼程序开始后,如果当事人不想通过诉讼及判决形式来解决纠纷或救济权利,那么作为法院而言,也不能无视当事人的这种意思,进而应当终止程序之进行及做出判决。
然自由以法律为限制,本为该原则应有之义,亦为古代市民法以来的传统。[5]权利乃非个人制度,而为社会制度,即法律认许权利,实不仅在谋个人之利益,而在谋社会利益——故私权之行使,亦必有其适当之范围。[6]他方如承认权利之无限制行使,则有超过权利之社会职分,致有害社会生活,故宜有于消极方面限制其行使之必要,是谓权利滥用之禁止。[7]因此,私权的行使并非一个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治领域,私权自治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权利冲突的矛盾。在民事诉讼这一个完整的空间内,当事人私权利运行的空间与法院公权力运行的空间在运行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张力与对抗,二者运行的空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8]因此,在司法运作的实践中必须对行使撤诉权的容许性空间加以考量,所谓的私权自治并不能合乎逻辑地证成二审撤诉权的存在。
一方面,虽然民事诉讼法具有公法的性质,但由于其解决的纠纷是私权利争议且又鲜明地打上私法的烙印,作为私法基石的意思自治原则因之必然渗透到诉讼程序之中。[9]292其中,私法自治对作为公法的民事诉讼法领域进行成功渗透的直接体现,便为当事人的处分权。当事人提出什么样的诉讼标的要求法院予以裁判、其诉之声明的内容和具体范围如何,均应当由其自行决定和提出,法院不应当干涉和主动予以变更或突破,对于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事实和证据,也应当在当事人提供的范围之内予以斟酌,即使是需要法院进行阐明的场合,如果当事人对法院所阐明的事项不予采纳,则仍然应当遵循当事人的意愿对案件做出最终的处理。[9]288并且,基于当事人关于程序之进行具有主体地位,除了诉讼标的具有实体法上处分权外,关于寻求权利之所在并进而解决纷争之程序,亦具有程序上处分权。[10]也就是说,处分原则的内容是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的综合,包括双方当事人对诉讼的整体进行处分的权利、通过原告的积极主动而启动程序的权利、确定诉讼标的权利以及以申请向前推动诉讼以及提前——也就是说不经判决——结束诉讼等权利。[3]63
另一方面,当一方当事人提出这种终结程序之动议时,还需要调节其与对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而且,对于法院而言,也需要关照“如何不让此前进行的程序完全变得无意义”之问题。[4]238首先,法律作为资源配置的机制,效率的内在价值属性理应得到重视。司法诉讼是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要耗费稀缺资源,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而且同样存在着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11]因此,或许在一审判决之前允许当事人自由撤回起诉并不失其合理性;但若诉讼程序进行到一定程度就不能完全对当事人的撤销权加以放任,否则难免会导致“起诉—上诉—撤诉—再起诉—再撤诉”此等司法资源浪费的循环出现。其次,就判决结果而言,被告难免会对一审判决有所期待,若以意思自治为由不对撤诉权加以规制,则可能损害被告的期待利益。如在“彭长清诉李燕玲”一案中,因为彭长清预先向甲法院提起了确认买卖合同无效的诉讼,故乙法院拒绝受理李燕玲提起确认买卖合同有效的起诉。在诉讼过程中,基于李燕玲准备的证据更为充分,甲法院支持了李燕玲的观点,认定该合同合法有效。而后,彭长清不服,提起了上诉。在二审过程中,彭长清欲撤回起诉。若对彭长清的这一撤诉申请加以认定,那么该合同是否有效的争议依然存在。李燕玲在请求彭长清履行合同协议而需对合同的效力加以主张之时,仍需另行起诉才能解决此一争议。这就使得李燕玲在彭长清提起的确权之诉中,期待法院能对合同效力加以合法判断的利益落空,且此确权之诉不同于侵权之诉。侵权之诉中,被告作为被攻击一方可以拒绝原告的赔偿请求。若原告对此拒绝行为不通过司法救济的途径加以反对,则原告的赔偿请求就不会对被告产生拘束力。因此,被告除了面临再次被诉的风险和花费一定的诉讼费用之外,尚无其他损害存在。甚至,再次被诉的风险可以通过禁止原告再诉的规定加以防范。但是,确认之诉则不同。即便原告撤回了确认合同无效的请求,只要原告不承认该合同的有效性,则被告就必须诉诸司法救济的手段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是说,只要原告不承认被告的主张,就必然会被被告再次提起二次诉讼。即便被告另行诉诸诉讼手段且法院的判决支持了被告的诉讼请求,诉讼的拖延显然也会造成合同履行的过度迟延,从而对被告造成额外的负担。最后,若允许原告在二审中可以自由的撤回诉讼,就可能使得原告在诉讼选择之中投机取巧,显然有违法律之目的。比如,原告在甲法院获得了不利的一审判决,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因形势不妙而撤回该诉讼,并再次以向另一法院起诉的形式规避原审法院对原告不利的事实认定或法律判断。(2)
综上所述,私权自治并不能必然证成二审中撤诉权的存在。是否在二审中赋予原告撤诉的权利,尚需综合各种因素。如果司法权过于谨慎地对当事人的撤诉权加以限制,难免有损权利主体独立思考并不受干涉地安排自己行为的自主性;而若放任当事人自由地处分其所享有的撤诉权,又难免有损其他当事人的权益,且可能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
二、规范审视:二审撤诉权之法律指引
如前所言,私权自治的理论并不能有效证成二审撤诉权的存在。因此,原告是否有权在二审中撤回起诉的评价,则需遵循三段论法的推论。其中,三段论下的大前提——寻找及其内容与意义之确定系法律规定之萃取,[12]222即必须通过法律层面的分析考察在何种情况之下二审撤诉权有着适用的空间。就我国具体法律规定而言,有关二审撤诉权的法律规定分别为《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5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规定》)第191条的规定。若仔细加以分析,可知《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57条不能成为二审撤诉权的规范来源;仅《若干意见的规定》的第191条才是适用二审撤诉权的合法依据。
法律的适用通常被认为系逻辑之三段论法的应用,它以法律规范之一般的规定为大前提,然后再将具体的生活事实通过涵摄过程归属于法律构成要件下形成小前提,最后透过三段论法的推论,导出规范该法律事实的法律效力。作为法律规范的最为直观的表现形式,法条有完全法条与不完全法条之分。其中具备完整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之法律规则的法条,一般称之为“完全法条”,如《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而不完全法条只有与其他法条相结合时才能创设法效果的力量。这种法条或用来详细解释完全法条的构成要件、构成要件要素或法律效果,或将特定的案件排除于另一法条的适用范围之外并借此限制起初适用范围界定过宽的法条,或就法律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的一部分指示参照另一法条,甚至对某些事实加以法律效果上的拟制。[13]138故不完全法条主要包括说明性法条、限制性法条、指示参照性法条、拟制性法条四类。[13]137-144按照上述分类,《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57条均属于不完全法条。就《民事诉讼法》第157条的实际含义而言,它并不意味着在第二审程序中可以适用一审普通程序的所有规定,例如“提起反诉”。且《民事诉讼法》第13条也表明了诉讼权利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进行。因此,若无其他完全法条的存在,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57条这两个不完全法条并不能单独产生赋予原告在二审中撤回诉讼的效率效果。也就是说,只有根据《若干意见的规定》第191条这一完全法条,原告才能在二审中申请撤回起诉。此时,原告撤诉并非完全是其自主决定之体现。根据法律根据,诉讼各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和解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而若原告不撤回起诉,诉讼各方当事人也难以达成和解合意。因此,基于诉讼和解而撤诉的原因力因素,也有被告意思表示的存在。[12]222根据上述的分析,二审撤诉权的适用必须得以《若干意见的规定》第191条为大前提,而非《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157条。
其实,仅在符合《若干意见的规定》第191条规定的法律要件之时,允许原告撤回起诉就符合权利行使的法律目的。撤诉相对于放弃自己的诉讼主张而言,仅仅多了一个再诉可能性而已。就撤回诉讼的动机而言,可能包括以下几种:①起诉的对象错误,如诉讼过程中发现被告并非侵权之责任主体;②诉讼退让,利弊权衡之后,原告不愿意再通过诉讼追究被告的民事责任;③诉讼理由不充分或证据不足,故原告暂时撤回诉讼重新收集证据或等待关键证人;④骚扰被告,原告试图通过撤回起诉再起诉的方式骚扰被告;⑤拖延自身民事义务的履行时间,起诉——撤诉——再起诉的循环可以使得权利义务关系处于可争执状态,从而影响义务的履行;⑥规避不利判决。在一审已做出的判决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原告以撤回起诉后再次提起诉讼的方式,规避某一法院或某一合议庭的对其不利影响的意见。对于起诉的对象错误、诉讼退让的情形,原告若撤回诉讼一般可取得被告的同意,故可以以和解撤诉加以解决;观之骚扰被告、拖延义务的履行、规避不利判决这三项动机,若在未取得被告同意的前提下允许原告撤回起诉,则难免有助长不诚信之嫌疑,且有违公序良俗;至于基于证据不足而撤诉的,若忽视被告之意见,也可能有失公平,毕竟此时原告是否具有规避不利判决之动机,尚无从分辨。并且,如果法院做出本案之判决而仍允许可任意失效,则现法院之努力归于徒劳,将有违诉讼经济,甚至法院被随意嬉弄的可能性也并非不存在。因此,以诉讼当事人达成撤诉的和解合意为前提,方可允许原告撤回起诉,亦符合法律在利益保护权衡上之正当性。
当然,存在不意味着合理。法学作为一门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其基本问题在于在法律判断中经常需要进行价值判断,即不能以完全的以科学方法对某一法律问题加以审查。[13]1对于法官如何借助法律(或者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获致正当的个案裁判之问题,有时尚需凭借法官所独具的智慧与良心加以判断。如果撤销诉讼并未创造了一个“从被告的利益上看不经被告同意就不允许被取消的诉讼情状”[3]100——例如被告既未递交答辩状亦缺席于诉讼程序的情形——那么可以适当允许原告在未征得被告同意的情况下即可撤回起诉。
三、制度设计:二审撤诉权之程序抑制
利益一直被认为是法律制度背后的实质性因素,法律制度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本质上就是法律所调整和确认的各种利益的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良好的法律制度需以协调和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为目标。这就意味着,法律制度的设计必须遵循利益平衡原则,从而使利益体系处于和平共处、相对均势的状态。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法律的权威来协调各方面冲突因素,使相关各方的利益在共存和相容的基础上达到合理的优化状态。这一原则也必然体现到民事二审程序中撤诉权的设置方面。一方面,《若干意见的规定》第191条考虑到了原告的利益,并为原告撤回他所提起的诉讼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如果任由原告在不利的诉讼状况下随意撤回诉讼,随后又允许原告在对自己有利的前提要件下又重新起诉,则显得对被告而言极不公正。[3]15因此,结合《若干意见的规定》第191条的规定,本文认为二审中原告撤回起诉以原告提出申请和被告同意为要件,同时为了尊重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原告撤回起诉的请求需在二审法院的生效判决做出之前提出。具体而言,二审撤诉权之程序抑制的具体要件为以下几点:
(一)二审撤诉以原告申请撤回诉讼为前提
在二审程序开始以后,若原告已经在法院外与被告达成了和解,原告便有可能撤回诉讼。原则上,在生效判决做出之前,或者生效判决做出之后但尚未确定的,原告都可以申请撤诉;生效判决一旦确定,则不能撤诉。与撤回上诉是由上诉人所为不同,二审中撤回起诉仅一审原告始可为之。即便诉讼当事人已经达成了和解协议,被告也无权替代原告向法院提出撤诉申请。并且,原告撤回起诉的申请只能采用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
(二)二审撤诉须征得被告的同意
尽管撤诉是原告对法院进行的意思表示,但一旦诉讼进入二审程序,为保护被告的利益与诉讼效率,原告的撤销行为须经过被告的同意。在这种情形下,是诉讼当事人的合意而使诉的撤销成立,并不仅仅是以原告的申请为其效力发生要件。如果被告不同意原告撤回起诉,而原告经两次合法传唤后仍拒不到庭的,则法院必须针对他发布缺席判决或者依照案卷状况做出裁判。其实,这种限制性规定在外国民事诉讼中,并不鲜见。如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甚至规定,“在被告答辩之后,原告撤诉必须经过被告同意”,且这种规定与法、德的规定也是完全一致的。[2]8
需注意的是,在被告既未递交答辩状亦缺席于诉讼程序的情形下,可以例外地允许原告在未取得被告同意之时自由地撤回起诉。但是此种例外只能适用于非缺席之人提起上诉的情形。若是被告提起了上诉,仍需征得被告同意。若被告提交了书面材料,在辩论准备程序中已经作了申述,或在口头辩论中已经做过辩论,这表明被告已经进入应诉状态,其目的是要利用诉讼谋求驳回原告请求的判决,因而诉的撤销须经过对方同意。[14]另外,如果原告的撤回表示是在书状中做出并已向被告送达,且通过书面方式告知了被告沉默的后果,而该被告在该书状确定的不变期间内沉默,可视为做出批准。
(三)二审撤诉的期间限制
若被告表示了同意,原告可以在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但发生既判力以后就不再允许撤诉。即在双方当事人已经可以协商并依双方之意思终结诉讼之情形下,法院特别需要照顾到如何使双方协商之结果实际地成为双方当事人今后应当遵守的纠纷解决基准[4]238,且尚需不违背生效判决的既判力。
四、效力嬗变:二审撤诉权之实体迁异
从传统意义上撤诉的法律后果而言,原审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申请撤回起诉获得法院准许后,将产生整个诉讼事件不再系属于法院以及导致诉讼程序终结的效果。对当事人来说,不能再请求人民法院按原诉讼程序继续审理此案;对于人民法院来说,也无需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判。[15]并且,已经做出但还没有发生既判力的判决失去效力,不需要明确地撤销;在撤诉之后做出的判决没有效力。[16]967另外,撤诉是撤回已起诉(或者反诉)提出的提供法律保护的请求,它使诉讼系属溯及既往地消失,但并不阻碍重新起诉(在部分撤回时甚至可以在进行的程序中重新起诉)。因为撤诉仅仅是舍弃在该程序中的裁判,并不彻底舍弃该案件中的法律保护。[16]963且从诉权消耗的理论来讲,原告撤回诉讼意味着诉讼程序又回到原来的状态,原告撤诉后表明诉权并没有消耗,仍然可以再次使用。[17]对此,我国《若干意见的规定》第144条给予了符合性的回应。
然而,基于一审法院已经费时费力地制作了一审判决的事实,若允许当事人在二审程序中自由地撤诉而使该判决无效,进而使此前所有的程序归于无效,这将在诉讼经济上构成很大的浪费。有鉴于此,为防止花费双倍的诉讼时间、精力和费用,作为立法而言,存在着以下两种的选择,要么在本案的一审判决做出后禁止当事人撤诉,要么允许其撤诉但撤诉后禁止其提起再诉。这种撤诉之法律后果的嬗变在外国的民事诉讼中并不罕见。前者如属英美法系国家的英国和美国以及属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均以一审宣判前作为申请撤诉的期限,从而消除了二审中原告撤诉的可能性[18]292-293。此时,由于法律对撤诉的时间结点做出了限制,故一般不限制其再诉的可能性。此时,原告撤回起诉仅仅是熄灭诉讼、熄灭诉讼程序,但仍保留其权利。[19]后者如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在诉讼判决确定之前,从一审至控诉审或上告审均可实施撤诉。[18]292-293但是,根据日本民诉法的规定,本案终局判决做出后,撤销诉讼人不能就同一事件再次提起诉讼。[18]286-287日本所谓的终局判决(3)包括一审程序中的终局判决、控诉审中的终局判决以及上告审中的终局判决。其中,一审程序中的终局判决则相当于我国的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尽管日本允许原告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均可撤回起诉,但对于一审判决之后的撤诉行为进行了禁止再诉的约束。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对一审判决做出之后的撤诉权采取了以禁止撤诉为原则、允许撤诉为例外的模式。其中,允许撤诉的前提便是诉讼当事人能够达成诉讼和解。结合以上所述,二审和解撤诉的法律效果应该有别于一审撤诉的法律效果,即承受禁止再诉的后果。
五、结语
和解撤诉制度的确立与适用,不仅使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有了相应的制度保障,也保护作为防御性参与诉讼一方的当事人的期待利益,还能使人民法院得以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合理地利用司法资源。然而在现实状况中,存在着大量突破了和解撤诉的制度设计而允许原告撤诉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二审撤诉权的适用必须得以《若干意见的规定》第191条为大前提,在取得了被告同意的程序基础上方可允许原告撤回起诉。且二审和解撤诉的法律效果应该有别于一审撤诉的法律效果,原则上就同一诉讼应该禁止再诉。
注释:
(1)李海涛.论民事二审程序中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几个问题.载《法律适用》2011年第2期,第78-81页。另外,李海涛法官的举例并不恰当.如原告一般不会对准予离婚的一审判决不服,最多是对其中的财产分配的部分判决不服.
(2)不同的法院对同一诉讼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判决。
(3)随诉讼审理之进行,当达到可以对诉或上诉做出结论之状态时,法院应当及时终结并做出终局判决。
[1]赵钢,占善刚,刘学在.民事诉讼法.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318-319.
[2]叶自强.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
[3][德]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M].第6版.周翠,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153.
[4][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M].林剑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38.
[5]俞江著.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私权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18.
[6]陈瑾昆.民法通义总则[M].北平:朝阳大学出版,1930:386-388.
[7]吴学义.中国民法总论[M].上海:世界书局,1934:176.
[8]张嘉军.民事诉讼契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116.
[9]刘学在.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292.
[10]沈冠伶.示范诉讼契约之研究[J].台大法学论丛,2004,(6):88.
[11]章剑生.行政诉讼判决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38.
[12]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M].第五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22.
[13][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38.
[14][日]中村一郎.新民事诉讼法讲义[M].陈刚,林剑峰,郭美松,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45.
[15]张卫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96.
[16][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下册].李大雪,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967
[17]张卫平,陈刚.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20.
[18]廖永安.民事诉讼理论探索与程序整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92-293.
[19][法]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下)[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044.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Plaintiff’s Cancellation Right in the Appeal of Civil Proceedings
SHI Zhen1,ZENG Ling-chao2
(1.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f Chongqing ;Chongqing 408000,China;(2.Shenzhen Market Supervisory Authority;Shenzhen 518000,China)
Proprietary autonomy can not verify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free exercise of cancellation right in the appeal of civil proceedings,and also the Section13 and Section157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can not be the standard basis of the cancellation in the appeal.The application of the cancellation in the appeal must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ection 191 of the Supreme Court opinion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ertain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Procedure Law.Until the Application for withdrawal of the plaintiff,the defendant agreed to the withdrawal and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such elements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under the ruling,can the plaintiff be allowed to withdraw the complaint,and to avoid the plaintiff’s abuse of the litigation rights,it is not allowed to take the repeat complaint..
cancellation;the prohibition of the repeat complaint;conciliation in the litigation;proprietary autonomy
D925.1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672-0539(2011)06-066-05
2011-09-17
石珍(1985-),男,湖南邵阳人,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西南政法大学宪法与行政专业法研究生;曾令抄(1984-),男,广东梅州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
刘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