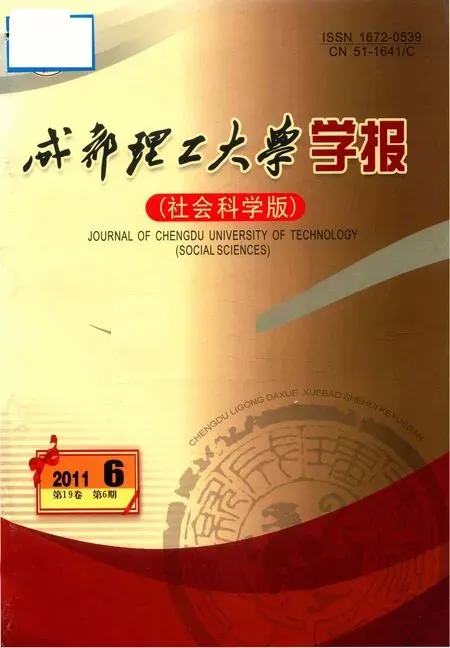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若干争议评析
2011-03-31彭思彬
彭思彬
(福建师范大学 法学院,福州 350108)
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若干争议评析
彭思彬
(福建师范大学 法学院,福州 350108)
2011年4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的立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其间若干自草案公布之初就存在争议而在正式立法中未得到呼应的些许问题、存疑、争鸣无疑还将继续,如选择性冲突规则运用是否妥当、涉外协议离婚法律适用规定有无必要、“没有共同国籍”情形下法律适用是否遗漏,等等。着眼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内在逻辑、国际社会最新立法经验和中国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适用实践,应就以上问题做进一步完善和修订。
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争议
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婚姻家庭关系,即婚姻家庭关系的主体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或者引起婚姻家庭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事实与国外有关。其范围一般包括涉外婚姻的成立及效力、涉外夫妻关系、涉外离婚的条件与效力、涉外父母子女关系及其他家庭关系。
2011年4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是就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的立法,应当说不论是在结构体例的安排还是在内容的臻定上,较原有的立法和草案来讲,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为我国涉外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的实践提供了相对完备和明确的依据。然研无止境,争鸣无疆,其间若干自草案公布之初就存疑而仍得到延续的些许条款、讨论,无疑还将继续。着眼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内在逻辑、国际社会最新立法经验和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适用实践,本文就其中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一、规则还是方法——有条件的选择性多边冲突规范是否应当运用?
选择性多边冲突规则是指冲突规范的系属中包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结点,但只选择其中之一来调整有关的国际民商事关系的冲突规范。其中,可以任意或无条件地选择系属中的若干连接点中的一个来调整某一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称为无条件的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而只允许依顺序或有条件地选择其中之一来调整某一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称为有条件的选择适用的冲突规范[1]。在这种选择性多边冲突规则中,每一个连接点在确定的时候已然都体现了法律能够维护、促进或实现冲突规则所要支持的实体结果、国家政策和立法目的。
《法律适用法》第三章“婚姻家庭”首条规定,“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从冲突规范的技术性来看,这里采用了有条件的选择性法律适用规范。其后该章中的“夫妻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关系”、“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协议离婚”的法律适用都运用了这种有条件的选择型多边冲突规范。
那么这种有条件的选择性冲突规范是否适合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呢?是否适应我国该类涉外法律关系实务的需要呢?在草案征求意见时,这个问题存在若干争议。以涉外婚姻的实质条件为例(现《法律适用法》称为“结婚条件”),有学者认为,婚姻的实质要件适用婚姻缔结地法是一项最基本的法律适用原则,我国应采纳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保持现行立法的连贯性,对涉外结婚实质要件采用单一双边冲突规范,直接规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而无需采用选择性冲突规范。即“结婚的实质要件,适用婚姻缔结地法。”[2]也有学者明确表示,《法律适用法》整个立法有限制行为地法的倾向,不符合国际潮流。例如,结婚、离婚以适用行为地法或法院地法最为通行,因这最易操作。所以应当强调行为地法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婚姻方面。[3]
依笔者见,学者之论和立法条文之迥异,无意中再次凸现了不同冲突法立法价值观之交锋,在这里,欧洲传统国际私法与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冲突法之立法政策摩擦再现。前者强调“法律适用立法的明确性、连贯性、便利性”,而后者侧重于法律选择的灵活“方法”,强调运用这些方法所得的法律选择结果能体现某些既定的目标和政策,学界谓之“规则(rules)与方法(approaches)”的不同。正如学者论,当前的国际私法趋势中,两大国际私法体系已在可能的限度内兼容对方的立法政策,推动了整个国际私法立法的合理化进程,而我国国际私法虽在形式上一直以传统冲突规则为主体,但也应在有限的范围内吸纳借鉴美国现代冲突法的理论和方法。[4]上述观点已成共识,但就此处讨论的婚姻法律适用问题来说,争议的焦点就是选择性多边冲突规则是否超出了这个“有限的范围”,是否适合婚姻法律关系这个具体的领域,是侧重“规则”还是侧重“方法”呢?
笔者认为,从选择性多边冲突规则本身的特点和我国涉外婚姻冲突法立法所处的阶段和应持的立法政策来看,我们在这个领域使用现在规定的有条件的选择性多边冲突规则是可取的,而且是一中立法技术上的进步,这实际上做到了规则和方法的两者兼顾:
细斟每一个选择性多边冲突规则可见,每一个连接点在确定时已然都体现了法律能够维护、促进或实现冲突规则所要支持的实体结果、国家政策和立法目的,可以说借鉴并改进了冲突法革命中产生的“政府利益分析说”等理论,实际上具有了单边主义的某些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它实际上具有了传统冲突规范之法律适用的明确性。巧妙的是,当每一个具有单边冲突规则特征的连接点排列在一起,则构成了包含多个以最密切联系国家原则为指导而确定的连接点之集合,这样则使得审理案件的法官可根据特定的条件选择某个特定连接点,因而是一种灵活的“优选方法”。而笔者认为,最为关键的是,我们此次法律适用立法中采取的是“有条件的依次选择的方法”,这样使得法官在比较多个国家法律的优劣进而做出选择的目的更加明确化。正因为如此,这种选择性多边冲突规则在一定限度内融和了传统多边冲突规则和单边主义方法、优选方法的合理内核,并被有的学者称为20世纪中期后推动当代国际私法革命性发展的“后冲突法革命”。[5]因而在这个冲突法选择规范中,由于“依次的有条件的”保障,“规则和方法”实际上是谐和共存的,堪称完美。
从上述对选择性多边冲突规范的特征分析亦不难看出,其立法意图昭然,即要保护或促进某种实体结果:其一,促进某些法律行为有效成立,如遗嘱、民事行为能力、普通合同等法律行为的形式有效性或实质有效性;其二,促进某种身份关系的成立,如非婚生子女的准正、认知、夫妻关系的确立,甚至促进某种关系的解除,如离婚。而就我国目前涉外婚姻的实际状况来看,由于物质经济生活水平的差距和生活方式、福利待遇的不同,钓个“洋金龟婿”实际上仍是不少国内青年女性的梦想。虽然实践中的确存在若干国内女青年不知对方状况被骗而缔结了“原本不该结”的婚姻,但一旦此种事情发生之后,与其一概确认其婚姻无效致使“赔了青春又折财,竹篮打水一场空”,有些情形下则不如确认婚姻的有效性并依据有效的法律处理双方的实际权利义务,这样恐怕要更能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更符合他们的合法预期,同时对于处于转型中的我国相关的社会关系的稳定也是利大于弊。总而言之,我国目前的冲突法立法价值仍应以“追求法律适用的实体公平正义”为目标,而以“保护本国当事人的利益”为实践要义,以法律适用的“明确、高效、便利”为主要运用的“中间立法水平”。因此,我国目前对涉外结婚的条件采取这种选择性的多边冲突规则不但可行,实际上还应在可能的范围内逐步扩大和运用,如在其后该章中的“夫妻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关系”、“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等法律适用,也都运用了这种有条件的选择型多边冲突规范。这种做法也切合了国际私法立法中相关的最新发展趋势,如《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44条、《德国民法施行法》第13条,均规定了这种有条件的选择性冲突规范。
二、独创还是保守——有限制的意思自治是否该引入“协议离婚”?
本次《法律适用法》最鲜明的独创当属关于“协议离婚”的法律适用规定了。《法律适用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协议离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的,适用办理离婚手续机构所在地法律。”该条不但整体运用了前述的选择性多边冲突规范,而且将有限制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引入离婚领域。“协议离婚”这一规定在当今国际社会尚属首例,从目前我国实践中是否需要运用涉外“协议离婚”之法律适用状况来看,恐怕的确能算得上是超前立法。然而是否需要这样的“独创”,学界也是存在争议的。
详言之,这里应该涉及到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第一,意思自治原则是否应当引入离婚领域?第二、涉外离婚是否合适采取“有限制意思自治的协议离婚”这种我国“独创”?
就第一个问题,在本次《法律适用法》制定过程中,在婚姻家庭法律关系中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理论”呼声较高,这种呼声在“夫妻财产关系”以及“涉外离婚”的法律适用立法中都得到了回应。夫妻财产关系之所以成为意思自治扩展适用范围中当仁不让的领域,不仅仅是因为其本身是杜摩兰早在16世纪提出著名的“意思自治理论”的最初摇篮,更因为其契合了契约关系的部分实质特征。学界对这种扩展基本无异议,只不过对于原草案一审稿中赋予当事人没有任何限制的选择法律的权力提出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在其后的草案和正式立法中都得到了采纳。然而关于意思自治是否可以引入涉外离婚领域,对此似乎一开始就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婚姻符合契约的本质特点”,因而应将意思自治引入涉外离婚法律适用领域;[6]也有学者认为,“一旦婚姻关系破裂,在判决离婚的情况下,总是一方当事人处于主动而另一方处于被动,要么不想离婚,要么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无法达成统一意见,这种状况下希望当事人对法律选择达成协议只能是水中望月。因此,只有在协议离婚中,当事人选择法律作为准据法才具有可行性。”[7]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我国不宜允许涉外离婚采用协议离婚方式,因而没有必要单独规定协议离婚的法律适用规则。”[2]因此,他们自然也不同意将“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用于协议离婚的法律适用了。
笔者认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虽然对“契约”有天然的调整亲和力,婚姻也的确具有一定的契约性,但由于在婚姻关系合理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无论从情感上还是从社会习惯上来看,都几无可能就将来可能发生的离婚达成协议,若于婚姻缔结之初时就做出这种“防范未来”的协议更是令人觉得滑稽可笑,因而婚姻关系中的身份、情感特性首先使得意思自治原则的主要特色及功能——“预知预判”这一特点得不到发挥,因此其在离婚领域的价值几无显现。而一旦婚姻关系濒临破裂诉至离婚的,几乎总是一方当事人处于主动而另一方处于被动,要么不想离婚,要么对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无法达成统一意见,这种状况下希望当事人对法律选择达成协议无异于水中捞月。
那么如若采取协议离婚呢,离婚的意愿和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都可以通过双方协商而达成,是否就有了意思自治原则的用武之地了呢?笔者认为,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类似国内协议离婚中的此“意思自治”非“涉外法律选择”中的彼“意思自治”,前者是就实体内容而言的协议,完成起来虽不能说水到渠成但应当是自然而然,而后者是就相对专业的法律选择,就情感而言,一般情况下心力交瘁或伤心欲绝之时很少可能理智地去选择这种本身司法成本较高、专业性较强的动作;而如若一方仅为了自己的利益预期着力刻意地选择某个法律的话,而这种“刻意”往往极有可能导致本可以协商的实体内容上之协商性遭到破坏,更勿言法律选择了。由于涉外婚姻的特殊性导致在涉外离婚中一方对另一方往往少有共同的“连结因素”,一方对另一方选择的这些国家中往往没有共同的利益预期。
如若上述分析“为情所扰”,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协议离婚的方式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协议离婚的效力一般不能得到外国的承认,在国内法上允许协议离婚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也并不主张涉外离婚的当事人采取协议离婚的方式。这是在涉外法律关系的实践处理中我们必须重视的一个事实。即便是新近颁布或修订的国际私法立法中,一般没有协议离婚的法律适用条款,更没有将离婚的准据法完全交给当事人自由选择的例证。因此从当事人的利益维护和离婚判决能够得到承认的角度,我们并没有多大必要单独规定涉外协议离婚的法律适用。
虽然我们在此次的创新中也运用了“依次的有条件的”可供选择的有限意思自治,但笔者认为,这一立法初衷可能更多着眼于协议离婚中的财产分割问题中的意思自治,而夫妻财产分割实际上属于夫妻财产法律关系问题。就夫妻财产法律关系而言,此次《法律适用法》已经规定了有限制的意思自治,没有必要再专门规定协议离婚中的意思自治。实际上国际上通行的离婚诉讼的标的一般仅限于解除配偶关系,各国在承认他国离婚判决中一般也都仅限于解除配偶关系,而为了保护本国相关当事人的利益,一般就离婚财产的分割等问题需要另行起诉适用法院地法。而关于离婚的意愿和子女抚养的问题所达成的协议很多情况下也可以在诉讼离婚的调解过程中达成。因此我们同样没有必要为了离婚中的财产分割专门规定协议离婚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宜保守而不宜过多“独创”。
三、舍弃还是遗漏 ——“没有共同国籍国”之时的法律适用缺失与偏颇?
《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夫妻人身关系,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第二十四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
上述两条法律适用规则均没有设定当“没有共同国籍的”应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如若这是一种遗漏,有意思的是其后的第二十六“协议离婚”中却不无具细的列举了当“没有共同国籍”时的多种可适用的法律。如若这是一种有意舍弃,那么,不知“夫妻人身财产关系”和“协议离婚”的实际状况中有何差别能让前者舍此种“法律适用”,是否前者基本上不会出现“没有共同国籍”,而后者则较可能出现“没有共同国籍”的情形呢?
倘若没有事实数据的统计,笔者认为上述逻辑推定显然是可笑的。就概率而言,夫妻人身、财产关系发生于每一对夫妻之间,理当包含了涉外婚姻中的每一种的法律状态,虽然不一定每一对涉外夫妻都会发生相关的需要法律适用的法律纠纷,但立法本身需要这种前瞻性以备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之解决有明确依据;而“协议离婚”必然只发生在部分涉外夫妻之间,就算这一部分的比率再大也不可能超过前者,更何况涉外离婚是否合适采取“协议离婚”的方式仍有待商榷。因此,无论是无意的疏漏还是有意的舍弃,未来的法律适用法的修改都应当在夫妻人身、财产关系中加入“没有共同国籍的应如何适用法律”的规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法律适用法》第二十一条中“结婚条件”虽然对 “没有共同国籍”时的法律适用做出规定——“结婚条件,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没有共同国籍,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或者国籍国缔结婚姻的,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但这些规定却仍然让人疑惑。我们不禁要问,假设一对异国年轻夫妇旅行结婚,他们在旅行途中的某个偏远的小国缔结了婚姻,由于双方没有共同国籍,偏偏那个国度既非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也非其一方国籍国,那么倘若发生纠纷,应当如何适用法律呢?因此,第二十一条既然已考虑到“没有共同国籍”的情况,却又为何生硬地增加一个预行又止的“中间条款”,个中缘由让人存疑。笔者认为,下一次法律适用法的修改应该对此有一个明确的回应。
四、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结婚条件”和“结婚手续”之法律措辞妥当否?
《法律适用法》在第三章“婚姻家庭”中第一条和第二条分别规定了“结婚条件”和“结婚手续”,笔者认为这个表述相当的口语化。依据其法律适用规定的具体内容,此处的“结婚条件”应当指的是结婚的“实质要件”,而“结婚手续”则应当指的是“结婚的形式要件”。
然笔者认为,表面意思虽似相同,其立法效果却迥异。现行法律适用法经过四稿草案的审议,遗弃了国内民法理论和国际私法理论界已经惯常使用的“结婚要件”中的“结婚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却仍使用了“结婚条件”和“结婚手续”这样的不严谨的立法语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首先,“结婚条件”本身这个术语,如果不看其法条后面的具体内容,很容易让人误会为“结婚要件”的不规范表达,也容易让人误解为最新的立法又重蹈原来民法通则不区分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而规定结婚法律适用规则之“覆辙”。虽然仔细阅读其法律适用规则规定之后可释疑,但此种非专业的法律术语的表达仍有不够严谨之嫌。而“结婚手续”,依据中国人传统理解,既称手续,总有一定的流程,经过一定的机关登记或其他认可的过程,似乎结婚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必须经过一个特定的程序。然事实恐怕并非如此。使用“结婚形式要件”则不包含这样的意义,其本身指代“是否需要特别的形式要件?”以及需要什么样的形式要件”两层含义。正因为这两种要素世界各地迥异,所以才需要在法律适用中考虑到运用多种连接点来适用。因此运用“结婚形式要件”表述,应当更为合适。
如果认为法律表述尽量通俗化、口语化可以增加法律的普及度或可理解性,那么这种想法未免忽略了《法律适用法》在实践中运用最多之主体是经受过法律基础教育的法官、律师,拿破仑民法典那种“让农民在油灯下阅读”之伟大理想似乎天生不适合法律届的“阳春白雪”之国际私法,至少在当前阶段是如此,而在法学教育中如延续这样的不严谨表达也实为不可取。
除此之外,是否需要明确规定“领事婚姻”也存在不少争议,尤其是实践和教学中我们往往只注重领事结婚,但实际上领事离婚也有相关的棘手问题,如外交部领事司许育红女士在报告中曾提及德国只允许领事结婚,却不允许领事离婚,如此在实践当中应当如何解决法律适用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目前的立法都仍然没有依据。又如在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适用立法中,是否要区分结婚、离婚的条件和效力这两个实际上法律含义不同的状态呢?限于篇幅,其他一些存在争议的问题笔者不再详细论述。
论及至此,笔者深觉,新的法律适用法的颁布绝不仅于定纷止争,而更在于另一发现、完善之旅的开始。
[1]韩德培,肖永平.国际私法[M].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汪金兰.关于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立法探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的相关规定[J].现代法学,2010,32(4):159-172.
[3]陈苇.陈苇教授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征求意见会》[EB/OL].(2010-10-7)[2011-06-28].http://www.swupl.edu.cn/scjy/content.asp?did=&cid=629152010&id=970941859.
[4]徐崇利.规则与方法——欧美国际私法立法政策的比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法商研究,2001,(2):20-29.
[5]郭雪,孟欣.浅析当代国际私法中的选择性多边冲突规则[J].经济与法,2005,(12):130-131.
[6]李寅.涉外离婚法律适用之浅议——从意思自治原则谈起[J].金卡工程 经济与法,2010,(10):74.
[7]林碧冰.我国在解决涉外离婚法律适用问题上的举措[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31(1):115-120.
Discussion on Some Controversies about Legislation Applicableto Foreign Marriage Relationships
PENG Si-bin
(law schoo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hich was put into effect on April,2011 has mad a marked progress on the applicable to foreign marriage relationships.Whereas there still have some disputes about this part which haven't been settled and the controversies will go on in the future,such as whether the adopting of selective applicable rules is proper,etc.The above controversies are discussed here in light of the internal logic requirement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untries and the applicable practice of China in the this area should be born in mind.
marriage and family relations invdving foreign;application of the law;controversy
DF971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672-0539(2011)06-082-05
2011-09-14
彭思彬(1979- ),女,福建宁德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私法。
刘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