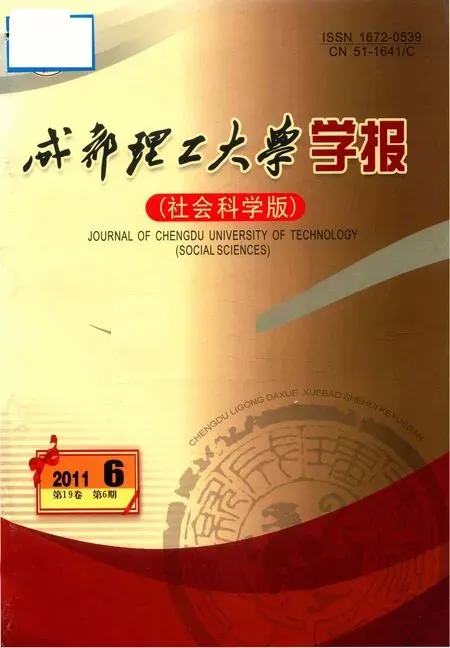从勒菲维尔改写理论赏析林纾的翻译策略
2011-03-31张洁
张 洁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59))
从勒菲维尔改写理论赏析林纾的翻译策略
张 洁
(成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59))
林纾是我国晚清时期的翻译奇才,他的翻译作品典雅流畅,风行一时,因而他的翻译思想、翻译动机、接受环境、对原作的“误译”和“不忠”等都被深入研究和评价。他也因为对原作的“误译”和“不忠”而饱受争议。从翻译学文化操控派代表人物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视角来看,林纾的“误译”和“不忠”往往是他刻意选择的结果,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改写,是他在当时社会文化的操控下,对原作做出的赋予其二次生命的调整,即是林纾在中国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诗学观等因素影响下对西方文学所进行的改写。
林纾;改写理论;意识形态;诗学;翻译策略
林纾 (1852~1924)是中国近代文学史和翻译史上的代表人物,他翻译了180余部外国小说,以娴熟精湛的古文吸引了清末民初的广大民众,为中国人了解西方文学开辟了新的途径。林纾的译作中由于存在大量对原作的改动而饱受争议,多年来,中国文学界对此进行了高度关注,林纾的翻译思想、翻译动机、接受环境、林纾的“误译”和“不忠”等都被深入研究和评价。总体而言,这些研究大多从传统的翻译理论如“对等”、“信达雅”等出发,以原文为中心,关注文本对比。随着翻译研究理论的发展,以以色列学者安德烈·勒菲维尔(Andre Lefevere,1946~1996)为代表的操控学派从译入语文化的视角出发,着眼于翻译中的意识相态、诗学、赞助人等外部因素,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翻译活动,将翻译置于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基于此,本文以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为视角,探讨翻译活动中文化外部因素对于林纾翻译的影响。
一、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简析
勒菲维尔在他的著作《翻译,改写和文学名声的制控》(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1992)中从文化视角出发,分析讨论了各种源语言的翻译作品。他明确指出,翻译实际上是对原作的改写,无论翻译、选文、撰史、批评或者编辑,都是改写的不同表现形式。他揭示了不同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如何操控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改写,他不仅跨越了语言、国籍、民族的界限,还在一个广阔欧洲文化语境下来研究某些文学作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所受到的不同的操控。
意大利有句描述译者形象的著名谚语“翻译者即背叛者”(Traduttore,Traditore)[1]。对此,勒菲维尔辩解道:“永远地删去那句格言吧,翻译者不得不成为背叛者……他们别无选择,只要他们留在自己生来进入或后来移入的文化疆域里就不得不这样做。”[2]翻译者是生活在特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环境中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他们可能会根据需要对原作进行任意的改写,或者说任何一个译者都试图以自己的行为去操控目标语的文化进程。勒菲维尔认为,所有的翻译从本质上而言都是译者对原著的改写,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一方面,翻译作为最明显的一种改写形式,能使一位作者或一部作品的形象体现在另一种文化中,从而具有最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成功的译者实际上操控着原著在目的语中的接受和传播。另一方面,出于身处不同文化背景的原因,译者可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原著进行任意改写,有时甚至他们本人都别无选择或者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这样做。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往往不甘心完全遵从于原著,而是要彰显自己的语言风格,特别是有独立意识形态主张和诗学观的译者更是力图以自己的译作去影响目的语的文化进程,这个过程就是操控。
勒菲维尔认为,文学是一个系统,它的改写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具体来说,内部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外部因素则指赞助人。从内部因素的制约过程来说,当一部文学作品与主流观念相差甚远时,专业人士会出来进行干预和遏制。外部因素所指的赞助人的力量可能指某一个人,也可能是宗教组织、政党、阶级、出版社、大众传播机构等。赞助人最关心的是意识形态,涉及到诗学的问题,他们通常会把处理权力交给专业人士。文化研究学派的开放式研究方法从译者主体性和译入语文化出发,反对翻译标准的固定化和价值判断,这无疑为翻译方法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基于改写理论的林纾翻译策略分析
首先,林纾生活在清末民初,经历了中国从封建社会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衰落。在他不同译作的序跋中,他都对自己的翻译目的做过不同的论述。早期,他顺应当时“西学中用”的社会思潮,输入新思想以开阔国人的视野,唤起民众觉醒。到了晚清,列强入侵,他期望通过译作警醒国人,以求爱国保种。1901年,他在《黑奴吁天录·序》((Uncle Tom’s Cabin)中,首先陈述了美国资本家“酷待华工”、“或加甚于黑人”的现实,又揭露了因国力荏弱,“为使者复馁慑,不敢与争”的岌岌可危的国势,然后他情辞恳切地写道:“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3]196他翻译《利俾瑟战血余腥录》(Histoire d’un Conscript de 1813)之目的,是为了让读者读后“或不至于触敌即馁,见危辄奔”[3]205。在《雾中人》(People of the Mist)里他写道:“非慕思那之得超瑛尼,正欲吾中国严防行劫及灭种之盗也。”[3]232林纾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4]42的强烈责任感,呼吁国人奋起反抗,认清西方列强以吞没为本性的实质。
其次,林纾不仅推崇英国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将这种贴近现实生活、抨击时弊的作品介绍给国人,还输入了西方的文学观念,为中国作家提供了创作的新视角,改变了国人的小说观。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他认识到,西方人重视小说戏剧,且善于利用小说“兼言其政治之得失”[4]43,促使社会进步。他的学生朱羲胄曾说:“……国人乃知西方有文学,……而小说之体裁作风,因之日变,此皆先生倡导不朽之功,国人未之能忘者也。”[5]
林纾的翻译受到时代的局限,他的翻译目的、功能、思想都打上了特有的意识形态烙印,这必然影响到他对原作的处理。此外,由于他的古文功底颇深厚,师从桐城派宗师吴汝纶,因而他十分重视译文的流畅性和接受度,在翻译时下笔如飞,挥洒自如,遇到原作中不符合他的诗学观或意识形态时,也多有删改或增添。
首先,为了使作品符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和主流诗学,他把原文的标题大多改写为“记、传、传奇、录、史”等典型的中国古代小说标题。如《贼史》(Oliver Twist)、《孝儿耐女传》(The Old Curiosity Shop)等,并十分迎合中国传统的“孝、悌、忠、信”的伦理观。据薛绥之考证,他还删掉大量有悖于传统道德观的语句和中国人比较陌生的宗教描写。在《黑奴吁天录》的序言中他写道:“是书为美人著,美人信教至,语多以教为宗。故译者非教中人,特不能不为传述,识者谅之。”[3]196
其次,为了使小说引人入胜,符合中国传统小说的架构习惯,他还常常采用增添的手法使情节连贯易懂,并刻意改变原作中叙事的倒叙、插叙和补叙的描写手法。在《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的译文中,他增添了这样的说明:“外国文法往往抽后来之事预言,故令观者突兀惊怪,此其用笔之不同者也。余所译书,微将前后移易以便观者,若此节则原书所有,万不能易,则仍其文本。”[6]48最后,中国传统小说里对于环境和心理的描写并不重视,读者往往认为乏味,更喜欢以情节和人物语言刻画人物性格,林纾对此类描述也常常采用删节甚至省略的手法处理。如在《块肉余生述》的原文里有100多字对于医生性格的描述,林纾仅译为“医生平惋不忤人,亦不叱狗,名曰赤力迫。”[6]8对于书中许多细致的环境描写,林纾干脆省略,只字不提。
可以看出,林纾的“误译”和“不忠”往往是他刻意选择的结果,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改写,是他在当时社会文化的操控下,对原作做出的赋予其二次生命的调整。钱钟书先生曾这样评价林纾的改写和翻译:“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狄更斯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7]译品的生命力,应该是区别译品好坏的标准之一,林纾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加以补充和润色,首开意译之先河,全然不拘泥于原文的句子结构,他不仅能真切传达原著中的风格情调,其部分作品的表现力甚至胜过原著,深深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三、结语
林纾的翻译活动是勒菲维尔改写理论的完美诠释。通过对其作品的研究,可以看到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对翻译的操控。高质量的翻译活动是赋予作品自主生命的二次创作,译文要受到读者的接受,成为译入语文化的一部分,必须有符合该文化的自主生命。作为一个不懂外文的古文大家,林纾在我国翻译史上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是令人深思的。在研究翻译活动的过程中,文本对照不再是研究的唯一中心,社会文化因素也逐渐受到极大的重视。当然,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不是绝对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是无限扩大的,翻译理论的基本属性是矛盾与互补,每种理论在某些具体的领域都有自己的优势,而在另一些领域则会显得苍白无力,只有采取科学客观的态度,才能给译者一个公允的评价。
[1]王宁.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J].中国翻译,2009,(5):22.
[2]Lefevere 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13.
[3]阿英.晚清文学从钞(小说戏剧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
[4]袁荻涌.林纾的文学翻译思想[J].中国翻译,1994,(3):42.
[5]朱羲胄.贞文先生学纾记[M].上海:世界书局,1949:68.
[6]狄更斯.块肉余生述[M].林纾,魏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14.
[7]钱钟书.林纾的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6.
On Lin Shu’s Transl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y
ZHANG Ji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engdu 610059,China)
Lin Shu was a significant translator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of China.He was renowned for the elegance and fluency in his translations.Many scholars deeply probed into his thoughts,motives,social background and infidelity in translating western literature.Based on Lefevére’s rewriting theory,Lin Shu’s translation strategy was an outcome of his intentional option to give the original works a second life which was manipulated by specific social ideology and poetics at that time.
Lin Shu;Lefevere;rewriting theory;ideology;poetics;translation strategy
K05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672-0539(2011)06-101-03
2011-06-23
成都理工大学研究基金“从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解读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成果之一(2010YD12)
张洁(1977-),女,山东高密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刘玉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