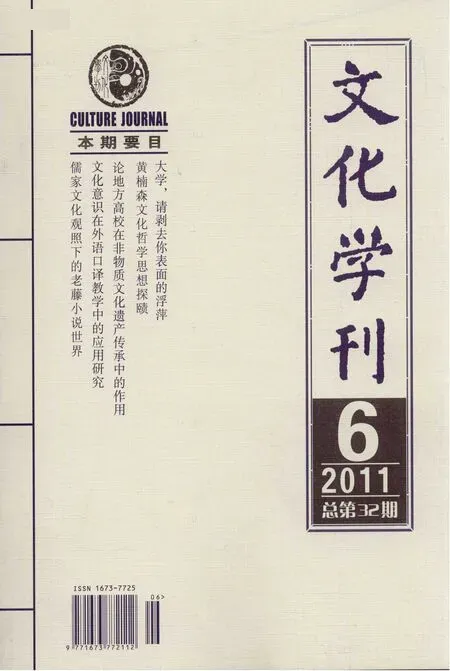从元典看中西人生价值观——以《圣经·约伯记》与《楚辞·九辩》个案为例
2011-03-20蒋金运
蒋金运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圣经·约伯记》被誉为世界文学中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它书写约伯经受上帝的考验,经历了人世的种种不幸,在信仰与动摇的精神矛盾中,痛苦地探索人生及苦难意义的过程。与中国文学里程碑式的作品《楚辞·九辩》比较而言,《约伯记》所反映的是生活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2世纪前后的犹太人的生活状况和心态体验,而《楚辞·九辩》则体现了以屈原、宋玉为代表的中国先秦时代人们对人生目的、人生苦难的思索和经验。人类在面对相同或类似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时会产生大致相同或者说类似的心理和情绪体验,又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地域、民族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人类对人生价值的呈现出各自的特征。比较《楚辞·九辩》和《圣经·约伯记》,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 《九辩》和《约伯记》,进而我们可以全面地把握楚辞和圣经,进而更好地认识中西方文学和文化。
一、正义意识——合理的人生价值取向
对人生价值意义的探索是文学作品书写的永恒主题。在世界不同的文化体系里,文学作品呈现出了各自的合理的人生价值取向。人类的生命价值追求有两种:一是注重人的社会价值,关注人的社会存在,以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人生的价值;二是注重人的个体价值,关注人的个体在世界上的自由存在,将个人的利益放在首位,或者通过远离社会现实,追求一种精神超越功利、世俗的自我,达到自由的境地。人类对这两种有限生命价值追求的心理越强烈,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也越强烈,对实现自我的要求也越迫切。而且,人有生死,生命有限,能否实现或坚持生命价值的追求会导致人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主动追求理想,提升生命的价值,以积极的方式来消解生命有限性的焦虑,这是一种积极入世的生命追求;放弃理想,回避矛盾,超越现实功利,求得精神解脱,这种以幻想的方式消解生命有限性的焦虑,是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追求。
《约伯记》同《圣经》的其他部分一样,核心的观念是赞美上帝、敬畏上帝。我国学者刘洪一说:“圣经中的各部分,无论是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还是其他诗文集,贯穿始终的一个基本主题即是对上帝的各种赞美,对上帝至上权威的论证和维护。这一思想是《圣经》正典中不可动摇的中心思想。 ”[7]如《诗篇》唱道:
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2]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
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
因为他说有,就有;
命立,就立。[3]
《约伯记》中约伯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4]
在《约伯记》中撒旦说:
耶和华问撒旦:“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说:“约伯敬畏上帝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 他必当面弃掉你。”[5]
从引文可知,圣经要求人们维护上帝的权威,但人们敬畏上帝是会得到回报的。约伯的赞美上帝、“敬畏上帝”并不是无故的,他始终是那种“敬畏”的受益者,他和上帝之间似乎存在有一个“契约”:约伯用丰厚的供奉证明自己对上帝的虔诚,又用虔诚带来的物质利益去丰富自己的供奉。约伯是神的信徒和“仆人”,他的命运同神的恩惠密切相关,对神的敬畏可得到儿女、财产和奴婢这些神的赏赐;约伯经受了神的试探考验、认罪自责并得到神的满意欣赏后,约伯立即“从苦境转回”,得到了“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并且馨享延年,“满足而死”。[6]约伯从忍辱到对神短暂的批判怀疑直至重新皈依,表明了一个“好仆人”有热烈而虔诚的坚定信仰,不过这种坚定的信仰是处于神的垄断之中,双方存在着一种供需利害关系,神的恩典和约伯的敬畏,构筑了一只信仰的天平。约伯想得到“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的财产与福寿,必须对神怀有一种执着的敬畏。以敬畏的执着换得神的福佑恩泽,这是一种堕入世俗的执着。
正是这种似乎合理的“契约”和约伯的执着,构成了人类与上帝互相依存而又互相对立的关系,上帝和人类的言行互相诚实正直可信,使上帝成为“义人”的榜样,也使人类乐于争做“完全正直”的“义人”,心目中形成一种正义意识:当给人类提供利益时,上帝会得到人类的敬畏,甚至当“利益”被上帝暂时收回时,受益者也有足够的信心,即“义人会得善报”;当“义人不得善报”而恶人得到上帝善报时,上帝会惩罚恶人的不义之举。这种正义意识是建立在一种互惠互利基础上的合理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建立在“正直诚信”上的理性的道德判断。这种正义意识培养出了约伯的理性批判精神。“乌斯地”“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约伯经历了“丧失儿女、财产”和“全身长满毒疮”撒但的两次试探后仍然对神的敬畏不减,终于经过三轮对话后产生对上帝的怀疑和批判,他说:
我每逢思想,心就惊惶,浑身战兢。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公牛孳生而不断绝,母牛下犊而不掉胎。他们打发小孩子出去,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他们对神说:“离开我们吧!我们不愿晓得你的道。全能者是谁,我们何必侍奉他呢?求告他有什么益处呢?”“看哪,他们亨通不在乎自己,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恶人的灯何尝熄灭?患难何尝临到他们呢? 神何尝发怒,向他们分散灾祸呢?”[7]
约伯在这里呈现了恶人反享平康的事实,通过自己现实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对上帝不公的批判和对神学学说的质疑,挑战了上帝的权威。这是一种超神学的道德判断的“正义意识”的体现。在纯神学的话语中,是非判断 (或事物正负价值判断) 的标准建基在以上帝为核心的神学思想上。对上帝的批判和怀疑实质上就是对以上帝为中心的神学价值体系和价值取向进行挑战。约伯在与上帝的论辩中先关注的是以色列民族的现实利益,不是神学中追求的人生来世那种彼岸的虚幻冥想的利益,不是神学对超功利伦理规范的关注,而是人在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和实际利益的伦理规范,是“人间道德”而非“神学道德”,至此,人间道德的追求同神学道德一样,成为一种具有至上价值的道德追求,就像安森·莱特纳所言,“约伯向上帝挑战,只是因为他把在上帝面前说实话当作是一种道德责任。”[8]需要说明的是,约伯的世俗道德追求也是一种积极的入世人生态度,因为个人道德往往扩展为社会道德,个人道德是社会道德在个体成员身上的体现。
与《约伯记》“义人”约伯一样,《九辩》中诗人通过生活的经验和情感的体验,呈现出了一种正义意识。一方面,诗人诉陈自己为人忠谨、诚实正直,“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9],“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10];另一方面,诗人伤感时势,心系家国,表现出自己的批判怀疑精神。诗中揭露了奸佞误国的黑暗现实,再现了贫士失职的凄苦生活,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愤慨之情。诗人曾一度在楚王身边供职,也有过君臣和谐的美好回忆,“尝被君之渥洽”[11],但接着形势就变了,诗人“以为君独服此蕙兮”,孰料“羌无以异于众芳”,楚王完全是把他作为一般才能的人看待。此时,楚国国内时俗工巧,群小当道,贤人远走,诗人写道,“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12],“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却骐骥而不乘兮,策弩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距跳而远去。凫雁皆唼夫粱藻兮,风愈飘翔而高举。”[13]终于,诗人也失职了。失职之后寂寞的诗人仍时时记起君王往日的宠顾,“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自己身处浊世却保持诗人的高尚节操,决不随波逐流,“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14],只是“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去乡离家外出游宦,但始终希望在仕途上有所进取,很想当面向君王倾诉衷肠,“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15]尽管诗人再也没有得到君王的垂青,但仍寄希望于君王并表示对君王的祝福:“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16]这些都是诗人对自身不幸遭遇的怨愤,对污浊现实的批判以及关于高尚节操的表白。这是一种对正义事业的执着追求。在整首诗中,见不到神摆布的痕迹,见不到对神的顶礼膜拜,人的自由和尊严掌控在自己手中。诗人体现出的对于现实的关怀和积极进取精神,是将人生价值寄托于人生理想的实现,将个人融入社会的积极入世。可以说,诗人批判黑暗的现实,自己身处浊世却保持诗人的高尚节操,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执着追求,这与约伯的世俗追求相比,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生态度。
从上面对《九辩》的分析可以看出,宋玉的忠谨正直、心系国家的社会道德规范关注的是走向衰落的楚国的现实利益,是人渴望报效国家、建功立业心切的现实世界社会伦理规范,即将人的生命价值建基在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非 “神学道德”,是诗人追求的具有至上价值的道德。
《约伯记》和《九辩》这种建立在道德评判标准上的正义意识,说明人类早期共同的人生价值追求和心态体验,反映出两种文化中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二、人本意识——人生的终极追求
人们在人生追求并非一帆风顺,往往会遇到种种挫折。在挫折面前,他们以各种方式或逃避现实,或勇于承受,真正显现出了自己的本质,体现出人生的终极追求。
在《约伯记》中,约伯对神的坚定信仰伴随着一种现实的世俗精神,这是一种在强烈的神学意味之下的渐渐形成的世俗精神。约伯基本上仍是一位有真正血肉之躯的人。当撒旦第一次试探约伯用耶和华的手毁掉了约伯的一切所有时,伏在地上跪拜耶和华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17]这是约伯对现实重压的忍耐承受。当撒旦的第二次试探,使约伯“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经受极度痛苦并接纳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之后,约伯便开始向人“吐露哀情”,诅咒自己的生日,后悔自己的出世,他说:“原我生的那日和说怀了男胎的那夜都灭没”,“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绝气?为何有膝接收我?为何有奶哺育我?不然,我就早已躺卧安睡,和地上为自己重造荒邱的君王、谋士,或与有金子、将银子装满了房屋的王子一同安息。或像隐而未现、不到期而落的胎,归于无有,如同未见光的婴孩。”[18]面对如此的生存困境,苦难中的约伯开始诅咒生日,厌恶生存,这是约伯试图对生存困境的超脱逃避。不仅如此,约伯最终在友人的误解下,要求与上帝理论。约伯不惜自己的生命,勇于与神争辩,“我厌恶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出现了约伯“与神辩论”的义举,对他自身的自由存在的受限产生焦虑,并发出了强烈不满与怨恨,“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19]这是约伯的勇敢抗争。最终约伯降服在他所信靠的人格化上帝面前,“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20]。约伯真正希望的并不是真的将在世的肉体归于尘土,而是渴求重新得到自由的生存空间,重新得到上帝的丰厚恩赐,那些能让他充分享受自由的资本。约伯洞察到了人的在世有限性阻碍了人超越这种有限性的可能性,因而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与焦虑。这种忧虑和焦虑还表现在人的生命短暂、时光易逝看法上,“人为少妇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直等他像雇工人完成他的日子。”[21]生命短暂、时光易逝,阻碍缩短了人充分享受现实世界的自由时空,使人容易形成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和恐惧。
约伯的生命有限性的焦虑主要涉及自己的现时境遇,集中在那些与人的现世生活密切相关的内容上,通过此类的论辩陈述现象、分辨事理,来表述对现行不合理境况的责怨、不满。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和世俗精神表征了神学笼罩下“人”的自觉意识,在反复陈述人的追求和不公平待遇时,都明显地是将“人”作为关注的主体和中心;即使是在抒发人生的虚无甚或诅咒生命,也都与 《圣经》的“神本意识”形成强烈的反差。另外,约伯对神的赞美实际上是对人本身的赞美,因为在古希腊人想象中,神人是同形同性的,“希腊人的神是为着人的利益而存在,所以他赞美神也就是赞美自己”[22]。“人”被提升到重要的地位,人的现世情感和生命体验得到突出和张扬。在约伯身上显示出了一种与神学精神相对立的世俗化人本意识,一种对本我地位个体生命自由价值的寻求。这种以人为本的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的主体精神,并成为人类的一种终极追求,对西方世界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约伯记》作为一篇宗教哲学性的作品,二千多年来不断地在人心中激起了共鸣也正是因为它在“人性”上的自然流露。
在《九辩》中,宋玉面对不遇于君主的失意遭遇和草木摇落萧瑟的秋景,尽情地倾诉着自己的困难、向往和追求,始终贯注着一股强烈的生命忧患意识。
首先,《九辩》诗中叹息的虽是宋玉一人的不幸,歌唱的是个人的悲愁,关注的是个人的命运,具有一定的人本意识,其实最终关注的是诗人的家园——楚国的盛衰。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学派林立,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占主流地位的对个体生命和人生观的思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儒家的人生观,主张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另一种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生观,它关注的是的存在,要求人们彻底摆脱功名利禄、权势地位观念的束缚,通过远离社会现实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儒家人生观是一种较为先进的人生哲学,通过立德、立言和立功,可以使人生有所作为,实现人的社会价值。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否定个人功业,将人生归为虚无,无所作为,不利于社会发展,因此,儒家的人生观成为当时士人的首要选择。宋玉对家园的关注承自于他的前辈屈原,“窃慕诗人之遗风兮,原托志乎素餐。”[23]《离骚》主人公苦苦追求的是美政这项国家的事业,并表示愿为之奋斗献身,全然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屈原在《离骚》中说:“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24]屈原将实现个人生命价值具体落实到国家强盛事业之上,将两者予以统一,并将国家强盛事业的追求作为自己的人生终极追求。宋玉所处的时代同屈原所处的时代却不同。这时楚国饱受战争的摧残,大片国土沦丧,楚国人民处于动荡不安的局面。楚国是否灭亡?国人生存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成为楚国国人关注的焦点。对民族灭亡的恐惧和国运的衰落的感伤,对楚国命运和自身命运的迷茫,在《九辩》诗中书写成孤独的悲秋感叹,“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分草木摇落而变衰”[25]、“事绵绵而多私兮,窃悼后之危败”[26];诗中一切怨愤和批判,也是因为自己同屈原一样处境恶劣、报国无门但心系家国的真情流露,只好哀叹,“窃悲夫蕙华之曾敷兮,纷旖旎乎都房。何曾华之无实兮,从风雨而飞飏?”[27]宋玉将个人的存在意识同家国及国人的存在紧紧联在一起。虽然宋玉没有达到屈原的精神境界,但至少在他的终极追求上是始终与家国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宋玉也有对岁月流逝的忧虑和焦虑。“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悷而有哀叹。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怅而自悲。”[28]诗人悲叹岁月如流,老大无成,一方面,诗人对自身存在关注,为自己年老空虚、栖身无地而忧虑,体现了一定的人人本意识;另一方面,国事多变,自己不能徘徊不前,“事亹亹而觊进兮,蹇淹留而踌躇”[29],体现出为国事担忧的紧迫感、使命感。诗人的人本意识也寄托于家国兴衰的大我。
再次,《九辩》也书写了诗人的反抗,那就是他唯一能采取的隐遁尘世、寄情山水的道路。“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乘精气之抟抟兮,骛诸神之湛湛。骖白霓之习习兮,历群灵之丰丰。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苍龙之躣躣。属雷师之阗阗兮,通飞廉之衙衙。前轻车京之锵锵兮,后辎乘之从从。载云旗之委蛇兮,扈屯骑之容容。”[30]这种举动,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反抗,揭示了诗人非常矛盾的心态和痛苦的境地,“愿沉滞而不见现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愗而自苦。 ”[31]他想“布名”,却又没有机遇,“愿自直而径往兮,路壅绝而不通”[32];他要“沉滞”,可又忘不掉楚王的知遇之恩,“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33]这种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使得宋玉的反抗始终不能采取彻底的决绝态度,而且,诗人还不时地用“中庸之道”告诫自己,“欲循道而平驱兮,又未知其所从。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桉而学诵。性愚陋以骗浅兮,信未达乎从容。”[34]诗人最后只好去外乡游宦、寄情山水,寻求超脱,但缺乏前辈屈原的洒脱,“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35],以死殉国,而是虎头蛇尾,仍寄希望于君王,“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36]。
《九辩》中诗人同屈原一样,意识到了个人的巨大价值,也非常注重发掘人的个体价值,并渴望实现个人价值,只不过将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协调起来,最终使个人融入历史,将个人价值的实现寄托于家国的兴盛事业上,因此,《九辩》所体现出的人本意识,显示出了一种与超越世俗的人本意识,一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将关心国计民生与实现个人价值统一起来。《九辩》中的个人孤独情感,一方面是对人生短暂、时间无限的生命有限性的焦虑的情感抒发,另一方面,是对在有限的生命中报国无门、老大无成的情感抒发。宋玉的这种孤独情感引起了有志之士的感情共鸣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及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等作品中的类似情感。
通过比较发现,《约伯记》中的人本意识突显和张扬人的现实情感和生命体验,不论是赞美上帝,还是与上帝争辩,不论是默默忍耐,还是寻求解脱,都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得到丰厚的回报,将个体生命自由作为人的终极关怀。《九辩》中将心系家国怀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以最大限度地提升人生价值作为自己的人生奋斗目标,无论是揭露黑暗的现实,还是感激君王的恩德,无论是悲叹“春秋逴逴”,还是寄情山水、寻求超脱,都将家国的盛衰与个体生命紧紧联在一起。一种更关注人的个体价值,另一种更关注人的社会价值,这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都关系到如何把握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实质上是一个人的人生观问题,因而也是一个全人类都必须面对的普遍问题以及人类文化、文明的根本问题。
三、共同的心路历程、不同的人生价值求索方式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圣经》和《楚辞》都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原创性的文化典籍。《楚辞》作于前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之间,《圣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我国著名学者冯天渝提出了“文化元典”理论,认为:“如果把一个民族跨入文明门槛(以金属工具和文字发明与使用为标志)之前,称作该民族的‘儿童时代’,把跨入文明门槛的初期称作‘少年时代’,那么,随着金属工具的普及,国家和城市的发展,较复杂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该民族进入创造力空前旺盛的‘青年时代’,而元典正是各文明民族‘青年时代’的创造物……与人的个体生命发展史的青年期颇相类似,各文明民族在其文化发展的‘青年期’也有区别于此前、此后的独特性格和异乎寻常的创造。在这一时期,人们思考的深度已从第一序列进入第二序列,即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开始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作深层次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和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进而反思自处之道,首次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辫证地而不是刻板地,表达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用典籍形式将该民族的‘基本精神’或‘元精神’加以定型。这种典籍便可以称为“文化元典”。[37]据此,中国古老而又影响深远的典籍——《诗经》、《楚辞》、《易经》、《尚书》、《春秋》、三《礼》以及《论语》、《墨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先秦书为“中华元典”,而称《圣经》为“希伯来元典”。《楚辞》和《圣经》作为文化元典的历史地位是无庸置疑的。与此相似,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在对人类文化史进行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说法。他认为,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从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又是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他把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他说: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中国哲学的各种派别兴起,这是墨子、庄子以及无数其他人的时代。……在巴勒斯坦,先知们奋起:以利亚、以赛亚、耳卜利米、第二以赛亚。……这都是在几世纪之内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出现的。[38]
根据这种理论,《楚辞》和《圣经》都是轴心时代的产物。“文化元典”理论和“轴心时代”说法都揭示了《楚辞》和《圣经》所处的相近历史阶段及相似的历史地位,揭示了探求人类基本精神的共同心路历程。
宗教和艺术是人类认识未知世界的智慧和理性的表现,是人类试图摆脱苦难获取力量的方式。《约伯记》作为圣经这部犹太民族宗教经典一部分,是犹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其作品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近千年间。因此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经历几代人编撰、加工和整理逐渐完善而成的;《九辩》是继《离骚》后的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长篇政治抒情诗,是宋玉的个人创作。一个借助于宗教的道德完善,一个艺术的情感宣泄。在人生价值探索的方式上,两者都将有限的人生放置在无限的宇宙长河中去考察,探索人生的奥秘,指示人生的方向。
首先,两者都追寻了人类苦难的原因。《约伯记》表现在“义人不得善报、恶人反享平康”的原因探寻上。在探寻的过程中,约伯以人的立场去看上帝、看世界,“向上帝挑战”,只是因为他把在上帝面前说实话当作是一种道德责任,这是一种求真,真即道德,所以,在观察世界的思想运思上,以一定的理性认知消减或替代神学冥想,以现实功利和世俗道德为判断事物的标尺及价值取向,体现出了一种人文精神。《九辩》则表现在忠臣不得重用、奸佞谗臣得宠上。在探寻的过程中,宋玉以儒家人生观――立德、立言、立功为人生圭臬,强调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巨大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一种求善,善即德。这是肯定、选择了儒家人生观的结果,无疑也是高扬理性精神,进行理性思考的结果。
其次,两者的正义意识都体现了积极的入世上。《约伯记》中的约伯失去家产和儿女,受到毒疮之痛后“与上帝争辩”,最后得到“加倍”,老迈满意而死;约伯对生命短暂、时光易逝的焦虑,是因为害怕人充分享受现实世界的自由时空缩短和断裂。这些表明约伯乐于世俗的、浓厚的人生欢愉。宋玉通过悲秋象征性的宣泄情感,体现出了中国人的坚强意志和温柔敦厚品质,有一种现实生活中的积极进取的精神。
再次,在个人价值的追求上,约伯是利己的,宋玉则是利他的。在《约伯记》中,“契约”中的利益原则平等公平原则贯穿于约伯的言行中,关注的是个人的现实情感和生命体验突显和张扬,关注的是人的个体价值,是一种个人的世俗化的执着追求,而在《九辩》中,儒家的实践理性贯穿于诗中,人生价值的追求同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将人的人生价值寄托于人生理想的实现,将个人融入社会。即使自己身处浊世却保持诗人的高尚节操,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执着追求,更关注人的社会价值。最后要指出的是,以个人价值为人生价值的终极追求与以社会价值为人生价值的终极是两种相辅相成的人生价值观,两者可以互相启发、互相参照。现实的人生和理想的人生是人生价值追求的两极。波兰著名历史学家可西多夫斯基指出:“圣经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是人类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它是一部洋溢着鲜明的生活气息,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伟大作品。”[39]而“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独耿介而不随兮,原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原托志乎素餐”[40]这些言论表明诗人人生价值追求与屈原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是一脉相承、互相印证的。人生价值的追求积淀了一定的人生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内容,表现了人类同各种问题和障碍展开斗争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文化、文明的历史和形态。无论“希腊模式”,抑或“中国模式”,还是“犹太模式”,都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不同形态,不肯等量齐观,值得重视和尊重,正如学者张广智指出的,汤因比在《历史研究》感到,“以往只用‘希腊模式’来套用其他文明的历史,确有牵强之处,也不足以包括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形态,必须再加上‘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并把‘中国模式’与‘犹太模式’等量齐观。”[41]晚年的汤因比对西方社会的现状感到忧虑、不安与失望,他预言西方的优势终将消失,瞻望未来,他把希望寄托在东方,“如果说,二十一世纪是东亚人的世纪,并非惊人之言。”[42]汤因比的言论令世界震惊,更令人深思。
[1] 刘洪一.与上帝论辩——试论〈圣经〉中的人文精神[J] .外国文学评论 1999,(1):73-84.
[2] [3] [4] [5] [6] [7] [17] [18] [19] [20] [21]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中英对照(和合本·新修订标准版)[M] .南京:中国基督教协会 2000.939,867,777,776,834,803,777,779,788,833,793.
[8] Anson Laytner.Arguing w ith God:A Jew ish Tradition[M] .New York:Jason Aronson Inc.,1990.33.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40] 吴广平.楚辞全解[M] .长沙:岳麓书社,2007.307,318,315,312,314,318,307,327,318,009,305,323,312,321,321,327,326,328,315,318,055,327,318.
[22] E.M.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1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48.
[37] 冯天渝.中华元典精神[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5.
[38]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39.
[39] [41] 张广智.克里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196,242.
[42] 汤因比.半个世界——中日历史与文化[M犦.台北:台湾枫城出版社,197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