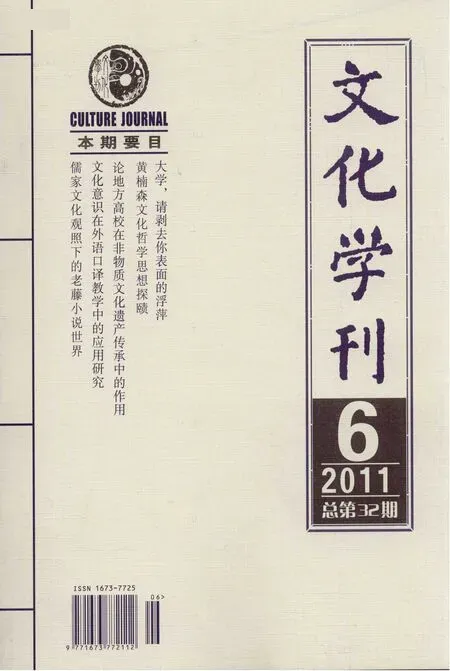试述古典批评当代化的可能性
2011-03-20范小娟
范小娟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众所周知,古典批评普遍运用直观感性的思维方式与言说方式,使具体的批评带有浓重的诗性气质,这集中表现为古典批评家们在具体批评中对“言外之意”的推崇与实践。许多学者由此认为古典批评的这一特点会使许多重要的范畴,如风骨、神韵、气象等缺乏明确定义,出现对其内涵无法得到确切剖析和界定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这种言说方式的模糊性及不确定性正是古典批评焕发新的生命力的前提所在,在学术界处处高喊古典批评现代化、当代化的今天,许多人单一的认为古典批评走向当代的唯一途径就是运用西方理论来解读古典批评,他们没有看到古典批评家们对“言外之意”的推崇就是实现古典批评当代化的重要路径。
“言外之意”强调运用最少的语言表达出最深刻、最丰富的多角度多层次的内涵和意蕴,对作品的批评之言所表达的意是不确定的,其言带有强烈的模糊性与多义性,这正是古典批评具有的独特的审美魅力,而古典批评家对“言外之意”的推崇实际上最早是从道家文化中生发开来的,“道家文化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主要有三方面:虚静其心,法天贵真,言外之意”,[1]从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开始,对“言外之意”的重视与强调在整个中国古典批评史中形成了一条粗大的红线,影响巨大并贯穿始终。继老子后,庄子在《天道》中说“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明确的提出“得意忘言”这一重要命题,而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钟嵘在《诗品》中“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的表达也是对这一命题的发展,到晚唐的司空图认为创作的最高境界在于“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欧阳修也有类似的看法:“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到严羽更明确提出了“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观点,而清人王士禛的“神韵”说得也是对这一观点的继续发展。显然,“言外之意成为创作中的一种自觉追求,并在理论上不断得到充实”,[2]古典批评家们对文学的要求与哲学的最高境界趋同一致,诸如陶渊明所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本文的目的并不在于只是去梳理“言外之意”这一批评观的来龙去脉,更值得提出的问题是,古典批评对“言外之意、象外之致、文外之旨”的强调本身说明古典批评带有强烈的开放性、未来性,这也是古典批评能够走向现代、实现当代化的重要条件。传统批评的许多范畴堪称经典,经典虽意味着难以超越的标竿和榜样,但并非意味着它们是封闭、墨守成规、一成不变的,如“意境”这一重要的批评范畴,其内涵就不可能是生而固定的,而是自其萌芽之初其意义在历代都得到了不同层次的拓展,先秦时“意”与“境”是分开的,具有不同的含义,“意”作为一个文论范畴并未具有美学上的情趣、韵味的意义,而最早将“意”与“境”连起来用的是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格》中,他认为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这里的意境虽与后世审美范畴的意境有诸多联系,但也不等同于后来的意境,而后意境这一范畴的意义在每一时代都得到新的发展与挖掘,直至其审美意义完全成熟,到王国维先生那里成其集大成者,但意境的发展并非到这里就停滞不前了,到近现代仍然有许多文人学者运用新的角度、方法不断对意境这一传统批评范畴做出新的不同层次的挖掘与阐释,同时,意境这一传统批评范畴也在不断地实现其自身的当代化历程。
在具体的批评方法上,由于传统批评对“言外之意”的言说方式的推崇,批评家们通常运用的是感悟式批评,感悟式批评虽然存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缺少科学精神和方法”[3]的问题,但它强调运用感悟与直觉的审美方式,在潜心品尝的过程中顿悟式的直接把握作品的高妙境界,这种批评“在吉光片羽的即兴评说中往往闪现灵思,妙语惊人,使人茅塞顿开,受益匪浅”,[4]钟嵘的《诗品》是第一部诗话作品,他品诗论诗,用的就是这种直觉式思维方法,“在直观感悟中,心与物直接对话而无须以逻辑推理作中介”,[5]他在评价范云、丘迟时说:“范诗轻便婉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看这样的诗,会让人“有一种妙不可言的领悟,感受到甚至比定性分析更清晰的内容”。[6]一方面,这种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直观感悟式批评也为后来欣赏者的解读保留和提供了空间,在《世说新语》中对作家作品的批评就可以充分的说明这一点,在《容止》篇中对嵇康之子的评价“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对王恭形貌的描述是“濯濯如春月柳”,可见,这种以物喻人的批评常常只用一字或几字就能全然将人物的内在素质与外在形貌描述殆尽,诸如松、鹤、山、龙、柳等,一方面这些极简的词语“能准确概括出人物内在品格与精神风貌的某些特点,传达出许多朦胧微妙的审美感受和信息”,[7]另一方面,这样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述方式又充满了难以说尽的多义性和模糊性,它保留了进一步批评的可开发性、可阐释性,给欣赏者留下了诸多想象的意味,更给人留下只可意会、不可言诠的回味无穷的审美享受与愉悦。
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批评方式很有可能造成最初的批评者与后来的批评者完全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后来的批评者可以对最初的批评进行二次、多次的挖掘,从而实现与古典批评的对话和沟通,这类似于西方著名的接受美学的观点,不管怎样,每一时代的理解者必然会受到他所处时代各种因素的影响与限制,通过对传统批评的重新解读,甚至“解构”,传统批评也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产生新的多重理解的可能性,用西方流行的观点,古典批评由此也获得了新的“陌生性”,诸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言,“一部作品能够赢得经典地位的原创性标志是某种陌生性”,[8]因为“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9]这里虽是讲文学作品,但同样适用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独特就在于这种陌生性,传统批评虽被奉为经典,但不可能是封闭的,它只有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审美素质,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最终,不同时代的理解者产生基于与其时代相统一的不同的新的批评与阐释,传统批评也就实现了相对于理解者所处时代的“当代性”,当然,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者同样可以针对传统批评,运用不同的方法视角作出与这一时代相统一的与前人完全不同的理解,那么,古典批评也就实现了我们这一时代的当代化,仍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批评的当代化并不会在今天就终结或是停滞不前,由于古典批评言说方式的开放性,它们会随同时代的变迁而焕发新的生命力。简而言之,由于“其理论文本面向未来并对未来有所期待,期待在自我革新中与时俱进”,[10]那么每一时代的批评者都可能根据其社会历史环境的不同对传统批评有新的阐释和挖掘。
实际上,当代批评的根本价值及其健康的发展趋势是在于建构一个通过古今对话、中西沟通而实现的充满多元化、包容化的批评体系,“批评是对话,是关系平等的作家与批评家两种声音的汇合”,[11]其实,不光是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对话,更有可能是中国批评者与西方批评者、古典批评者与现当代批评者之间的对话,对于后者,就存在一个如何跨越时间障碍的问题,基于这一点,古典批评的当代化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是进行古今对话的基础和前提,而古典批评在言说方式上对“言外之意”的推崇恰恰就为实现古典批评的当代化提供了重要条件,也为实现古典批评的当代化提供了可能。
[1] [2] [5] 李建中.中国文学批评史[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5.
[3] 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三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3.
[4] 蒋述卓.文学批评教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215.
[6] 曹旭.诗品研究[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66.
[7] 熊月华.世说新语品评人物的审美特征及影响[J]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6,(1).
[8] 哈德罗·布鲁姆.西方正典[M] .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
[9] [意] 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M] .黄灿然,李桂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3.
[10] 徐中玉.中国文论的我与他——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第二十七辑)[M]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9.3.
[11] [法] 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M] .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三联书屋,1988.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