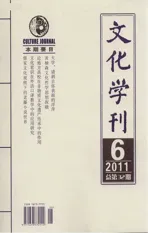略论佛教对唐代图书事业的影响
2011-03-20马小方
马小方
(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福州 350007)
中国佛教发展到唐代进入鼎盛时期,宗派林立且理论充实。唐代佛教的观念、信仰以及处世态度、人生哲学等,在消化理解的基础上,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在文化领域,佛教和中国的文化、文学深深地融合在一起。图书事业作为唐代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
一、佛经翻译和整理事业的空前发展
鼎盛发展的佛教促使译经事业的发展。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成绩可观。太宗贞观三年(629)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才终止,前后译师二十六人。译经制度也更加完善,参与人数更多,规模更庞大,组织更严密,设立了译主、笔受、度语、证梵本、润文、证义、校勘、监护等专门的职务掌管译经中的不同事务。这一时期的译经可谓人材优美、原本完备、规模庞大、组织精密。著名的译经家有玄奘、义净、一行、不空等,中国译经史上四大译经家有两家(玄奘和不空)就出现在唐代,其中,玄奘法师曾亲至西域,后所携来经论六百五十七部,使我国佛典的翻译如日中天。“玄奘之广弘大乘,义净之专重律藏,……其文字教理之预备,均非前人所可企及也。”大量的佛教典籍翻译过来,无疑成为唐代藏书的重要来源。
统治者也十分重视佛典藏量,不仅大量翻译佛教经典,而且用官费从事写经活动。唐代写经活动规模很大,据统计,自太宗到德宗年间共译出经、律、论等428部,2612卷。如唐太宗分别于贞观五年(631)和贞观十六年(642)“敕法师玄琬于苑内德业寺为皇后写佛藏经”、敕“为穆太后写佛《大藏经》,敕选法师六人校正”。又如: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去世后,武则天发愿敬造三千部《妙法莲华经》、《金刚经》为已逝父母祈福,此次写经活动持续了七年之久。
1900年6月22日,中国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问世,据统计其中佛教经卷、写本约有25000多卷,且大多为唐代的作品。唐代的佛典藏量可见一斑。
唐朝佛教翻译规模宏大,典藏量高,藏书处也星罗棋布,遍布都邑山乡,政府为此建立了专门佛教藏书机构,使得经藏制度在唐代得以完善成熟。唐代诸多寺院皆为佛经典藏处,大寺都有经藏、或楼、或阁、或院、或堂,经藏内的藏书,排架有序,还专门有主藏僧管理。大量佛教翻译作品直接影响图书内容和数量,不仅增加了藏书量,而且丰富了藏书品种。
佛教经典的汉译不仅促进佛法的弘传,同时也充实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佛教经典中富有文学价值的佛教经典极多,如描写佛陀的生平事迹的《普曜经》、《维摩诘经》;采用许多譬喻故事,阐扬佛法妙义的《法华经》;采用梵文韵体叙述佛陀一生故事的《佛所行赞》;四、五、七言格律合用,文字生动精彩的《佛本行经》等,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影响极大。
二、繁荣的唐代佛教文学
(一)佛教经典著述
自两晋南北朝开始,中国僧人就已有了自己的著述,从经序、注疏、论著以至目录、史传的编撰,丰富和发展了“三藏”的内容。此后中国僧人的著述不断增加,至唐代佛教撰述之丰富,数目之繁多,难以具列。初唐时的类书《法苑珠林》,言及中国僧人著述有三千余卷。尤其是开元年间,撰述作品应该十分丰富,据《新唐书》载:“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粗计《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唐代著作2125家、2304部、40065卷,其中释氏94家,1300余卷。
(二)佛教题材作品
首先,文人创作出大量的佛教题材作品。唐代官僚文士中很多如权德舆、韦应物、白居易、孟浩然、王维、柳宗元、李白、贾岛、穆员、刘禹锡、李贺、韩偓等等,皆信仰或者不同程度地支持佛教。佛教的教义、教理也深刻地影响着唐代文人的精神世界,也为文人的文学创作提供多样的灵感、意向和题材。反映到作品中就产生了诸多佛教题材的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士人与佛教的广泛联系,如游历、交往、赠答等,诸多与僧人的广泛交往也大量地反映到诗歌中,《全唐诗》中此类诗多达二千首。唐代的很多作家的作品中也都有佛教影响的印记。《全唐诗》里中国文人有佛教有关的作品就达两千多首,或诗题直接与寺塔或僧人有关,或诗题未体现但诗中有与佛教相关的词语。有的在诗中直接讲佛理,如李颀《宿莹公禅房闻梵》“始觉浮生无住着,顿令心地欲昄依”;有的则表现禅机,如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全唐文》中直接与佛教相关的作品也比比皆是,就拿佛教净土宗来说,文中仅仅题名直接相关的就有百多篇,如苏颋《净信变赞》(《全唐文》卷二百五十六)、王维《西方净土变画赞(并序)》(卷三百二十五)、王维《西方净土变画赞(并序)》(卷三百二十五)、李白《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并序)》(卷三百五十)、任华《西方变画赞》(卷三百七十六)、权德與《画西方变赞》(卷四百九十五)、白居易《画西方帧记》(卷六百七十六)等,不尽枚举。
其次,僧人也创作了很多的文学作品。这在诗歌领域的表现尤为明显。受空前发达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唐代世俗诗人之诗多为咏僧的题材内容,而僧侣中能作诗者亦比比皆是。尤其是在中唐的大历时期,诗僧辈出,蔚然天下。《全唐诗》卷806至卷851所收皆为僧人之诗,收了一百一十五家,共四十六卷,两千八百余首,约占《全唐诗》的二十分之一。刘禹锡曾在《澈上人文集纪》中列举了一大批的诗僧,又在《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诗序》中说:“自近古而降,释子以诗闻于世者相踵焉。”虽然唐以前也有僧人写诗,但无论是诗僧还是僧诗的数量都相对较少,东晋至隋代近百年间,有诗僧仅四十余人,且作品寥寥,而唐代无论诗僧人数之众,还是作品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的诗篇成为全唐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类诗歌加上文士所作的咏僧等作品,竟占 《全唐诗》总数的百分之十左右。
佛教在唐代的广泛影响,直接拓广了文学的体裁,丰富了书籍的内容。俗讲与变文,就是这时出现的新文体。文学作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无疑丰富并充实了唐代图书事业的内涵。
三、蓬勃发展的寺院藏书
唐代寺院藏书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有唐一代图书数量增长极快,与佛教的发展和寺院藏书有直接的关系。唐代的东林、西明等著名的寺院,都藏有大量的佛经。
寺院藏书的发展是寺院佛教活动影响的结果。寺院是弘扬宗教、讲经说法、修身养性的场所,藏书也主要以佛家典籍为主。寺院时常组织辩经、讲经活动,寺院会将这些活动中的各种资料加以整理、抄写成书,有时一些高僧亲自参与,促进了藏书的发展。唐代佛寺藏经十分丰富,史载初唐的西明寺,有藏经三千三百余卷,其藏书至龙朔初年达5000余卷;中唐的庐山东林寺,有图书一万卷。
由于唐统治者信奉佛教,因此受宗教风气的影响,很多居士文人与僧侣交往甚密,甚至将自己的文集赠于寺院收藏,而且“天下名山僧占多”,绝大多数名山都有寺院,远离尘世的地理优势也利于保存文化典籍,是颇为理想的藏书之所。白居易就曾分藏自己文集于圣善寺、东林寺、南禅院,并将自己的文集赠于香山寺、东林寺等,仅在龙门香山寺的藏书就多达5270卷,此举无疑丰富和发展了佛寺藏书。
唐朝写经活动,为寺院藏书打下了基础,刺激了寺院藏书的快速发展。官方写经如上述唐太宗与武则天之例,规模宏大,唐代宗时曾从宫里拉出两车《护国仁王经》送给资圣寺、西明寺。至于民间的抄经、诵经更是达到惊人的地步。
此外,中国僧人的著述、中外佛家弟子的交流以及名士的赠藏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且唐代中外文化交流日频,佛僧交往尤其明显,往来僧人多携经书翻译研究,如玄奘归国时就带回经论657部。
寺院佛教藏书也是国家图书馆——秘阁佛经藏书的一大来源,同时为国家编纂工具书的组织活动提供丰富的文献支持。唐代诸多的寺院皆为佛经典藏处,且有专门的主藏僧负责管理经书,其藏书自身的整理工作,又产生了大量佛经目录。
四、成果丰富的佛经目录
唐代佛教的发展亦在目录学中得到反映并影响其发展,应该说佛教丰富并完善了唐代图书目录和分类学。
随着佛经翻译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约在公元二世纪后半叶就已开始了汉译佛经目录的整理,随后,由于统治者的鼓励和组织,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目录学著作。官修目录中西晋荀勗的《中经新簿》已经著录佛经,发展至《七录》已经对换了《七志》中道、佛两类的位置,先佛而后道。
唐代鼎盛的佛教衍生出数量众多的佛教经录著作,如贞观初年玄琬所编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显庆三年(658)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龙朔三年(663)静泰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等。另外更多带有经录性质的,如麟德元年道宣编《大唐内典录》、靖迈撰《古今译经图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明佺等编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开元十八年(730)智升撰《续大唐内典录》,后又编 《续古今译经图纪》、《开元释教录》、《开元释教录略出》,贞元十年(794)圆照撰《贞元续开元释教录》、十六年(800)又编成《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同时有华严寺沙门玄逸对于入藏各经的卷次、其目详加校定而撰成的《开元释教广役历章》。批量出现的佛经目录中包含着许多版本学、目录学上的创新之举,促进了版本学、目录学的发展与成熟。
这类经录中价值较高,在我国目录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是唐开元年间智升编撰的 《开元释教录》。它质量精美,分类更精密,且子注详细,成为唐代及后世一切写经、刻经的依据。此经录凡二十卷,分“总括群经录”和“别分乘藏录”两大类,“别录”的最后两卷为“入藏录”,收集经籍1076部,5084卷,集前此经录的大成,并首次将中国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智升还在《开元释教录略出》中创用以千字文编次的方法,这对于卷帙浩繁的佛教典籍的整理、庋藏及检索等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后来我国第一部木刻版大藏经《开宝藏》就是据此雕印成书。
后世学者如梁启超、陈源等都给予《开元释教录》很高的评价,综合说来它分类体系严谨完备,代表了佛经目录最大的目录学成就;著录详尽,充分发挥了目录学的推荐作用;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等等。
五、书籍制度及图书版本学的新发展
佛教刺激了唐代书籍制度及图书版本学的新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书籍装帧形式的变化。在唐代,书籍制度由旧形式向新形式的发展过渡中,佛经文献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受印度贝叶经形式的启示,经卷改为经折装,又称梵夹装。此后演化为旋风装,从而进一步产生了册叶制度的最早形式蝴蝶装。由于佛经这一契机,书本的编纂体例和装订形式有了创新和发展。(资料待详实)
其次,图书出版事业的正式出现。佛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佛教经典的大量需求,佛教信徒通常把写经视为“功德”之事,写经越多,功德越大。唐代社会对于佛教崇信之风已达到空前的境地,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宗教宣传的大量需要,因此只靠抄写传录显然境界已经不能满足对佛教经典的大量需求,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在客观上对印刷术的产生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具有便捷、快速的复制大量复本特性的新技术——印刷术便在这一背景下得到应用和发展。
唐代社会上的印刷品,内容已十分广泛,其中的珍品多为佛经文献。1990年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佛教经典就占总量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其中许多印刷珍品都在中国乃至世界印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有学者还认为佛教徒是雕版印刷的发明者,只是雕版印刷产生的具体时间还不能确定,但唐初已有雕版印刷品流行是不争的事实,咸通九年的《金刚经》、武周时的《妙法莲花经》等已是十分成熟的雕版印刷品。可以说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兴起,促使我国古代开始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图书出版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