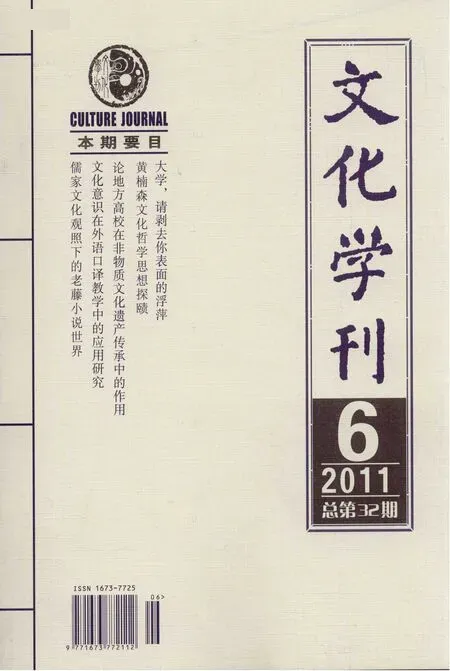作为权力反思文本的《白豆》、《白麦》
2011-03-20刘希
刘 希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香港 999077)
《当代》杂志2007年第三期刊登了作家董立勃的长篇小说《白麦》,这是当年倍受好评的“西部传奇”《白豆》的续篇。董立勃展示了西部垦荒背景下女性的婚恋悲剧和人性美丽,更表达了对权力体制中人性走向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下野地农场中来了一批“支边”的青年女兵,白豆和白麦一对姐妹在这片特定的政治领域中,开始了多舛的命运和情感的历练。《白豆》中的人物辅线“白麦”在这部后续小说中浮出,继白豆心灵成长之后,白麦也在生活的打磨中开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开始了心灵的逃亡和对一种权力体系自觉地疏离。在那样一种组织做媒、政治成婚、女性没有主动选择权的年代里,白豆白麦两人的自我觉醒都是由生活的启蒙而来,并经历了从对“组织”和那一套政治话语的真心服膺到对它们的怀疑和背弃。白豆在自己的婚姻上从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干部”听凭组织安排到挣脱权力操纵,从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生活苦难中有了自我意识的复苏,坚定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白麦比白豆长得漂亮,被选做军区首长老罗的夫人。作为一个“得益者”,白麦也从对“组织决定”的充分信任到自己挺身而出营救被冤枉的白豆的丈夫胡铁,开始了背弃“组织”的一种个人抗争。同时在这过程中,白麦也和白豆一样遇到了真正的男子汉。作为西部广阔地域上的自由灵魂,这些男性凭其勇敢、正义、有担当的人性魅力和他们深爱的女性一起成为这边荒野地上的动人的传奇。
白豆、白麦二人的思想转折是两部小说中的关键,不过这种自我觉醒倒并非是爱情的启发,而这正是董立勃小说的核心价值所在——作者并非是要塑造两个主人公的“女性意识”,她们的醒悟只是因为她们在生活的昏聩和残忍面前有一种对人的基本尊严的肯定,对公正的追寻和对事实真相朴素而坚定的秉持。与其说她们是“为我”,不如说是一种“无我”、“舍我”给了她们正直而勇敢的人性光辉。白豆在得知玉米地里的强奸真相后义无反顾地为冤枉的胡铁奔走,一种要补偿而嫁给他的心理产生于在他们萌生出真爱之前。白豆几经碰壁但始终没有放弃,可以说,是那种公正的不得实现促使她怀疑自己曾经百般信任的 “组织”,是在对那种公正追寻的过程中才开始一种个体精神的复苏,个人选择的肯定和个人幸福的追寻。
对于白麦来说,她最终主动提出与首长 “老罗”离婚的关键原因是老罗作为组织权力的化身并不愿帮助胡铁脱离困境,反而利用职权为自己开脱嫁祸于李山——也就是出于对 “公正”的怀疑。对正义实现的努力促成了白麦对丈夫的冷眼审视,她脱离这场自己曾经深深受益的政治婚姻寻求自由,并不是因为自己对李山产生的美好的情愫,也不是因为老罗没有选择留在下野地做一个正常的老百姓。“下野地”比之乌鲁木齐首府,是不仅仅只有一种自由生活的,白麦的选择更多是出于她在这种权力体系中对那种个人专断、残忍冷酷的深刻感受,出于她对那种“政治上的成熟”的自觉的疏离。
因此可以说,与其对着白豆白麦两个女性大谈自觉的女性意识,不如更多地看到她们在漠视个人权利的 “革命”时代语境中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对作为人的基本处事原则的正直感和女性身上那种天然的善良,仁义和自我牺牲。白豆对“接纳了不洁的自己的老杨”的感激,对冤屈的胡铁的感情,白麦对蒙难的老罗的扶助乃至为了他屈身于“造反派领袖”杨来顺,都闪烁着人性中最美好的光芒。
但是从女性视角看去,白麦用极端的方式救助“有恩于”自己的老罗,自觉地将自己贬低与男权社会所规定的“道德劣势”,却可以说不自觉地达成了与男权的合谋。在老罗得知白麦委身于杨来顺后,白麦请求老罗动手把自己杀掉,但又说“对你来说不值,会脏了你的手,会坏了你的名声。”“这个错,男人不会原谅”。联系白麦之前“把自己一生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的不由自主的动作”,白麦那种用男权道德对自己的审判也许更多与她在这张政治婚姻中的依附地位有关。白麦的这种悲壮的献身,这种“仁义”让人震撼,同时不能不令人悲叹。
然而,可贵的是白麦最终还是象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样地“出走”了,在脱离家庭的过程中,白麦竟和娜拉有着一种惊人的相似。她们都是通过主动付出,独立担当责任达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并在这一过程中认清了男性的对女性摆脱依附地位的潜隐的恐惧。可是说比之娜拉,白麦多了一种对“组织代表”老罗的权力专制、男性专制合二为一的体认。当娜拉不愿再做男人们“玩偶”的时候,经历过文革这场荒唐而丑恶的人性闹剧的白豆白麦们又何尝看不到人其实也很容易变成一种 “权力的玩偶”呢?
“白麦在心里认定,老罗还是老罗。经历了一场劫难的老罗,还是劫难前的老罗。”所以白麦在老罗脱离危机重新当政后没有再做别人艳羡的“首长夫人”,她坚决的离婚决定回归了了个人的价值和意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组织”无所不能的神话。
相对于小说女主角们从生活的磨难中一点一滴实现自己对权力的疏离和对个体价值的回归,小说中批判的男性们似乎都是紧紧把权力和欲望抱在一起。这种权力与欲望的合谋,表面上却披着冠冕堂皇的政治话语。马营长希望运用手中的权力占有白豆,但他却用“组织帮助”“恋爱自由”的名义给自己的行为建立合法性。不同于胡铁自始至终为个人幸福与“组织”抗争,杨来顺这个同样追求白豆的男人,当他是平头百姓,处在权力外围的时候,虽然自觉服从政治权力对白豆的安排,但却一定要通过对白豆的施暴实现自己男性权力,而一旦文革开始,杨翻身做了造反派进入了权力中心,他的权力不仅使欲望合法,而且欲望的倾泄变成权力彰显的标志,杨一定要得到白麦不仅是要发泄欲望,更是对自己这个造反派首领的权威的认定。
杨来顺的形象让我们想起了苏童《罂粟之家》中的乡间流氓陈茂。当杨来顺作为造反派向“反革命走资派”革命时,陈贸是作为乡间无产者向地主进行土地革命,但相同的是他们操纵的权力更多地导向了对于对方女性的性占有。陈贸把强奸地主女儿当成暴力推翻阶级,身体暴力即革命暴力;杨来顺则把政治权力和性权力紧紧结合在一起,权力欲望与个人欲望同构,于是,两篇小说都通过这种男性欲望的投射实现了对“权力”的反讽。
《白麦》中还有一个核心男性,老罗。这个“老首长”、“老革命”相对于私欲集身的杨来顺形象更为复杂。首先,老罗在权力实施的过程中同样潜藏着一些男人阴暗的私欲。他偷偷给不知情的白麦做绝育手术;他在知道白麦为胡铁奔走而失踪的消息后做出“不杀(胡铁)不足以平民愤”的决定,而实际上背后有着对白麦强烈的解救胡铁 (不服从组织纪律的人)的自由意志的极大反感;他对李山的劳改判决,表面上说“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是必要的”,实际上也是出于对年轻英俊的李山的嫉妒和可能与白麦产生私情的恐惧。
老罗的人生原则只有一种,那就是 “革命原则”和“组织原则”,并无个人价值个人权力的空间。老罗最后承认胡铁“不是一个坏人”,但也坚决地认定他却是“一个反革命”,且而自始不肯认错。“我没有错”,他说。政治的机制和逻辑早已深深内化为他的行动准则,甚至排除了人性化的视角。“我不能因为他救了我,我就不讲原则了。我在党旗下宣过誓,为了党的事业,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我怎么可能为了报恩,朝反革命分子低头认错。”在老罗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不近人情”的革命机器。
老罗一直让人反感吗?《白麦》作为《白豆》的续篇,渐渐将老罗向圆形拓展。在小说高潮部分的戏剧性场面:造反派与白豆白麦两个两军对垒之时,老罗的光荣革命历史当即浮出,此时,他也是一个不亚于胡铁的英雄形象。曾经骑兵团的团长,曾经“出生人死”,“为了共同的理想流过血”,他以一种“冬天将会过去,春天就要到来。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绝不会让江山被坏人糟践”的理想主义的信念,重新指挥这些当年的骑兵打败了造反派,实现了那种老的“红色”对这种新的“红色”的胜利。我们可以说老罗这种坚信自身权力有着“革命正义”的思想是种可怕的“左”的东西,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一种形而上的真诚信仰是怎样融入进这种炽热的革命理想的。文革后老罗重新当政,“文化大革命让他明白了群众的伟大,明白了要做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就要确实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那么,我们会赞颂老罗的结论吗?老罗与他之后的“革命领导人”之间真的只是一种从天而降的断裂,他的遭遇真是只是全然的无辜吗?老罗被杨来顺打成“反革命”和老杨把胡铁打成 “反革命”不是不同样的可怕呢?老罗为什么没有经历内心的劫难,没有更深的反思呢?这是我们在《白麦》中无法止步的。
文革过后,权力体系实现了新一轮的升降浮沉。“经历了一场劫难的老罗,还是劫难前的老罗”,然而经历了几场劫难的白豆、白麦们,却再也不是懵懂单纯的白豆、白麦们了。她们经历了权力的支配和束缚,却在生活的磨难中因秉持最基本的人的尊严而渐对权力怀疑,抗争和疏离,从而在这种宏大的政治语境中真正作为一个个人自我觉醒起来。《白豆》刚出来时,董立勃曾经在他的《人性的冲突最好看》一文中说“在白豆的身上体现了我对女性的理想,甚至是对整个人类的理想。……她身上洋溢的人性美,是人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它和时代,和政治,和时尚,和贫富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人,都会被这种魅力所吸引。”比之于小说中在政治中心浮沉的杨来顺老罗们,白豆、白麦们作为这个权力网络中突围逃逸出的女性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人性美的慰藉,更有一种让我们对于权力和权力意识的冲决和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