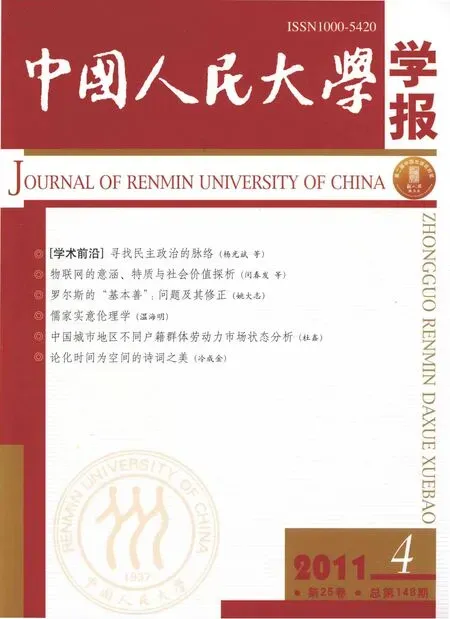卢梭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和普遍意志*
2011-02-10崇明
崇 明
世界、国家和个体的关系是现代人确定自我认同的视域,甚至可以说现代性的演变就是在这些关系中呈现的。卢梭的政治思想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对这些关系的思考中展开的。卢梭试图为人类的政治和道德奠定坚实的基础。他和其时代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承认存在着普遍人性和普世道德,但并不相信人类能够和应该生活在一个具有主权的世界城邦当中,也就是说,他不认为可以通过世界城邦来实现普世道德。这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对历史和当时世界的观察而得出的现实主义结论,而且是因为他认为人的政治本性决定了人必须在局部的、特殊的共同体中生活。虽然卢梭拒绝了世界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民族共同体不可以成为人类普世道德的载体。事实上,如果不是在民族共同体中落实普世道德,后者将流为空谈。卢梭指出,政治共同体应该在普世道德的基础上建构属于自身的普遍意志,通过公民身份实现人的道德。社会形成之后,自然个体与他人建立关系并经过社会生活的转化成为社会存在,然而个体在自然状态中的自爱转化为一种利己自爱,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可能堕落为比自然个体远为恶劣败坏的存在,必须通过共同体意志的普遍性来克服个体意志的偏私性,实现个体作为公民和道德主体的自由。所以,共同体的普遍意志是人类道德自我发现和生成的重要途径。此外,每个政治共同体都是有着特殊历史和性格的存在,普遍意志本身只有与这种特殊性相结合才具有生命力。
一、普世博爱和人类普遍意志
卢梭一直对普世道德持某种复杂的态度。他虽然承认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道德并且视之为人类道德的尺度,但他始终没有充分阐释这一道德对于人类的真正意义。在少年时期,卢梭对普世道德的这种模糊态度就已表露出来。在十六七岁时写作的一个关于普世历史的文本中,卢梭指出:“我们所有人都是兄弟,我们的邻居对于我们而言像我们自己一样珍贵。著名的费奈隆说过,我热爱人类甚于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甚于我的家庭,我的家庭甚于我自己。如此充满人性的感情应当是所有人共有的。”[1](P488)普世博爱为爱确立的先后次序为人类、祖国、家庭和自我。但接下来卢梭指出,我们同样有理由关心自己和身边的人与事,这两者并不冲突。我们是普世大家庭的成员,要了解这个大家庭就必须了解其成员;而且每个成员无论其力量大小,他在这个大身体(corps)中都是有用的。卢梭从普世性自身的正当性以及普世的人类存在和作为其成员的个体之间的必然联系来论证个体自爱的正当性,把个体自爱的正当性建立在个体对于整体产生的效益上。
在给《百科全书》写的“论政治经济”词条中①该文最初刊登于1755年11月出版的《百科全书》第5卷。,卢梭区分了政治体(le corps politique)和世界各自的普遍意志。卢梭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后来在《社会契约论》中详细阐发的普遍意志(volontégénérale/general w ill)②笔者认为这一概念更为恰切的译名是普遍意志而非中文世界熟悉的公意。这一概念从上帝的普遍意志发展而来,经过卢梭的转化旨在表明由共同体所有成员共同形成的、针对每个成员的普遍性的意志。普遍性突出所有人的全体参与以及针对全体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公共性则更多的是针对私人性。概念:“政治体也是拥有意志的道德存在;这一普遍意志以全体及其每个部分的保存和善好为目的,是法律的源泉;它对于国家的所有成员而言,无论就他们彼此的关系以及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来说,是正义和不正义的准则。”[2](P245)从这个界定来看,普遍意志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体的灵魂。然而,这个意志的普遍性只是相对于政治体的成员而言的,对于其他共同体来说,这个意志则是个别的:“尽管国家的意志对于国家的成员而言是普遍性的,但对于其他国家以及他们的成员则不再是普遍的,它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个别的和个人的意志,这个意志在自然法中获得正义的规则。这样仍然回到已经建立的原则当中: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这个大城邦就成为一个政治体,自然法是其普遍意志,而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过是其个别的成员罢了。”[3](P245)
因此,在每个政治体的个别意志之上还存在着全人类的普遍意志,也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成为所有政治体意志的正义规则:“这些同样的区分可以运用于每个政治社会及其成员当中,从这些区分中可以得出最为普世性和最为确实的规则,根据这些规则人们可以评判好的或坏的政府,并且普遍地来评价所有人类行为的道德。”[4](P245)区分不同意志并识别最普遍的意志成为卢梭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卢梭区分了四个层面的意志:个人意志、团体意志、政治体的普遍意志、世界的普遍意志即自然法。卢梭对团体在政治社会中的消极作用充满忧虑。政治社会总会由更小的社会也就是团体构成,每个小社会也会形成自己的意志,这个意志对于小社会的成员来说就是其普遍意志,但对于政治体来说就可能是背离政治体的普遍意志的个别意志。一个小社会的尽责的优秀成员在大的共同体内可能是一个糟糕的公民。“个别社会总是应当从属于包括它们的大社会,人们应当首先服从后者而非前者,公民的义务优先于元老(sénateur)的义务,人的义务优先于公民的义务。但不幸的是,个人利益总是和其义务成反比,社团越小,责任越发不神圣,个人利益就越发增长。这无疑证实了最为普遍的意志也总是最为公正,人民的声音事实上是上帝的声音。”[4](P246)这段话与少年卢梭引用的费奈隆的话一样表现出世界主义的精神。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人民指的不是某个共同体的所有公民,而是全人类。
二、何为普遍人类?
如果“最普遍的意志也总是最为公正”,那是否意味着对卢梭而言,了解这一全人类的普遍意志并将其运用到政治生活中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卢梭没有致力于阐释这一意志,也没有对自然法的内涵和实践意义予以详细说明,以至于有研究者认为卢梭完全否认自然法的存在。在《社会契约论》和《日内瓦手稿》中,卢梭针对狄德罗撰写的百科全书词条“自然权利”讨论了普遍社会、人类和自然权利的问题。在这个词条中,狄德罗提出将普世性的自然法作为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从上面提及的卢梭的普世主义精神来看,我们本来应该期待卢梭会完全赞同狄德罗的观点,更何况这一时期卢梭和狄德罗是交往密切的好友,然而,卢梭却全面批评了狄德罗的观点。
狄德罗通过和一个假设的“暴烈的思考者”的辩论来说明自然法不能通过个体从自己的激情和欲望出发来进行推导。这个暴烈的思考者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为了自己的生存和需要来保全自己并牺牲他人的权利。[5]此思考者显然是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的人。狄德罗指出,这个思考者虽然试图使自己的逻辑是彻底的甚至是“公正的”——因为他承认别人和他拥有同样的权利,但他没有权利要求别人接受他的逻辑,别人完全可以拒绝冒生命的危险并为了确保生存而宁可放弃主宰他人的欲望。狄德罗由此表明,个人的利益、偏好、要求不足以成为正义和自然权利的基础,只有能够满足所有人即人类的福祉的权利才能成为自然权利,所以必须以致力于所有人的生存和福祉的全人类的普遍意志作为自然权利的前提和来源。正因为这一普遍意志的目标是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它必然是好的。每个个体的自然权利就是做符合和不违背普遍意志也就是全人类利益的事情的权利。每个个体要向普遍意志询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所在,理解自己作为“人、公民、臣民、父亲、子女”等不同身份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那么,如何才能了解普遍意志?到哪里向这一普遍意志求教?狄德罗认为人类的普遍意志是人性的声音,可以说无处不在。无论是在文明民族的成文法中,还是在野蛮人的社会行为中,甚至在人类的敌人①狄德罗认为,只听从自己的意志、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他人和人类的意志和利益的人就是人类的敌人。Denis Diderot.“Droit naturel”.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Diderot_denis/encyclopedie/droit_naturel/Encycl_droit_naturel.pdf p.6.之间的心照不宣的协定和人类的愤怒和仇恨中都可以看到普遍意志。在历史性和经验性的知识之外,个体可以诉诸理性来发现普遍意志:“理解力在激情平息时思考什么是人可以要求于他的相似者以及他的相似者有权要求于他的;在每个个体那里,普遍意志是这一理解力的纯粹行为。”[6](P6)狄德罗相信人人都具有的某种普遍的理性能力能够使人知道如何以公正的方式对待其同类。可以说,普遍意志是个体依靠理性战胜激情后所形成的道德原则。
卢梭显然对狄德罗这一粗糙的论证不满。他并不否认存在着人类的普遍意志,也并不反对从这一普遍意志中推导出自然权利,但问题在于人类社会的现实和哲学家所构想的理想的普遍社会相距甚远。普遍人类或者普遍社会只存在于哲学家的观念中,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是有待建构的。由于不存在普遍人类,并且由于人的理性非常软弱,因此,个体往往无从了解人类的普遍意志,或者即使了解,常常也不会接受它作为自己的道德原则。
在《社会契约论》和《日内瓦手稿》中,卢梭延续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社会批判。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之后,人类因为相互需要而形成相互敌视却又不得不相互依附的奴役关系:“让我们变坏的原因也同样是让我们成为奴隶的原因,这些原因在败坏我们的同时对我们进行奴役;我们对软弱的感受与其说是源于我们的本性,毋宁说源于我们的贪婪:随着我们的激情在我们之间制造分裂,我们的需要却让我们彼此接近,我们越是成为我们的同类的敌人,我们就越不能缺少他们。”[7](P282)如果在现实中存在一个普遍社会的话,那是一种被普遍敌意而不是普芬道夫所设想的普世善意所支配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最大问题是社会并不能为因相互需要而陷入不幸中的人提供有效帮助,而且它会使强者更强而弱者更弱,结果导致弱者成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
卢梭所要追问的是,在被敌意和依附所支配的普遍社会中人类意味着什么?卢梭认为人类一词让人产生的是“纯粹集体性的观念”,但这个观念并不假设在构成人类的个体之间存在任何真正的联合。卢梭在这里指出了世界主义的问题:世界性的人类不过是一种观念,并不指涉任何实质性的纽带。如果人类要从纯粹观念成为一种实质性的存在,就必须使人类成为一种“道德人格”。这种道德人格的特征是“具有一种共同生存的情感,这一情感给予他某种个体性并使他成为一个整体;具有普世性的动机,它使得每个部分为了一个普遍的、与整体相关的目的而行动”。[8](P283)这一道德人格必须有属于其自身的、不同于其组成成分的特质,有一种作为人类交流工具的普遍语言,其公共利益不是所有个别利益的汇集而是大于所有这些利益的总和,因为公共利益存在于这个整体的纽带当中,而且是个体幸福的来源。这最后一点是卢梭思想的关键之处。在卢梭看来,共同体是个体利益和幸福的来源,一种整体性的公共存在是其成员的个体存在的保障,也就是说,个体只有在共同体当中才能获得有意义和秩序的存在。狄德罗所构想的全人类显然还不是这样一种共同体。
人类并不是具有共同纽带的共同体,从人类的普遍意志出发建构自然法和自然权利将遭遇到两个根本的困难。首先,如何让关心自己的生存(这一保存是自然的首要准则)甚于一切的个体看到普遍意志与他自己的生存和利益息息相关,让他认识到服从普遍意志将会促进他的保存和利益,或者说如何让他看到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求他服从普遍意志?[9](P286)卢梭同意狄德罗的说法:普遍意志必须是个体依据理性战胜激情而得出的认识。这意味着独立的个体要做到自己和自己分离并且战胜自己,但卢梭对个体理性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深表怀疑。此外,卢梭指出,在人特有的能力中,理性是最晚发展起来的,而通过理性对观念进行普遍化的能力尤其难以获得。因此,理性自身的力量是很虚弱的,理性自身会出错,往往在它自以为追随普遍意志时而事实上背弃了普遍意志。[10](P286,1414)
其次,即使个体通过理性发现了普遍意志,也并不必然愿意服从它。在一个以个体利益为中心的社会中,个体会这样推论:如果恪守义务不是相互的约定并且得不到法律和强力的保护,也就是说,如果违背义务的行为非但得不到惩罚而且能够带来更大的利益,那么,这个社会的法则显然不是自然法,而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这种情况下,我为什么要遵守所谓的自然法?在现实中,人类是由民族构成的,只对自己负责的主权国家的行动所依据的正是这种利己主义的原则。义务必须具有相互性并且得到法律的支持,而抽象的人类所要求的义务恰恰缺乏这种相互性以及法律的支持。①卢梭认为:“一切正义都来自上帝,唯有上帝才是正义的根源。但是,如果我们当真能从这种高度来接受正义的话,我们就既不需要政府,也不需要法律了。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完全出自理性的普遍正义,但要使这种正义能为我们所公认,它就必须是相互的。然而,从人世来考察事物,则缺少了自然的制裁,正义的法则在人间是虚幻的。”卢梭:《社会契约论》,48~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在卢梭看来,由于事实上不存在一个作为道德人格的人类,至少说自然没有形成这种道德人格的人类,因此,从这种纯粹观念的人类出发形成的自然法不可能对人产生约束而具有政治意义,狄德罗从人类的普遍意志出发构想的自然权利是非常虚弱的。
三、世界城邦
如果人类能够找到途径构建一个世界城邦,那么,这种世界大同是否为人类应该追求的最完美的状态?卢梭对此仍予以质疑。世界城邦表面上以一种普世道德和对每个人的权利的尊重超越了各民族在种族、宗教、文化、政治、利益等方面的差异,然而,这种普世道德却可能因为消解了共同体的政治和道德纽带而削弱了人的道德责任和能力。城邦公民被人取代的后果并不会像世界主义者期待的那样,把人变成世界公民从而提升其道德水准,相反,因为人失去公民德性而成为空洞的道德主体。世界主义是一种非政治的泛道德观念,而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政治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世界主义对共同体政治的瓦解必然会剧烈改变人的状况。
人在历史中发展变化,在走出自然状态后群聚而居,只有在他所生活的小群体中个体才会形成社会关系的概念。自然人先于公民而存在,但自然人是一种前道德状态的人,是公民社会状态使人获得对人的认识,或者说是社会使人“从愚蠢有限的动物变成一个有智慧的存在、一个人”。[11](P364)因此可以说,人通过成为公民而成为人。如果没有在公民状态中形成的对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人不可能对普遍意义上的人所应当具备的特质有所理解。卢梭告诉我们,人必须通过政治来自我发现,而如果存在世界城邦的话,其起点必然是共同体。个体对普遍社会的理解受制于他所在的小共同体:“我们根据我们的个别社会来理解普遍社会,小共和国的建立让我们设想大共和国,我们只有在成为公民之后才开始在严格意义上成为人。因此,我们看到应该如何看待那些自称为世界主义者的人,他们以对人类的爱来辩护他们对祖国的爱,自吹热爱全人类,为的是有权利谁也不爱。”[12](P287)这里,卢梭对世界主义者的批评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世界主义者认为对人类的爱高于对祖国的爱,后者必须以前者为前提。但在卢梭看来,人没有祖国则不会形成人类的概念,对人类的情感应该是由对祖国的情感所引发的。第二点批评更为重要,世界主义如果不转化为一种具体的伦理关系则可能沦为空谈,甚至是个体回避其政治责任的借口。
共同体的形成及其产生的社会和政治关系促成了道德的发生,但也成为人的存在的构成性因素和限度。如果要摆脱这一限度,则意味着要求人超越其自身的情感和道德习惯。卢梭指出:“人类的情感似乎在向全世界扩展时会不断淡化减弱,我们对鞑靼人或日本人遭受到的灾难不会像对欧洲人遭受到的灾难一样感同身受。应当以某种方式限制和压缩利益和同情的范围,从而使之能够有行动的力量。然而,因为我们身上的这一倾向仅仅对于那些和我们一起生活的人才是有用的,在同胞公民当中集中的人性,因为彼此来往的习惯和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共同利益而在他们中间获得一种新的力量。”[13](P254)同情是人性的本质特点之一,它可以指向人类当中任何一个受苦的人。但是,人的情感能力却是有限的,会受到人的生活空间的限制。在共同生活和分享中所产生的情感要远比普遍抽象的同情更为强烈。更重要的是,要使同情确实发生作用,必须使它转化为关心和帮助受苦者的行动。同情只有在共同生活中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纽带。政治生活是共同生活的重要形式,因此,作为自然情感的同情在经过共同生活的政治化之后会产生强大的力量。
前文曾指出,卢梭之所以质疑狄德罗以全人类的普遍意志作为自然权利的前提,根本上在于人类远不是能够以共同纽带把所有人凝聚起来的道德人格,而这里卢梭进一步质疑了这一道德人格是否可能、可欲。即使某种统一人类的世界城邦能够实现,这个城邦也因其无法成为人们的认同和情感对象、无法为世界提供共同生活而不能成为真实的、有生命力的共同体,沦为一种虚幻的道德和政治想象。所以,普遍人性只有在有限的共同体中才能充分发挥其效力。换言之,缺乏某种具体的政治和社会形式的普遍人性可能只是一种情感而不能成为某种道德和政治力量。卢梭指出,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把普遍人性及其情感进行集中和压缩,使公民成为人的载体,使公民在共同生活中养成的美德散发出人性的光芒。
四、共同体的普遍意志
如何集中和压缩人类的普遍人性而使之具有生命力?卢梭致力于把狄德罗所设想的人类的普遍意志压缩为共同体的普遍意志。①美国学者Patrick Riley勾勒了普遍意志从神学概念转化为政治概念的思想史。他主要讨论的是普遍意志的转化,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其收缩。Patrick Riley.The General w ill before Rousseau.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卢梭从普遍人类后退,拒绝了启蒙的世界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也因此放弃了普遍性,相反,卢梭认为自己针对现代性的弊病所提出的政治、宗教和教育方案均是普遍性的。他在《爱弥儿》中指出,任何有人的地方都可以采用他提倡的教育方法。[14](P243)他通过萨瓦神父之口讲述的自然宗教正是他为了超越不同宗教的偏见而试图在良心和理性之上建立的普世宗教。在《社会契约论》中建构的立足于普遍意志之上的共同体同样也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模式。[15](P360)
卢梭对普遍性的追求出于他对人的两方面的理解。首先,自然人所拥有的自由和善成为政治建构的规范性参照。虽然在进入卢梭所设想的政治共同体之后自然自由将被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所取代,前道德的善也将被道德关系所取代,但正如卢梭对普遍社会的讨论所揭示的,人进入社会之后所制造的奴役和邪恶显然是对自然状态的自由和善的背离和败坏,普遍性的自然自由和自然之善仍然是政治构建的衡量标准。必须找到一种办法医治社会之恶,或者说用一种完美的技艺来克服“初级的技艺”——在需要、欲望特别是利己自爱中形成的扭曲联合——对自然造成的伤害,在新的基础上重建自由和道德,实现幸福和正义的结合,使“人类的敌人”成为有德性的公民。[16](P288)这一完美的技艺就是平等自由的个体通过自己与自己立约实现和其他个体的联合,建构政治共同体。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所有加入这一共同体的成员的生命、财产和自由。[17](P248)进入这个社会契约的个体把自我及财产转让给共同体,这个转让事实上是每个个体把自己的意志、财产和力量放在一起,接受普遍意志的领导。[18](P361)普遍意志是对个体意志进行普遍化的结果。在卢梭那里,普遍意志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构成了道德的保证。
在卢梭看来,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联合均以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为基础。①卢梭虽然对斯巴达、罗马等实现了公民平等的古代共和国褒奖有加,并从它们那里汲取思想资源,然而,从他对奴隶制的批判来看,卢梭不会认为这些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共和国实现了普遍意志的治理。卢梭虽然经常表达他的祖国日内瓦给他带来的自豪,称之为自由国家,然而他对日内瓦民主表象后的寡头政治实质有深刻洞察。这种不平等的联合是强力和欺骗的结果,它带来的压迫和奴役破坏了正义和道德。霍布斯、洛克构想的以平等、自由等自然权利为基础的政治联合,在卢梭看来也仍然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因为它没有考虑这一联合所激发的利己自爱对人的束缚和扭曲。利己自爱使他人的认可成为个体衡量自我价值的依据,结果人们生活在他人和社会的眼光以及评价之下,在表面的平等和自由之下事实上存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舆论的统治和道德的沦丧。面对历史和现实中无处不在的不平等和依附关系,卢梭把建构一种消除依附、真正实现平等和自由的政治联合作为其政治哲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他理想中的政治联合的关键之处在于把普遍意志作为联合的基础。一种政治联合只有在确立了普遍意志的情况下才是自由和平等的联合。这一联合通过社会契约来实现,而这一契约的全部条款可以归结为一点:每个参与联合的人把他自己及其全部权利转让给共同体,由共同体的普遍意志加以支配。[19](PP360-361)这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激进的集体主义行动,也是卢梭被指责为极权主义的证据所在。然而,这种全部转让绝非共同体对个体的剥夺,因为它的目的事实上是使个体得到共同体的保护从而充分保障个体的自然权利,并且只有在进入共同体之后,个体对财物的占有才能转化为财产权。在卢梭看来,普遍意志通过把自然自由转化为受到共同体保护的公民自由、把无限制的占有权利转变为合法而又有保障的财产权,克服了自然权利可能带来的冲突进而创造良好的政治秩序,而秩序在卢梭的思想中是道德的前提,对良好秩序的热爱是正义的体现。[20](P589)
社会契约所要求的全部转让首先使得每个人在进入共同体之后处于一种完全平等的地位,其次实现了个体与共同体的合一从而消除了个人因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和共同体利益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全部转让将通过每个人对全体的依赖彻底消除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依附关系。个体对全体的依赖或者说个体意志与普遍意志的一致保证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而这种一致使得个体对全体的服从事实上是个体对自我的服从。个体对自我的服从保证个体意志不会成为他人意志的奴仆,自由因此得以确立。由于普遍意志致力于共同体成员的最大利益,因此它必然是公正的,而个体意志与普遍意志的一致意味着前者也必然受到正义的指引。换句话说,在以普遍意志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中,个体借助普遍意志能够抑制利己自爱产生的利己主义和支配他人的欲望。
作为社会契约主要条款的全部转让和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共产主义回应的事实上是同一个问题:如何消除个体私欲和共同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因为这一对立是共同体的道德腐败和不正义的根源。和柏拉图不同,卢梭并不想建立某种共产主义公有制。他明确指出,这种全部转让并不是使个人的财产成为主权者的财产,它并不改变财产私有的性质。[21](P367)事实上,这一转让的目的是使个人财产得到共同体的保护而成为一种合法的拥有,而这种合法性的概念促进了正义概念的形成:“从自然状态进入公民状态的过渡在人身上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在其行为中用正义取代了本能,为其行动赋予了先前缺乏的道德。”[22](P365)[23](P858)这一转变形成了义务和美德的观念,使人从前道德的自然人转化为有道德的公民。这种转化是个体通过普遍意志重新认识个体欲望以及自我和他人关系的结果。
因此,卢梭的普遍意志一方面是上帝的或全人类的普遍意志的收缩,同时又是对个体意志的提升和扩展。这一双向进程的目的是把自由从个体私欲的奴役和普世情感的虚弱中拯救出来,以共同体的普遍意志来实现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
卢梭以人的普遍本质为参照论证了共同体普遍意志的正当性,可以说,他仍然是通过理性来发现普遍意志的必要性。这样,他仍然无法回避他对狄德罗的批评:软弱的理性如何能够发现或者让人服从普遍意志?卢梭事实上试图回应这个挑战。首先,在《社会契约论》中,他像霍布斯一样把社会契约阐释为某种由事物性质决定的产物。在霍布斯那里,社会契约是自然法的条款之一,而自然法是由人的自然欲望推导出的。对于卢梭而言,社会契约的条款则是由联合这一行动的性质决定的,以至于构成社会契约的诸条款在任何地方都相同并且都得到了默认。[24](P360)不过,卢梭不得不承认,在权利、理性、正义与事实和历史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差异。[25](P297,603)事实上,每个共同体的组建方式都各不相同。虽然只存在一种把人统一(unir)起来的方式,人们在现实中看到的却是成千上万种把人聚集(rassembler)起来的方式。[26](P297)那么,如何才能克服权利和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使得共同体确实被普遍意志支配呢?
五、普遍意志与爱国主义
我们看到,卢梭在其看上去非常现代的政治建构计划中加入了非常古老的因素。卢梭诉诸神一般的大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来帮助一国的公民认识和服从他们的普遍意志。卢梭求助于大立法者和公民宗教的意图是在未能以政制创造民情之前以某种超凡的力量来形塑政制需要的民情,以此来弥补理性的不足。无论是大立法者的立法还是公民宗教,其目的均在于依据每个共同体的特质培育公民对于共同体的情感,从而使个体意志自觉地认同和接受普遍意志。因此,在卢梭那里,普遍意志并不是一种消除共同体差异的同一化力量,而是使普遍意志与每个共同体自身的特殊性结合起来。对于立法者和治国者来说,既要以普遍意志克服特殊性中背离它的因素,又要使这一特殊性成为对它的有力支持。
卢梭并不试图通过社会契约和普遍意志来消除民族之间的差别。虽然一切立法体系的目的都是所有人的最大福祉,而这一福祉可以归结为两点即自由和平等,但这种普遍性的目标必须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加以调整。这是因为:“除了一切人所共同的准则之外,每个民族自身都包含有某些特殊的原因,使它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并使它的立法只能适合于自己。”[27](P393)虽然每个国家由此形成的制度未必就其自身而言是最佳的,但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一定是最适合的。卢梭认为每个民族应该根据自身的物质状况、人民的性格以及两者的关系来立法和建立各种制度,如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其土壤、位置等选择适于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所制定的政治法律是否优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第四种法律——国民心灵中的法律或者说民情是否优良,从根本上说,在于民情是否能够保证民众充分认同甚至热爱这些法律。
因此,仅仅让公民遵守法律是不够的,还必须让他们热爱法律。法律是普遍意志的产物,一个公民如果热爱法律,则意味着他愿意以个体意志服从普遍意志,也就是说他具有德性,因为德性意味着个体意志对普遍意志的服从。[28](P252)德性不只是对普遍意志和法律的服从,还是对法律的超越,因为它使人愿意投身于法律所没有规定但有益于所有人的最大福祉的行动,甚至为此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29](P328-329)在共同体中,对所有人的最大福祉的关心也就意味着对国家的关心。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爱国之情的产物:“德性的最伟大奇迹是对祖国的热爱所创造的。”[30](P255)对普遍意志的热爱是普遍意志能够战胜利己主义个人意志的必要条件,而这种热爱事实上就是爱国主义。对祖国的热爱使个体公民对共同体产生认同,从而使祖国的声音代替自然个体的声音成为公民的指引,公民因此把祖国颁布的法律作为自我给自我颁布的法律,实现公民自由和道德自由或者自律的合一。在卢梭看来,公民不仅用自己的理性构建和接受普遍意志,他的情感也应该参与其中;普遍意志不只是要说服公民的理性,它也必须能打动公民的情感。政治的基础不仅仅是理性,还必须是友爱和激情。这种情感来自于每个人对他所生活的土地的热爱,来自于他在所参与的共同生活中得到的智慧、道德、友爱。土地和共同生活构成了祖国,祖国必须能够把这种情感放在她的公民的心里。[31](P260)由于祖国只能是历史中形成的特殊共同体,有其自身的法律、风尚、习俗,而特殊共同体塑造了其成员的性格与偏好,因此,爱国主义必然首先是一种特殊主义的情感。然后,由于普遍意志是人类的道德实现之路,爱国主义也因此成为人类道德建构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普遍意志和爱国主义是卢梭思想中最引发争议的地方,也是卢梭遭人诟病、被指责为极权主义先驱的根本原因。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卢梭建构普遍意志的出发点以及他对爱国主义的前提的界定。这个出发点和前提就是:共同体必须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为每个公民的生命和利益提供切实保护。这是社会契约和普遍意志的基本规定和要求。对公民生命和权利的保护是祖国对于公民的一项义务。国家不能违背和伤害民众的利益,不能使民众在祖国觉得自己是陌生人。在卢梭看来,任何一个公民遭到来自于其他公民的不正当的伤害,就表明普遍意志已经不存在,或者说契约和社会联盟无论是在利益上还是在法上都已经不存在。卢梭以斯巴达、马其顿和罗马为例说明自由的民族多么珍惜每一个公民的生命。一个自由的民族必须承诺保护其最微不足道的成员,一个成员的安全和国家的安全同样都是公共事业。在卢梭看来,“政府可以为了一群人的利益牺牲一个无辜的人”这样的准则不过是暴政的发明。[32](P256)卢梭认为,远不是全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体,而是全体应该保护每一个个体。他突出平等的普遍性,意图在于防止任何人特别是官员把国家变成满足其个人私欲的工具,使得国家沦为一部分人掠夺另一部分人的机器。普遍意志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个体权利的保障,如果个体权利被践踏,普遍意志也就不复存在,爱国主义自然也无从谈起。卢梭虽然提出以义务作为政治体的原则,但认为公民服从法律的义务首先是以统治者对公共事业的义务以及国家保护公民的义务为条件的,因此,培育民众的美德必须从官员的榜样和国家对公民的保护开始。普遍意志和爱国主义的根本指向是每个公民的生命、自由和德性。
六、结语:人的境况
从人类的普遍意志收缩的共同体的普遍意志,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人类的普遍意志,对此,卢梭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尽管国家的意志对于国家的成员而言是普遍性的,但对于其他国家及其成员则不再是普遍的,对于他们来说成为个别的和个人的意志。”这样一来,每个人和自己的同胞处于公民状态中,但却和全世界的其他人处于自然状态中。[33](P264)由各自拥有其个别意志的国家构成的世界是一个可能发生冲突和战争的世界。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共和国也可能会发动战争。不过,卢梭倾向于认为,这不是由共和国的普遍意志的不正义造成的,而是公共商议被蒙蔽和滥用的结果。公共商议并不必然反映普遍意志,因为难免会有人操纵公共商议使之服务于某些人的利益,从而背离普遍意志。更为重要的是,即使公共商议本身无可挑剔,由此发现的普遍意志也未必是正确的,因为人民自身并不总是能够正确地理解什么对他而言是好的。在政治共同体中,“普遍意志总是正直的,但指导它的判断却并不总是开明的”。[34](P380)也就是说,普遍意志的意愿是好的,但其依据的理性判断却可能是错误的。即便是构成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实现了普遍意志的统治,战争的阴影仍无法完全消除。不难理解,卢梭为什么对在当时的欧洲和世界以联盟或联邦的方式实现永久和平不抱希望,因为当时的欧洲多为个人意志统治的君主制国家。对于君主而言,自身的强大远比和平繁荣更为重要。
不过,卢梭并没有因为共同体的普遍意志可能具有的排他性而将其放弃,他深信,人生活于共同体中,这构成了人的政治境况,甚至就是人的境况和条件本身。超越这一境况也就意味着摆脱人性的限制。放弃共同体的世界主义可能才是非人性的。普遍人类对于个体而言过于遥远,个体对人类的情感虽然是一种自然的情感,但在现实社会中非常淡薄。人类社会的爱的秩序更多地与费奈隆的理想背道而驰。因此,普世道德必须下降而进入到人的具体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存在中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必须把普世道德政治化,而这种政治化的途径就是共同体的普遍意志。共同体的普遍意志至少在共同体中把处于奴役和敌对状态的个体转变为自由、平等、有德性的公民。而前文提及,卢梭认为公民品质是人的品质的前提。自由、平等、德性在作为一种公民属性之后也会因此而成为人的属性,公民对同胞的情感也因此可以扩展到外国人中。至少,卢梭告诉我们,战争是主权者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自然法要求人不得杀害他的相似者。普遍意志创造的不仅仅是公民,也是相似者,这个相似者的概念在民主时代特别是全球化的今天成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推动力量。不过,卢梭始终反对以抽象的人取代特殊的公民,因为这将背离人的境况。
[1]Jean-Jacques Rousseau.“Chronologie universelle ou Histoire générale des temps depuis la creation du monde jusquesàp resent”.in Jean-jacques Rousseau,Oeuvres Comp lètes,ed.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Gallimard,1959—1995.t.V.
[2][3][4][7][8][9][10][12][13][16][17][25][26][28][30][31][32][33]Jean-jacques Rousseau.Oeuvres Comp lètes,ed.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Gallimard,1959-1995.t.III.
[5][6]Denis Diderot.“Droit naturel”,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Diderot_denis/encyclopedie/droit_naturel/Encycl_droit_naturel.pdf.
[11][15][18][19][21][22][24][27][29][34]Rousseau.Du Contrat Social,in Jean-jacques Rousseau,Oeuvres Comp lètes,ed.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Gallimard,1959-1995.t.III.
[14][20][23]Rousseau.Emile,in Jean-jacques Rousseau,Oeuvres Complètes,ed.Bernard Gagnebin et Marcel Raymond.Gallimard,1959-1995,t.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