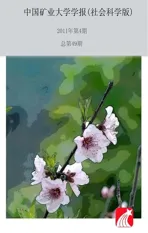斯坎伦和帕菲特论人的道德行为如何可能
——基于理性、理由及个人的阐述
2011-01-12文雅
文 雅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斯坎伦和帕菲特论人的道德行为如何可能
——基于理性、理由及个人的阐述
文 雅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从西方传统的理性概念出发,分析“理性”及其衍生的理由、合理性等相关概念,通过聚焦当代道德哲学以理性和理由建构证成原则的两大代表——斯坎伦和帕菲特——在这几个概念阐释上的同异,特别是他们在“不合理性”上的分歧,指出在多元的世界里,个人的道德处境是我们需要廓清的主题。
理性;理由;合理性;不合理性;不偏不倚的理由
一、道德困境的多重抉择挑战理性的道德普遍原则
人们在实施道德行动和进行道德评价的时候,必须面对的第一问题就是作为行动和评价主体所持有的道德原则的证成,证成的前提总是要归结到对人的本性的说明。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秉承的是理性主义的传统,由于理性在哲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语义流变,使得我们对它和由它衍生出来的概念(例如理由、合理性、不合理性及个人理由等)常常难以把握,因此要理解道德哲学的争论和原则证明,对以上重要概念的澄清和说明就显得尤为关键。
如果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于人性结构的三重划分,那么人本性中最为牢固和高贵的东西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由于易变和极具有个人性的一面,在古希腊崇尚稳定和承诺不变性的思维模式里就是低于理性的,因此难以承担寄托道德原则的说明。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按照他对事物德性的理解,如果说某个事物的德性在于其功能的完成的话,那么作为人固有的理性,人之德性就在于理性及其完成。但是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德性的产生仅在于认识事物和理念本身的理智德性,而在于实践智慧的正确运用。理性固然重要,仍要回归到实践和生活才具备意义。
启蒙时代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对理性的极大尊重,启蒙精神提炼了人性中这部分特质作为平等的基础和来源,人类共同具有的理性使得人们能够在理论和现实中都找到普遍的重合点,因此可以通过这种普遍性来建构我们的道德哲学和精神世界。正如康德提到纯粹自然科学和纯粹数学何以可能的时候,在谈到人类道德何以可能的时候,我们需要从人类普遍的理性出发来寻找答案。康德哲学的三个主题分别是: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可以期望什么。围绕这三个问题,康德整合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为人类理性设定了一个边界,即有限的理性无法认识到物自体,但同时他也肯认人可以借助有限的理性实现真正的实践层面的自由。康德所完成的工作是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转化为人与自身的关系,人只有为自身立法才能还原对整个世界的认识。在康德哲学中,只有上帝和人享有“理性存在者”(rational beings)的地位,上帝在一定意义上是物自体的投射,是“纯粹理性的理想”,也是理论建构的需要,因此人类的理性存在才是需要关切的对象。由于康德强调偏好和善良意志,假言命令和绝对命令的对立,要将一切欲望和情感,甚至是偶然性剔除出我们的道德原则之外,在“理性”之中也就没有上下文或说情境可以提供道德考虑的线索。康德的理性法则是“这样行动:你意志的准则始终能够同时用作普遍立法的原则。”[1]这条法则没有事先给定的价值前提,在法则提出之前并没有一个关于什么是正确或说是“好”的价值说明,行为的正确和无错仅在于法则本身的逻辑,如果行为没有违背这个逻辑公式,那么它就是可以成立的。这个公式提供了一个独立而简单的判断标准,我们能够依据标准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来评价行为。但康德公式屡遭诟病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如果道德行为和情境脱离的话,那么我们就难以在实践生活中完全彻底的应用这些道德准则,而且这种一元的道德准则在处理道德困境的时候往往会导致两个或多个享有对等道德重要性的选择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采取哪种行为呢?
现代道德哲学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即理性(rationality或reason)是需要在情境中被说明的东西,与此相关的理性的(reasonable)和合理的(rational)是两个有联系的但是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到,它们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康德,理性的与合理的分别对应《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以及其他著作中的绝对命令和假言命令,前者是纯粹实践理性,而后者是经验实践理性。[2]罗尔斯接受了W.M.西布里在《合理的与理性的》疑问中的解释,认为理性品质不是由“合理的”推导而来,也不与“合理的”相对立,但与利己主义是不相容的。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分在于:理性的个人是“由一种社会世界本身的欲望所驱动的”,他们主张的是一种相互性;“合理的”适用于单个的主题和联合的行为主体,也就是说,“合理的”总是作为一个仿佛有着人格意义的个体出现,它总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和慎思而行为,虽然并不一定仅仅关注自我利益,但是却缺乏“特殊形式的道德敏感性”。理性的和合理的不能互相从对方中推导出来,从而也不能丧失它们的特别地位,理性的行为主体可能缺乏主体的目的,而合理的行为主体则可能缺乏正义感。而且在另一方面,理性是公共的,但是合理性却不是公共的。
二、对具有客观性和个体性的理由回应构成个体的道德行为
罗尔斯虽然认识到了“理性的”和“合理的”之间的界分,但是在斯坎伦看来,罗尔斯还是没有完全抛弃从康德以来的以理性为基本概念的传统,即认同形式论证和逻辑规则来给定道德原则,忽略了道德生活中的实质性理由。
斯坎伦运用了一个和康德类似的概念来描述人类,即理性造物(rational creature)[3]10,理性造物有着各种各样的(包括为了信念,或者包括为了意图、恐惧和赞美等其他)态度而做出认知、评估以及被理由(reason)说服的能力,这是理性造物者特有的能力;理性能力就被收束在对理由的说明之中,从而经过理由来定义理性,连接了理由(reason)和合理性(rationality)。斯坎伦在这里所作的转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采用中文的字面译法,我们很容易捕捉到“reason”一词的语义变迁,它从一种作为公共性和普遍性存在的“理性”变成了具有相当浓厚的个人色彩和情境感的“理由”,并最终落脚在“理由”上。斯坎伦之所以要做这样的转换,目的就是要告别基于单一的理性来说明道德原则的他所谓的既往的“契约论”的做法。道德的原因和动机不在于理论理性的推演和逻辑进程,道德必须要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来寻找根基。契约的各方总是处于一种交互的状态,他们的理由受到多重因素的牵制和说服,这一点上斯坎伦的理解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其实是大同小异,但与此同时,理性被斯坎伦约化为可以通过理由得到说明的能力。
斯坎伦指出,在理想化的状态下,合理性的行为者要做的包含理想化的三个可能维度是:拥有对自己境况和行为方式后果的完整信息,对适用于在那种境况下某人的理由之完整范围的意识,以及关于这些理由支持什么的完美无缺的推理。但是由于理由的多样性,要提供一种系统和实质性的说明是非常不可能的[3]21。这三个维度都可以归纳为个人的能力,有似于阿马蒂亚·森所提议的将个人自由归属为能力,斯坎伦将理想的理性归属为在全备信息基础上的能力,而且是可以输入实质性理由的,在这种意义上来阐释理性就可以提供一个可平等化的导向道德的可能。理想的理性的理想性正在于对行为主体的描述是无可挑剔的完美状态,至于谁能够保证占据住这样一种状态,斯坎伦没有给出答案,我们在实践生活中也肯定遭遇不到这样的人,只能说,任何一个具体情境下的具体的行为主体只能享有对整体世界的局部认知,他并非了解错误的知识,却一定只了解和自己相关的理由与信息。我们可以共享的理性限度到底应该设定到何种程度,以及我们所谈论的情境中的个人应该处于何种知识和情感的状态,这是斯坎伦以及帕菲特都需要回应的问题。
如果说斯坎伦在理性和合理性之间设定了相互转化的条件,并通过理由定义了合理性,再将道德的原则和动机托付给理由的话,那么帕菲特在这一点上和斯坎伦是一致的。帕菲特的主要论证在于,相对于合理性的定义说明了不合理性,重点分析了理由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的观点。帕菲特和斯坎伦都认为从理由(reason)和合理性(rationality)的观点来概括道德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道德理论的理解。作为理由的客观主义者,他们都坚持,一个道德行为如果是错误的,仅在于它违背了某个有理由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原则,这些原则提供了规范性的力量和作用。根据Sarah Marshall,斯坎伦阐述理由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理由判断的客观性,主张个人能够根据理由采取特定的态度,执行特定的行动,而不论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理由,因此就要求斯坎伦采纳以下观点,个人有达成同意的理由和道德地行动的理由,与他们的欲望无关[4]13。这也是帕菲特所持有的观点。
帕菲特在on what matters一书开篇就提到,“我们是既能够理解又能够回应理由的动物”[5]67,正是对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的一个注解,理性在帕菲特这里被置换为理由,而且理性的表现在于人类的理解和回应理由。这个问题从古希腊以来到现在都是人们想要解决的,既然人们可以回应理由,那么理由在人类行动中究竟起着何种作用。在《理与人》中,我们有理由去进行的行动总是与行动者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相关。为了汇合客观主义的理由论证,帕菲特详细区分了理由的类别,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大多数人都通常是在蕴含理由(reasonimplying)的意义上来使用“应当”和“应该”这类词汇的。我们回应的是蕴含了决定性的理由(decisive-reason-implying),理由应该是独立的不依赖于事实本身的好或说价值的,否则理由就无法构成规范性的力量来约束和促成我们的行为。从理由到行动这个过程,包括理由本身以及行动本身,我们都可以做出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评价,这就涉及到认识和实践,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断裂和错位。认识的合理性不一定能够就一定指向实践的合理性,二者的实现虽然可能有所重叠(overlap),但是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
首先,愿望和行动的合理性依赖于我们有意为之的做(doing),也可能依赖于我们对所做之事的信念。帕菲特论证,除开一些的确蕴含有明确规范的信念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据此行动的信念本身的是否为真或是否合理并不构成相关性。因为个人持有的信念都是不尽相同的,对我来说是相关的合理信念,对其他人来说就未必如此。如果我们对相关的理由给定的事实没有任何信念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合理行动的根据了。因此具有合理的欲望这件事只能说在某一方面是合理的,而不能完全决定我们的行动是合理的,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某些不合理的愿望合理地去行动,这样一来我们的行动又具备了某种合理性。所以帕菲特的合理性要满足多个条件:行动是对理由的很好回应,理由所依据的信念内容是合理的。
其次,信念的合理性来自程序的合理性,即它是否是从其他合理的信念中被合理地推导出来的。信念与信念之间有一种真值的传递,如果作为前提的信念是认识上不合理的,那么据此得出的信念肯定也是不合理的。但是同样的情况却不会发生在信念和愿望及行动的关系中,认识上不合理的信念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实践上不合理的愿望和行动。
其三,认识和实践的断裂和隔绝在帕菲特之前已经被广泛彻底地论证过:如休谟派和霍布斯派认为我们行为的动机不在于规范性的认识,而在于自身的某种关注和根本性的东西,康德则认为认识本身就能提供某种动机,类似于“无人有意作恶”,我们之所以不能道德地行动仅在于没有完全认识到德性本身。帕菲特提供了一种折衷的方案,他区分了信念的合理性和愿望与行动的合理性,前者的合理性主要在于我们是否很好地回应了信念所依据的认识或真理相关的理由或表面理由,而后者的合理性则依据的是我们是否很好的回应了拥有这些愿望和行动的实践理由或表面理由。
三、个体道德行为的对与错在于其对实质性理由的符合与背离
在“理由”问题上,斯坎伦和帕菲特都赞成实践理由所具备的客观本质,因此可以提供规范性的力量来担当我们行动的指南。但是,在接下来对根据理由作出行动的判定中,二人关于“不合理性”(irrationality)的定义却出现了歧见。
斯坎伦认为,不合理性“在最为清楚的意义上就是在一个人的态度与其自身的判断不能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他关于不合理性的狭窄定义,可以说是在非常形式的意义上限定了不合理性的发生条件。如果一个人做了一个在通常情况下看来是不合理的选择,但是就形式而言,他的态度和判断相一致的话①例如帕菲特在on what matters一书中所举的例子,三个人在痛苦和轻微疼痛中所作出的不同选择,第一个人选择明天的一小时痛苦而不是下一周任何一天的轻微疼痛,因为明天是周二,他相信决定性的理由在于他对未来周二的痛苦漠不关心;第二个人选择明天的一小时的痛苦而不是今天稍后的轻微疼痛,因为我们更强烈的理由在于相较于较为遥远的将来我们更应该关心更近的将来。第三人选择明天的六分钟的痛苦而不是今天稍后的五分钟的轻微疼痛,但是他的信念是仅仅是时间的不同并不能造成合理的重要性区分,虽然持有这种信念,他仍然选择明天的较长时间的痛苦。在帕菲特看来,这三个人都各有其不合理性,分别体现在信念、事实、理由以及行动。,那么他的不合理仅仅在于他在实质上就是错误的。帕菲特批评了斯坎伦,指出这样我们就可能为我们的错误行为提供辩护,因为按照斯坎伦的观点,即使我们经常不能回应那些非常清晰和决定性的理由,我们也能够因为对那些给定理由的事实,以及那些合理的愿望或行动没有信念或者持有错误的信念避免某种不合理性的产生[5]137。形式的合理性肯定是不足够的,由于一旦如此设想就可能产生许多在常识看来无法接受的结论,比如那些对实践理由有合理的信念,而且承认自己无法回应这些理由人反而比拥有不合理信念且不愿承认错误的人更加的不合理。并且斯坎伦这个态度与判断的匹配说还可能导致他自己竭力反对的道德相对主义:即如果仅仅因为我们不能回应某些规范性的信念就将我们的愿望和行动归结为不合理的话,那么对有些人来说,在没有给定的真实理由和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我们的不合理性就仅在于我认为自己不合理的时候才成立,道德从而就沦为完全的主观化的东西。
帕菲特声称自己是在普通意义上使用“不合理性的”,它的含义大致等同于“值得强烈的批评,类似于我们通常使用的表达‘愚蠢’、‘蠢笨’和‘疯狂’的词汇。”因此帕菲特的“不合理”是较为宽泛的和接近常识的,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推演。Marshall指出,斯坎伦反对在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不合理性”的根据是无法认识一个理由不一定就是不合理的,我们不能认识理由很可能是由于慎思的时间有限,或者是推理的前提有错误,它们都不一定预示着不合理性。因此在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之间遗留了一段灰色的区域(grey area),这段区域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4]15,而是说任何一个信念、态度、判断和行为都可以存在于其中,因为它们本身或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得到合理或者是不合理的评价。
简言之,要满足帕菲特的不合理的指责较为容易和宽泛,只要行动遵循的理由或者行动者在回应理由的时候是不合理的,那么行动就是错误和不合理的,他可以诉诸的斥责不合理的标准相对丰富;但是斯坎伦关于不合理的指责则较为狭窄,只有在提出的形式条件得不到遵守时,行动才是不合理的,至于行动的理由和行动者本身的不合理性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需要通过实质性的理由来进一步论证。也就是说,在帕菲特这里,合理性和不合理性之间的灰色区域要更广阔一些,斯坎伦那里的情况则刚好相反,因此相应地,要满足帕菲特的完全合理的条件就更加严格,必须满足确定的合理性要求,比如不要有相互矛盾的企划,并意图做那些我们相信我们应当去做的事,这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从认识到实践全部是合理的;要满足斯坎伦的完全合理的条件就是他设定的理想的理性人,虽然严苛,但是却不必要是现实的,而毋宁说是一种完美假说。如图1所示:

图1 斯坎伦与帕菲特关于合理性和不合理性的界限区分
对于不合理性和合理性的界限区分的差异反映的是斯坎伦和帕菲特在理由所能提供的规范性原则上面的分歧。二者的理想都是要构建一个具有客观主义效力的原则,与康德和罗尔斯一样,他们的原则要满足形式的要件,因此是具有理性的普遍约束力的,但同时又期待实践的应用,因此他们的理由不是由理性发散和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形形色色的理由中上升为理性原则的。
但是对于从理由达到理性原则,二者的进路是不同的:斯坎伦构建的方式是个人主义限制,而帕菲特依据的是不偏不倚的理由或说非个人的理由;前者强调一般意义上的合理性是系统性的,而不仅仅是意外和偶然的,这对于理性造物来说就足够了,理性造物有时候的无理性只需要一条标准来衡量。这种狭窄的限定更适合我们在理论以及普通的场景下使用,实质性理由的加入能够使问题更加明朗和清晰。“我们应该诉诸于关于一个人是否有理由的直觉,而不是诉诸关于不合理性的直觉。”[3]15相比斯坎伦将不合理性仅归为实践层面,帕菲特认为认识上的不合理性也是应该纳入考量的,不合理性可以拆分为很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使得全部的链条具备了不合理性。因此实质性理由不需要在其他部分被输入,我们确认理由的地位时应当采纳一种类似于理想旁观者的视角。
四、达致理性原则的不同进路:个人的和非个人的理由
道德哲学最终必须回归实践,而实践生活是由个人和个人所处的生活场景呈现出来的,所以道德哲学在原则的论证和驳斥中往往会设计出思想实验来模拟现实中可能会面临的道德处境,如果一个原则不能通过思想实验的校验,那么它就是需要被修改的或者说是不合理的。斯坎伦和帕菲特正是在思想实验的构造中提出、增补和修改了关于理由的个人性和非个人性的论证。
有别于康德设想的单薄的个体和罗尔斯在无知之幕笼罩下的理性人,斯坎伦试图以非常个人化的理由来为道德原则提供限制。而且斯坎伦特别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理由必须是来自单个个体的观点而不是任何集体的或者是非人类的观点,所以它拒绝为任何功利主义的打算提供出路;此外,这种个人主义的理由也不是任意和偶然的,个人的某种特殊偏好和兴趣不能成为合理拒绝的实质性理由,它必须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般理由”,这被斯坎伦称之为“个人主义的限制”。
帕菲特则认为个人主义的限制并不能完全脱离功利主义的影响,斯坎伦对功利主义的攻击没有切中要害,功利主义的关键不在于对数字的关切而在于如何在人际中分配利益。在理由的客观性方面,帕菲特比斯坎伦走得更远,他认为我们切实的理由必须奠定在不偏不倚的某个价值基础上。作为“self”的东西并不可靠,经过对个人同一性的心理连续性的还原处理,个人作为主体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同一性是可以人际拓展的。很难说,个人在道德处境当中的面目到底是怎样的,它的具体性和抽象性在斯坎伦和帕菲特的争论之后仍然非常模糊。对斯坎伦来说,个人的实质性理由所包含的内容尚未明确,与此同时,就帕菲特而言,作为客观主义的价值基础又无从论及。当然,帕菲特在很多时候都尝试使用常识的观念来澄清语词,可是如果常识可靠的话,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道德原则呢?理性本来是为了解决普遍性问题而被发掘的,在经历了从理性衍生到理由和个人,
又从个人回归到理性的综合阶段之后,个人的自由和能力的限度,以及个人的重要性和道德原则的相关性仍然是我们在今天多元的世界里需要廓清的主题。
[1] (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1.
[2] (美)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江苏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0.
[3] (美)托马斯·斯坎伦.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M].陈代东,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Sarah Marshall.Scanlon and Reasons[A].Matt Matravers(ed.).Scanlon and Contractualism.London:Frank Cass,2003.
[5] Derek Parfit.On What Matters[M].draft of 23 January 2009.
Rationality,Reason,and Individuals Between Scanlon and Parfit
WEN Y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of“rationality”and analyzes the related concepts such as“rationality”with the reason for its derivation and its being rational.The focus i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canlon and Parfit in their argumentations about“irrationality”.In a pluralistic world,the moral situation of individuals is the subject we need to clarify.
rationality;reason;rationality;irrationality;impartial reasons
B82
A
1009-105X(2011)04-0026-05
2011-10-15
文雅(1980-)女,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