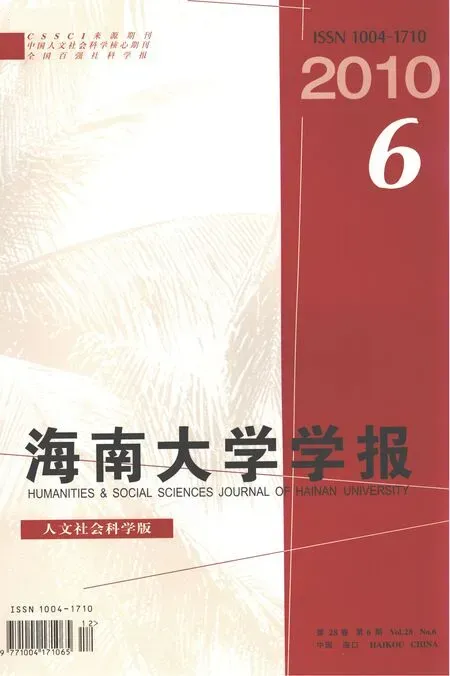语篇构式与回指确认
2010-12-19许宁云
许宁云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3)
语篇构式与回指确认
许宁云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 201303)
探讨将构式语法研究范围扩大至语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将Östman(2005年)的语篇构式理论应用于诗歌语篇的回指确认。诗歌也是一种语篇构式类型,诗歌构式的主要功能范畴是韵律和节奏,它们虽是诗歌语篇的形式成分,却对应着与其匹配的稳定的意义。这种配对的形式-意义关系形成了诗歌的构式义,它作为心理构体储存于认知主体的深层记忆中。在解读诗歌语篇时,可激活诗歌构式的赋义机制,启用构式义,从而促进诗句之间的语义关联,支持语篇中零形回指语的有效确认。
语篇构式;构式语法;构式义;回指确认
一、构式范围之辨
“构式”(construction)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Goldberg对构式是这样定义的:如果说C是一个构式,那么当且仅当C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Fi,Si>,且该形式或意义的某些特征不能从C的构成成分或从其他业已存在的构式中推测出来[1]。据此定义,“小品”是构式,因为该词的意义不能从其构成成分“小”和“品”的意义中推导出来;句子“他教我语文”也是构式,因为该句所含的“给予”义难以从动词“教”或其他成分的意义中获得。在构式语法中,构式可以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语素,也可以是单词、复合词、惯用语和句型,而比句型更大的结构体尚未纳入构式的范畴。石毓智指出,“构式语法所谓的construction没有包括由单句(clause)组成的更大结构体。不论是生成语言学派还是认知语言学派,他们所关心的最大语言单位为单句,单句以上的单位一般不在他们讨论的范围之内。然而由单句所构成的更大语言单位“复句”或者“篇章组织”(discourse structure)也有稳定的形式和语义功能,按照构式语法的定义也应该属于一种构式,然而该理论并没有把这些包括进来,……”[2]①如古汉语存在一种篇章组织:
形式特征:S1,S2,……,是 +X+也。
语义功能:评判性质或者下结论。
其中的Si通常代表单句,“是”是指示代词回指其前的内容,X为评判的内容,“也”是判断的标记。
例如:
(1)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2)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3)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2]
由此可见,构式语法在研究范围上有待进一步拓展。因为“构式语法不但是一种研究思潮和理论,即所谓的构式主义取向,而且是一种观察语言(形成过程和方式)的方法和所取的态度,即构式主义态度”[3]。这种方法和态度可视为一种方法论,它具有统摄或总揽全局的作用,亦即无论是何种语言现象,只要具备Goldberg定义中的构式特征,就应使用构式方法论来进行探讨和分析。而且构式语法采取的是基于使用的(usage-based)研究路径,研究对象是所有实际存在的语言现象和实际使用的语言,因此构式语法不应把研究范围局限于句子层面,而应向更高的层次攀登,向更远的目标迈进。
二、语篇构式及其特点
赫尔辛基大学的Jan-Ola Östman认识到了构式语法的局限性,提出应将构式语法的研究范围扩大到语篇。就构式语法的语篇转向,Östman[4]126提出4个观点:1.许多语篇都是规约化的;2.语篇与句法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3.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和规约性(conventionality)是相对语境而言的;4.构式语法(CxG)需认识到类似于语篇样式(genres)的整体框架的用途。
就规约化语篇,Östman认为,将构式语法囿于单句主要是传统因素造成的,其实在合乎语法的句子和合乎语法的段落或篇章/语篇之间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它们的规约化程度以及听话者的可接受程度都是标量性的。那种将语素和单词视为构式,而将复合句、段落和篇章/语篇排除在外的做法不具备任何本体、方法论或认知上的基础。构式语法认为构式在形式和意义上存在规约化的联系,然而这种规约性具有程度差异,尽管语言结构超出句子范畴,其规约认可度可能会有所降低,但其形式和意义之间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就句法与语篇的关系,Östman认为,构式语法及生成语法一向重视句法层面的研究,而忽略语篇研究。其实句法和语篇之间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动、对话的关系。对于框架,Östman指出,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框架之外,还应有一种语篇层次的框架,如语篇样式这样的框架。这种整体性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何在特定场景中某种语言表达是恰当的,可以对语篇解读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可以进一步明确语篇话题、图式以及特定语篇样式在语篇理解中所起的作用。Östman认为,我们不仅要掌握一个语词所引发的框架信息,而且还需了解该框架本身所包含的知识信息,这种综合性框架可称为“语篇构式”(discourse construction)。与语法构式一样,语篇构式②Östman使用的是语篇模式(discourse pattern)这个术语,为了与“语法构式”保持对应,笔者选择使用“语篇构式”(discourse construction),简写形式也相应变为dc。也是抽象实体,同时它和框架一样也是一种认知现象。
Östman指出,构式语法的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尽可能将语言中的所有构式都纳入其研究的范围之内。因而要了解一种语言就必须对该语言中的所有结构形式加以探讨,尤其是边缘性的语料,包括像Thank you,Goodbye之类的惯用语,以及各种各样的套语和成语,因为它们与传统的句法研究对象一样,都是语言和语法的重要内容。倘若如此,像报纸标题之类的句法语义也应是构式语法关心的问题,而且缩略语、海报语言、社会心理的语言变体、残缺句、甚至是外语学习者的中介语都应成为构式语法予以关注的对象。鉴于此,Östman指出,如果各种类型的语句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就势必需要在构式语法中建立某种机制,来表明在何种场景和语境下,某种形式结构是可接受的或者说是符合惯例的。
另外,Östman还区别了语篇样式和语篇类型(text type)这两个与语篇构式密切相关的概念。它们都是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二者都关涉到社会惯例、互文性和语篇的程序性释解,但两者在语篇解读的视角上有所不同,前者注重与社会和交际场景相关的外部关系,而后者则注重语篇内的内在关系。语篇样式体现的是基于人类各种活动的语境场景,如菜谱、讣告、死亡通知、餐桌交谈、神话故事、医疗咨询等;而语篇类型指的是语句组织成语篇的方式,如议论文、记叙文、指示文、说明文、描写文等。如在记叙文中,通常将句子、话语等前景化信息成分按照现实生活中事件发生的实际顺序进行自然排列,而在议论文中则需将这些信息成分按论点、论据和论证的逻辑顺序进行缜密安排和有效组织。再比如,一部小说是“小说”样式的一个例示,它可以用记叙文的形式写作,也可以用议论文或说明文的形式写作。同样记叙文并不局限于神话故事和小说,菜谱也可以用记叙文的形式拟就。
虽然在框架特征上,语篇构式类似于语篇样式和语篇类型,但与其不同的是,语篇构式是一个抽象的心理构体,是一种理性化的认知模型(ICMs)。譬如当谈及菜谱这个话题时,首先想到的不会是写作菜谱所惯用的指示性语篇类型,也不会是对照菜谱做菜的相关行为,而是关于菜谱的理想化认知模型,即菜谱的典型样式──先是标题,然后是纵向列出的原料明细,最后是表明制作过程的指示性语篇。这种语篇构式有助于语篇的理解和生成,因为它是“对语篇的整体性感知”[4]132,或称完形感知,它构建了整个菜谱的前后连贯。如果不使用指示性文体,而用其他语篇类型来表述烹制过程,那么读者需花费较大的认知努力来判断此语篇是一个菜谱语篇。“认知努力大”是因为“其它文体”造成了与完形表征的冲突和失谐,之所以最终能判断出来是菜谱语篇,是因为作为解释性框架的语篇构式能赋予语篇一定的关联性,也就是说,该语篇构式会向“非指示性局部语篇”分派“指示”的意义,这是语篇结构暂时改变局部语篇意义和用法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语篇构式的功能(即语篇构式义)可对进入构式的非指示性文体形式所对应的语篇意义施加临时的压制和修改。
另外,ICM会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拿婚姻ICM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有“无媒不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等认知模型,而在现代社会,这些认知模型变得不再那么典型。就菜谱来说,在中国,菜谱中一般将调料或佐料单独列出,且不具体标明做出的菜是供多少人食用;而在西方,一般不会单列调料,而是将它与主辅料一并列出,并明确供食人数,如在标题下方注有“Serves 12~14”,此信息也可置于原料列的上方,如“Yield:12~14 Servings”。因此中国菜谱ICM中存在“不定飨客数,调料单独列”这样的认知模型,而西方菜谱ICM中则含有“明确飨客数,调料不单列”这样的认知模型。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方的饮食文化存在差异,中国菜注重“色香味俱全”,因而所用的佐料较多,需要单独列出;而西方菜注重优化的营养结构,烹饪上讲究不多,因而佐料较少,不需单独列出。另外,中国人烧出的菜一般放在一个盘中,供大家一起享用,而西方人通常将做好的菜分发到各自的盘中单独食用,所以西方菜谱需标出供食人数,而中国菜谱则无此必要。
三、语篇构式在诗歌语篇回指确认中的应用
诗歌也是一种语篇构式类型,可表征为[dc poetry]。诗歌构式的主要功能范畴是韵律和节奏,它们是诗歌语篇的形式成分,可增强诗句之间的语义关联。诗歌语篇的构式意义可使人们对语篇进行一种“超前宏观处理”[5],所形成的解释性框架可对语篇表层中出现的语法失范、语义失谐等现象加以修改和压制。试看下面这首由苏步青先生题写的诗句:
(4)a.Øi无忘任重红专健,
b.Øi莫负岁寒松竹梅;
c.他日神州迎四化,
d.Øi登临共举庆功杯。
(引自《复旦的树》)
该语篇中标记“Ø”的符号是指该句中被略去的指称语,因其虽具实际意义,但却未实现为具体语形,故称其为“零形回指语”。该诗的a、b两句中连续使用了两个零形回指语,因为:1.a句中的指称对象具有较高的显著度和可及性。苏步青校长题写该诗是为了勉励复旦乃至全中国的学子,据此可知a句中的零形回指语指称的是包括学子和作者在内的通指性指称对象“我们”,该指称对象在语篇语境中具有较高的显著度和可及性,因而具有较高的可预见性和可忽略性[6]③基于Li&Thompson的理论,Chen试图通过对语篇语境的分析,深入探讨汉语中第三人称指称对象的零形回指运作机制。他对现代汉语叙事语篇中三种回指形式选择和使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三种回指形式分别为零形回指、代词回指和名词回指。他指出,现代汉语语篇中零形回指的使用主要取决于是否满足“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和“可忽略性”(negligibility)这两个基本条件。;2.b句使用零形回指指称前句的指称对象(“我们”),是因为该句与前一句之间具有较高的“连接度”(conjoinability)。Li&Thompson[7]指出,“连接度”指的是发话者对语篇中小句之间联系程度的感知,或者指的是一个小句与前一小句组合为一个语篇单位的难易程度。如果两个小句之间的连接度较高,那么一般倾向于在第二个小句中使用零性回指,结果就会出现主题链(topic chain)。
另外,a、b两句同属一个语义空间(semantic space),反映的内容是“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怎样”,因而该空间可称为“现时空间”。该空间建立后,后续语句的起始语词“他日”作为空间构建语(space builder)又建立了一个“未来空间”,反映的是“有朝一日我们将怎样怎样”这一语义内容。从前述内容的“现时空间”到后续内容的“未来空间”是一种语义空间的转换。语义空间的转换破坏了a、b句所形成的语篇片段与c、d句组成的语篇片段之间的语篇连接度和主题连续性。既然例(4)中的语义空间的转换降低了主题连续性和语篇连接度,那么(4d)句中的主语回指语按理应是显性回指语,而句中却依然使用了零形回指语,这似乎与上述Li&Thompson的连接度限制条件相抵触。或许消解这一抵触的其中一个因素是注意焦点。Li&Thompson指出,连接度并不是一种能预测到零形代词和显性代词之间不同选择的绝对性规则,仍然存在着连接度原则所不能解释的例子。请看下例:
(5)[Para.1]
a.香的辣的Øi(赵匡胤)都吃遍了,
b.猴头燕窝Øi都吃腻了。
c.天下样样名菜Øi都吃着无味道。
[Para.2]
d.这一天,Øi忽然想起了当年吃过的小豆腐j,
e.Øj很可口。
f.Øi就下了一道菜谱圣旨——小豆腐。
《赵匡胤吃小豆腐》
此例中,句d的起始部分是一个时间副词短语“这一天”,它标示了另一个段落的开始,同时也标示了一个新主题的开始,然而尽管如此,此句还是使用零形代词来延续上一段落的主题链。句e的指称对象是另一个主题(次主题/副主题)“小豆腐”,因而它偏离了原先的主题,然而后续的句f也仍然使用零形代词,而不是显性代词“他”来指称原先的主题“赵匡胤”。对于此类现象,Li&Thompson的解释是,当某个主题成为当前的注意焦点时,即使在连接度条件的限制下,也可以使用零形代词。“注意焦点”论对于解释例(5)是比较有说服力的,然而若用于解释例(4)则显得不够充分,因为对于前者,“赵匡胤”是个贯穿整篇文章的主题,因而它在作者和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占据相当突出的“焦点”地位,而对于后者,“我们”这个主题是从语境中推导出来的,且仅在第二句中有一次共指的指称对象,因而虽然也称得上是“注意焦点”,但其聚焦程度相对较弱。因此作者在生成语篇时,以及读者在解读语篇时,必然会启用其他相关的认知机制来支撑零形回指语的合法使用。笔者认为,该认知机制是诗歌语篇构式的赋义机制。

图1 例(4)中诗歌语篇构式的赋义过程
语句之间的衔接关系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照应、替代、省略、连接和词汇搭配五种④参见Halliday,M.A.K.&R.Hasan.Cohesion in English[M].Longman,1976.,还包括结构衔接(如结构排比、对仗等)、逻辑衔接(如通过later,consequently,the next morning等词汇进行的衔接),甚至还有音系衔接(如音调、韵律等)[8]。就例(4)中的诗句语段来说,它们具有许多诗歌所特有的结构对仗、前后押韵等特点,而且对于读者或受话者来说,他们通常会对诗歌持有一种主观认同性和认知先设性,也就是说,在他们处理诗歌语篇之前,已拥有一种对诗歌的先在的或先入为主的感觉和图式,“感觉”通常表现为朗朗上口和自然流畅,“图式”通常表现为诗歌的典型整体框架和常规语言组织形式。这些因素都可促进诗歌语篇的局部和整体连贯性,而这些因素则共同构成了诗歌语篇的构式意义。在此构式义中,韵律这个功能范畴较为重要。如该诗的韵式是a-b-c-b,在韵法上押的是脚韵,即b句中的“梅”与d句中的“杯”在“ei”音上押韵。而且该诗是七言绝句,结构对仗,在音律上每句都是三个“顿”(音步),如第一句“无忘/任重/红专健”。因此,即使b和d句之间分处不同的语义空间且两句之间隔着缺少语义关联的c句,b和d句之间的主题连续性和语篇连接度并未导致减弱,这是因为在诗歌语篇构式的解释性框架中,韵式、韵法、音律等因素共同作用于语篇的认知处理,给b、d句之间赋予了语义上的关联,从而增强了二者之间的主题连续性和语篇连接度,故而在d句中使用零形回指语也就顺理成章了。以上便是诗歌语篇构式的赋义过程,如图1所示。
四、余 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诗歌语篇构式是语篇构式的一种,它是从诗歌语篇的生成和理解中抽象出来的心理构体,在形式和意义上具有较为稳定的匹配关系;它是构式语法在研究范围上的拓展,也是语法构式在语义层面上的进一步延伸。语法构式适用于局部语篇的语法和句义研究,而语篇构式可将局部语篇与整体语篇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微观释解与宏观关照交互作用的效果。本文所探讨的是诗歌语篇,是运用语篇构式进行语篇研究的一个尝试,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另外本研究所使用的语料是格律诗,当然对于自由体诗来说,在结构对仗、诗句押韵等方面自然有所缺乏,但它使用的毕竟是诗化语言,因而具有鲜明的节奏感,这些构式意义元素也会赋予诗句间一定的关联,虽在连接度上可能存在差异,但仍能促使高可及性回指语在语篇中的应用,具体的应用模式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1]GOLDBERG A E.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5:4.
[2]石毓智.构造语法理论关于construction定义问题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08-111.
[3]陈满华.关于构式的范围和类型[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8(6):6-11.
[4]ÖSTMAN Jan-ola:Construction discourse:A prolegomenon[M]∥BENJAMISN J B V.Congnitive grounding and theoretical extensions.Philadelphia/Amsterdam:[Sl.],2005:121-144.
[5]熊学亮.话语的宏观结构[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1):19-23.
[6]CHEN P.A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ird Person Zero Anaphora in Chinese[M].Bloomington:Indiana Linguistics Club,1984:3.
[7]LI C I,THOMPSON S A.Third-person pronouns and zero anaphora in Chinese discourse[M]∥GIVON T.Discourse and syntax.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9:311-335.
[8]胡壮麟.有关语篇衔接理论多层次模式的思考[J].外国语,1996(1):1-8.
Discourse Construction and Anaphora Resolution
XU Ning-y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Shanghai 201303,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integrating discourse phenomena into Construction Grammar,then applies Stman(2005)’s Discourse Construction Theory to anaphora resolution in poetic discourse.It holds that poem is a type of discourse construction,and the primary functional category of poetic construction is rhythm which,as a formal element of poetic discourse,matches with it a stable meaning component.This form-meaning pair constitutes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which,as a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s stored in memory,and in the production of poetic discourse,the meaning assignment mechanism of poetic construction is activated,b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to facilitate the semantic relevance between verses,thus assist in resolving zero anaphors in poetic discourse.
discourse construction;Construction Grammar;construction meaning;anaphora resolution
H 141
A
1004-1710(2010)06-0086-05
2010-05-20
上海市教委支出预算项目(教预07-45);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09YS264)
许宁云(1969-),男,江苏南京人,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英汉对比与翻译和语用学的研究。
[责任编辑:林漫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