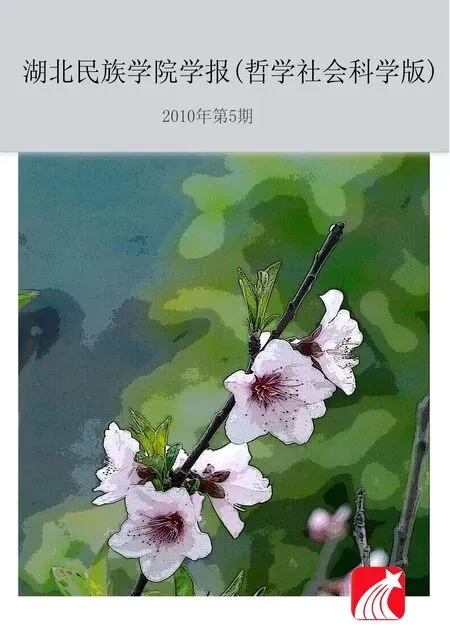正史中的胡床及其变迁
2010-09-06黄清敏
黄清敏
(闽江学院 历史系 ,福建 福州 350108)
正史中的胡床及其变迁
黄清敏
(闽江学院 历史系 ,福建 福州 350108)
胡床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原以来,对人们的生活起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以后发展为交椅,考诸正史,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和宋元之后是这一坐具运用得最为频繁的两个时期。探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此外,政治制度、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思想观念等对这一坐具的变化都曾产生了影响。
正史;胡床;交椅;变迁;民族融合
胡床,顾名思义,胡人用的床,不是汉民族的家具,亦称为马扎、交床、交椅、交杌等。汉代及其以后的文献记载不少,描述的很清楚:它源于西北惯于迁徙的游牧民族,是一种以绳条为面、可以折叠的凳子。胡床是一种便携式坐具,由八根直材构成,两根横撑在上,用绳穿过座面,两根下撑为足,中间各两只相对相交作为支撑,交接处用铆钉穿过作轴承,造型简捷,实用方便。它可张可合,张开可作坐具,合起来可提可挂,携带方便,用途广泛。对中原地区人们传统的家具、生活起居习惯和礼仪风俗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考诸正史,或可理清这一坐具的变迁轨迹。
一、正史中胡床的使用及其变迁
自汉武帝凿通西域以来,“丝绸之路”的开通,使中国与中亚地区、印度以及西北少数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异域习俗风行一时。正史中关于胡床的最早记载见于《后汉书》:“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1]3272。灵帝生活于东汉末年,约 168—188 年在位,可知这种胡式坐具约在公元2世纪末时传入中原地区。汉魏以前,在人们的起居生活中,无论是席地,还是坐床榻,都以跪坐为合乎礼节的坐姿。箕踞,则是不礼貌的行为举止,并且还形成了一整套以跪坐坐姿为基础的约束人们行为方式的礼仪制度。所以,胡床这一可供人踞坐的高足家具虽已传入,但其使用者往往遭到社会舆论的非议,在社会生活中传播范围有限。汉灵帝崇尚胡风,论者即指其“此胡妖也,其后董卓多拥胡兵,填塞街衢,虏掠宫掖,发掘园陵。”[1]3272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幸灾乐祸的意味,将其视作亡国的征兆。所以这一时期,还不具备广泛使用这一外来坐具的社会环境。至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引发五胡乱华之后,胡风劲吹,游牧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冲击相当剧烈,传统的礼仪制度也不能幸免,从而为胡床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至魏晋南北朝,胡床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史载“泰始(265—274年)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盘,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蓄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2]823。几乎在社会生活的各种场合都能见到胡床的影子。正史中自《后汉书》以下,“胡床”之名随处可见。众所周知,正史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胡床这一坐具名称之所以频频出现,正是它得以广泛应用的最好例证。综观正史中的胡床,其所运用的场合大致有:
1.战事行军:胡床因其轻便易移,在军队中曾被普遍使用。战事纷扰之时,这种折叠式的坐具屡屡出现于两军对垒的阵前。东汉末年战乱不休,史载曹操与马超作战,“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3]34。可见当时曹操是坐在胡床上指挥军队作战的。宋朝大将刘沪“坐胡床指挥进退”[4]10495。清顺年间,将领坐在胡床上观察战争情势的情形也很常见:据记载,沈攸之举兵叛乱齐时,“攸之乘轻舸从数百人先大军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军,有自骄色”[5]446。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一日数十接。太祖坐胡床督战,(刘)基侍侧,忽跃起大呼,趣太祖更舟。太祖仓卒徙别舸,坐未定,飞驳击旧所御舟立碎”[6]3780。
2.用于狩猎等准军事活动:狩猎是一项带有军事演习性质的活动,以示安不忘危。原始社会人类为了获取食物,不得不想方设法猎取野兽。当农业和畜牧业充分发达足以满足人类需要的时候,狩猎活动就具有了多方面的意义,练兵即为其中之一,而射箭则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狩猎活动中用胡床的例子,可见《三国志》的记载:“(苏)则从(魏文帝)行猎,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将斩之”[3]493。射箭活动中用胡床的例子,突出的是东晋王济与王恺较射赌“八百里驳”的故事。“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恺亦自恃其能,令济先射。一发破的,因据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来,须臾而至,一割便去”[2]1206。
3.用于行旅路途:由于胡床可放可收,易于携带,使用便利,因此在旅行时,胡床成为一种轻便坐具,随时可以放下休息。或步行携带,或置于车、船中。刘瓛是南朝宋齐时代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博通五经,尤精礼学,著述多种。“游诣故人,唯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问答”[6]679。车、船中也经常携有胡床,《晋书》记载:“谢艾与麻秋华战,下车踞胡床,指挥处分”[2]2242。在旅途中,轻便易携的胡床自然要比其他的坐具更受欢迎。
4.用于家居生活:胡床在家居生活中运用也十分广泛,室内室外都有使用的记录。《晋书》记载王恬在庭院里使用胡床,“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发,神气傲迈……”[2]1755;颜延之于室外使用胡床,“延之于篱边闻其(张镜)与客语,取胡床坐听……”[5]579;陈高祖陈霸先于楼阁之中使用胡床,“独坐胡床于阁下,忽有神光满阁,廊庑之间,并得相见……”[6]259。胡床也是宫廷中常用的坐具,除前引汉灵帝、陈霸先外,还可见天平元年(534年)东魏孝静帝使舍人温子升草敕致高欢,“升逡巡未敢作,帝据胡床,拔剑作色。子升乃为敕曰……”[7]14;侯景甚至在床上摆设胡床,史载他篡梁以后,在宫中“床上常设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8]862。从正史中,我们不仅仅可以看到诸多男子使用胡床的事例,女子也不乏其人,这两例都见于《北史》的记载中,《北史》记载尔朱敞出逃后,“遂入一村,见长孙氏媪,踞胡床坐,敞再拜求哀,长孙氏愍之,藏于复壁之中。”[9]1768还有一例是隋唐时期郑善果的母亲崔氏,史载她“性贤明,有节操,博涉书史,通晓治方。每善果出听事,母恒坐胡床,于障后察之。闻其剖断合理,归则大悦。若行事不允,或妄怒,母乃还堂,蒙被而泣,终日不食”[9]3007。
胡床的用途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场合,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的记载,由于它轻便易移的特性,情急之下甚至可作发泄怒气的工具,史载梁太祖生气时曾以胡床掷部将[10]212。行动不便时,胡床也可作移动工具,起到担架的作用,光绪三年(1877年)陈豪“因病乞休沐,将去任,有淹讼久未决,虑贻后累,舁胡床至厅事判定,两造感泣听命”[11]13084。胡床收纳时可节省空间——悬挂:曹魏时裴潜为官衮州,两袖清风,“尝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挂柱。”[3]673北齐武成皇后胡氏“自武成崩后,数出诣佛寺,又与沙门昙献通。布金钱于献席下,又挂宝装胡床于献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9]522。胡床的形制依据持有者的不同,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装饰,如上引之例中北齐武成帝生前所坐的胡床即装饰有宝物,《宋史》则记载曹彬虽为皇亲国戚,却自奉清廉,“衣弋绨袍、坐素胡床”[10]8978,曹彬获得的赞许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达官贵人并非人人都如曹彬那样朴素。当时朝廷用于怀柔远人、赏赐少数民族首领的就是“金饰胡床”[4]10087。
胡床由于东汉时期崇好胡物的汉灵帝而得以传入中原,时至隋朝却又由于忌讳胡名的隋炀帝而更名,《贞观政要》记曰:“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11]。隋炀帝有鲜卑血统却尤为忌讳胡人,因胡床两足相交,遂改名交床。宋代程大昌在《演繁录》中也说到“今之交床,制本自虏来,始名胡床。隋以谶有胡,改名交床”①。对此,胡三省进行了较详尽的注释:“交床以木交午为足,足前后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错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后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窍以穿绳绦,使之而坐。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可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12]。从这些材料来看,隋唐时代的胡床,只是名称发生了改变,其特征并未发生变化,仍是折叠凳。但是要更改一个民间沿袭已久的词汇远非皇帝一纸诏令能实现的,所以胡床一名一直使用,直至清朝正史仍可见这一名称。交床这一皇帝钦定的名称在正史中出现,竟然迟至元朝,而且仅有4例:《元史》中的1例交床作为皇帝赏赐的物品出现,《明史》中的3例则见于礼仪舆服中,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不大。宋朝是中国所有家具定型的最后一个时期,胡床的形制至此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靠背,舒敛自如的交椅诞生了。据陈增弼先生考证,宋代交椅共有4种类型,即直型搭脑、横向靠背式;直型搭脑、竖向靠背式;圆形搭脑、竖向靠背式;圆形搭脑、竖向靠背,附加荷叶形托首[13]。搭脑是指椅背最上部的横向杆件,圆形搭脑在宋代被称为“栲栳圈”。栲栳原指用柳条或竹篾编成的笆斗之类的盛物器具,宋代交椅的圆形搭脑看上去弯曲如栲栳,故而得名。交椅的出名还与卖国贼秦桧有关,宋人张端义在他的著作《贵耳集》中描写了这一段史实:“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宰执侍从皆用之。因秦师垣(即秦桧)在国忌所,偃仰片时坠巾。京尹吴渊奉承时相,出意撰制荷叶托首四十柄,载赴国忌所,遗匠者顷刻添上,凡宰执侍从皆有之,遂号太师样。今诸郡守卒必坐银校椅,此藩镇所用之物,今改为太师样,非古制也。”[14]据这一段资料分析可知,吴渊为了讨好秦桧,在圈形搭脑的顶端又加上了荷叶形的木构件,以方便人们休息,避免仰头时头巾坠落。但是由于这种有荷叶托首的交椅结构复杂,又与秦桧相关连,不久就退出中国人的家具行列也就不足为奇了。通计二十五史中,胡床及其演变的交床、交椅出现的次数如图1所示。

图1 正史中所见胡床、交床、交椅出现次数统计表
二、正史中胡床出现的两个高频率时期
统计二十五史中,胡床、交床、交椅共计出现115次,这一坐具出现频率最高的时代,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多用于战争及日常生活等非正式场合;一是宋元之后,多见于内廷仪仗卤簿中。
胡床于东汉末期传入中原,但运用的范围多限于社会上层贵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迎来了胡床运用的第一个高峰,这与这一时期风俗文化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首先是胡汉风俗文化的冲突与整合。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汉族风俗文化与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交流最激烈、最频繁的时期,也是两种风俗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会的时期。此时汉族风俗文化对少数民族风俗文化的吸收和摄取首先就表现在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风俗方面,胡床的普及应用即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古代中国没有坐具,宴请、会客、读书皆席地为之。所谓“席地”,即跪坐在席子上,坐时,膝盖着地,臀部坐在后脚跟上,双手放在膝前。如果臀部坐在席上,双膝在身前屈起,足底着地,双手后撑;或者双膝平放,两腿前伸分开,形如簸箕。这种姿态,古时,人们称为“箕踞”、“箕倨”、“箕股”,简称“箕”或“踞”。在日常生活中,“踞”被视为一种不文明,不符合礼仪的动作,是最失礼的坐相,因此,《礼记·曲礼上》规定:“坐毋箕。”《史记》记刘邦踞床接见郦食其。郦生见了不拜仅作长揖,还批评他:“足下必欲诛无道秦,不宜踞见长者。”[15]358刘邦自觉有愧,连忙站起整理好衣裳,请郦生上坐。相反,在非正式场合或个人独处时,仍采取跪坐姿势,则被认为是礼教的楷模,如汉魏时的高士管宁,史载其“常坐一木榻,积五十年,未尝箕股,其榻上当膝处皆穿”[3]359。降至魏晋南北朝,逐水草而徙的游牧风俗与农耕为主的汉人风俗在战争与经济交往中产生冲击与整合。胡人“苟利所在,不知礼义。……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15]2879。胡人几乎没有礼法底蕴的价值观与伦理观,连同其游牧的生活方式,在胡汉杂居融合的过程中,使汉人渲染了不少胡气。在并入汉习俗轨道的过程,胡习俗也以其固有特质对汉习俗系统加以冲击、改造。蛮野而充满生气的北族精神,给高雅温文却因束缚于礼教而冷淡僵硬的汉习俗带来新鲜空气。北魏崔浩说:“太祖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16]811,指的便是这种趋势。胡床在魏晋南北朝的广泛运用,正是汉人对胡人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认同与吸收。其次是礼教控制的松弛。自东汉末年以来长达四百年的分崩离析导致的割据性,使统治者的精力多集中于对皇权的争夺和巩固,对思想文化的干预弱化,更遑论对社会生活的礼制控制和规范。而山岳崩溃式的社会离析,走马灯式的改朝换代,更令人悟兴废之无常,哀人生若尘露,连一代雄才曹操都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苍凉悲叹,这与乐观进取的秦汉文化精神全然另成格调,使士人们不再致力于皓首穷经,而是及时行乐,以游戏人生的态度虚度岁月,放诞不羁,个性解放。逐渐形成了言行怪异、藐视流俗、离经叛道的生活内容,他们往往率情任性,行为举止多横斜逸出于传统规范之外。如王徽之与桓伊之例,王徽之路遇桓伊,请其吹笛,“伊时已显贵,素闻徽之名,便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2]2118。他们不交一言,因为王、桓二人要欣赏的只是纯粹的音乐之美,除此之外任何东西都是多余的,包括语言。这样的举动看似怪诞不合情理,但在魏晋士人看来却并无不妥。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人们对于踞坐逐渐采取较为容忍的态度,史载梁武帝的侄子萧藻“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模”[8]362,萧藻由于跪坐而被奉为正面典型,这正从反面说明了踞坐的流行。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更多的是考虑它的实用性,使它更接近于现实、更具有直接的目的性和更符合人们的生存需要,而不在乎它是否合乎社会礼仪和传统习俗,垂足而坐的胡床得以广泛运用实不足为奇。
其次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行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流行却在魏晋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深受战争离乱之苦,精神苦闷,来自佛国的召唤使人们痛苦的心境得到慰籍,更加助长了人们对“登天堂”一类死后幸福生活的憧憬。统治者更是把佛教当作一剂治国良药,所以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在北方统治者看来,因为佛出西域,被视为“戎神”,更容易为北方百姓所接受,故其传播要比在南方民族中更为广泛、更为深入。在精神解脱和实利追求的双重作用下,此时佛教信徒剧增,香火大盛。南方则大批营建寺院,唐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便是极言南朝佛寺之多。其实,南朝佛寺何止480座,史书中记载仅梁朝“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6]1721。普通百姓也常“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8]670。南北的盛况,形成了佛教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潮。佛教的盛行,把异域文化带到了中原大地,异域的价值观、审美观通过佛教造像和壁画中的人物形象、服饰、家具等方面慢慢渗透,影响到当时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铿铿锵锵、断断续续的石窟开凿声,描绘着天竺佛国家具式样的壁画渐渐地进入人们的眼帘。这些佛与菩萨的坐具和使用的高型家具,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画面,是完全新鲜的、前所未有的、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把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比做一池春水的话,这些佛国家具就像一阵猛烈的春风吹皱了千年来不曾动荡过的平静水面,冲击着中原地区古老的习俗。天竺佛国的大量高型家具,如椅、凳、墩等,随之进入了中原地区。这对中原地区的生活习惯,特别是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从此,中原地区传统的席地而坐的起居方式开始动摇,伴随着高型坐具而来的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地改变着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
再者当推服饰形制的变迁。中原地区传统的正襟危坐除与礼制密切相关外,还受到服饰形制的制约。魏晋之前下衣极不完备,人们在裳内多着胫衣,胫衣就是只有两条裤管,穿时套在膝盖与脚眼之间,后发展为一种没有裆的裤,这从另一侧面解释了箕踞无礼的真正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裤的变化相当大,可以说是发展为现代上衣下裤形式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人们或著上襦下裳,或著袍、衫等长衣服,著裤主要是为腿部保暖,故《说文》对裤的解释为“绔,胫衣也”,即其主要作用是保护小腿。《释名》称:“裤,跨,两股而跨别也”,即两条裤腿是分开的,在档部并未缝合,其形制类似于今天的套裤。因此汉代家境贫寒的人不穿裤是相当普遍的,甚至官员亦有不著裤去办公的。至魏晋时期这种样式的裤子仍相当多,如三国魏许允任中领军,得知大将军司马师下令逮捕李丰。“欲往见大将军,已出门,中道还取裤,丰等已收讫”[3]304。许允不著裤而能出门,显然身著袍服等长衣,而且所穿的大概还是那种不合裆的裤子。不过在上身穿短装时,则必须穿合裆的裤子,即北朝所谓的合裤。由于北方气候严寒,游牧民族终日生活在马背上,因此穿著裙、袍等服装都显得不方便,故北方游牧民族很早就已穿用满裆裤,这种满裆裤行动方便,而且节约制作材料,所以自汉代传入中原后,首先为下层劳动人民和军队所接受,并逐渐向社会各阶层扩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满裆裤应用日趋广泛,这就为更多的人采用垂足而坐的坐姿提供了可能。
唐代正史中胡床的记载很少,胡床运用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是在宋元以后,这一坐具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大大减少,而是较多地出现于车舆礼仪中。这一时期“胡床”与“交床”、“交椅”名称在正史中都有出现,它们之间似乎存在天然的分工:在内廷仪仗卤簿中多用“交椅”、“交床”,在其他日常生活场合则用“胡床”。探究这一变化出现的原因,首先宋元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时期,北宋时是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南宋时,先是宋、金,后是宋、元的南北对峙。各个并立政权之间既有征战也有和平,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接触交流比较频繁,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蒙古人是游牧民族,住穹庐,室内也没有特殊的家具摆设,为了适应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一切物品以方便提携为主要原则,因此,他们统治汉人虽然接受了汉文化,却也保存了部分自己民族的生活方式。由此风气又开,胡床在正史中的记载开始增多。其次是在两宋时期,垂足坐已成为了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坐具做为室内的一种陈设,它的尺度要先取决于建筑的室内空间。最初的原始住宅甚至不能被称为住宅,只是一些可以聊做遮挡的掩蔽物,是原始人类通过对一些自然现象的观察后,为了不再风餐露宿而仿“建”的房屋,这种建筑的使用功能可以说是当时建筑的唯一功能。其主要形式有原始巢居与穴居。人们最初掘地为穴的筑造物是非常简陋和低矮的,内部空间也相当有限,这就决定了当时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坐具,他们的生活起居是以地面为中心,坐卧都在地上完成。为了追求舒适一些的环境,人们在地上铺上柴草、树叶或兽皮等,这些铺垫物可视为“席”的前身。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的起居方式,使矮座家具一直被持续使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宋代是我国古代建筑发展的高峰期,统治者从缔国之初即强调以文安邦而停止武力,即所谓“偃武修文”,至南宋时更是为得到所谓平安而甘心偏居南方一隅。时人皆有忧患之心而又居于繁华之地,忧患之心不可解,而繁华之地却让人们产生了苟且偷安之心,渐渐沉缅于享乐。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之下,有条件者都大肆修建居室。宋元社会居室虽有定制,建筑式样也规定“凡公宇,栋施瓦兽,门设梐枑。诸州正牙门及城门,并施鸱尾,不得施拒鹊。六品以上宅舍,许作鸟头门。父祖舍宅有者,子孙许仍之。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为饰,仍不得四铺习檐。庶人舍屋,许五架,门一间两厦而已”[4]3600。虽然宋朝政府颁布实施了这些规定,但是能否起到实际作用处当别论。现实生活中,建筑房屋时违反国家政策的现象屡见不鲜,越礼逾制现象普遍,如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时,“居室服用以壮丽相夸,珠玑金玉以奇巧相胜,不独贵近,比比纷纷,日益滋甚”[4]3577,可以肯定,违规者大有人在。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朝廷之所以不厌其烦地颁布各种禁令,大概是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许多与朝廷规定相左的房屋建筑,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已才强制推行法令来加以遏制。房屋日益华丽,以高型桌椅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基本定型。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导致家具的更新换代。传统的低矮家具已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求,因此高型家具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远古至唐代前期,中华民族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气候较为干冷,在寒冷的气候下席地而坐,行跪坐的姿势可以收敛四肢,用长衣遮蔽,以保持温暖。所以,虽然这时候垂脚坐具渐入中国,但原来的生活方式仍然存在。唐代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气候潮湿阴冷,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自然被摒弃。垂足而坐的生活方式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萌芽,经历了漫长的隋唐五代时期的过渡,到了两宋时期最终取代了几千年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生活的普遍形式。也正是因为这种新的起居方式的确立,极大地促进宋代家具种类、形制及室内陈设的变革,与这一新的生活方式相适应的高型家具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并逐渐壮大,人们的活动中心也由以床为中心渐渐向地上转移,并最终形成了以桌椅为中心的生活习俗,从而也促使家具的尺度逐渐增高。从北宋末到南宋初,高型家具大发展,垂足坐已完全取代了席地坐。考诸正史,椅凳类高型坐具的出现多在宋元以后,说明中国历史上起居方式的大变革至此已经彻底完成。
再次,宋代以来习俗日奢也是胡床这一简单坐具在日常生活中减少的原因。宋代朝廷以禅让的方式取得政权,而非汉唐那样从马上取天下,因此宋代统治者缺乏汉唐朝廷的励精图治精神,而是贪图安逸,纵情享受。北宋建国伊始,宋太祖就对臣下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17],这是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所玩的“杯酒释兵权”的把戏,殊不知这一金口玉言为赵氏王朝定下了享乐性品位,宋代因此对享乐性奢侈生活的认可和推崇尤为显著。受此影响,宋代社会始终弥漫着一股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奢侈风气。南宋朝廷则偏安一隅,统治阶级成员更是腐败之极,满足于守着残山剩水,纸醉金迷、宴安度日是也。纵观两宋,奢靡汰侈之风贯穿南北始终,为前代所未有,上行下效奢靡之风席卷全国,人们竞相奢侈,逐渐习以为常。不仅京都如此,而且奢靡风气遍布全国,如史载川陕四路“尚奢靡”[4]2230,两浙路“俗奢靡,而无积聚”[4]2177。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富户达官的住宅,在院落的布局、设计、构筑以及装饰等方面,越礼逾制,追求宽敞豪华,民间居室已突破礼制的束缚,日益追求舒适豪奢,上行下效流风相煽,使社会风俗愈来愈带上奢侈靡佚的色彩。这种风气的熏染之下,胡床这一简单坐具的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作为一临时性的坐具,其缺陷即在于不能倚靠,宋以后人们贪图安逸舒适,就给胡床增加了扶手和靠背,成为一种可倚靠的坐具,最终演变成了交椅,这种交椅保留了可折叠的特性,因此多用于仪仗卤簿或贡品中,装饰十分华丽,或为“金交椅”[11]3085,或是“银饰之,涂以黄金”[18],藩国进贡的则是“金银七宝装交椅”[4]14063,人们终究是希望能生活得更自由更舒适一些的。坐榻的高度可以突出高高在上的权威和地位,足以满足人们世俗的尊卑心理,还由于人们对舒展的坐姿在潜意识里的追求,使高型坐具最终取代低型坐具成为占主流的室内用品。

图2 正史中椅、凳出现次数统计表
三、结语
椅子作为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衣、食、住、行中“住”的关键环节,人们无论工作、学习还是休息,都不能离开椅子的依托,它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器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椅子已成为中国古代家具的象征。椅子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标志,与当时的社会生产水平、政治制度、生活方式、风格习俗、思想观念等因素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家具是由低型向高型发展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民族融合和外来文化的传入,高型坐具开始出现。此后,高型坐具不断增多并日益舒适化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至宋代以后,椅子成为家具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考察这一小小的坐具,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促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动因。椅子的出现到成熟,从简单造型到复杂的结构,逐渐系统化、装饰化、合理化、实用化。椅子这一小小的坐具是时代文明的反映,每个时期社会的要求不同,椅子就会有不同的新特点,椅子的发展与时代是密不可分的,是互相依靠,互相促进的。
(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闽江学院历史系07(2)班陈文培同学的帮助,特此致谢!)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沈约.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8]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9] 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0] 欧阳修.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 吴兢.贞观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2:7822.
[13] 陈弼增.太师椅考[J].文物,1983(8).
[14]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6] 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50.
[18] 宋濂.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59.
责任编辑:谢娅萍
Hu People's Bed in Official History and Its Evolvement
HANG Qing-min
(Department of History,Minjiang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Hu people′s bed to the Central part of China in the late Eastern Han dynasty,it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eople′s daily life.After Song dynasty,It had developed into folding chair which,according to official history,is the most popular seat the after the Wei,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s well as Song and Yuan Dynasties.The main cause of this phenomenon is national integration.Besides,political system、life style、culture and custom、concept and thought also contribute to the evolvement of this seat.
official history;Hu people′s bed;folding chair;evolvement;national integration
J520.9
A
1004-941(2010)05-0083-06
2010-08-20
福建省教育厅2008年A类社科项目“福州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A08147S)。
黄清敏(1972-),女,福建武夷山市人,硕士,副教授,现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