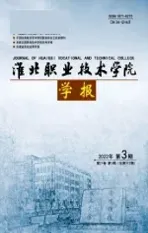论禅学文化哲思的审美趋向
2010-08-15沈晓燕
沈晓燕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系,安徽蒙城 233500)
·文化艺术研究·
论禅学文化哲思的审美趋向
沈晓燕
(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史系,安徽蒙城 233500)
禅宗文化具有中国传统美学极为鲜明与突出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追求超越人世的烦恼,摆脱与功名利禄相干的利害计较,以达求绝对自由圆融的人生境界。可以说,禅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资源,在经创造性现代转化后,将对现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理想境界构筑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舒展国人性灵呈现出隽永的现代审美情趣。
禅宗文化;传统文化;人文资源;参禅悟道;安祥心态;道德重建
中国文化自商周以来便在“一元文化”专制的政策与实际存在的“多元文化”的矛盾斗争中发展,每当一元文化专制强化,社会文化便由僵化而走向崩溃,斯时必然会出现多元文化竞争的局面,以塑成中华文化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是在西汉儒学专制强化所导致的儒学僵化、社会笼罩着一片信仰危机的机遇下,被请进中国的。“白马驮经西来”,禅宗文化以新颖的思维方法、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以刺激启发,使其僵硬的躯体焕发生机,促成了道教的创立、改革和魏晋玄学、宋明新儒学的创生,形成儒、释、道“三元共轭”的文化格局。
一、禅学文化的人文渊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禅”不是可传递的什么物体,它是一种心态、一种境界、一种启示性。六祖慧能大字不识一个,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只听了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印证了佛法,成为开启一代风气的著名禅师。名相的知识,空洞的概念,这些向来与禅宗无缘。禅宗虽然也讲公案,讲话头,用语言文字表说,然而那些不过是“家家门前火把子”。各人的火把可以不一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功用,即照亮真理世界,虽然它们本身并不是真理世界。这就使“禅”的真精神、真意义不能像知识、学问那样可以传授,而只能以澄明的本心去体验、参悟。所以,参禅应该既不是一种仪式化的姿态、一种功利化的工具,也不是一门可以傲人玄博的学问、一项可以标志人格素质的知识。“禅”容易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枯寂无为的。以正统自居的儒者们排斥异端时,常给“禅”捏造的罪名便是“主虚而不务实,尚无而不本真”、“古井无波,尽日枯坐,只可谓这养生,却有何手眼达生尊生耶”、“禅静只恐坏了天地之生心”等。然而这些不过是禅师之末流,禅法之表象,是那些儒者戴着有色眼镜的观照。耕云禅师说云:参禅最重要的是“因正果圆”,如果“因地不真”,便会“果遭迂曲”。[1]22现实社会的有些人“参禅”是因为觉得“禅”很玄很妙,想要作一个很玄很妙的人;有人参禅是因为在滚滚红尘中有了挫折感、无奈感、绝望感,想在参禅的过程中寻求心理上的安慰;有人参禅是借助这种途径佞佛谄佛,企图以自认的“虔诚”换取神佛的保佑。这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心理,甚至还不如商品社会中的等价交换。他们很像一则古代寓言中的某类人物,把一杯薄酒、一个猪蹄子供奉上天,要求的却是上天赐给地王五谷丰登,猪肥牛壮。可以说,抱着这样的动机参禅,自然不能发扬禅的真精神或实现禅的真意义。禅宗文化的审美价值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参禅”可以造就安祥心态
禅学主张“参禅”并非是古井无波。而是“万事与人一般”,并不摒弃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从这个角度说,参禅并非是“主虚而不务实,尚无而不本真”。[2]58“禅”强调的无非是“自性”的觉解,“佛法”的现量呈现。当人们为“执”所迷,为“障”所惑的时候,“自性”泯灭不见,自然就被认为是“无”;当人为官能构陷,为欲望牵制的时候,“佛法”被迷雾所遮蔽,自然就被认为是“虚”。孰不知参禅追求的正是最普遍的“真”,这种普遍甚至存在于屎溺之中;追求的正是最绝对的“实”,这种“实”不是小聪明小计谋所获得的即时的实惠,而是在安祥心态下的“正受”。也就是说,既是真正的感受,又是真正的受用。禅宗文化这种真正的感受与受用使人充满生命的活力,使人保持应付外界的最佳状态,使人不在欲望的凌迟下“焦虑”或者“无聊”。更重要的是,使人在生命的本然状态之下真正地享受生命。
2.“参禅”可以提升精神境界
冯友兰先生曾指出:行道德之事者未必是真道德。[3]61譬如说,蚂蚁们亦可为杀“敌”而奋不顾身,但人们不认为这是一种“道德”的行为,因为蚂蚁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缺少“觉解”,并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同样的,有的人也行道德之事,但是他们也不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或者按照某种习俗,或者是出于一时的偶然,甚至还有可能出于某种功利目的。所以,这些人行道德之事仍旧出于“自然境界”,或者是“功利境界”,严格地说不能认为是道德的。而参禅强调的正是人与宇宙本然关系的感悟,解决的正是人在天地之间如何安身立命的大问题,而这正是冯友兰先生所言的“天地境界”,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精神境界。在此境界下,调节人们关系的伦理规范、道德行为才真正具有了意义。在今天,说得具体一点,参禅甚至还能促进高明的思维方式。美国《文化评论》刊物曾登过一篇对德里达的访谈录,里面谈到德里达声称他平常竟然还是参禅的!他说:东方的“禅”有着极高明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二元对立、主客二分”等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着极大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他写作《书写与歧异》时的思路。[4]92总之,“禅”在当今的意义不能以世俗的功利眼光加以观照,虽然精神层面的东西经常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难以言传,但它的意义仍能够在人们的具体审美体验中呈现出来。
3.“参禅”可以维系道德重建
我国自古以来,强调“以德立国”。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人,诚意正心、博施济众、明因慎果、慎独自律,中国传统社会赖此得以良性运转数千年。道德是维系社会安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要素,道德状况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密切相关。降至现代,我国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无序状况,导致我国道德滑坡的原因众多,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现代中国人不信因果,甚或嘲笑因果,认为诚实就是傻冒,做恶即是能干。由于这种心态的支配,一部分人便滑入肆无忌惮、胡作妄为的邪道;即使有法律禁令,也会铤而走险。加之市场经济驱使贪欲的炽盛,更是冲毁着本已脆弱的道德堤坝。诸种事实令我们尖锐地意识到:能否重建当代中国道德文化,不仅关系到我国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发展,而且更关系到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存亡盛衰。
二、禅学文化的审美价值
禅宗文化注重人生的身心净化,并不推崇效率至上,淡化对物质生活的贪恋;主张以简朴的物质消费获得生命必需的生存,而更多地关注精神与心灵的解脱,完善道德人格,求证菩提正觉。在这个人生目标的大前提下,物质感官享乐也便能得到合理合法的调节。简朴的消费观点,一方面可以缓和强大的生存压力与紧张,抑止贪欲驱生的邪恶;另一方面由于适度使用自然资源,而与自然界保持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与此相反,那些奉持高消费观念的人们,则容易肆意地掠夺、挥霍自然资源;如果本地资源有限,便容易引发向外扩张的野心,穷兵黩武导致血腥战争。事实证明,简朴的消费观念看似缺乏“市场效率”的现代意识,即所谓以消费促进生产的谬论,却是人类和平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禅宗文化又是根植在中国历史与文化土壤里的一种价值创造,迄今已是具有两千余年悠久的历史。这是一个极其真实的传统,活在当代,活在世人的心灵深处。但如何去体认及开掘禅学文化传统。大致说来,禅宗与现代社会当存有如下几个层面的关系:
其一,禅学文化乃当今世界信仰重建的重要资粮。面对着一个时代更替,固有人生寄托失落,而商品经济狂潮的冲击,又使知识怀疑、精神空虚、一再向外驰求、缺乏生命反省,等等,社会、精神现象亟需一个供人精神反省和心灵关怀的新型价值信仰体系。传统儒学的德性知见,似难独当此任。佛教文化之悲智双运、真俗无碍、德性与知性并重的智慧,可以为信仰重建提供新理路。其关于空、无、缘起的哲学知见,经创造性的诠释,可使人们于流动、变迁、失落之中窥见本相,认识自己的生活真实,既能适应生活变异而随缘,亦可真实如常自性不变。
其二,禅学文化有助于中国文化之重建。佛教哲学的深奥精妙已为学人所公认,只是由于对宗教文化心存偏知,促进学人对此知识传统开掘不力,或者浅尝辄止,或者过河拆桥,援佛入儒,又转而斥佛。本世纪以来,佛家智慧已成为东西方哲学得以汇通之津梁,同时也成为许多思想家诸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人构筑自己哲学体系的基石,其在文化重建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已是显然。佛教哲学智慧注重名相分析、概念清晰及逻辑严密,可使中国哲学的价值观念秩序化、明朗化,呈现理性意识和思辨特征,息妄求真、由迷转悟、转识成智等生命智慧,可以解决现代人面临的无根无向的困扰及现代生活中机械化、专业化种种问题,从而成为中国哲学知识与价值并重的现代内涵。
其三,禅学文化可以纠正当今社会的某些精神偏向。时下有气功、周易相学等热潮,在健身之中呈现为超越祈求倾向,从而流失于迷信。即使是寺庙中善男信女群集礼拜烧香,也大都是个人求福之事,反映出神秘崇拜特征。林林总总,正可反映现代人心量的狭小及精神空虚而表示出的偏向。佛教文化的真实内容,实际是生命本真的启迪和觉悟,是对生活中虚幻、染污、执迷等现象的斥除,并承认世界的变迁意义,主张随缘而消旧业,在主张真实自持和同时予世人以自觉自救的方便,并把价值关怀祈向始终指向人间世俗的生活,崇尚“平常心即道”,以求众生安乐、国土庄严。[5]66如此类问题获取重视,非但可以彰显佛教的现代意义,纠正当前佛教发展中的一些偏向;同时也可能使人们注重“以终极关怀为目的”的宗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力求有一个公允平和的认知,为当今整个世界“无家可归”的精神迷失中,寻觅解决之方便及其真实所在。而禅学文化在中国未来多元文化竞争、文化重建中堪以承当特殊重任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宽泛的文明自觉
人类文化近几百年来尤以物质文明的进展愈来愈快,但从整体上看,人类创造文化的活动还几乎是盲目的、受异化力量驱迫的,不断征服自然以解决人与自然界的矛盾,结果是物质财富虽然增加了很多,却招来自然界的无情报复,导致生态失衡及人与人矛盾的激化、与自己精神家园的疏离。对“怎么样”的问题虽然有了许多解答,但对更为根本的“为什么”的问题,却比古人还更茫然无知。对创造文明的目的、路线和创造活动的价值、后果,对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还缺乏明晰的自觉,也缺乏对自身创造活动的控制能力,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巨大缺憾。佛学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以禅思开发的超越性智慧,以全宇宙为座标,冷静审视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揭露人生的缺陷,指出人类文明创造活动的目的,终在突破现前的痛苦、无常、不自由而趋向永恒、幸福、自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虽是阻碍人类实现这一目标的直接障缘,但这两种矛盾,终以人与自身的矛盾为本。因此,人类创造文明的活动,应以解决人与自身的矛盾、建设精神文明为枢机。只要实现自身生命的圆满变革,一切矛盾自然消解无遗,作为文明终极目标的永恒、幸福、自在才能真正实现。只知向外追逐征服自然,终难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终难脱出痛苦、无常、不自由的境地。这种深彻的文明自觉,乃现有各种文化所或缺。佛学独具的照彻文明大本的智慧,堪作全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可以提醒人类冷静审视文化创造活动,反省自身,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三大关系,重视“人的革命”,端正文明航向,防止逐物不返、征服自然等文明偏弊,保持清醒的文明自觉。
2.自心自我的如实觉知
人类对自心这个主枢者、创造者、价值承当者认识之深浅,已成举世公认的最大缺憾,作为生存和一切价值建立基点的自我之迷失,成为折磨当代人的一大苦恼问题。对自己身心的研究,对真正自我的追寻,必将为未来的科学、哲学所重视。然科学研究人自身,多用研究物质现象的方法,用以研究人自身尤其是极为灵妙的人心,显得支绌艰难,哲学所用逻辑思辨的方法,在探究人自身存在问题时也难以得其究竟。禅学以“如实知自心”为解决人存在的根本问题、解脱成佛的诀要,对人心不仅有八识五十五心所等详悉解析,有对假我、真我之明辨,更有禅思内求以自制其心、自净其心、自识其心、体证真正自我的特殊技术,可藉之以窥透心灵黑箱,发现真正自我,必将被未来的人类所珍重。
3.人文主义与科学精神
佛学超越民族、国家、种族等畛域,高扬“众生平等、皆有佛性”的大旗,强调“以己为洲”、“以法为洲”,不仰赖上帝鬼神,而主张依自己力量,依本然如是的真理自净其心,自己解放自己,并以平等普度众生、利乐众生为必尽之责任。这种对众生的高度尊重、高度关怀和高度的人文主义精神,在诸宗教中可称独一无二,最容易被全人类普遍认同,成为系全人类于一体的精神纽带。佛学更强调“以法为师”,以宇宙人生法尔如是的真实为最高皈依处,教人“如理作意”,通过使自己主观认识完全符契客观真实的修行实践,实证真实而确立正信,其理论与修证体系,乃经佛陀和无数佛弟子的修行实践所证明,具可验证性,任何人只要肯依教奉行,都可在自己身心上体证。[6]佛学重智尚真,崇重理性,强调用理性思维推论,以步入实证真实之径,其教义极富理论性、哲学性而又超理性、超哲学,其有关身心世界的诸多说法,不断被科学发现所证实,其思维与实证方法,颇与科学相契合,当代多门前沿科学的发展,都表现出与佛学遥相接轨的趋势。佛学的这种人文主义、重理智尚验证、非有神论的特性,超越了宗教,最能适应和满足科学时代人类的宗教需要。佛学重视物质生活的完善,提倡掌握“五明”等知识技术尤其是“工巧明”(科学技术)以利益众生,可以纠治东方儒家文化等轻利轻商、从而不利于发达物质生活的弊端;佛学又特看重精神文明,力揭逐物不返、耽溺物欲的祸害,可以补救西方科技文明片面发达物质生活的偏弊。
总之,佛学在未来文化重建中的作用和价值,大概不应只是主要庄严一种古老宗教,度化多少人出家修道、得大成就,不应主要用来满足少数厌世阶层、好奇阶层的宗教需要,不应只是社会文化橱窗中的陈列品、点缀品,而首先应作为多元文化中的长者、领队者,以领导文明的姿态、入世担当的精神,面向全人类,挑起化世导俗的重任,参与、投入现实生活、“两个文明”的建设,给人类提供掌握文明航向的智慧,给个人提供安身立命的大本,促进科学的统合、飞跃,及政治、法律、教育、民族关系等的改善,促进世界和平和生态平衡,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合理转型。这是作为人类智慧最高成果、具有诸多文化优势的禅宗文化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综上所述,禅宗文化具有中国传统美学极为鲜明与突出的重视人生并落实于人生的特点,追求超越人世的烦恼,摆脱与功名利禄相干的利害计较,以达求绝对自由圆融的人生境界。可以说,禅宗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资源,在历经创造性现代转化后,将对现代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理想境界构筑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为舒展国人性灵呈现出隽永的现代审美情趣。
[1] 商聚德.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石家庄:河北文学出版社,1991.
[2]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3] 章海山.当代道德的转型与建构[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4] 许思园.中西文化回眸[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5] 刘崇顺.社会转型与社会心理变迁[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7.
[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D946.5
A
1671-8275(2010)04-0038-03
2010-05-05
沈晓燕(1972-),女,安徽蒙城人,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责任编辑:张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