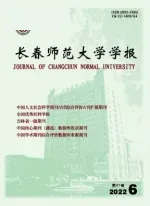《活着》内在意蕴解读
2010-08-15李丹丹
李丹丹
(长春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
《活着》是余华在20世纪90年代初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继《在细雨中呼喊》后进一步显示了他创作上的转向。作品以朴素的现实主义手法,讲述了小人物的生活与命运,但使人颇为费解的是小说题目与内容之间的悖论——题名为《活着》,讲述的却是一个个关于死亡的故事。面对这样的文本,读者总是不禁想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解释,领悟其内在的思想意蕴,破解其中的谜团。
从文学理论上讲,文学文本的意蕴可以分为历史内容、哲学意味和审美意蕴三个层面。文学文本意蕴层的呈现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有的往往首先凸现的是与作品题材密切相关的历史内容层面,因而也被称为本事意蕴或形而下意蕴,如历史题材的作品多是如此;有的则以较新颖的形式直接引领、敦促读者进行哲学意味的探寻,因而又可称为形而上意蕴,如一些现代派或先锋派的作品多是如此。而且有的作品还会出现超常规的单纯化或复杂化两种极端的形式,即仅有审美意蕴或是具有多重意蕴。但是文学文本意蕴最一般的呈现方式是审美意蕴层、历史内容层和哲学意味层。[1]我们也不妨以此来解读《活着》的内在意蕴。
一、审美意蕴层:亲情与人性的感动
当我们阅读余华这本仅有12万字的薄薄的小书的时候,内心总是充盈着丝丝缕缕的辛酸与感动。这感动首先来自于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浓浓的亲情与美好的人性。
在艰苦的岁月中,福贵一家人相依为命,几经聚散离合,生离死别,但彼此心中始终不变的是对亲人的牵挂与惦念。虽然全书的主体都是以农村老汉福贵自述的形式写成的,平实、质朴,但仅凭字里行间流淌着的纯真、自然的情感就足以打动人心。当福贵背着凤霞要把她送回到城里寄养的人家时,“她 (凤霞)的手在我的脸上一摸,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那户人家去了。背起凤霞就往回走,凤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走了一段她突然紧紧抱住搂我,她知道我是带她回家了。”读到此处我们的内心怎能不生出柔柔的感动,体会到父女情深?
福贵独自一人埋葬有庆的情景也会使人潸然泪下,“我用手把土盖上去,把小石子都捡出来,我怕石子硌得他身体疼。埋掉了有庆,天蒙蒙亮了,我慢慢往家里走,走几步就要回头看看,走到家门口一想到再也看不到儿子,忍不住哭出来声音……”当福贵和家珍从坟地回到村口,作者写了这样一个很巧妙精彩的句子——“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它不禁让人联想到盐撒在伤口上的感觉。这感觉当然是来自痛失爱子的父亲的内心。品味着这句话,让人久久不能自已。
书中不仅表现了令人悲伤心痛的情感,也不乏一家人生活温馨与喜悦的情景。比如,凤霞出嫁后,福贵经常到城里去看她和二喜,回来就要和家珍说半晌凤霞屋里屋外的事,说得口干舌燥,说得废寝忘食——“一说说到天黑,村里人都差不多要上床睡觉了,我们都还没有吃饭。”浓浓的亲情就从这些或是叫人潸然泪下,或是让人忍俊不禁的场面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在书中,透过余华那些平实、质朴的文字,直抵我们内心的还有家珍的贤淑勤劳、凤霞的聪慧能干、有庆的天真善良、二喜的质朴憨厚、苦根的乖巧可爱,以及福贵内心深处深沉的父爱,对妻子的体恤和对外孙的疼爱。当苦难一次次袭来的时候,这些人间最自然最朴实的情感、品质,也就显示了最美丽最动人最高尚的力量,“使作品增添了人文关怀的色彩。”可以说,“余华对人性恶的表现惊世骇俗,令人目不忍睹,有振聋发聩之功效;余华对人性善的描写令人辛酸,令人同情,令人荡气回肠。”[2]也让我们再次重温了人性的善良与美好,从中首先获得了一份美的感受与体验。
二、历史内容层:生活的艰辛
透过余华所讲述的动人故事,我们体会到内心感动的同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命运的波折与多舛。
在小说中,福贵一家人似乎总是被一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所操控所掌握,一步步走向他们的宿命。福贵只因帮一个小孩去敲门,就阴差阳错地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于是才有了后来与家人分离并死里逃生的故事;医院的医生为了抢救县长的老婆,就不惜将有庆这样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的血抽干,造成了有庆的死亡。其他次要人物,如老全、龙二、春生等的死亡也各有各的原因——老全在战乱中被子弹击中而死;龙二因为赢了徐家的田产,在土改时被定为地主而遭枪决;身为县长的春生则在文革中被定性为走资派,因受不了虐待而上吊自尽。文革中,连村里的队长也被城里来的革命小将带到城里打得鼻青眼肿……仔细思量,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生的偶然事件背后其实隐藏着历史的必然,这只看不见的命运之手其实就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历史文化背景。人不能拉着自己的耳朵脱离自己生存的环境,所以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都是无法回避的。文学理论上也给环境作出了这样的定义——所谓环境是指环绕人物、形成其性格、造成其命运或心态,并促使其行动的一切外部条件的总和。环境包括人物的活动场所,即环绕他的各种人际关系以及与其发生各种联系的自然环境和物质生活条件,亦即小环境;还包括由人物的具体生活环境所透射出的社会时代背景和历史趋势,此即大环境。[3]
余华虽然没有特意对社会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大环境进行细致的渲染、描摹,没有对特定的历史时期或重大事件给予浓墨重彩的描绘,但是故事发展的时间进程、先后顺序却交待得清清楚楚:抗日战争—国内战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包产到户。从时间跨度上看,《活着》借助福贵40多年的生活经历折射出中国从抗日战争到包产到户40多年的历史进程。从中我们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环境与人物的密切关系,感受到这些重大事件对人物生活、命运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它们有时就直接构成了某些人物的命运。在战乱与政治的浪潮中,老全、春生、福贵、有庆们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只能被时代的潮流所裹挟、左右,普通的中国百姓只能像一颗颗棋子一样任凭摆布。历史上的社会政治事件往往造成一代人无可逃遁的现实生存状态。正如余华自己所说:“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4]所以,从历史内容层面上讲,《活着》也让我们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对那些过去的历史又有了一些形象的认识。
但是,福贵老人最终超越了环境对他的摆布,显示了更高的精神意蕴,以自己的行为与生存姿态叩问形而上的哲学意味。
三、哲学意味层:关于活着的哲学思考
如果仅仅凭着以上两层意蕴,《活着》还不足以产生如此震撼人心、透彻深远的力量。它与众不同之处不仅仅在于让我们对美好的情感与人性产生美的感受与体验,告诉我们生活的不易与生命的脆弱,更在于引导我们作形而上的思考。其实,余华正是以他的作品在向人们传达出一种面对死亡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面对生命的态度,探讨活着的态度、活着的意义。恰如意大利《共和国报》(1997年7月21日)所说:“这里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去不死。”[4]
在福贵的一生中,亲人一个个地先他而去。父亲从粪缸上摔下来,母亲生病,妻子家珍贫病交加,女儿凤霞生孩子时大出血,儿子在给县长的妻子输血时被抽干了血,女婿干活出了意外,小外孙苦根生病刚刚好一点儿却吃豆子吃得太多了……于是,所有这些亲人都离他而去,永久地在世界上消失了。当福贵一家人的生活刚刚露出些许亮色,苦难、意想不到的灾难就悄悄地向他们逼近了,带给他们沉重的一击,夺走他们唇边刚刚绽露出的一抹微笑。但福贵,这个经历过人间大富大贵、大灾大难的乡间老汉,没有被厄运打倒,最后他与一头老得没人要的老牛相依为伴,坚强地或者说坚韧地活着。
对死亡事件的重复,也构成了作品的一大特色。可以说,重复一直是余华创作上的自觉追求,他的重复大都可以归类为事件重复。事件重复,就是指某一类型的事件反复出现。在叙述话语中可以抓住两个事件中的相似特征而形成重复。这种重复的效果是使不断发展、流逝的生活事件中某些东西有节奏地重复显示,从而提示出一种恒定的意义或产生某种象征意蕴。[5]其实正是凭借这种重复,余华在作品中告诉给我们一个返璞归真却被长期遮蔽的道理——为了活着而活着,从而表现出了强烈的解构性,对既往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的解构。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余华的作品使死亡成为生命中正常的一部分,打破了笼罩在死亡之上的精神光环,去除了对于死亡的许多幻想。重复的叙述,写出了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展示了忍耐、达观的人生态度,从而使我们正视平凡的现实人生,而不能逃向崇高的理想、不正常的情绪或语言编织的谎言之中。[2]
余华的《活着》不仅写出了中国人几十年的生活史,更体现出对终极意义的探询与思考——人为什么而活着,人应该怎样活着。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思想意蕴,于是才有了“说不完的莎士比亚”、“读不完的《红楼梦》”等说法。《活着》的内涵也是非常丰富的,甚至也很难阐释穷尽。它远远超出了形而下的层面,而充满了形而上的哲学意味。恰如余华自己所阐述的那样:
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当然,《活着》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我知道,《活着》所讲述的远不止这些。”[4]
因此《活着》不仅体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性,而且也具有了更为博大深广的世界意义,因而在国外也广受好评,曾获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韩国《东亚日报》(1997年7月3日)也曾这样评论到:“这是非常生动的人生记录,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经验,也是我们活下去的自画像”。德国《柏林日报》 (1998年1月31日)说:“这本书不仅写得十分成功和感人,而且是一部伟大的书。”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活着》将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在人们的心灵史中长久地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留下一个动人的故事,也留下一道刻骨铭心的印记、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教学参考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80.
[2]邢建昌,鲁文忠.先锋浪潮中的余华[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75,87.
[3]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18.
[4]余华.活着[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3,3,封底.
[5]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