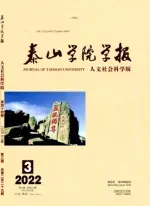论周作人的隐逸倾向及其影响
2010-08-15许海丽
许海丽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山东 济南 250013)
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算得上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曾经因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杰出贡献而倍受赞誉,也曾经因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落荒、变节而倍遭谴责。他的一生,有过光辉灿烂,也有过寂寞荒凉。他的为人,有过“浮躁凌厉”,也有过“冲淡平和”。他既是流氓、叛徒,又是隐士、绅士。他在风雨飘零的十字街头建造着自己的塔,在世事的变乱与内心的矛盾冲突中挣扎了一生。辉煌过,落魄过,屈辱过,冷漠过。但不管他有过什么样的经历,他始终不遗余力地追寻着他理想中的生存状态:隐逸。
一、周作人的隐逸之路
简单的说,周作人一生有过三次可以称得上隐逸的情况:
(一)辛亥革命后至五四前期
1906年,周作人东渡日本。在日本的六年,周作人受到了西方文明的熏陶和日本文化的影响。他和其兄鲁迅一道,以思想界战士的姿态广泛涉猎,寻求启蒙救国的途径。他们关注救亡立国,改造国民性,内心充满了革命的热情。然而, 1911年周作人从已经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日本归国后,却遭遇了深深的失落。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只是昙花一现,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国内局势一片混乱。面对这种混乱的使人窒息的国内局势,看着处身于水深火热却麻木不仁的国人,周作人心灰意冷。这一时期的周作人在东南一隅的绍兴,做教员,译介书籍,“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月抄书”[1],心态悲凉、郁闷。辛亥革命前,他常常做政治、法律、国际形势等方面的文章。如留日期间写的《日俄新协约之观念》、《论国民应具法律知识》等。辛亥革命后,周作人则转向了书籍介绍、风俗调查、儿童教育等学理性较强而无须投入太多热情的方面。从时政前沿到学术本身的撤退,在周作人来说是有着复杂的心理基础的。它既包含了周作人对审美文学观的自觉追求,也暗示出了贯穿周作人一生的矛盾性格和其后的复杂运命。
(二)五四落潮后至附逆前
在经过了辛亥革命后几年的沉默之后,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和鲁迅一起“呐喊”于文坛之上,他甚至比鲁迅更为激进。关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正越来越被重视,在此不多言。本文旨在谈他的隐逸情况。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周作人发觉自己身陷愚民的包围之中。面对命运的多桀和社会的退潮,他感到苦闷、彷徨,不知该往何处去。他发表于 1921年 4月的《歧路》一诗很能表达他当时的矛盾心态。“我不能决定向哪一条路去,我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在同年的 6月,周作人再次将这种苦闷向朋友孙伏园倾诉:“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如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面对歧路,究竟该何去何从?鲁迅选择了在绝望中抗战,而周作人在经过了痛苦的彷徨之后却选择了黯然退隐。1921年一场大病成为他隐退的契机。在西山养病期间,他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对过去的生命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价值进行历史的反思。他开始偏离从前的轨道。
1922年大病出院后,周作人开始写《自己的园地》,声明“我们自己的园地是文艺”,要“依了自己的心的倾向”去种“自己的园地”。之所以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长期的失望和焦虑使周作人厌倦了所努力的启蒙事业,另一方面,也是包含了周作人对文学审美观的自觉追求的。只是,对麻木的国民的失望,对社会变革中的残酷斗争的惧怕,对黑暗现实的清醒认识使他在耕耘“自己的园地”时越来越退往消极遁世一路上去。1924年后,他开始大量创作闲适小品,以遣散一腔愁绪。1925年 2月发表的《十字街头的塔》更是把自己消极遁世的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吆喝几声,以出心中闷声,不高兴时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其实,作为“五四”的启蒙者,他并非完全忘记了五四传统,在他的闲适追求里,也时不时会冒出重新振作起来的愿望。他在《元旦试笔》中说:“等我好好的想上两三年,或者再去发愤开荒,开辟出两亩田地来,也未可知。”在《沉默》一文中,也说:“将来别处看有什么机缘再来噪聒,也未可知。”所以他在五四以后虽然曾宣布要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只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和个人生活的艺术,但他还是参与了“三·一八”运动和“五卅运动”。真正使他失望的是 1927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革命青年的被屠杀,给了周作人很大的刺激。他更加不愿也不敢从塔里走出。1928年 11月,他写了《闭户读书论》,为自己找到了在乱世中消遣的最好办法,也标志着周作人隐逸生活的正式开始。倘若没有抗战的爆发,也许这种隐逸会伴随他终老,但造化弄人,他的以隐士生活自全的愿望终于在日本的威逼利诱下破产了。
(三)抗战胜利后的狱中生活和解放后的新生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为他在抗战时期不光彩的“汉奸”生活付出了应有的代价。1945年 12月,周作人被捕,之后经过关押、受审,最终于1947年 12月 19日由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汉奸罪“处有期徒刑十年”。但周作人并没有服满十年的徒刑,就同南京一起解放了。周作人在押期间为三年零五十天。关押期间,周作人不得不隐遁在小小的牢房里。不过,他在坐牢期间也未停顿著译。当时不但作了一百六十多首带有一些消遣的意味的打油诗,还做了一件非常严肃刻苦的工作,便是翻译英国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书。他当时在一个铁制饼干盒子上架起一块木板,作成可供写字的“桌子”,在这张“桌子”上从事翻译和写诗[2]。
出狱后的周作人比较平静,文化部门的领导也给予了他适当的照顾。周作人晚年,是以戴罪之身居住在北京八道湾,可谓大隐隐于市。当时他和外界的联系极少。与海外的联系仅有两人,一个是帮助他出版《知堂回忆录》的曹聚仁,一个是与之信函交驰的鲍耀明。后来这两人均将周作人的书信编印出版。周作人晚年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凭着古希腊文、古英文和古日文之长技,以及学贯东西的广博文化知识和深湛的文学修养,他完成了大量繁难的译作。解放后 17年中他翻译了 29部东西方文学作品,其中有希腊文学作品 19部,日本文学作品 7部,俄罗斯、乌克兰和波兰各 1部。这 17年的译作量比以往 40年的总和还要多。可以说,解放后的周作人在低调的隐逸中为发展新中国的翻译事业和增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总算多多少少弥补了一点汉奸生活的耻辱。
二、周作人自身及其作品中的隐逸精神
在古代的隐逸理论中,有一个概念是“隐逸精神”。简而言之,是儒道释融合而成的一种文化精神。我们首先来看看他身上的儒道释思想的因子。
五四时期,周作人对于儒家学说是持批判立场的。他的思想甚至比鲁迅还要激进,他曾经提出“摒儒者于门外”,对儒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五四落潮后,他对于革命产生了怀疑。他开始放弃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纯粹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他提出了“生活的艺术”命题,逃遁到个人的艺术世界里。他的这种选择与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比较契合的。
佛教对于周作人的影响同样深远。他的五十自寿诗“半是儒家半释家”很能说明这一点。可能是受“老和尚转世”说的影响,周作人对于佛教始终有一种特别的喜好。1903年的一场大病使他与佛教中的某些东西产生了共振,自此之后,他开始广泛地接触佛经。1905年他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就已开始看《大乘起信论》、《楞严经》、《诸佛要集经》、《投身饲饿虎经》等经卷。留日期间,他一面师承章太炎学习梵语,一面试图以佛经文体重译《圣经》。1921年,周作人在北京西山养病期间,更是大量阅读佛经。三十年代周作人有感于佛经“于汉文学的前途也有绝大的关系”,还新增“佛典文学”课程。可见,周作人对佛经一直是青睐有加的。佛教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渗透进他的生命体验之中,对他的人生理念、心理情感以及生活方式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对于道教,周作人虽颇有批评,然而观其隐逸,却带有很深的老庄道家色彩。道家的自然观和个人主义文学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体现与张扬。
他所具有的佛禅道的意识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他的创作中,融合为一种隐逸的文学品格。在他的小品文中,贯穿着一种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和闲适隐逸的生活情趣。讲茶道,行酒令,谈棱角,记鸟声,赋草木,写虫鱼,在琐细物事的记叙中涉古猎今,率性而谈。他的《乌蓬船》写坐船游水乡的“理想行乐法”,有着文人士大夫的雅趣。淡淡远山,渺渺水波,烟树长桥,红蓼白萍,皆收眼底。在迷人的湖光山色中悠闲地泛舟,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那种与自然交融、与万物合一的逍遥闲适的道禅境界。《故乡的野菜》记清明前后吴越乡野间妇女与小儿郊外吟唱歌谣、采摘野菜的田园之乐,有着质朴的乡野之趣。至于那“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中所蕴涵的优雅情调更是让我们低徊、神往。平和冲淡的艺术风格,流转自如、无所拘羁的用笔,明显带有佛道的运思方式和启悟特征。
周作人说过“虫鱼之微小,谣俗之琐屑,与生死大事同样的看待,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庶乎其可矣”[3]似乎很契合于儒道的自然观。儒家与道家都以自然为重,但儒家的自然观是以人的眼光去审视自然,而道家的自然观则是以自然的眼光去体悟人生。周作人早期,更倾向于儒家入世的思想,他提倡“人的文学”,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包括自然风俗。而后来则从“人的文学观”转为“草木虫鱼”论。“由草木虫鱼,窥知人类之事”,道家的色彩更浓厚一点了。
他也杂取了佛教多苦观和虚无空寂观念来品尝现实人生的况味。他用“苦雨”“苦茶”这些带有苦涩气息的意象来反映人生的孤寂和痛苦,与佛教的人生皆苦的教义极为相似。同时他也懂得佛教的超脱和通达,懂得苦中作乐。他要“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4]。他要“在这被容许的时光中,就这平凡的境地中,寻得些须的安闲悦乐”[5]。周作人是以一个爱智者的理性态度,把佛教教义当作一种宗教哲学来对待的。
三、周作人“隐逸”的多重影响
(一)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
俞平伯、废名是周作人最亲密、最信赖的学生兼朋友,也是在创作风格上最深得周作人隐逸精神的两个作家。评论家阿英在《俞平伯小品序》中说:“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形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一流派的重要人物无疑是俞平伯和废名。阿英说这一流派的形成是由于“思想上的一个倾向”,我认为这一倾向用“隐逸”一词概括最为恰当。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中,有一批曾经参与过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中坚分子在流血的斗争中感到了自身的无力。他们以“隐逸”和“闲适”作为生存的理想状态,把艺术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在艺术世界里寻找寄托和安慰。
陶然亭的皑皑白雪,秦淮河的月影灯彩,还有春阴里的桃花,西湖上的美景,让俞平伯沉入一种朦胧的意境里了。似梦非梦、空灵玄妙,“其滋味有如开笼的飞鸟,脱网的游鱼;仰知天地的广大,俯觉吾身之自在”……从五四时期高呼文学的“平民化”到五四落潮后对“风花雪月”文学的转型,俞平伯几乎经历了和周作人一样的由“入世”到“出世”的心理流程。儒道释的思想在他心里杂揉着,争斗着,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目和侧重表现于他的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中。
废名更是与儒道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家乡黄梅是禅宗圣地,他从小便沐浴在拜佛礼道的浓厚气氛中。他的精神导师周作人“半是儒家半释家”的二元文化观也深深影响了他。他不但在生活中喜欢坐禅修道,在创作中更是努力调和着儒道佛,融其教义于文学创作中。废名笔下人与自然合一的美好意境触目皆是,举不胜举。《竹林的故事》中的竹林,《菱荡》中的陶家村,《桥》中的史家庄,这些桃花源般的地方与那些清水翠竹般自然的少男少女如阿毛、三姑娘、细竹、琴子、小林等相谐相融,形成一幅幅美丽淡雅的人物山水画。在这里生命与自然相契相合,浑然无间、福慧圆融。我们感受到了佛家的慈悲、儒家的放达和道家的纯粹。生命,就在这一派安然中诗意地栖居着,“从此黑暗的世界也都是光明的记忆”……
(二)周作人与林语堂、梁实秋
周作人的闲适小品文,不仅影响了俞平伯、废名的创作,也深深影响了林语堂、梁实秋等人。20世纪 30年代,林语堂以其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为阵地,高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笔调”,把闲适小品文的创作推向一个高潮。20世纪 40年代梁实秋又以《雅舍小品》,延续了现代小品文的香火。他们用轻松、随意的“娓语体”书写“宇宙之大,苍蝇之微”,在闲适之中品味苦涩,在趣味之中追求智慧。以周作人、俞平伯、废名为主要代表的“隐逸派”文学与以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为代表的“闲适派”文学,有许多共通之处,但又有着细微的差别。“隐逸”本身是包含着两方面内容,它不仅有轻灵飘逸,也有苦涩沉重。时代的动荡变迁给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理与生活造成强大压迫,“隐逸”成为他们逃避高压统治,在黑暗中求生的策略。我们观周作人、俞平伯的散文,都有着浓浓的“苦涩”味。废名那些超尘出世的田园小说,也寄寓着淡淡的哀愁,比如《柚子》、《阿妹》等。
林语堂、梁实秋作为疏离时代主潮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然也难免有惆怅失落的苦味之作,但在风格上是更多地继承了周作人的“闲适”一面的。林语堂提倡“幽默”,《戒烟》通过令人发噱的喜剧场景,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妙趣横生的艺术世界。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中,风雅幽默亦随处可见。比如《女人》一篇,就用轻松的笔调写出了女人的善变、多疑、饶舌、胆小以及灵巧和耐力。林、梁在作品中,表现出追求趣味的倾向,这一点是和俞、废不同的。
(三)周作人对当代作家的影响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当今社会的日益浮躁中,一些文化人开始了闲适的选择。他们一反过去积极参与社会的姿态,从以前不屑或无暇顾及的日常琐事中寻找生活的乐趣。谈花鸟、谈虫鱼,谈禅、谈道、谈棋艺……,报纸杂志上洒满了洋溢着温柔情愫和宁静心境的散文小品。
从余秋雨、韩少功、阿城、张承志、王蒙、贾平凹等等文人的创作中,我们感受到不同的精神脉络。鲁迅、沈从文和胡适、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构成了几种文化背景在许多文人身上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来。倡言“以笔为旗”的张承志、韩少功和王蒙承续了鲁迅的传统,然而,更多的文人偏爱的却是周作人传统。汪曾祺、阿城、舒芜、谷林、黄裳、张中行甚至董桥等人的文章都流露着淡淡的周氏余韵。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
四、探讨周作人“隐逸”的意义
周作人是一个复杂的人物。笔者无意对他本人作出评价。我只想绕开历史细节的是是非非,而仅仅发掘周氏思想的精华。他的“隐逸性”是我寻找到的一个切入点。
隐逸作为一种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它几乎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相伴始终。隐逸文化所呵护的一批士人及士大夫,相对于封建政统现实,成了边缘人,相对于文艺审美实践,则成了主角和旗手。宗白华先生指出,汉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是人精神上最自由、极解放、最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富艺术精神的时代,其诗、书、画等奠定了后代文艺的基础与走向[6]。
我们现在的时代当然不是动乱的时代,但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化给转型中的人们带来了焦躁感,同时也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当有人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前进时,另一些人则退回到传统的精神家园去寻找安宁。童话诗人顾城曾隐居激流岛,试图建造自己的桃花源,轮椅上的史铁生走向宗教,寻求让灵魂安歇的良方,还有北村的基督徒情结,张炜的葡萄园梦想等等都表达出了这些有着传统理想的文人的“隐逸”情怀。
隐逸的最大价值在于,丰富了文艺体式,提升了文艺境界,促进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书法、绘画、山水田园诗、闲适小品文,哪一样能脱离得了隐逸精神呢?至于农业文明、园林艺术、旅游业的发展也无不与“隐逸”所蕴含的自然观息息相关。所以探讨“隐逸”是有着现实的意义的。尽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思想的矛盾,现代人的隐逸较之古代往往呈现出复杂和沉重,但不能否认的是,古代的隐逸文化正在以新的变体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据一角。看看那些寄身于图书馆甚或影视媒体的身影,看看那些不停奔波着的人们,流浪者般焦灼心灵的低诉、呼唤和徘徊,我们有理由相信,“隐逸”正在进行,而且被现代人需要着。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267.
[2]李景彬,邱梦英.周作人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303.
[3]周作人.谈笔记 [A].秉烛谈 [M].长沙:岳麓书社,1989:134.
[4]周作人.喝茶 [A].雨天的书 [M].长沙:岳麓书社,1987:48.
[5]周作人.死之默想 [A].雨天的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7:15.
[6]宗白华.宗白华全集 (第 2卷)[M].林同华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