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女词人丁宁先生
2010-04-27石楠
石 楠
(作者为安徽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难以湮灭的记忆
丁宁字怀枫,号昙影,又号还轩。我的藏书中有她两个版本的词集,都是蜡刻油印线装本。一为她的门人卓孟飞先生以华师大教授周子美校编刻印的《还轩词存》(1957年8月印)为基础增补校刊的《还轩词存》(1978年月11月印),为丁老所赠;一为丁老故去后,安徽省图书馆以《还轩词存》为基础,收入尚未入集的佚作编为拾遗一卷附其后,易名《还轩词》的补遗本(1986年6月印)。我将它们和另一些手抄、影印线装本诗词放在一起。可我却很少去读。只是在找资料的时候,偶尔看到那宝蓝色封面上的题签“还轩词”或“还轩词存”几个字,会蓦然想起丁老,她的形象也随之闪现在我的面前,但那只是一瞬,很快就隐遁了,俗事和写作覆盖了她,把她推到了我记忆的深处。但到合肥开会的时候,有时也想起她,曾起意要去寻找她的埋香地,想去瞻仰她的墓园,与她作次阴阳两隔的心灵交流。一打听,方知安徽省图书馆于1988年3月已为她移墓扬州,她落叶归根了。心里便会泛起一缕思念和愧疚的涟漪。因为在她逝世后,我曾有心为她作传,并在心里向她许下这个诺言。
记得那是在我的处女作《张玉良传》面世不久,我就把为她立传列入我第二部书的选题,为之作过艰难的努力,找过她生前的很多朋友,但未能觅到写传的基本素材,她的资料在她故去前就开始流散。她没后人,她内向的性情,加之险恶的时势,她将自我深深藏起,越发沉默寡言,更不喜欢随便向人敞开心扉,倾吐她的不幸身世和她悲凄的情感经历,朋友们对她的身世也只了解个大概,连画个轮廓的线条都不够笔墨,我自感无力刻划出她词人丰富的情感天空。除了她留给人间的204首词,她的真实的个性和她丰富的内心世界都随着她的故去而失去了,我无能透视她,更无能复活她。况且她的旧雨新知都很珍爱对她友情的拥有,有的对我的这一创意给予热情的支持,为我提供知情者线索。可更多的是回避,分明他手里拥有丁老珍贵的纪念品,却百般回避我的采访,找上门去,也密不示我。我很沮丧,只好放弃。但每每想起这个选题的失败,心里就觉得有愧于丁老。有愧于她那些给予我热情支持的朋友。丁老故去已二十九年多了,我怎么会突然想起要写这篇怀念文章呢?这得感谢合肥的文友完颜海瑞先生。他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筹编一部写合肥的美文,约我写一篇。并说他曾听徐味老先生说,我研究过丁宁,命我写篇有关丁老的文字。
二十世纪三大女词人之一
这个电话像一杆桨棹,让深埋记忆湖底的往事泛了上来,把我带到了三十年前的1979年。那年我四十一整岁,从工厂调到安庆市图书馆古籍部刚刚一年。丁宁先生在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因为都是从事古籍书管理,工作性质的相同,她又是这一行的专家,很自然就知道了她。并听说她在破四旧的时候,为了保护省图数十万册古籍珍藏,以她的睿智和不畏死的英勇气概,怒斥命她交出库房钥匙给红卫兵的副馆长,以死相护,并献出了她个人的珍藏,与红卫兵斗智斗勇,保全了数十万卷的珍贵古籍。她以生命捍卫文化遗产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对她心生敬意。又听人说她身世凄凉,没有配偶和子女,孤身一人,图书馆就是她的家。但那时我并不知道她还是著名的倚句高手。一次和前辈蒋元卿老先生的闲谈中,他说丁老的词填得很好,被词评家称作二十世纪三大女词人之一。并说华师大的施蛰存教授对她的词很欣赏,评价很高,并从抽屉里找出一本他自制的剪报簿,翻到一页,指着用红笔划了道道的地方让我看,施教授在秩数并世闺阁词流后说,“她们都卓尔成家。然以《还轩词》三卷当之。则以文采论,亦足以当帜摩垒,况其赋情之芳馨悱恻,有过于诸大家。”①
那时我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喜欢读书,读过一点古今中外名著和一点唐诗宋词元曲之类,根本还不知文学的门朝哪里,只是文学百花园篱笆外的一个眺望者,文学舞台下的一个观众,把文坛想象成瑶台净土,对作家和诗人充满崇敬,对文学充满了向往。就想走近丁老,去了解她。从那时起,对她就心向往之。
全国古籍善本书编目的一个会议在安徽省图书馆召开,我和蒋元卿老先生一道到合肥出席会议。那年丁老76周岁,已退休,因她对流略学的贡献和她的词名,省政府授予她省文史馆馆员的头衔。她也出席了会议,蒋老介绍我认识了她。她满头银丝,脸色枯黄,一脸的病态,每一道皱纹里都堆积着岁月的风霜,她的眼神里流溢出坚毅和淡淡凄凉。这是阅历和学识造就的一座老书城的肖像,我就有了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好像有了某种心灵的默契,她拉住我的手,邀我到她住的地方去看她养的猫,说她的猫可爱极了。
她与猫的传奇
那是初冬时节,天气很冷,她穿着厚厚的深蓝色的卡布棉衣,袖口和前胸都有污垢,走路也很缓慢,我扶持着她。她住的是平房,我已记不太清了,好像是消遥津省图古籍部边上的一间屋子。她推开门,大约四五只猫咪就迎上她咪咪地叫,她宝宝宝地唤着它们,给它们拿吃的。可有只小黑猫并不去抢食,而是像个爱撒娇的小姑娘,绕着她的腿脚直打圈圈,一会舔她的鞋,一会咬住她的裤脚往铺着旧棉被的藤椅那里拉。她这时的脸仿佛绽开的黄花,她笑着对我说,你看,你看,它多懂事,多通人性,它是怕我累了,要我去坐椅子。她示意请我落座,她也坐了下来,就跟我说起她和猫的故事。在那饥饿年月,她养的一只大黄猫经常在夜里到逍遥津捉鱼。它却自己不吃,而是含回来给她。它第一回捕到鱼是一天夜里,她正似睡非睡,突然感觉到蚊帐在动,她就拉亮灯,撩开帐门,大黄就蹲在她床前,它的面前躺着一条足有一斤重的鲫鱼,它的一只脚压着鱼身,鱼尾巴还在不停地拍打着地呢。她的眼睛一下潮了,一把抱起了它。把鱼放进一只木桶里用水养着,大黄从她怀里溜下来又出去了,那晚它一连捕回来三条鱼,它竟然知道把鱼放进桶里,不再来叫她。在那种一条鱼就可以救活一条命的时候,她不敢独享,很多邻人都吃过大黄捕的鱼。她还养过一只像雪球样的波斯猫,眼睛像蓝宝石样美,人见人爱。她说,那不是只猫,是一个精灵。每次她发胸口痛,它就伏到她的怀里,用一只右爪一下一下地给她轻轻捶拍。后来被人偷去了。她伤心了很久。我能感受得到,她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漫长人生岁月中,猫给了她很多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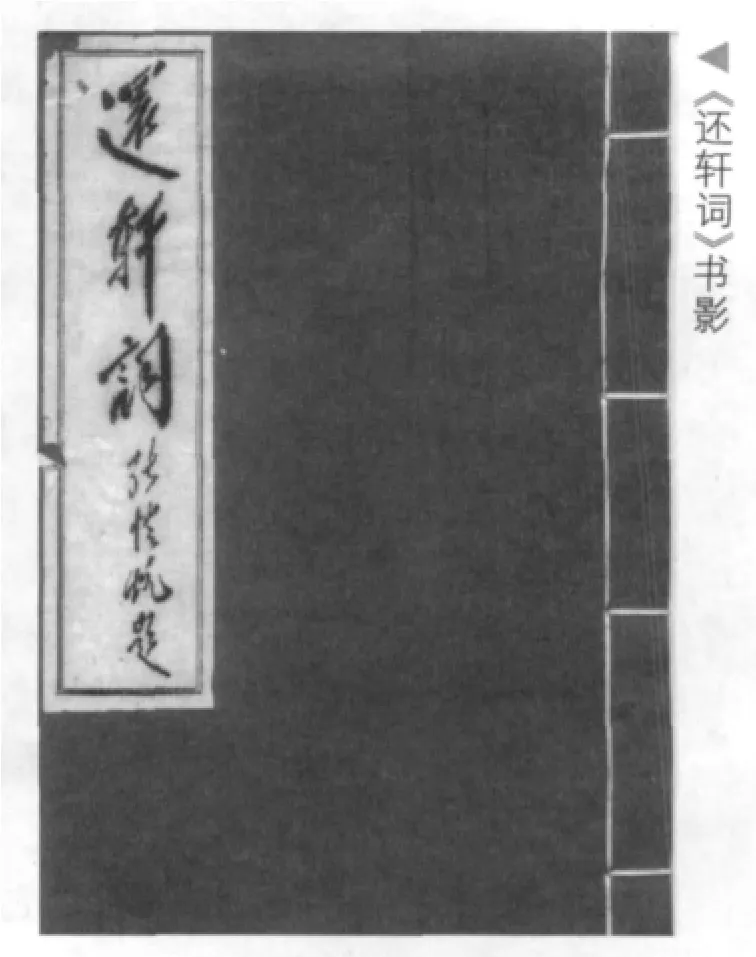
我们谈了很久,从猫说到了古籍善本,再说到词。我想向她讨要一本词集,但又不好意思开口。便说我很想读她的词,没找到。她起身躬腰从一堆书中抽出一本《还轩词存》递给我说,这本送你吧。就是1987年11月卓孟飞先生校补刻印的《还轩词存》。翻开首页,映入眼帘竟是郭沫若给她的复信,作为代序印在前面。我的眼睛遽然一亮。一看复信的时间,郭老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又是全国文联主席,深得毛主席爱重的大诗人,这么大一个官竟然给她亲笔复信,在信中对她的词进行了品评,给予了很多赞美,并让他的夫人于立群亲笔抄写了他的近作,“附上以为您抛玉引砖之报”。丁老看出了我的惊讶,便淡淡一笑解释说,她是一个不愿攀龙附凤甘愿寂寞的人,给郭老寄书写信是为了拉大旗做虎皮,不得已而为之,那时,有人上纲上线批评她的词是“处幸福之世,为酸楚之音”,想拿她的词作文章,加害于她。她欲辩无言,就寄了一本给郭老。郭老的回信让她逃过了人生的一大劫难。这封信还起到了为她的词正名的作用,扩大了她词的知名度。她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对郭老心怀感激。后来郭老还到合肥来看望过她,对她也是个鼓舞吧。她还向我出示了于立群书写的郭老的两首诗。

初识竟成永诀
我们只是初识,却谈得很投机。临走时,她还送我一张她的照片。不曾想到初识竟成了永诀。第二年的9月15日她就离开了人世。这个不幸消息让我悲痛了很久,我懊悔没有再去看她,失去了最后一次走进她心灵和解开她身世之谜的机会。特别是未能写成丁宁传,成了我一块心病,深觉愧对一个以书为命,以词为魂,以猫为伴的孤独老人,她应该为更多人所知,她的那些悱恻凄清的诗句应该永存。好在还有不少人记着她,更有她的乡人王立自先生经数年的艰苦努力,搜集到了她很多不为人知的资料,写了一部她的传《寒树啼鹃丁还轩》。她的事迹和她的作品可以传世了,我深为愧疚,但又很欣慰。
“儿时弄笔红窗下,片语珍无价。中年觅食暂离家,不道故园从此即天涯。老来潦倒书城卧,蠹卷青灯伴。吟魂消尽漏将终,双鬓萧疏黄叶堕西风。”这是重印《还轩词》时丁老作的《虞美人》。这无疑是她为自己人生写就的一篇总序文。了解了她一生经历的坷坎,也就不难理解她的词为何那样悱恻凄清哀婉动人了。凡是流传后世的文学艺术经典无不是寂寞之果,最能动人心弦的诗篇也往往来自孤独和凄苦的灵魂啊!苦难也会开花,有时还能绽放出不朽的光辉呢!
写到这里,该搁笔了。可猛然想起高启那首我非常喜爱的梅花诗,灵感一闪念,萌生出一个奇想,将其改动几字,来个画蛇之足,添在我这篇纪念文字的后面,借为结句。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丁宁(原“何郎”)无好咏,
词林(原“东风”)愁寂几回开。
注释:
①施蛰存《北山楼钞本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