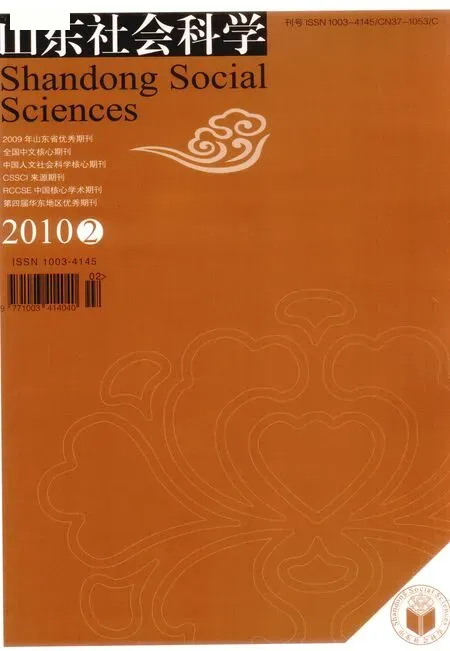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
——巴迪欧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
2010-04-12蓝江
蓝 江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
——巴迪欧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
蓝 江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0)
在《元政治学》中,巴迪欧从“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这一命题开始,利用数学的集合论解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但是这种解构并不是同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同流合污,而是一种让枯萎的马克思主义的花朵上重新绽放出唯物主义辩证法鲜花的涅槃重生。当巴迪欧用“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摧毁掉石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表之后,他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一种新的活力,也仅仅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能被看作为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巴迪欧;后马克思主义
在《元政治学》中,巴迪欧一语惊人:“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①Alain Badiou,M etaopolitics,Trans by Jason Baker,London:Verso,2005,p58.也正是这个类似于宣言的话语,使得巴迪欧的思想被人归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尽管巴迪欧自己从来没有认可过这个指认。不仅巴迪欧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毫不领情,而且他还将矛头指向公认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拉克劳和墨菲,并从根本上拆解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命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相信,巴迪欧以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或许,在这个意义上,他叙说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后马克思主义”。
一
如果要理解巴迪欧在何种意义上是“后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破解巴迪欧设下的第一道谜题,即为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迪欧的这个指认与拉康著名的“女性并不存在”那个命题有天然的家族近似性。
拉康的“女性并不存在”试图表明,相对于男性的菲勒斯 (Phallus)中心主义情结,女性的形象完全是作为一种想象被构建起来的,这种构建天生与女性的能指的匮乏有关。拉康指出:“女性不能被叙说。没有关于女性叙说的东西,女性与一种想象性的大写主体 (S/A)有关,在那个意义上,女性是被双重化的,她是一个非整体 (no-whole),因为她与一个Φ有关。在我这里,我所谓的Φ指的是没有所指的能指的菲勒斯,即在男性那里,建立在菲勒斯的欢愉 (jouissance)的基础上。”①J acquesLacan,The Sem inar of Jacques Lacan,Book XX:On Fem inine Sexuality,Trans by Bruce Fink,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8,p81.换言之,在拉康看来,女性在能指上是一个匮乏的空,她被某种象征性和想象性的主体伪装起来。这个象征性和想象性主体展现出女性的心理结构并不是对男性欲望作出的反应,而是对男性的性态 (Sexualité)想象作出的反映。这种作为男性欢愉形态想象将女性建构为一个大写的主体,这个大写的主体将千差万别的女性共同书写成依照男性菲勒斯中心主义神话的名称 (nom)。因而,多希尔·莫娃对此的评价是中肯的,她指出:“什么是女人,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只有一种答案: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女人的身体是她不断追求可能性的场所。”②DorilMoi,W hat is a W oman And Other Essay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59.或者我们可以将此翻译成典型的巴迪欧式的语言,女性是作为纯多 (pur multiple)的样态展现出来的,而女性永远是这个纯多样态的不恰当的名字出现的。毕竟,这个名字本身与女性并不是完全对应的,它并不能包含所有女性样态,但它以大写的同一性来命名女性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以这种想象性和象征性关系构建了女性的性态,或许这才是拉康提出“女性并不存在”的原因所在。
巴迪欧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是否具有类似的结构呢?与拉康的命题不同的是,巴迪欧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作为一种Φ的对应物出现,即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男性 /女性”那样呈现为“马克思主义 /非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更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是相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Φ中心的想象性建构出现的。但是与拉康命题一致之处在于,和“女性”一样,在巴迪欧眼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缺乏 (manque)的能指,它作为一个大写的一,一个名字,填补了诸多被归属于其中的样态构成的深渊 (abysse),并掩盖了这个名字同其中诸多样态之间的沟壑症候,让其呈现为一种连贯性和平滑的表面。
然而,在巴迪欧看来,这种连贯性的平滑表面完全是一种象征性的虚构,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之中,根本不存在一个始终连贯的核心内容,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呈现为诸多断裂的模式之间的拼贴,而不是衔接,它们唯一相同的,不过是他们都共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名字,但是在这个名字之下,实质上,并没有界定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换句话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命名,与其说是描述性的,不如说是非描述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命名并不包含某种实指性内容,之所以某些学说和思想可以共称为“马克思主义”,是由于他们在一种非连续统的语境中延伸。正如分析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在谈到命名问题时指出的:“当一个名称‘一环一环地传播开来’时,我认为,听说这个名称的人往往会带着与传播这个名称的人相同的指称来使用这个名称。”③索尔·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梅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年版,第 74-75页。也就是说,当我们可以用“拿破仑”一词来命名一个历史人物时,同时也可以用“拿破仑”来命名一头猪 (如同乔治·奥威尔在《动物庄园》中那头名叫“拿破仑”的有野心的猪)或者一只土豚鼠,但是在实质上,真正的拿破仑和奥威尔的猪以及那只土豚鼠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它们唯一的共同点仅仅在于他们共同使用了“拿破仑”这个名字。
当然,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模式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拿破仑同奥威尔的猪之间那样的关联。有人坚信,在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延续的诸多样态中,存在某种不变的恒常性,这种恒常性定义了何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第二国际、列宁、斯大林乃至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延续之后,甚至加上卢卡奇、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萨特、阿尔都塞等等名字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几乎无法在这些名目下找到那个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恒常性,它们之中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脉络,也没有类似于重叠共识式的交合点,我们看到的只有一个集合,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的集合,它们被以某种方式归属于这个集合。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名为“马克思主义”的集合中找到一个可以从总体上概述出所有被命名为“马克思主义”样态的思想的全部轨迹,或者说,我们能否找到一个平滑的叙述,将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头至尾毫无例外地贯穿起来,而这正是巴迪欧思考的核心问题。
集合论是巴迪欧用以重新诠释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者重建本体论的重要工具。巴迪欧在巴黎高师期间,受到了法国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他加入了“认识论小组”,经常聆听科学主义思想家康吉莱姆和卡瓦耶斯的课程,在“认识论小组”中,他第一次接触到康托尔的集合论,并很快对之如痴如醉,他将康托尔的集合论思想大量地应用到他的哲学写作之中,并将这种集合论的思维作为其思想展开的主要线索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思考,无疑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康托尔的集合论中,康托尔设定了一个假设,即集合是一个连续统(continuum),这就是著名的连续统假说。连续统假说是康托尔集合论成立的前提,与那种被预先设定一种统一的量性的数学不同,他必须说明集合中的多个元素如何能够在一个集合之中。集合中多元素的一不是自明的,那么其中的一由何而来;如果集合中的多元素不存在一个一,那么集合作为一就无法存在。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康托尔设定了集合的诸多元素之间存在一种连续性,也正是这种连续性使得集合成为统一的连续统。但是连续统假说一直没有得到证明,为了保证集合论的根基不受动摇,策梅罗 -弗兰克尔集合论(ZF)将康托尔的连续统假说作为一种集合论的公理体系出现。但是这种强制性作为公理的表现遭到了哥德尔和科恩的质疑,尤其是科恩最后指出:“按照集合论的公理,康托尔的连续统假说是无法证实的。”①Jason Barker,Alain Badiou: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Pluto Press,2002,p10.巴迪欧最后采纳的是科恩的力迫法来解决集合论的一的问题,力迫法通过主体性的强制性命名将集合中的所有元素统合在一个名字之下,这个名字成为一种附加在诸多元素之上的类性真理程序,而这种类性真理的获得正是通过减除 (déduction)得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祛除了或者忽略了元素身上可能与那个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的相关质性存在症候性断裂,多的元素被统一地置放到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程序之下。
更明确地说,对于巴迪欧而言,“马克思主义”的集合之中的诸多要素之间并不必然具有一种连续性,相反,要素之间是断裂性的拼贴。它们之所以能够构成一个集合,完全是出于科恩所谓的“力迫法”的作用,通过某种外在的强制性,赋予了这些要素可以被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从而在表面上获得了某种看似平滑的一致性,但正如齐泽克所揭露的那样,在这些平滑的外表下面涌动的却是这些多样而断裂的要素彼此间无法消除的深渊,它们作为症候被外表暂时性消除了。实质上,巴迪欧试图表明,在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想象性连续的基础上,断裂的诸多要素之间根本不存在一种可能被看做贯穿于所有的要素之间的恒常性线索,这种恒常性本身基于康托尔集合论的连续统的假设,这是一种彻底的虚构,事实上,当策梅罗和弗兰克尔以公理的方式强制性认可这种连续性假设时,连续统假说已经进退维谷了,当哥德尔和科恩的研究彻底穿破连续统假说的光怪陆离的外表后,我们基本上已经确定,根本不存在一种可以将所有名曰“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贯穿起来的恒常性,除了那个共同的名字之外,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一个可以用来概括“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坚信:“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
二
尽管巴迪欧否定了在命名为“马克思主义”的集合中不存在一个大写的一,但他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是有具体所指的。巴迪欧说:“正如我已经指出,席尔瓦·拉扎鲁 (Sylvain Lazarus)认为,在马克思与列宁之间与其说是连续和发展,不如说是断裂和更新。同样,在斯大林和列宁之间,在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亦是如此。而阿尔都塞表达了另一种断裂。不过更为复杂的是,在所有这些断裂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态中,没有一种是完全一样的,所有这些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绝对不连续的集合的 (空的)名字。”②Alain Badiou,M etaopolitics,Trans by Jason Baker,London:Verso,2005,p58.显然,巴迪欧的意思是说,在我们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内部,在一个被想象为一种连续性的政治史的历程中,这个集合并没有呈现出某种内在的连续性,相反,它们之间是断裂的,彼此之间是没有共性的。值得注意的是,巴迪欧在这里并不是指经典马克思主义同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断裂,而是被一些人认定为正统的主流马克思主义之间,也并不存在某种所谓的一脉相承的线索和体系,这种所谓的线索和体系无非是某种此时此地的政治性想象的建构的产物,相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呈现为一种断裂的历史,尤其是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之间,甚至我们可以为这个名单继续加上恩格斯、考茨基、卢森堡、托洛茨基等等,在所有这些公认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间,没有一个可以作为贯穿始终的线索和本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质性实指的内容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按照巴迪欧的说法,“所有这些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绝对不连续的集合的 (空的)名字”。
在这一点上,与其说巴迪欧受到了其恩师阿尔都塞的影响,不如说受到了他的毛主义的同志席尔瓦·拉扎鲁 (巴迪欧和拉扎鲁都是法国的左翼组织“政治组织”(Organisation politique)的创始人和核心人物)的影响,拉扎鲁曾将政治的历史模式分为内在模式和外在模式,拉扎鲁界定的内在的政治模式有四种:
(1)圣鞠斯特 (Saint-Just)的革命模式,这种模式发生在 1792—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之间;
(2)马克思的经典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历史是政治的主观化范畴,这种模式发生在 1848年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到 1871年 (巴黎公社)之间;
(3)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模式,其特征是其政治的条件 (即无产阶级政治能力必须认识到其自身的条件,而党将这个要求具体化了),这种模式建立了苏共和苏联,它发生的区间在 1902年 (列宁的《怎么办?》)到1917年 (苏联的消逝以及党内的“分层”)之间;
(4)毛泽东的辩证模式,其特征是政治的辩证法,从而同所谓的历史“规律”区分开来,这种模式可以对情况和结构进行动态的处理,这种模式发生在中国革命战争期间 (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统一战线),其发生的区间是从 1928年 (毛泽东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到 1958年 (朝鲜战争结束)之间。①Alain Badiou,M etaopolitics,Trans by Jason Baker,London:Verso,2005,pp39-40.
巴迪欧指出,拉扎鲁之所以列举四种模式,是为了反对一种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态度,而这种历史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形象,是在一种命名下生产出来的。换句话说,名字作为命名填补了不同要素的沟壑,并设定了在这些要素间进行平滑过渡的基本原则,用巴迪欧的话来说,命名使得这个绝对不连续的集合可以被思考,名字使这个集合获得了一种标准,在这个标准下,一切要素都可以被计数为一(compte comme un)。于是,整个集合获得了一个贯穿所有要素的真理,巴迪欧称之为类性真理 (véritégénérique)。类性真理的出现使得原先那个绝对不连续的集合的显现 (présence)获得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也就是说,作为原先的集合是一种不可读的情势(situation),在可以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的结构化之下,所有的要素可以从这个计数为一的真理的角度进行阅读,每一个独特性 (singularité)的要素被绑缚在了这个类性真理的十字架上,绝对不连续的集合的要素之间的裂缝也在这一刻被缝合了,集合获得了一种整体性和平滑的外观,这种平滑的外观正是一种被想象性建构起来的结构,巴迪欧称之为情势状态 (état de la situation)。
情势与情势状态的区分是巴迪欧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巴迪欧指出,“我所谓的情势是直接显现出来的所有的多”,②Alain Badiou,L’être et l’événement,Paris:Seuil,1988,p32.它具有流变性和不稳定性,其复杂的显现与存在导致了其不可能被思考,亦不可能被认识和理解,即使我们在一刹那偶尔抓住了它的踪迹,也未必可以看到它 (对于巴迪欧,甚至包括齐泽克和阿甘本,都坚信这种显现的存在是一种永远无法触及的真在 (réel)),相反,在那一刹那,它从我们的双手的隙缝中又悄悄溜走了。情势状态是一种主体操作的后果,它以类性真理对不断漂浮的多的样态进行结晶化,使得它们可以在一个计数为一的原则下进行阅读和理解。巴迪欧指出,这种阅读和理解本身就是原生情势中的多的扭曲 (torsion),在一定程度上,情势状态下的类性真理缝合了各个元素的裂缝,掩盖了显现的在 (être)同计数为一后的在者 (être quaêtre)之间的差异。在被凝固化为在者,涌动的在的力点 (offsite)被再生产(représenté)为计数为一的项值 (ter me),那个用来命名集合的名字对集合进行了再生产,使得集合可以永恒地作为一延续下去。在“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计数为一的名字再生产着处于这个集合内部的各个项值,当我们习惯用生产力、生产方式、阶级、革命等范畴来描述和概括马克思主义时,马克思主义中的各个项被一次又一次地再生产出来,并成为对那个大写的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名字的佐证。
但是,问题在于,在的活跃性力量决定了其不可能永远甘居于计数为一的名字的描述之下,它是流动的和漂浮的,也就是说,在的情势相对于情势状态,总是会超过那个大写的一设定的内涵,即溢出 (excès)。显现的诸多的在对计数为一的类性真理的溢出不是一种偶然性或可能性,而是一种必然性,这是一种齐泽克所谓的普遍的例外,换言之,流动性的多作为在总会漂移出情势状态的大写的一所设定的范围,从而相对于一,构成一种过剩(surplus)或溢出。过剩和溢出的出现是必然的,因为情势状态的一并没有彻底根除掉在各个项值上与其相异的部分,这使得一与多之间的断裂的症候不是被解除了,而是被掩盖了。既然症候未能解除,那么变成潜在性 (virtualité)的症候始终会以某种方式爆发出来,一旦症候以溢出的方式爆发,它就会将自身呈现为一个不能被大写的一所消化的事件 (événemnet)。
事实上,在拉扎鲁设定的四种内在的政治模式中,相对于那个大写的“马克思主义”,都存在着某种溢出。以最经典的马克思的模式来说,马克思本身的文本就呈现出不稳定性。比如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之前,可以以某种方式来贯穿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和文本,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也是坚信从具体的生产方式来审视人类历史发展脉络的马克思。但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打破了对马克思文本上的这种连贯性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文本作为一个统一体 (大写的一)的形象由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产生了巨大的危机,这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无论是相对于后人(包括恩格斯在内)对马克思的理解,还是相对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的归纳都无疑是一个溢出。这个溢出从根本上打破了那种同一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是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过剩,一个溢出,尽管它不至于颠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认知的总体理解,但是它如同一根刺深深地扎入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解之中。按照巴迪欧的理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件。
当然,事件的出现并不一定是摧毁性的,但是,如果不让溢出的事件对情势状态进行彻底的颠覆,就一定要求主体对事件进行包含性操作。这种包含性操作仍然是以计数为一为目的的,换言之,事件之后的主体的操作试图从一种新的计数为一的方式重新对事件及其集合进行计数操作,使溢出的事件在一种新的情势状态中变得可读。事件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为了恢复这种平衡,必然要求情势中的主体对事件做出反应,以新的方式将其纳入到计数为一的体系之中。譬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现之后,立刻有不少学者对这篇带有溢出性质的手稿进行表态,有人认为它是马克思不成熟时期的表现,以不成熟的马克思将这种溢出纳入到原先那个成熟的马克思的大写的一之中。而另一些人从中发掘出一种迥异于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人学马克思主义,从而在一种新的计数为一的情势状态中来理解这个溢出的文本。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那种绝对的整体性形象已经被打破,而且在文本中,这种碎裂之处不仅仅只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处,许多碎裂的痕迹在大写的一的外表下被掩盖了,而这些被掩盖的碎裂之处或许在某种斜视(齐泽克语:looking awry)的目光中作为一种流溢从那个大写的一的内部溢出来。
正是溢出的存在,导致了大写的一对断裂性的多的缝合是临时的和失败的,那个羸弱的名字下的内容已经作为溢出从其内部流走了。可以想象,巴迪欧所指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摧毁的正是那个作为实质性的大写的一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不同模式之间的断裂性的症候始终隐伏着,一旦条件满足,它将以溢出的方式重新将各个样态之间的裂缝撕裂开来,那个空的深渊再一次被显露出来,或许我们在这里聆听到巴迪欧的呼声,作为一个被溢出的大写的一,“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
三
或许正是由于巴迪欧的这一宣告,有人开始将其划入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后马克思主义近来在学术界十分流行,不仅在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后马克思主义都是一个诱惑力十足的指认。当然,将巴迪欧划入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并非毫无根据,在这些人看来,巴迪欧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的指认是从内部解构和终结了“马克思主义”,他是在“马克思主义”崩塌的废墟上来阐发其思想的,因此,无论是从时间关系还是从本体关系来说,巴迪欧的思想都无疑是一种后 -马克思主义。
关键的问题在于,巴迪欧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是否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终结式的宣告,他是否像丹尼尔·贝尔在六十年代一样,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图式终结了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第一图式,或者干脆像今天被称作后马克思主义的旗手——拉克劳和墨菲一样,以“后马克思主义”的指认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超越?因此,在澄清巴迪欧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必须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尤其是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析。
在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他们第一次将自己的见解阐发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通过缩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僭妄及有效性范围,我们与这一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某些东西——即以它的范畴来把握宏大历史的本质或根本意义的强烈的一元论渴望——发生了决裂,我们的著作总体倾向是不是这样的呢?毫无疑问,答案只能是肯定的。只有我们抛弃以普遍阶级的本体论式的特权地位为基础的任何认识论优势,才真正有可能讨论马克思主义范畴有效性的现实程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地声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后马克思主义中。已经不再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再维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看法,自然也更不可能再保留关于共产主义是没有对抗性的透明社会的观念。”①Laclau&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London:Verso,1985,p4.
由此可见,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以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工人阶级的普遍主体和阶级的本体关系,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描述和预测,从而从内部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对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的诉求。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拉克劳和墨菲相信,马克思在十九世纪提出的“工人阶级”的范畴已经不能适用于今天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正如拉克劳所说,在今天,“工人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中意味着他参与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它们并不严格地取决于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中有更多的可以是新的激进的社会斗争的场所,并且它们 (即新的激进斗争)被连接起来的方式并不依赖于预先既定的模式——就像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旧式区分的情况下那样——而将是领导权斗争的结果,因而它大体上将保持这开放性。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那里的‘阶级’概念只不过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对应于 19世纪明显的社会一致性的综合,但是对于今天理解反 -资本主义斗争的逻辑和模式,这一综合所能提供的助益越来越少了。正因为资本主义在多种意义上脱出了马克思所预言的方向,今天我们才不得不对他的阶级概念提出质疑。”②拉克劳:《阶级“战争”及其以后》,载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年版,第 71页。引文根据英文略有改动。也就是说,拉克劳将马克思的工人阶级作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总体性范畴加以解构,在“工人阶级”之名下,同样掩盖了具体的不同时空中工人的具体差异,诸如女性问题、同性恋问题、社会弱势问题、第三世界问题等,实际因素在阶级的大范畴 (也是一个大写的一)下遭到了遮蔽。于是,拉克劳和墨菲坚持用边缘性团体对中心的反抗,来重新阐述在新的资本主义环境中反抗资本主义的模式问题,这就是他们二人力主的领导权策略和激进政治,用一个消解的、不可化约的大众 (拉克劳在他另一本书《论民粹主义理性》中将其命名为民粹主义)来担当新的主体。
显然,巴迪欧不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尽管巴迪欧也认为马克思原先的一些分析范式的确已经无法用来剖析今天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但是巴迪欧绝不会像拉克劳和墨菲一样简单地抛弃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范式,相反,他坚定地站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对立面,从不同维度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换言之,尽管我们可以将巴迪欧归结为一种终结或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也绝非拉克劳和墨菲那种拒绝从阶级分析范式来看待资本主义现今发展的“后马克思主义”。正如齐泽克指出的:“巴迪欧的‘后马克思主义’无论如何都不能对流行的解构主义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论”的消解有什么作用,相反,他是唯一坚决地抵制解构主义教条,并将之看作新的陈词滥调,看作怀疑论的一个当代版本的人。”③Žižek,Slavoj 1998,“Psychoanalysis in Post-Marxism:The Case ofAlain Badiou”,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97,2:235-61.
无论是同源性,还是前沿性的对立,更准确地说,那种认为巴迪欧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家族相似”的想法都是不准确的,相反,当我们仔细推敲起来,它们是不兼容的,它们各自诞生于对马克思主义终结或者危机的不同评判上。它们的理论轨迹尽管连接了许多相同的点,但它们的最终景象却是迥异的。
这种差异究竟位于何处?巴迪欧既不是用其他主体范畴来取代那个被看作不合时宜的“工人阶级”主体来执行反 -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策略,更不是站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坚持“工人阶级”仍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当仁不让的主体。事实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巴迪欧就深入地思考过主体问题,他结合拉康的理论和法国式的毛主义思想,将主体理论置于唯物主义理论的中心。
更准确地说,巴迪欧的主体理论是一种行动理论,他不从任何先在性的主体范畴来介入到社会政治运动之中,简言之,革命的主体是在运动中生成的。在革命运动之前,任何以某种固定的范畴来承担革命主体的范式都遭到了巴迪欧的拒绝,即使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也并非一定是合格的革命主体,因为在这个群体中,既存在真正的受压迫者,他们唯一的希望是砸碎一切去创造一个新世界,但是也存在马克思所说的流氓无产者和工人贵族,他们在这个队伍之中分化着无产阶级的力量。相反,那些非无产者群体未必不能承担革命的使命,只要他们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内在地对人的压制,并将斗争的锋芒指向资本主义,他们仍然可以是合格的革命主体。一言以蔽之,巴迪欧的主体不是看预定身份,而是看主体在运动中的行动。在 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巴迪欧对这一点更加自信。在这场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中,作为主体承载者的并不是所谓的“工人阶级”,而是学生、教师、记者、专栏作家等等。在这场运动中,他们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革命主体。相反,拉克劳和墨菲的反抗主体仍然是先在性的,也就是从现有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被划分为剩余物(séd iment)的存在者的角度来思考社会主义策略问题。事实上,在巴迪欧看来,问题并不在于那个剩余物,而在于资本主义划分剩余物的方式,也就是说,剩余物作为剩余物的划分本身就是不合法的,当拉克劳和墨菲从这种剩余划分来反抗资本主义,最终只能再次堕入到资本主义的彀中,最终与资本主义的结构同流合污。
在革命运动中生成主体,这种运动的价值正是在于去颠覆一种既有的资本主义框架,利用漂浮的、流溢的多来冲破资本主义的情势状态,这种在运动中生成的漂浮的、流溢的多不可能被资本主义的类性真理所完全消化,也就是说,它们必然相对于资本主义存在溢出,在溢出中,资本主义的平滑的外表被断裂性的症候所撕裂,也正是在这个被撕裂的裂缝的深渊处,主体才作为主体出现了,它以自身的运动和行为投入到那个深渊之中。
因此,巴迪欧对唯物主义的坚持,永远不是为了“保护”那个陷入危机之中的马克思主义。那个逝去的或者行将就古的马克思主义不值得去挽救,对于巴迪欧来说,对马克思的思想最彻底的坚持就是让马克思在行动中去生成,去炸裂那些原先已经被美杜莎之瞳石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让马克思主义的新芽在真正的革命运动中去生成,这有如一只不死鸟,在政治运动的火焰中将自己燃烧殆尽,又涅槃重生。因此,对于巴迪欧来说,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对于巴迪欧而言的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在具体行动中涅槃的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对原先的形态的彻底拒绝和否定,而是一种重生,一种浴火式的涅槃。所以,在《主体理论》中,巴迪欧大声呼吁:“在今天,仅仅保卫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去保卫一种羸弱。我们必须去践行 (faire)马克思主义。”①Alain Badiou,Théorie du sujet,Paris:Seuil,1982,p198.或许正因为如此,巴迪欧更喜欢用后毛主义 (post-maois me)来称呼自己,以此将自己同那种实际上与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同流合污的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在 21世纪的今天,巴迪欧仍然用自己那些行动来验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并积极地将主体性力量投入到溢出性的革命实践之中,这种溢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溢出,也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范式的溢出。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巴迪欧的“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的真实含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将巴迪欧看做一个不断生成和涅槃的“后马克思主义者”。
A81
A
1003—4145[2010]02—0005—07
2009-12-25
蓝 江 (1977-),湖北荆州人,法学博士,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法国左翼哲学。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巴迪欧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09CZX0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文升 wszhou66@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