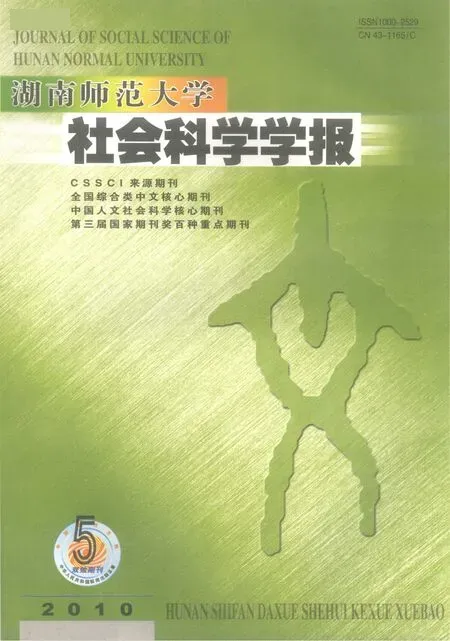社会信任与和谐社会建设
2010-04-11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朱 虹
社会信任与和谐社会建设
南京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朱 虹
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社会如何有秩序?信任无疑是最重要的建立社会秩序的微观机制之一。早在17世纪霍布斯就提出著名的“丛林假说”:人与人之间如果缺乏信任就将陷入人人相互为敌的生存困境。100多年前社会学家齐美尔对信任发出了“社会何以可能”的追问。他认为信任是促进社会整合的力量,我们的社会联结是无法建立在对他人的完全了解的基础上,如果人们缺乏起码的信任,社会就会解体。如果说霍布斯和齐美尔对信任与社会团结的思考仅仅是哲学思辨的话,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中叶呈现出高风险社会特征,信任与社会团结的关系成为一个重大而迫切需要解决的全球性的、时代性的课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信任的缺失成为乱像丛生的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人们对假钞、假证书、假货、虚假新闻和广告早已司空见惯;对专家的见解、知识技术的可靠性、对银行、法院、政府的信任都表现出信心不足;“杀熟”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导致夫妻、父子、亲友之间人人自危。信任危机确已成为导致社会秩序与人们本体安全丧失的根源之一。创建和谐社会就必须重拾社会信任。
重建社会信任,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信任。关于什么是信任,心理学的视角将信任视为“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事件中所拥有的一种期待”,信任是一种个人动机,也是一种态度。为什么有的人倾向于信任他人;有的人则倾向于怀疑他人?心理学家的解释是:信任依赖个体的人格结构,包括认知、情感、信心等方面。社会学家眼中的信任其实就等同于信任的社会功能。巴伯指出信任的社会功能一是维护社会秩序,为相互作用的行动者提供道德期望图式;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卢曼开宗明义地将自己的著作取名为:《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在卢曼看来,信任本身其实就是对付不确定性的一种策略,是化解复杂性的社会机制。如果没有信任,人类只能进行非常简单的当场互动合作,而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人们面对的是一个超级复杂的世界,因此,信任已经不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而转变为一个认知问题。信任简化认知,是人们进行复杂社会互动的基础。科尔曼对信任的诠释是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开始,他认为信任作为持久交易的“游戏规则”是在群体成员进行理性互动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守信用和信任他人将使双方都获得所期待的回报,否则两败俱伤。由此,科尔曼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社会资本,人们为什么要选择信任他人和保持诚信是因为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综上所述,信任具有多重含义:是一种对他人行为的乐观的、积极的期待;一种正面的社会态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控制机制;是应对复杂世界不确定性的简化机制;是一种能获得高利益回报的社会资本。
有趣的是,文献梳理可以得出有关信任的清晰含义,但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里,信任却是一个很少使用,且语意不详的概念。这是我们“社会诚信建设”课题在进行全国性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比如,当我们询问“你信任朋友吗?”“你信任陌生人吗?”被调查者常常表示无法回答,他们的理由是必须给出具体的背景,必须要有事件才能回答。无利害关系,或不打交道时对任何人都无所谓信任不信任。如此,我们每一道问卷调查题项都要设计一个具体的情景,而这一设计又必须是所有被访者生活世界中熟悉的。我们的定量调查遭遇非常棘手的困难,但却引发了对信任概念,以及当下人们纠结所谓信任危机的真正原由的重新思考。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信任是一种现代观念,还是许多持文化范式的学者认为的,信任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特质或称为地方性知识的集体习惯。在传统社会,社会结构稳定、人们世代固定在乡土社会,社会流动率低,传统文化中的宗教、道德、伦理就足以确保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无需强调信任问题。自给自足、田野牧歌式的生活模式,其实也是人们之间社会交往频度很低,绝少与不熟悉的人与事打交道的社会。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是身处变化莫测社会环境的现代人的虚妄之言,却是过去的现实。现在,人们对信任的普遍关注、或者成为一种本体安全的迫切需要,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们必须与变化的、陌生的、利害交关的人和事发生社会互动。信任危机确已成为让人们普遍感到不安的社会心理事件,但信任危机的发生并不仅仅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道德层面或者与社会失范的问题。其实,信任危机就是一种现代性的危机,是人类在风险社会来临后的不知所措。所以,我们认为信任是一种现代观念,因此我们去纠结信任如何丧失的伪命题,还不如去探讨现代社会如何建立社会信任,得以帮助人们适应并应对风险社会。
既然信任是一种现代观念,那么当下热议的重建社会信任的路径,就无法从传统社会文化中找寻和继承。中国人的传统信任关系,仅仅涉及到以乡土和血亲为纽带的人际信任,是与不流动的乡土社会结构相匹配,主要通过乡规民约等习俗对人们进行熏陶、濡化而得以传承。正如费孝通所说,“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这种传统的人际信任文化模式面对高流动性、高异质性的人群共同体是不能发挥社会控制作用的。
我们认为,社会信任的建设首先应当向西方现代社会学习,建立全面的信用体系。信用体系是基于技术分析和信息采集而形成,包括货币、知识、权力等社会交往媒介的甄别与评价。当然我们会说信用就是信用而不是信任,信任不是技术,也不是理性决策,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态度,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正面期待。我们认为,人们依靠信用体系能发展出一种新的信任模式,既系统信任。系统信任是通过利用信用体系的安全保障代替缺失的信息,进而赋予人类对待复杂世界偶然东西的稳定态度。比如,人们对货币信用的系统信任,就是通过连续性的、肯定性的使用货币的经验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的。“什么人都是假的,钱才是真的”、“养儿防老不如养房防老”的拜金主义价值观背后,隐晦地揭示现代社会人们从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向。系统信任的建立大大地简化了纷繁复杂的由陌生人组成的、大量的一次性社会互动所需的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复杂过程,使人们在无需通过人际信任,就能进行可预期的、有秩序的社会交往。随着信用体系日益细化、完美和合法化,最终将成为人们的先验信任态度,系统信任就建立起来了。从因熟悉带来安全感的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过渡,是一种伟大的文明进化过程,也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
其次,要培育崭新的信任文化。在农民即将终结的时代,乡土社会终将成为一个永逝的时代背影。我们已经踏上了现代性的不归途,儒家传统文化之余光难以照亮中国社会信任建设的未来之路。培育新的信任文化也许应该从理性的路径,而不是道德和伦理的路径切入。信任关系可以是理性的,也可以是后理性的,但很少是非理性的。我们把给予信任还是不给予信任、是守信还是背信作为一个人们理性选择行为,两害情相权取其轻,如果这种行为获得积极正向的报偿,守信行为就得以强化,使得行为者不断地重复这种行为,那么它就渐渐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人格的一部分。这种人格扩张到社会的层面就成为集体人格、国民性,进而固化为信任习俗,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倾向,一种社会资本。总之,我们认为,信任关系是可以通过理性选择而建立起来的,并且在适当的社会条件和环境下可以转化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倾向。目前,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进信用体系的完善,让守信者能获得更多的社会合作的机会;另一方面,还必须加强对不诚信行为的社会惩戒,方能形成培育新信任文化的社会条件和环境。
如果说以上两个建议来自信任与现代社会结构之间的理论推演,本文接下来提出的建议则来自我们课题组的实证调查的结果。建设诚信社会涉及到对政府、专家、符号、商业、人际方方面面的内容。调查显示,对政府的信任,尤其是对基层政府的信任首当其冲,是目前导致人们是否持有社会信任的基础;另外,媒体大量充斥社会失信行为的报道,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恐慌,强化了民众的信任危机感,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猜忌和冲突。最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是,读过南京“彭宇事件”新闻报道的人,不到8%选择“看见老人摔倒,毫不犹豫上前搀扶”的调查选项;而没读过该新闻报道者则高达84%的人选择“搀扶老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新闻报道可能产生的社会后果,对媒体议题设置进行前瞻性的监控;同时,还需着力培养民众的媒体素养,提高民众面对传媒报道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和质疑能力。最后,社会情感也是影响社会信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的调查发现影响社会阶层之间的信任,与是否有直接互动经历,以及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关系不大,而往往是基于强烈的情感联系。一个与同乡五个小偷同居一处的民工,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明确表明他信任那些小偷同乡,而不信任城里人;问卷调查中高达92%农村被调查者认为城市人不可信;那些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对自己的教友则非常信赖。通过增进社会各阶层、群体人们之间的社会团结与认同,是我们建设普遍社会信任的另一重要途径。
(责任编校:文 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