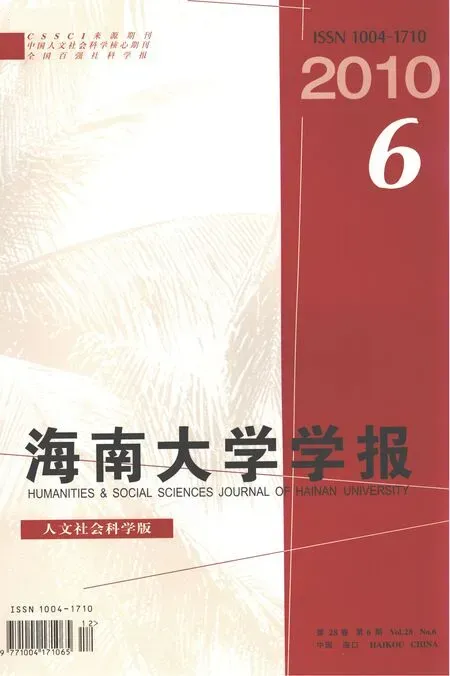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对Sein一词的词源学分析
2010-04-07张守永
张守永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241)
论海德格尔对Sein一词的词源学分析
张守永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241)
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关注存在(Sein)问题,从其前期的作品《存在与时间》到后期的《林中路》。一般认为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转向”,即从前期的此在为中心的基本本体论到后期的从存在出发来理解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对存在(Sein)一词进行了词源学分析,对正确理解海德格尔的“转向”有重要意义。
此在;存在;在场状态;真理
一、追问Sein词源的必要性
在《存在与时间》的导论里,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式的进步以及把存在问题当做逻辑学问题来处理的哲学进行了质疑,并声称“曾经以思的至高努力从现象那里争得的东西,虽说是那么零碎那么初级,早已被弄得琐屑不足道了”[1],由此海德格尔认为,存在问题在希腊时期还保留着对存在的“思的至高努力”,而到现在却经过形而上学化而降解到“逻辑学”,所以海德格尔认为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对存在进行了定义,所以他说存在虽然是最普遍的概念,但却也是最空洞、最晦暗的,所以需要重提存在问题以对其进行重新梳理。
因而,海德格尔提出了以此在为中心的基本本体论来重新审视存在问题,即此在是特殊的存在者,是对存在有所领会的存在者,因而存在问题可以经由此在问题得到澄清,揭示存在问题,因为此在的生存论的领会本身就是存在论的,由存在所规定了的存在样式,由此,通过生存论的此在可以展示存在问题。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也是对存在问题的重新梳理,但这次却提到了“无”的问题,并在30年代广泛地探讨真理问题,而不是从此在来讨论存在问题。其写作思路与前者不同,因而一般认为海德格尔在30年代发生了思想的“转向”,即抛弃前期所留有的传统形而上学的主体主义而转向非主体主义,或从此在转向了存在本身①。海德格尔本人对这种说法进行了解释,在《致理查德逊的信》中,海德格尔有这样的表述:“您对‘海德格尔Ⅰ’和‘海德格尔Ⅱ’之间所作的区别只有在下面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即始终应该注意到:只有从在海德格尔Ⅰ那里有待思的东西出发才能最切近地通达在海德格尔Ⅱ那里有待思的东西。但海德格尔Ⅰ又只有包含在海德格尔Ⅱ中,才成为可能”[2]。
而海氏在其后期的作品《林中路》里,是从林中空地来解释存在的,即存在本身被理解为林中空地之澄明本身,澄明本身就是隐蔽着的,所以就是解蔽即遮蔽意义的存在本身。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大地与世界的争执本身是真理本身,争执本身作为裂隙被带入大地之中而自行嵌合,这是对大地本身的规避力量的呈现,也就是对大地之“无”的表述。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一文中是要追问技术的本质,技术与形而上学都没有思考在场之为在场状态本身,思考技术也就是思考技术之为“座架”的本质,即摆脱技术的表象化、主体性、目的性的制作性,而从存在本身而来追问技术。
在《黑格尔的经验概念》一文中,海德格尔从本有(Ereignis)进行思考,并且本有之经验是现象学的显现本身。所以海德格尔的入思方式是思考显现所归属的在场状态(Anwesenheit)本身,思考在场状态之无蔽之为在场状态本身,也即从古希腊的无蔽本身而来思考黑格尔的经验概念对于存在之发端的经受和展开。这是回归到对存在之为本源的探问中来思考现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
而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中,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的本质是“求意志的意志”本身,在在场中已经设定了在场之目标,即意志是在场之意志,而所求之意志也已经早已从在场得到了思考,所以尼采的思维方式仍旧停留于形而上学范围之内。海德格尔却是要跳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去期备,这乃是一种思想的本质”,即入思,思入本源之中,即从存在来思考存在之为发端以及在形而上学中的完成。
《诗人何为?》是为了思考“贫困时代的诗人”里尔克是如何在技术时代思考神圣者,如何思考人类的拯救。在这里,海德格尔是为了追问命运性本身的保存,追问命运性之为命运性本身,而在《命运》一文中,海德格尔将命运思为同一即存在之二重性的展开,由同一而来的召唤是让人们共属于存在之本有,即存在之为二重性本身。所以,海德格尔通过里尔克的诗来探问形而上学的本质,即追问本源之历史到场,也即思考存在之历史性。
在《林中路》最后一篇《阿纳克西曼德之箴言》将存在本身思为裂隙、嵌合,是思考本源之为本源,本源之存在作为裂隙、嵌合是发送人的本质的,是对存在者的召唤,人恰恰是作为应答者才具有人的本质。本源之为本源是对在场之为在场状态的追思。在场状态本身是运作的二重性,即“显示/遮蔽”的二重性的运作本身,是澄明着的遮蔽本身,本有之运作。追思前苏格拉底哲人的思想也是为了追思遗忘了的存在本身,应召本源之为本源的召唤而入思,入思也是一种对本源的应答。
由此可以看到后期海德格尔试图从存在来追问存在本身,表明了其前期与后期之间的明显不同,因而需要回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海德格尔对存在所作的解释,并对中期的存在理论进行具体的分析,因而才可能理解中期开始的所谓“转向”的含义。所以本文的目的是要分析《形而上学导论》中的第Ⅱ部分——追溯“在”这个词的语法和语源,通过对这一章节的分析来理解海德格尔30年代所谓的存在问题。
二、海德格尔对Sein词源分析的独特性
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语法和语源的追问,不是追问日常的对于语言的语法和语源的规范,因为“这些东西老早就只还是指示人们去机械地剖析语言和订立规章的技术手段罢了”,“语言和语言思考都已陷入这些僵死的形式中就像陷入一架钢网中一样”[3]53,所以要追问语言的“原始的干涉之处”不是要固定在这些“框框套套”里,不是死结为固定的语法形式和语源,而是要追问语言本质的存在之处。
在海德格尔的《走向语言之途》,首先就对洪堡的语言观进行了批判:“洪堡把语言表象为某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以此为指导,洪堡来追究语言显示为何,即追究语言是什么。这个什么—存在被人们称作本质”[4],形而上学的学院式区分来自对essential(本质)与existentia(实存)的区分,本质存在就是事物的“什么—存在”,指事物的现实性存在,到场存在的存在者的确定无疑性。事物得到现实性存在就是事物的在场,事物作为在场者而存在,形而上学追求的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即通过在场存在者来追问存在者,而不是通过存在本身。所以形而上学追求对事物表象化,进而从主客分立的二元论来思考对象,但最终却落入作为主体的人,这是在尼采那里得到实现的,即作为绝对主体意义的人达到了无限制性的展开。
所以语言的本质不能从在场者的语言本身或者与其相关涉的存在者得到解释,而应该追问语言之为存在的本身,应该走向对于语言的本质存在的沉思,沉思语言的存在。所以海德格尔说“要为学校把精神世界从内心方面来从根本上加以改造,也就是说,要给学校创造一个精神的而非一个科学的气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一切立即陷入一片荒漠中”[3]53。
如果将精神考虑为形而上学性质的存在者,那么精神就会丧失其本质,要么沦为“智能”,进而成为服务于其他事物的工具。这种形式是对精神的误解。是传统意义上的主客分立的二元论思维,是从存在者来追问存在的。认识的程式化,对于对象表象的精确性、确定性,都是在存在者范围内进行的,通过对对象进行表象,通过各种形式的研究而应用方法和规律来计算事物,达到确定性,而在预先计算中,自然受到了摆置,由此自然成为了表象的对象,而作为表象的主体——人,却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
因而语言本质的追问不能从形而上学范围内去思考,对语言本质的沉思是要追问语言存在的开端。追问这个开端,是精神的本质要求,是重新赢获存在的努力,是为了将存在保持为存在自身,也就是保持开端之为开端本身,而不是遗忘开端本身的争执性,遮蔽开端而堕入形而上学的窠臼。而在语言的开端,首先要回到希腊人对于语言的沉思,因为“西方语法学之形成是从希腊人对希腊语言的思考中得出来的,这件事将其整个含义传给了整个过程。因为此一语言是(从思之可能性上看来)与德国语言并立为最强有力同时最富精神的语言”[3]56。
三、海德格尔对Sein一词的词源分析
存在(Sein)一词来源于希腊词语on,引文译作being,有学者分析on一词本身“兼有实义动词和系词的功能,故兼有‘存在’(以及‘有’)和‘是’两方面的含义”[5],即兼有存在的动作性状态,例如“生”“活”的活动状态含义,也有系动词的含义。亚里士多德说第一哲学就是关于on的哲学,海德格尔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分析on一词来源于eon,是在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时期使用的词语,都意指存在,所以他说“我们不妨带些夸张、但也带着同样真理性的分量断言:西方的命运就系于对eon一词的翻译”[6],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对此词的重视。
一般将作为动名词形式出现的das Sein(存在)认作存在,并认为是最熟知的、“不言自明的”,海德格尔却认为这恰恰是最成问题的地方。海德格尔认为,须要追问此词语产生的最初形式,要区分出作为动词的sein,以及不定式形式的sein,还有作为名词形式的das Sein,所以动词、不定式、名词就是须进行原始追问的词性。因而要熟悉此词的原初性质,就要通过对其最初形式的产生以及后来对此词的演变情况进行区分,因为语言的本质就诞生在语言最初创立的时期,即开端之时期。追问词语的本质就是追问语言开端的存在状态,而不是从后世的语言框架内来拷问此词的后期形式。
在动词、不定式、名词这个次序中,不定式是处于过渡阶段的语法形式。所谓不定式,“下述全名的简化的名称:modus infinifivus,无界说的,不确定的方式,这就是说,在一个动词展示其含义内容与方向的样式中是无界说的,不确定的”[3]56。在柏拉图时期,动词与名词“还被理解为全部词的应用上的名称”,名词意指“语言上的名称以区别于所称的人和事”[3]57,并且在后来的语法形式中,名词也指第三人称单数形式。而动词指的是抽象性的动作态势本身,所以是个完全抽象性的词语。
所谓不定式“已经指点着一个modus finitus(定式)了,亦即对动词的意指有所限定的方式”,拉丁词modus在希腊文中意指“偏向一边”,同时表示名词和动词的变格形式的“格”也是此意思,所以所有的名词变格和动词变格也是指某种偏向。所以动词变格和名词变格的意思为“下落,倾斜和偏向”,“在这层意思中就有一种从正直的直立的偏向,但是这个正直的直立,它直向上而成此立,出现而立,常住而立,希腊人就把它领会为在”[3]59,所谓古希腊的在意指在场,进入在场之中,因而也就获得了其边界,“自获其界”。所以在就是进入在场之中获得其形象(idea)的完满实现,所以这就是古希腊所意指的形式,“这个希腊人所理解的形之本质是从正在生起的把自身放入满界这回事中得出来的”。
所以,海德格尔说亚里士多德是从在场状态来思考存在的,事物之为存在本身就是将事物带到其在场之中,让其在在场之中得到呈现,这就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即存在状态,也就是其在场方式,所以“在场状态,即ousia,因此就意味着energeia(实现)”,也就是“被建立之物立身于无蔽状态中的在场”[7]1039。所以事物在在场之中得到显现的状态也就是达到其外观(idea),并在其外观之中得到静止状态的逗留,进入其外观的无蔽状态。“这个energeia(实现)乃是tode ti(个体、这个)即当下这个和当下那个东西的ousia (在场状态)”[7]1040,所以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tode ti(个体、这个)意义上的在场状态,也就是事物的如此—存在,这是第一性意义的在场意义,也就是事物的实存意义。而第二位意义上的在场是指处于在场之中的各种在场者,包括人、动物等之以类为分的各种在场之物,此种意义是事物的外观意义上的存在者,也是事物的“什么—存在”,也就是事物的本质意义上的存在。
古希腊哲学是从在场来思考在场者的,不定式也是从在场来得到思考的,而名词和动词所具有的变格形式也是通过此不定式的在场来得到表现的。海德格尔认为不定式所表现出来的动词和名词的变格是“附带表达出来,附带成立,附带让其得见”,所以后世所采用的各种语法形式对存在的表达是遗忘了存在之为存在本身的原初形式,是使希腊的思想遭到遮蔽的形式。而希腊人所考虑的在场却是双重意义上的“常住”:“1.作为出现着的自立,2.作为这样的自立却‘常住’,这就是说停留着,逗留”,因而名词和动词意义上的存在在“希腊人思想中恰恰是不在”。因而海德格尔在对柏拉图的对话篇(蒂迈欧)中对于变化的本质的考虑时,将变化的本质思索为“处所”,“变者就被摆到此处所‘空间’中去又从其中摆出来。但为要使此事成为可能,‘空间’就必须绝不沾染他无论会从何处收受来的任何外观的方式”[3]65,所以说希腊对在场的思考不是从作为外观的理念出发来考虑事物本质的,事物的本质在场是显现。
所以说此在场状态本身是一种以“空间”形式的处所来表示的,也就是此不定式形式的表示,这是显示动词和名词的变格的场所,此场所之为场所本身不是固定在场为在场者的外观的,而无论是动名词还是名词形式却都将不定式进行固定化为在场者的外观,所以通过把不定式改造成动名词,“在”就被说成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对象了,而名词形式的存在也是直陈式第三人称单数形式的在场者,是一个固定的对象。
海德格尔不仅要像希腊人那样思维,而且要返回到此本源之处而重新赢获此本源。因为海德格尔认为希腊人只是从在场思考了存在者,然而却没有进一步的思考在场之为在场的状态本身。海德格尔认为要思考在就是思考希腊词语physis(自然),其意思“是指卓然自立这回事,是指停留在自身中展开自身这回事。在这样起的作用中,静与动就从原始的统一中又闭又开又隐又显了。这样起的作用就是在思中尚未被宰制而正在起主宰作用的在场,在此在场中在场者就作为在者而起本质作用了”[3]61。所以physis一词是与在场状态相联系的,将在场者抛入在场之中的,在场者之为在场者就是从此词所开辟出来的在场之中获得其本质的,所以physis一词是为在场者而开辟在场之境遇的,也就是在场状态之无蔽境界的敞现,为存在者敞现了世界。
不仅如此,physis一词的开辟是一种“争执”形式的运作状态,即在一种对立的斗争中的持久运作状态,在此持久的斗争中,不是斗争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保持着此种斗争的势头本身,不消弭此种斗争之为斗争本身的态势,此种斗争就是“鸿沟,差距,宽度与裂缝”,因此,此种斗争是一个统一体。海德格尔称其为原始的斗争,此种斗争是一种原始的空空如也之境遇本身的运作的斗争态势,所以海德格尔说:“主宰作用,physis,就凭这些事业而在在场者身上完成了。”[3]62如此,世界才保持世界之为世界本身,即世界之为世界的在场本身是与大地的本身遮蔽保持着始终的斗争态势的,在这样的斗争中,世界作为世界出现而在场,而大地也作为遮蔽的“存在之无”的力量规避自身。
但是当这种斗争态势一旦遭到遮蔽,就陷入形而上学的在场者的斗争中,就将遗忘在场之为在场状态本身,而只是从在场者方面来考虑在场者之为在场者,于是造成了对存在的遗忘和遮蔽。因而在者也就是对象,是现成的可供使用的使用对象,是可以制作的对象,可以表象的对象,因而事物也就只是从其呈现的外观来得到设置和表象,这也就是应和了前面所说的从不定式到动名词的实体化倾向。而不定式本身是要从处所与“空间”来得到思考的,对于与其相关涉的人称、数、时间、语态、式、动词的变格以及名词的变格等,是附带表现出来的。而此处所与“空间”是要“必须绝不沾染他无论会从何处收受来的任何外观的方式”,“在其中并不表现出人称,数,式来的这样一个变化形式”,而到了拉丁文中,希腊人对此不定式的表示方式却遭到了改变,因而不定式就只是限制在人称,数等见地中了,“只剩下限制出来的形式上的印象起规定作用。”[3]66
因而,不定式形式是要思考与希腊词语physis相关涉的境况的,即不定式思索为处所与“空间”本身就是保持斗争态势而为在场者争取其本质的斗争态势,这种对不定式的思索是对希腊人对此不定式的思索的进一步思考,也就是不仅从在场来考虑在场者,而且要思考在场之为在场状态的无蔽本身。而此种思索也就意味着不定式本身是对一种运作状态的描述,而不是对现成在场者的描述,是不能实体化的,后来的对存在的实体化倾向都是对存在的遮蔽与遗忘,是将存在者当作存在,是形而上学的表述方式。所以海德格尔追问的是作为不定式形式的存在,而不是从动词变格与名词变格形式出发的存在。而作为不定式的存在本身是先于成形的存在者的运作态势,是运作态势所保持的争执本身,也就是后期海德格尔所说的裂隙,这是存在本身的运作,是空间的争取,是世界的成形,也是大地本身的规避力量,由此,存在才成为“之间”状态,于是也就是存在“与”时间中的“与”字的态势。这种“之间”态势正是存在本身的生成性经验状态,而不是作为固定化了的存在者的现成存在。所以海德格尔说“在就是升起的现象的在场,不在就是不在场,那么这个升起与下落的交互关系就是现象,就是这个在本身”[3]115。
四、结 论
基于以上分析,海德格尔对在的词源和语法的分析表明:海德格尔追问的是作为不定式的生成性经验本身,不是追问的作为名词形式出现的存在者。存在者是要从存在得到考虑的,而存在者固执于存在者的现成在场本身,未曾思考作为在场的在场状态本身,也就是没有思考无蔽状态的在场,因为现成在场者是停留于在场状态之中的,然而存在本身的思考却要追问存在之无,因为无是归属于存在的,存在的生成性经验本身就启示着无,启示着此种空空如也,也就是说存在是与不在场相关涉的,而希腊人虽然从在场来思考存在,却没有思考在场之为在场状态本身,这是需要继续追问的,也就是仍旧要追问作为在场状态之为出、入之间的关系的运作态势本身,此种运作态势是对不定式形式的生成性的经验。作为不定式形式的生成性的存在经验本身是要保持着出、入之间的运作关系的斗争态势,所以是作为澄明着的遮蔽本身的运作,是既要让世界显现而为世界,同时也要保持大地本身的规避力量,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追问的存在,作为生成性而经验到的存在运作本身,是对形而上学停留于存在者范围内追问存在者的本质的克服。
海德格尔对存在一词的词源和语法追问,是为了追问存在一词的存在本身,是从语法之存在本身来追问,即从存在来追问存在者,而不是从存在者出发来进行追问。以上分析也能从中期海德格尔的思索录像来延伸到其后期对存在的陈述,因而对存在的词源的分析就是为了打开通向存在的道路本身,从而经验此道路之开辟状态本身。由此才能够真正明白海德格尔中期的追问意图,以及后期对存在的陈述。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3.
[2]孙周兴.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1994:61.
[3]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M].熊伟,王庆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45.
[5]杨适.希腊哲学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7.
[6]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64.
[7]海德格尔.尼采:下卷[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On Heidegger’s Etylomogy Analysis of Sein
ZHANG Shou-yong
(Philosophy Depart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From Heidegger’s early workBeing and Timeto his later workHolzwege,he concentrated on the problem of Sein all his life.It is stated that in 1930s Heidegger’s thought took a turn,i.e.,a turn from his early basic ontology focusing on Dasein to his later thought,to understand the being from being itself.In his bookIntroduction of Metaphysics,Heidegger analyzed the etymology of the word Sein,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understanding Heidegger’s“turn”exactly.
Dasein;Sein;presence;truth
B 516.54
A
1004-1710(2010)06-0053-05
2010-03-16
张守永(1982-),男,山东济南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的解释学。
[责任编辑:王 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