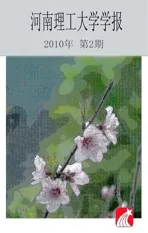魏晋“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2010-04-07胡红梅胡晓林
胡红梅,胡晓林
(1.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2.湖南省湘潭县第一职业学校,湖南 湘潭 411201)
魏晋“人的觉醒”与“文学的自觉”
胡红梅1,胡晓林2
(1.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2.湖南省湘潭县第一职业学校,湖南 湘潭 411201)
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时期,人的觉醒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由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全社会对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认识,进而促成了文学的自觉。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人的觉醒引发“文学的自觉”,从而导致文学创作、文学观念的自觉。
人的觉醒;文学的自觉;文学创作;文学观念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1]。由此,魏晋六朝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变革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乃至整个意识形态都经历了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转折变异。汉末儒家思想统治的崩溃,促进了各种思想学说的发展和流行,佛学的东渐,道家思想的流行,名士集团的大量出现,玄学的炽盛,清谈的盛行,以及九品中正制的实行等等,都在客观上催化了魏晋时期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促进了全社会对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的认识,进而促成了文学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的概念,是鲁迅先生最早从日本著名汉学家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那里借用过来的。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文学的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 sake)的一派。”[2]“文学的自觉”是文学走向独立的一种表述方式,其意在说明文学不是经学附庸,它有其自身的特性,必须讲究艺术的表现形式。文学的自觉是文学审美的自觉,是作家、评论家乃至读者们发现并认识到了文学的审美特质、审美价值与文学创作的某些固有规律。虽然人们对文学的审美感受早已有之,但长期停留于感性直观的阶段,直到魏晋以后才上升到了理性认识的高度。
“文学的自觉”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次划时代的进步。要认清这一历史转折的轨迹,除了微观的定量分析外,还要从宏观上对当时文学发展的环境和趋势作出总体性的把握和比较。本文试图从魏晋时期人的觉醒、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几个方面分析、阐述“文学的自觉”。
一、从“人的觉醒”到“文学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以“人的觉醒”为先导的。没有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没有尊重人的个性人格观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首次提出魏晋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并把它与“文学的自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从哲学的角度考察“人的觉醒”同“文学的自觉”的关系[3]。我们知道,“人的觉醒”是魏晋时代的一大特征。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的觉醒”,其特点是从殷周以来的“天”、“神”的绝对统治中逐渐觉醒过来,意识到人才是万事万物之本;魏晋时代是人的第二次觉醒,其特点是对汉代封建纲常礼教和西汉以来谶纬迷信的反叛,个人自由、放浪形骸成为一种时尚。
先秦两汉时期的先哲们虽然也对人生这个重大的课题进行过探索,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自觉的高度。孔子认为,理想的人格就是“君子”,“君子”能把某种先验的“仁”的原则化为生命个体的内在需求,并能在生命历程中加以实现。从表面上看,孔子还是重视个体的内在需求的,但他却是把“仁”强加给个体,而非个体本身的要求。比起孔子来,老庄似乎更重视个体生命本身,主张个性自由。但他们的人生理论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如何排除外界的干扰,达到“保身”、“全性”的目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无欲无求”、“少私寡欲”。这些观点固然体现着他们对生命个体的尊重,但却完全放弃了个体的正当欲求与主观努力,取消了个体的实践活动。这在实质上否定了人的主体意识,否定了人的自我观念,否定了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的“自由”和“自觉”的创造精神,使活人变成仅供统治者使唤的机器,显然不利于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不利于展示个体生命的价值。
自从董仲舒把“儒学”提升到“独尊”的地位,使文学本身以及文学理论批评都未曾摆脱经学的束缚。这导致了奉命文学、帮闲文学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作家缺乏创作的独立自主精神,艺术上的追求和新变被视为离经叛道之举,对文学本身的认识和探讨大体还停留在文学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现实政治教化)的关系上。与先秦时代相比,文学主要表现为更理论化。至于文学自身的艺术法则和创作规律,人们很少顾及,即使偶有涉猎,也只是只言片语之谈,缺乏理论的深度和概念的清晰度。
由此可见,先秦两汉的人们从人自身出发来探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度是不够的,根本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自觉”。与此相应,作为这个时期的文学也处在不自觉的状态。文学不仅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反而沦落成为“经学”和政治的附庸。特别是汉代,文学几乎完全成为“诗教”、“政教”的工具,不仅忽视了文学表现主体个性的作用,也没有给文学本身的审美特征以应有的注意。这个时期的文学理论虽然较先秦时期要系统得多,但文学的概念仍然是宽泛的、不明确的。
汉末魏晋六朝时期,现实战乱的血雨腥风;社会分裂的飘摇无定;灭顶瘟疫的无可抗拒;儒家所崇尚的社会伦理秩序在政治仕途的无情无义的倾轧中被击得粉碎;悲苦无告的生命流淌出来的鲜血,一点一滴地浇开了人们的觉醒意识:个体的生存与存在,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生的短暂与绚丽,命运的无常与追求,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精神的思考焦点。这就是,在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上,个体意识第一次从千年沉睡中醒来了,这是一个破天荒的历史进步。
玄学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社会人生和自我价值作更深层次的理性审视,并从本体论的高度找到了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受老庄哲学的影响,两汉以神学目的论为主导的宇宙观,转向魏晋以人格理想为存在的最高本体的人格本体论;汉人繁琐论证推衍的思维方式,转向注重觉醒的领悟和强调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新的思维方式;两汉士大夫急功近利、注重外在物质生活的满足的心态,转向以追求内在独立人格、超脱精神为特征的士大夫的个体自觉的心态,这种心态体现在审美方面,即表现为追求审美的人生。
二、文学创作的自觉
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最早出现的是文学创作的自觉。文学创作的自觉,是文学观念的自觉和文学批评的自觉的前提条件。但这只是理论上的一种说法,事实上很难将创作的自觉和观念的自觉截然分出个先后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很难说《诗经》、楚辞和两汉乐府就不是自觉创作的结果,它们最初的产生,很可能都是自觉的行为。但是由于它们不同程度地对经史、音乐,对社会、政治乃至强权表现出较大的依附性,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创作者不是有意为文学创作,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尚无文学的概念,所以他们的创作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自然也就谈不上“文学的自觉”了。“文学的自觉”不仅是自觉的创作,而且更应该是自觉地去创作文学;在作者没有意识到其创作属于文学,或者说不是自觉地进行文学创作时,不能说己经进入文学创作的自觉时代。不过应该承认,由于《诗经》、楚辞、两汉乐府从它们所属的音乐体系中脱胎出来以后,就只是以文字的形式流传,这为人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典型的范本,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表现生活、抒发情感、描绘自然、记述事件的模仿对象。东汉时期,人们己经有意识地仿照它们的样子,尝试进行文学创作了。《古诗十九首》就是人们仿照两汉民间乐府进行创作的一种尝试。虽然我们至今仍无法确认《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但它们与《诗经》、楚辞、两汉民间乐府却有较大的差别。它们不依附于经史,不依附于政治和强权,也不再是只作为音乐的附属品而存在。
两汉大赋如《子虚》、《上林》、《两都》、《二京》等,都没有摆脱政治附庸的地位,功利性十分明显,模仿的痕迹很重。作者或是奉命而作,或是为了晋身取爵等功利性目的而作,自觉的因素相对较少。到了东汉张衡《归田赋》的出现,汉赋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创作动因上,它彻底摆脱了功利性,改变了汉赋为君、为臣、为名、为利而作的传统,变成为时、为事、为自我、为感情而作。李善《文选注》以为:《归田赋》是“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而作,道出了张衡写作《归田赋》的主观原因。在内容上,它一改汉赋体物写志旧例,而是直抒胸臆,把抒情性放在了第一位;在表现方法上,它不像《上林》、《羽猎》等大赋那样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而是寓情于物,借景抒倩。在建安之前,文学创作的自觉只是一种个体行为,只是少数作家自觉的行动,尚未形成一种趋势,更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行为。
文学创作的自觉作为一种群体现象和普遍的自觉的行为,出现于汉献帝建安年间,以曹氏父子为中心,以建安七子、蔡琰为羽翼的创作群体的出现就是其显著标志。建安时期,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一个十分奇异的前所未有的景观,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描述的“俊才云蒸”的景象:“自汉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域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一时期,有作品传世的作家,除了领军人物三曹父子之外,还有建安七子等。钟嵘这样描绘建安时期的文学盛况:“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源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以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诗品序》)
应该承认,早在先秦人们就看到了“情”与“文”的某种特殊关系。《尚书·尧典》即有“诗言志”的名言。《毛诗序》发展了这个观点,进一步指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就具体地、形象地、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情”于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决定作用。此外,司马迁所说的“发愤著书”的“愤”,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的“怨”,显然都是指情感。由此看来,先秦两汉对文学作品中的“情”不仅不如六朝看得那么重,而且两者颇有质的区别。先秦两汉在肯定“发乎情”之后又特别强调“止乎礼义”的重要,他们用儒家的政治、道德原则去规范、限制诗歌感情的表达。魏晋以后则不然,陆机所说的“诗缘情”的“情”则未加任何限制,凡属于人类的七情六欲,无不囊括其中。钟嵘更是明明白白遍举了人世间形形色色之情,甚至把女子“扬蛾入宠,再盼倾国”的得意之情亦涵盖在内。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两汉与魏晋六朝虽然都讲情,但有本质区别,绝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由对个体生命的重新审视而激发起来的人的觉醒,使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创作显示出强烈的主体性色彩。他们从不太重视情到以情为重——从带有枷锁的情到不拘一格的人类的真情;从表现社会的集体的情,到抒发个人的独特的情——标志着文学观念的转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质的飞跃。六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独放异彩,是与文士们对“情”的观念与态度分不开的,更直白地说是“情”解放的结果。
三、文学观念的自觉
魏晋之际是“审美文化的自觉时代”,不仅表现在文学回归个体生命的写作意识上,也不仅表现在玄学聚焦自我人格的理性思索上,还不仅表现在以人物美的张扬为旨趣的所谓“魏晋风度”上,而是更典型更直接表现在审美理论的开掘和突破上。也就是说,“文的自觉”或“审美的自觉”,最重要的标志莫过于艺术美所达到的自觉,因为只有理论形态的自觉才是真正成熟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是我国文学发展到魏晋时代才出现的新态势,它是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冲跨后,新的思想解放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思想文化领域各个部门重新进行调整建构,从而对文学自身的性质、价值所作的新思考、新认识、新实践。从魏晋开始,文学逐渐摆脱对儒学附庸的地位,并以独立的新姿态面对人生,通过自身的演变,不断充实自己的内涵和表现力,以适应新的历史环境,尽量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这一历史转变是以文学观念的更新为起点的。
东汉末年儒家思想统治的崩溃,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为人们重新审视文学拓展了视野和思路;而建安作家自觉的文学创作,又为人们认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价值提供了依据。至此,文学观念的自觉已具备了两个最为重要的条件:思想观念的解放;文学作品的积淀。
严格地说,建安之前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虽然“文学”一词很早就出现了,但它最初的意义却是指文章博学,与今天人们所说的“文学”大相径庭。文学原是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先秦诸子言及“文学”,也多是在这种意义上。到了汉代,“文学”一词的意义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文章博学之外,“文学”还有文章学术的意思。和今天人们所说的文学意义较为接近的是“文章”,它将具有文学性和不具有文学性的文章全包括了进去,却把讲究韵律的诗歌排除在外。因此,人们对文章价值的认识,也就不仅仅是对文学的认识了。在魏晋以前,人们基本上是用儒家的价值标准来看待文学,把文学当作宣扬封建政教的工具,强令文学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按经学的轨道运行;有关文学自身规律的探索以及艺术上的创造,常常被视为背离儒教规范的行为。长此以往,当然就谈不上文学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文学“自觉的时代”也不可能到来。
曹丕的《典论·论文》之所以成为文学自觉的先声,就是因为它所表现的文学观是一种有别于汉人的新观念。曹丕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他更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文学理论家,他把自己对人生问题探求的理论成果汇聚并贯注于《典论·论文》之中,以文学观念的形式折射出魏晋时代人们对自身所做的超越前代的解剖。首先,曹丕第一次把文学的地位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真正地为文学确立起自己独立的地位。他从“经国”的高度来认识文学,并把文学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提到与事功并立的地位,这种认识却是前所未有。他超越了这个对文学轻视甚至唾弃的时代,以独特的眼光、超人的胆识和浓烈的情感去面对自己的时代,探求生命的真谛,从而提出了全新的文学观念。他充分地认识到,文学不是“小道”,不是“童子雕虫篆刻”,而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其次,基于他的人生观和生命观,他明确地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他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是魏晋时期“文学的自觉”思潮的核心理论,意味着作家应当“为艺术而艺术”,是对汉代“寓训勉于诗赋”的说教的一种挑战。两汉时代,文学从属于经学,文学的价值不在它自身,而在于它的“厚人伦、美教化”的外在功用。到了曹丕时代,随着对人的内在人格的追求,人们开始对文学作本体论的研究,对文学的内在价值和本质进行思考。“文以气为主”的学说便是在这一思考和探索的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些真正体现作者个人情感、理想的抒情诗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繁荣起来的。曹丕的“文气”说不再把伦理教化功能作为艺术的根本点和落脚处,而是通过确立“气”在艺术中的主导地位,将人的生命气质个性视为艺术的中介和核心。“文气”说的提出,在古典美学上第一次真正把理论焦点凝聚在人的自身,凝聚在人的生命个性情感气质中。它标志着文学审美意识的真正觉醒,为古代文艺美学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视域和理念。可以说,“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是“文学的自觉”的理论表现。
先秦以来的“诗言志”说是偏向于内向性、主体性、表现性的,然而其所“言”之“志”又偏重于一种主体性的伦理怀抱和道德情怀,而不是一种纯个体的生命情感体验。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说的提出,使艺术的伦理政教功能开始被疏淡,其内含的个体生命表现的意味则突显出来。然而“气”的美学内涵仍嫌宽泛和抽象,缺乏明确的理论规定性。陆机的“诗缘情”说不仅扬弃了“言志”论中生命性内涵的宽泛性和抽象性,而且使艺术的焦点、核心明确地凝定在个体的情感上,即将宽泛的“气”凝定在具体的“情”上。他用一种经典描述的文学化话语方式,精辟地揭示了艺术创作中审美心理的内在结构特征,体悟到艺术的审美本质和规律,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古代艺术美学已真正步入理论自觉和学术独立之门。他在《文赋》中反复指出:“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情瞳陇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就充分说明了“情”对于创作的决定性意义。钟嵘在《诗品》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他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时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离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此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这段话首先阐明了不用诗歌不足以抒发感情的观点,但又从另一视角揭示了情与诗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以及无“情”即无诗与无文的道理。
四、结 语
汉以前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更多地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规律,对文学自身的种种特点,特别是对文学的创作过程并未作认真的研究。从魏晋开始,在人的觉醒时代思潮推动下,带来了文学主体精神的觉醒和高扬,文学题材的开拓,文学抒情功能的强化和发展。同时,在老庄哲学的启发、暗示下,结合文艺创作的实践,对文学创作自身的发展规律进行思考和探索,也推动了文学自身艺术方法的更新和改善,这是文学向纵深发展的标志。人们对文学自身艺术法则的探究怀有广泛的兴趣,正是从对文学个性的认识开始的,或者说重视文学个性的新观念启发推动了文学自身艺术规律的研讨。显而易见,这也是人的觉醒引发“文学的自觉”, 从而导致文学理论、文学创作独立健康发展的历史必然。
[1]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 吴中杰·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李泽厚.美的历程[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毋爱君]
Human’sAwakeningandLiteratureDeterminationinWeiandJinDynasties
HUHong-mei1,HUXiao-lin2
(1.SchoolofHumanamp;Literary,HunanUniversityofScienceamp;Technology,Xiangtan411201,Hunan,China; 2.No.1VocationalTrainingSchoolofXiangtanCounty,Xiangtan411201,Hunan,China)
Wei-Jin and Six Dynasties are the major chang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during which the human’s awakening is the main features. The paper stresses that the awakening of consciousness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had promoted further understanding for the whole society of human values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and thus made a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ry self-consciousness. It is just the re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lives that inspire the people’s awakening up, which results in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literature showing the subject of intense color. And the people’s awakening leads to a “literary self-consciousness”, that causes the literature creation and the literature idea determination.
human’s awakening; literature determination; literature creation; literature ideas
2009-10-15
本研究成果属于“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教通(2004)284号]研究成果之一。
胡红梅(1976-),女,湖南湘潭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艺美学研究。
E-mail:hhm-hn@126.com
I206.2
A
1673-9779(2010)02-014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