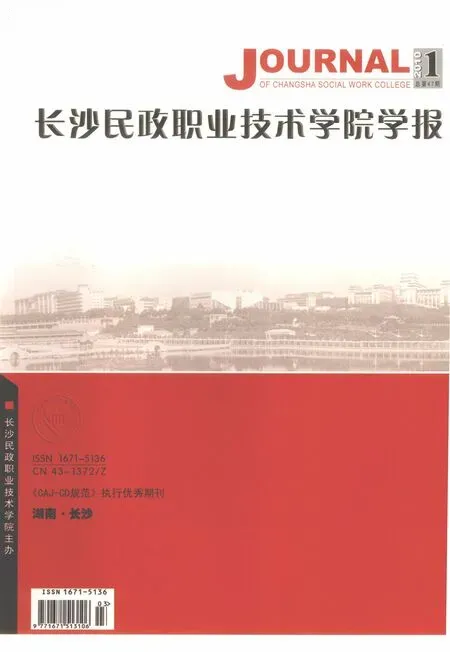王安忆的“故事”情结与小说创作
2010-04-04胡彩霞
胡彩霞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1325)
王安忆的“故事”情结与小说创作
胡彩霞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1325)
王安忆认为,一个故事本身就包含了一个讲故事的方式,经验性传说性故事和小说构成性故事是两个范畴。小说构成意义上的故事应该以严密的逻辑关系推进情节的发展。加强逻辑推动力可以促进长篇小说的繁荣。故事的地位是很重要的。王安忆的“故事和讲故事”观点是对小说本质的觉悟。
故事;讲故事;逻辑推动力;因果关系
王安忆在《故事与讲故事》中对“四不要”小说理论具体阐释为:“短篇的大道在于找着本来就是短篇的故事,长篇的大道则是找着本来就是长篇的故事。故事本身就确定了规模,规模本身也确定了故事[1]”。所以,紧随《故事与讲故事》之后的一系列小说理论如《故事不是什么》、《故事是什么》、《上海的故事》、《城市无故事》、《汪老讲故事》、《谁来听故事》、《我看长篇小说》、《我看短篇小说》都是从各个角度把她的观点阐释得更加清晰和具体,让人能够在她的反复阐发中理解和把握她的小说理论。
一、“小说就是讲故事”
故事是传统小说的中心。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几乎所有的小说创作,都是围绕着故事的编排布局来塑写人物与组织小说的。没有故事,也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一个传统的小说大师,也必然同时是一名故事大师。所以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家兼批评家爱·摩·福斯特说 :“小说就是讲故事。那是小说的基本方面,如果没有这个方面,小说就不可能存在了[2]”。王安忆也从自己创作的切身经验中体会到:“小说就是讲故事[3]”。她认为,“首先它 (指小说)是以讲故事为形态的”,“我们小说里需要用故事,这是一定的,我觉得小说一定要有情节和故事。这些故事我们要赋予它人间的面目,因为它绝对不是一个童话不是一个民间传说,它是小说,它要求一个写实的面目、人间的面目[4]”。
小说在形式上经历了一个简单到复杂的的过程。形式革命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作家开始不再信任故事。尽管一段时间之后,故事又一次回到了小说的灵魂地位,但在形式革命成为主流的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许多作家都认为,讲故事是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等人做的事,故事主导局面的时代已经过去,甚至,有些人宁愿相信那些玄奥的形式法则,也不愿再成为老实的说故事的人。但是王安忆在这样的情况下却能坚持自己对“故事”的观点,可见其具有远见卓识。青年批评家谢有顺发表的一系列理论文章的一些见解和王安忆的理论有着相似之处。他在《通往小说的途中我理解的五个关键词》中发表了对“故事”的看法:“我一度也被这种倔强的艺术姿态所吸引,后来,一个事实改变了我的看法。我发现,博尔赫斯可以不断被作家模仿,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永远无法被模仿。这告诉我,一个渴望标新立异的人,可以成功扮演形式先锋,但面对故事这个古老的形式时,他往往会露出马脚。一味地指责读者缺乏阅读训练是没有道理的,他们有理由对一个小说家提出故事上的期待。再后来,我又发现,几乎一切伟大的作家都讲故事,至少他们能讲故事[5]”。自现代主义艺术崛起以来,反故事的写作态度一度蔚然成风。事实上,故事体现了一种深切的人文关怀。所以,故事的地位还是很重要的。
王安忆在《故事与讲故事》中说道:“一个故事本身就包含了一个讲故事的方式。那故事是唯一的,那方式也是唯一的。……故事与讲故事的方式,与生俱来存在一体之中,犹如生命带着躯壳降生。……讲故事的方式隐在故事本体之中,看起来,就像没有讲述者似的,这才是故事与讲故事最本质的关系[6]”。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寻找故事,然后对寻找来的故事随物赋形。王安忆认为故事本身就包含了一个讲故事的方式,那是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契合,作者选择的叙述方式能演绎出故事的内涵。如在《小鲍庄》中,几条线索同时展开:捞渣的故事、小翠和文化子的故事、鲍秉德和他的疯老婆的故事、大姑和拾来的故事……这种多线索的情节安排,取决于生活本身的繁杂多绪,小鲍庄上人们彼此牵扯又相对独立的生活状态,这也充分体现了王安忆对故事的讲法的探索。《小鲍庄》一发表,当时的评论界对其结构有着很多说法。而王安忆却说,创作当初并非有意识地考虑结构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小鲍庄》的故事,本身就应该这样发生。王安忆自己也说:“如果说有一点成功的话,那便是我终于接近了《小鲍庄》故事本来的形成构造和讲述方式。我对自己最大的妄想,便是与一切故事建立一种默契,自然而然的,凭着本性的觉察到每一个故事与生俱来的存在形式[7]”。《小鲍庄 》是王安忆一九八四年出访美国归来之后在思想感情、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等方面都经历了极大的冲击和变化之后写成的作品,此作品对她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也就是从《小鲍庄》开始,王安忆就开始了她对小说叙事“逻辑性情节”的关注。
二、“小说构成性故事”[8]
王安忆曾写了《故事不是什么》和《故事是什么》两篇专论。文章的基本观点她概括为一句话:经验性传说性故事和小说构成性故事是两个范畴。理解起来,导致彼此间的区别的,是依附于因果性上的逻辑关系。故事由细节与情节两部分构成。情节即体现为因果关系的“故事链”,它对于故事建构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让它成为故事的焦点。因为这个通常以“故事梗概”为人熟悉的故事链,事实上已规定了故事的诗性空间,一个故事即是这个空间借助细节的具体落实。王安忆强调,不应当一味依靠经验、感觉来写小说,不能依靠借用现成的现实故事的情节来写小说,而应当重视超越经验的、小说的创作规律和创作技巧,重视小说情节的逻辑关系来安排小说情节。在王安忆看来,小说内在的推动不再仅仅依靠故事情节而更多地有自我的内在逻辑力量。逻辑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思想内容的存在。她所追求的正是超越个人的经验和感情,进入绝对自由的创造状态,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冒险。以极为有限的材料作出精心的设计和加工,不是凭借故事本身的完整、独特和丰富,甚至也不依赖作家的风格化,而把力量运用到叙述方式上去,依靠内在的逻辑力量,来补充个人经验积累和认识上的偏颇,从而突破个人性的限制。她曾说过:“物质部分落实到小说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便是叙述方式的面貌。所以,我常常想的是:我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叙述方式。而我以为最高的境界,应当是思想与物质的再次一元化,就是说,故事降生,便只有一种讲述的方式[9]”。王安忆将小说的叙述方式放在与小说的思想一样的高度,为每一个内容寻找最适合它的那个唯一的叙述方式,从而更好地体现小说的主题。这些理论主张近乎苛刻,不无偏颇。评论界对此也议论纷纷。但王安忆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却是沿着她深入思考过的方向卓有成效地前行。“雯雯系列”是王安忆小说的初创阶段,这个时期的小说中流露出的少女情怀,稚嫩而不失天真清纯。几乎代表和象征了王安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轨迹,而这一时期则被称为作家的“青春自叙传”时期。这个时期王安忆还没有确立属于自己的小说观,所以这个时期的创作表现出对于真实世界和个人经验过分的依赖,循规蹈矩于传统的小说观念。《纪实和虚构》、《伤心太平洋》真正可以称为王安忆对“逻辑性情节”观点探讨的力作。在《纪实与虚构》中,文中的“我”是坐着痰孟进上海的,给人的感觉有点类似曾祖父坐着孤舟飘流到海岛上。“我家”是从外面飘来的“外来户”,因而“我”从童年起就深深地陷入孤独之中。孤独和漂浮是互为因果的,而症结在于无根,所以才孤独才漂浮。小说中,“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去寻找家庭的根,与其说是为了摆脱孤独,不如说是为了摆脱漂浮。“我”苦苦寻找的结果,发现家族祖先也是同样经受着这种漂浮的命运,最后仍然获得了一个漂浮感。因此,漂浮是永恒的命运。从小说的表面看,《伤心太平洋》确实是纪实的,“我”就是王安忆,父亲是王 XX,曾祖父开创了我家的出洋史,同乡王木根说他还保留一本福建同安王氏家谱;母亲是茹 XX,她是个浪子的女儿,集孤儿与被抛弃于一身,解放后以“同志”身份重返上海,等等,都说得有根有据,无庸置疑。那些寻根究底地追溯的家族历史,或有真名实姓,或有亲属称谓,或据之于史籍记载,或亲身实地寻访,也言之凿凿,到于虚拟的地方则直言不讳地表明“我想”、“我猜想”、“我设想”等字眼。所有这些,与自传体小说几乎毫无二致。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把它当作自传体纪实小说,那又大错了,因为这一切确实是虚构的。所以,纪实与虚构的对立统一,是这本小说的特别之处。它貌似描述逼真,背景确实,时空具体,但所表现的实质上并不是一个可视的行动世界,而是一个不可视的内心世界。二者靠一种逻辑力量来推动小说的发展,使小说呈现一种实者似实而虚、虚者似虚而实的景观。此时特殊环境、特殊人物、独特性和语言的风格化等传统小说的写法都被普遍性大大减弱了。小说中的情节设置并不强调与现实对应,而努力突出情节之间的逻辑关系,强调情节的虚构意味。王安忆是怎样看待小说中的“虚构”的呢?在 1993年与台湾作家的对话中,她说:“我强调纪实,因为我采用的材料是真的,并且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我强调虚构,因为它是创造性的东西,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着这样的世界[10]”。而这篇对话录就被冠以“我做作家,是要获得虚构的权力”这样的标题。她还曾经说:“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是以虚构为职责。现实的材料放在面前,总是要以虚构的眼光去挑剔,挑上的用于小说了,挑剩的便闲置起来[11]”。由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之强调虚构,是就小说的创造性这个层面来说的,并不是指材料是来自真实还是虚构。她认为小说从本质上来说,是作家所创造的,是虚构和想象的。因此,她所说的虚构,是指小说的性质是虚构的。马原也在《阅读大师》中专门有一节谈小说的虚构问题,他认为:“对于小说家来说,所有的真实都是以片段的方式进入内心,……,一样的真实被作家们吸纳以后,作家们把它咬碎,将它重新组合。我想这可能类似化学反应,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反应生成新的东西,它跟原来的东西已经是完全两样了[12]”。马原虽然没有直接说出虚构和想象的作用,但从中可以读出他对它们的重视。所以说,王安忆的小说虽不具有传统小说故事情节的传奇性、亲近感,却摒除了情节设置的偶然性、随机性,使人物命运的设置与描写具有逻辑色彩,在必然性的构想中流露出宿命的意味。
正如有研究者所说,王安忆的《故事与讲故事》与同期的先锋文学观相比确实有一定的超前意识。在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中,故事的地位的确是很重要的,抛却故事,也就必然会失去读者。在当今现代社会,商品化日益猖獗,文学欲在现实社会中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而不被社会大众所忽略,在不违背文学的主体位置的前提下运用一些故事形式是完全有必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故事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当然,好故事必须说得有情有理,写作不一定完全遵照现实的逻辑,但情理的逻辑,却是不可违反的。情和理通过一种因果关系的内在逻辑把那些细节和经验聚拢在一起。违反了情理,留下了逻辑上的漏洞,小说的真实性和可读性就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王安忆的“故事”观是对传统小说观念的延伸,是对小说叙事理论的积极探索。她在讲述一个又一个故事的过程中实践自己的“故事”理念。其中关于小说创作中“逻辑性情节”问题的论述,对整个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当下的作家在具体创作中应该努力强化一种创造的意识,借用逻辑的力量,来弥补源于现实的经验材料的缺陷与不足,从而使小说创作获得新的写作源泉,得以繁荣和不断发展。
[1]王安忆 .漂泊的语言 [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335.
[2][英]福斯特 .小说面面观 [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23.
[3]王安忆 .心灵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2.
[4]王安忆 .心灵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274.
[5]谢有顺 .通往小说的途中 [J].当代作家评论,2001,(3):33.
[6]王安忆 .漂泊的语言 [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335.
[7]周新民,王安忆 .好的故事本身就是好的形式 [J].小说评论 ,2003,﹙ 3﹚ :34.
[8]王安忆 .漂泊的语言 [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345.
[9]王安忆 .漂泊的语言 [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342.
[10]王安忆 .重见象牙塔 [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74.
[11]王安忆 .重见象牙塔 [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
[12]马原 .阅读大师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324.
I206.7 < class="emphasis_bold">[文章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5136(2010)01-0133-03
2010-01-25
胡彩霞 (1978-),女,湖南娄底人,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助教、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