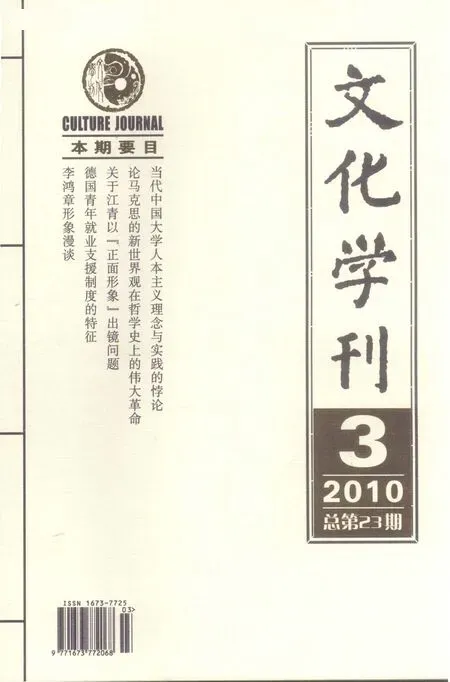从展示官场生态到揭示官员心态
2010-03-21苏楷越
苏楷越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学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着力描写当代中国社会官场现状、展示官场复杂险恶、记录官员命运沉浮的“官场小说”应运而生。特别是当湖南作家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推出后,一批“官场小说”更是接踵而至。从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系列到丁邦文的《中国式秘书》,从李国征的《后备干部》到吴国恩的《文化局长》、《宣传部长》等,令人目不暇接。近十年来,“官场小说”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据有关机构统计数字显示,仅2009年1至3月出版的“官场小说”就多达123种。十多年间,“官场小说”之所以畅销不衰,自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空间。在这十多年里,作为一幅幅当代中国社会官场“清明上河图”式的生态长卷,“官场文学”走过了一条从人物设置简单苍白、故事情节程式化到对官场生态和官员心态进行深入透彻解析、充分揭示官员复杂内心世界这一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历程。在从步入“类型化”到走出“类型化”的过程中,“官场小说”的读者也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的窥视欲满足“官场教科书秘笈”,到看到更多揭示官员复杂情感天地、细腻展现世间官场日常生态的阶段,这不仅仅只是分享作品中艰难式的教化和启蒙、腐败官员与反腐力量的较量,更是一次阅读境界上的超越。这一切都需要涉猎官场题材的作家不能陷入“类型化”创作的模式,而应进一步地拓展思路。正如作家吴国恩在创作《文化局长》和《宣传部长》时感言:“文学应该是放射状的,官场作为一种存在,成为文学描写的一个对象。我不过是借助官场这个壳,而它的核,却是文学所共同关心的东西,人性的存在及其变异。”只有在创作时具有这种认识,才能使作品有所突破。
一、走出“类型化”的模式
近年来,随着“官场小说”的热涌,“官场小说”逐渐走向“类型化”,逐步呈现出文字浅显易读、编撰情节共性、故事离奇、戏剧性强、人物性格单薄、人性探索功能乏力、社会批评功能退化等特征,致使“官场小说”中的官场原生态展示特性加强,文学审美愉悦作用削弱。有人说,小说创作的“类型化”是普通人阅读趣味的胜利,也是文学大众化的胜利。但在“官场小说”日趋“类型化”的过程中,“类型化”对“官场文学”只起到了简单摹写现实但又不能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的作用。于是,一批以“类型化”的面目匆匆出现的“官场小说”,只能在故事浅显、人物单一、一味追求情节热闹的模式中徘徊,以此满足那些对官场充满窥视欲者的猎奇心态。在功利目的鲜明的营销手段推动下,不少“官场小说”还被一些网站的读书频道分为“入仕必读书”、“晋升必读书”、“守位必读书”等。这样的“官场小说”分类法,自然也会使一些作家在创作时弱化文学审美功能和批判精神,过度沉浸于官场权利旋涡、人性险恶、黑幕交易的情节编织事件中不能自拔。文学批评家杨剑龙认为,中国“官场小说”乏善可陈,陈旧的全知叙事者视角,凶杀与情色元素,行文间缺乏多义性,满足于“批量复制揭秘”,同样的东西让人看多了必定起腻。面对在“类型化”过程中“书名双胞胎、内容克隆没商量、重复雷同之作比比皆是”的“官场小说”,这些作品似乎都相当于工业化大生产中固定型号、标码的零件,只要按其型号组装完成,就可顺利下线出厂上市。
这些“类型化”的“官场小说”也许会表层刺激读者的感官,但绝不会在深层触动他们的灵魂,激活他们的情感。由于受图书市场营销的“类型化”左右,对“官场小说”的写作者来说,首先是在落笔之前就有了一个类型的清晰界定,人物命运、故事情节等都在依照“类型化”的生产模式,在流水线上组装完成。也许在一些批评家看来,“官场小说”只是销售过程中的一种分类方式。但正是由于这种“类型化”的分类方式,在作家心中过于强化,使他们只注重展示官场生态图,为了满足人们对官场文化特有的猎奇心,甚至还不停地往官场这锅汤里添加各类暴力、色情、秘闻野史等诸种畅销流行元素。在这种以“类型化”模式批量生产出的“官场小说”里,无论是《领导司机》、《市长司机》、《谁坐在市长前面》、《中国式秘书》、《市长秘书》、《秘书长》,还是《国税局长》、《质监局长》、《反贪局长》、《挂职》等大量“官场小说”,往往只停留在揭秘式的事件陈列过程上,并未着力从文学角度去塑造人物形象,并未以批判的精神审视“官场文化”这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存下来的怪胎、深入解析官场中人性的扭曲变态。这样,在一大批“类型化”的“官场小说”中自然也就很少出现诸如王跃文的《苍黄》、《梅次故事》、《国画》,吴国恩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等突破“类型化”模式束缚,真正对官场政治生态、官员心灵世界充满人性关怀,对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给予深入透彻解读、真实生动再现的优秀“官场小说”佳作。《苍黄》等作品再一次告诉我们,在“官场小说”的创作中,不能只停留于初级“类型化”阶段止步不前,而要加大人物塑造和立意开掘方面的力度和广度,而要呈现人物性格发展演变历程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些又是在“类型化”模式内所无法完成的。因此,走出“类型化”模式这一误区,对于打破“官场小说”创作僵局,将会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二、探究“官场文化”中的人情人性
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官场文化”,自有其不成文但又被广泛认同的特征,也就是《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的作者吴思所归纳的“潜规则”,“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也正是这些“官场小说”中隐性的规则,使得官场中人们的心灵产生了某种变异。穿过贪官与“清官”、腐败与“反腐”较量的长廊,独辟蹊径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官员矛盾、焦虑的内心世界,揭示那种生存逻辑和生活氛围对人性的扭曲、情感的裹挟,并由此展现这些在宦海沉浮的官员与社会环境、体制结构间的激烈冲突,以及个人命运中的种种无奈,才是“官场小说”所应探究的终极目标。《驻京办主任》、《公务员笔记》的作者王晓方就曾讲过,“小说家的任务不是讲故事,更不是模仿生活,而是表现人的本质,揭示人性中最隐秘的东西。小说家必须有潜入裂开的无比深渊去一探究竟的勇气”。因此,“官场小说”作家要充分显现其独有的洞察世事与人情练达,通过对官场日常生态细致入微的描绘、对内在逻辑的诠释,进一步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官员形象树立起来。遗憾的是,在泥沙俱下、芜杂不堪的“官场小说”领域,这样的作品难觅其踪。
官场并不仅是官僚腐败、权钱交易、势力角逐的场所,在表面风平浪静、内心深处暗藏玄机的神秘领域里,官员们也有许多的无奈。而这正是“官场小说”应有的闪光点。王跃文在其新著《苍黄》中塑造的主人公既不是大义凛然的领导干部,也不是一脑门子官司的平头百姓,他就是一个在官场狭缝中顽强生存的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既是官又是民,既有民身上的寻常情感,又有官身上的规矩。于是,正义与邪恶、良知与贪婪都在这个在无奈、尴尬环境中生存的李济运身上交织。不合理与非做不可的事情反复地拷问着他的人性,探究着他的官德。一般的“官场小说”都在延续过去柯云路的《新星》、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书记》等“改革文学”、“反腐文学”的模式,即地方黑恶势力欺压百姓,腐败官员是他们的保护伞,老百姓最后终于找到一个说理的清官,讨回应有的公道。而在《苍黄》里,王跃文却告诉我们,官员同样也是受害者,官员也有优秀的,也有一般的。而迫害他的却是更大的官员。当迫害他们的官员倒了,他们却依然没有翻身。在王跃文的另一部“官场小说”《梅次故事》里依旧没有宏大的叙事、波澜壮阔的场景、惊天动地的冲突,有的只是些琐碎庸常的官场小事,一个个八面玲珑、在复杂的官场中游刃有余的官员。他们只是在遵循官场潜规则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当作家将这种纷繁复杂的官场潜规则,以及行走其间的官员们的游戏、内心深入的情感冲突淋漓尽致地再现时,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官场中人也就跃然纸上。王跃文在其创作谈中提及:“这部小说起名《苍黄》,原意是用《墨子·所染》里的典故。墨子见素丝入了染房,遍染五色,变化反复,面目全非,黯然神伤。‘墨子泣丝’也许并非多愁善感,而是由此感叹世事无常。苍黄还有一义,即带有青的黄色,就是青黄。既不是明快炽烈,也不是灰暗阴冷,而是一种中间色。”作家在《苍黄》、《梅次故事》、《国画》等作品中竭力追求的正是这种“浑浊感”。在他的心目中,官场只是他为其人物搭建的一个平台。这里的大小官人首先是一个人,他们有着常人一样的人性、人情、人欲。这样,作品描写的自然是谙熟官场潜规则,适应官场生态圈、生存环境的一群官员游戏,而不是从一开始就从“类型化”的角度设置人物、矛盾冲突。
近年来,一些成功的“官场小说”代表作往往都是从开始创作时就走出“类型化”这一严重制约“官场小说”的发展模式,打破“类型化”大批量生产的统一结构,在氛围营造和人物刻画上都力求多面性、复杂性和立体感,既有情节上的冲击,更有心灵上的碰撞,令人跟随主人公在一次次无形的博弈后,陷入无限的沉思。由此可见,时常被等同于“恶俗”、“庸俗”的“官场小说”,是能够在其通俗的结构里彰显作家的责任与良知,将可读性与耐读性有机地融为一体,把流行畅销元素与文化反思巧妙地统一起来的。让作品中的主人公既说人话,干人事;又思人虑,发人情。正如《后备干部》的作者李国征所说的那样:“文学的功能之一是引导、教育和启迪读者,跟随作品从更深层次、更大宽度、更高领域去认识人类自身,认识世界,而不是简单地靠暴露社会阴暗面来误导读者,或者靠展览原生态的官场丑恶现象来博得廉价的喝彩。”创作出《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的吴国恩,之所以能将“官场小说”写得让人心灵震撼,写出一个文化局长官场日常生活的同时,更让我们看到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局长文化”,同样也是因为他在创作时就认为“官场小说”这种分类其实毫无意义。由于这种认知上的升华,才使得他和王跃文等作家一样,真正将自己笔下的官场当成人间画卷,把官员当凡人来写。这也就是评论家潘凯雄在谈及《宣传部长》时说的,“这部作品和流行的官场小说之间的明显区别,那就是多了一番民间情感和真诚”。这“一番民间情感和真诚”,也正是这些年来图书畅销市场上持续升温的“类型化”“官场小说”“所真正缺失”的。在这些批量复制的作品中,往往是有了《领导司机》就有《市长司机》,有了《市长秘书》就有《秘书长》,有了《国税局长》就有《质监局长》、《工商局长》,无论是人物、情节、细节都是可以大量克隆,每个人物的心态、个性、情感历程的独特性历程显然无从谈起。至于说那种让广大读者心灵颤栗的真诚撞击就更让人无法企及。因此,面对“官场小说”这种非理性的热销,特别是当它作为一些人的“求职指南”、“晋升宝典”而出现时,以文学形式出现的“官场小说”,就需要在创作时严防作家心中艺术标准的随意跌落,大力拓展和深入开掘其作品的思想精神空间。防止在人为展示官场原生态现象时,使人物的人性空间极大地萎缩。在过度强调时尚好看时,使其人物灵魂不断矮化。因为对于一部优秀的“官场小说”而言,“可读性”、“好看”和“人性”、“深刻”之间并不存在尖锐的冲突,选择“通俗”也不意味着就要放弃“深度”。官场刺激和心灵震撼同样会在一个官场上发生。从官场入手,但又超越官场去更深入地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与反思,这才是当今“官场小说”亟待提高的方向所在。
当今畅销不衰的“官场小说”,脱胎于20世纪90年代的“反腐小说”。在《人间正道》、《省委书记》、《天网》、《国家干部》等“反腐小说”的代表作里出现的,一般都是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中领军人物与保守势力、腐败分子之间的生死较量。作家尽管也是表现官场,但主要还是展示正义与邪恶的交锋,催人奋进之时也引人深思。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般都不食人间烟火,让广大读者无法找到“身边人”的感觉。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更渴望看到一些贴近现实生活,切实反映官场生态、官员种种生活状态的文学作品。于是,一批以展示官场生态圈、带有一定揭秘性的“官场小说”就出现了。
当王跃文的《国画》面世后,读者对这一类型的小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值。但这十年来“官场小说”的持续热销,并不能代表其思想和文学价值的升值。尤其是近年来,在诸多市场营销手段的推动下,许多“官场小说”作者一味迎合一些读者窥视官场隐私、寻找为官“宝典”的心态,大量复制出一批交织着明争暗斗、尔虞我诈、情色暴力、黑恶势力、秘闻野史等各类流行元素的“类型化”“官场小说”。这不仅无助于人们对官场这一社会日常生存环境的认识,而且还导致广大读者对这个看似神奇的世界产生种种曲解和误读。
从昔日强化远离人间冷暖、只注重宏大叙事的“反腐文学”,到后来任自然主义泛滥、陷入重重“类型化”模式的套路,“官场小说”走过了一条从疏远淡漠读者到过分迎合读者的道路。近年来,随着广大读者和批评界对“官场小说”关注和研析的加深,这一领域的作家也开始反思自己的创作,并涌现出像王跃文的《苍黄》,吴国恩的《宣传部长》、《文化局长》等一批“官场小说”力作。这些作品走出了过去简单陈列官场原生态、随意堆砌官员众生相的初级阶段,开始真正步入生活于官场这个神秘而又特殊环境中的人之心灵世界。这里不仅有浓郁的人情,也有扭曲的人性,令人在激烈的冲突中感受人性的挣扎与无奈,在真实鲜活的故事里体味生命力的勃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