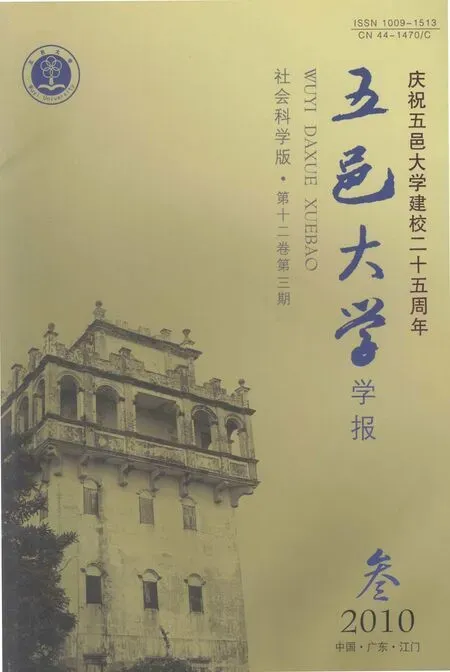“大众”的谱系
——“大众”一词语义变迁的考察
2010-03-21杨建国
杨建国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大众”的谱系
——“大众”一词语义变迁的考察
杨建国
(五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大众”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19世纪“大众社会”的兴起赋予该词政治、社会、心理三方面语义;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在整合原有三个语义场的同时,赋予该词一项新语义——文化精英关照自身的镜像;后现代消费社会中,精英和大众融为一体,“大众”又成为构建现实的拟像。
大众;文化批判;后现代;拟像
一、“大众社会”与“大众”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西方社会日益呈现出“大众化”的特征,“大众社会”理论成为资产阶级权力话语中的高频用语。“大众”一词有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三重语义。
“大众社会”理论和“大众”一词从一开始就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含义。19世纪“大众社会”理论的主要推动者路易·德·波纳尔德(Louis de Bonald)和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都是保守主义者,“大众社会”理论在他们那里表现为显性的政治斗争理论。“大众”被推到社会权力斗争的前台,同“政治煽动家”和旧社会秩序的代表构成社会力量的三极。旧社会秩序的代表
——君主、王室、贵族、教会,维持着社会的有序运行。随着“大众”的出现,冒出一批“政治煽动家”,这些人利用“大众”的愚昧和无知,挑动“大众”对抗统治者,导致社会的骚乱、信仰的迷失甚至文明的毁灭。对于保守主义的理论家来说,“大众社会”的出现已令社会滑到崩溃边缘,唯一出路在于“大众”的顺从与沉默,俯首贴耳地把权力呈献给旧社会秩序的代表。
“大众社会”理论引发了更多的学者对“大众”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 onnies)在他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对“大众”现象进行解读,赋予“大众”一词以社会学语义。滕尼斯对“共同体”和“社会”的定义是:“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1]52滕尼斯所说的“共同体”指家庭、庄园、教会等,其最复杂的形态是城镇,而他所说的“社会”则特指大城市,即“大众社会”。从“共同体”到“社会”的变迁不仅意味着地理位置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传统纽带的断裂。“共同体”是有机的整体,体现了真正的共同生活;“社会”成员彼此相邻却不发生联系,犹如沙滩上的沙子,数量巨大却始终是松散的颗粒,难以建起持久的建筑。能将“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因素只有一个
——利益,滕尼斯把“大众”的这种生存状态形容为“战争”。[1]330
传统纽带的断裂使“大众”一词不仅指向数量巨大这一物理事实,更指向个性丧失这一心理现象,“大众”一词又被赋予心理学语义。格奥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大城市与精神生活》一文中深入探究了大城市生活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影响。大城市精神生活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差异性的流失,原因在于货币经济的统治和随之泛滥的理性主义倾向:“大城市向来就是货币经济的中心……货币所关心的只是现象的共同问题,只是将全部质量和品质跟价值多少加以平衡的交换关系。”[2]261差异性的流失更表现为同质性对差异性的漠视和排斥。齐美尔把这种大城市特有的精神现象称为“大城市的傲慢”,其本质是“对事物差异性的冷漠,不是说迟钝得察觉不出事物的差异,而是认为事物的差异的意义和价值是微不足道的”[2]265。齐美尔的论述使“大众”的语义由物化的社会层面(人群的大量聚集)转移到质化的心理层面(“大众性”)上来。
二、文化工业批判中的“大众”
“大众”一词的广泛传播要归因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马克思·霍克海墨(Max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用一整章篇幅展开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对“文化工业”这个词,阿多诺晚年解释,即通常所说的“大众文化”。[3]法兰克福学派所界定的“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是资产阶级自上而下强加于“大众”的文化,是按照标准化原则生产出来的文化消费品。“文化工业”不能容忍任何异类的存在,对个性实行了空前的“清洗”。然而,个性幻像对于“文化工业”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标准化和风格化是“文化工业”中相互牵制的两个因素。阿多诺在论及流行音乐时深入探讨了流行音乐中标准化、风格化和伪个性化之间的联系。在阿多诺看来,流行音乐的本质就是标准化,所有流行音乐的创作者都会遵循一套不易的规则,如合唱部不超过32小节,音程限制在一个八度之内,使用单一调性等。[4]然而,创作者又总会添加一些与音乐的整体形式并无关联的“个性细节”,其繁复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严肃音乐,标准化被掩藏在风格化的外表之下。流行音乐的听众总是把注意力放到那些“个性细节”上,沉醉于伪个性化的幻像中,而音乐的标准化整体形式却超然其外,从不被留意。风格、个性、自由选择,这些“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幻想把听众牢牢地控制在流行音乐的标准化整体框架中,也把他们牢牢控制在资本主义总体性社会框架中。
“文化工业”批判所设定的“大众”概念将“大众”原已具有的三个层面上的语义整合在一起。心理学层面上,生活扁平化、人性单向度;社会学层面上,工业分工将“大众”囚禁在分散孤立的岗位上,“大众”既体验不到完整劳动成果带来的成就和喜悦,也感受不到劳动中实现的个体认同和归属感;而在心理学和社会学层面之上起统辖作用的是“大众”的政治学语义:“文化工业”批判始终立足于资本主义总体性批判之上,其目的是要揭示资产阶级利用“文化工业”控制“大众”、实现极权统治的机制,揭开他们制造的虚假个性的画皮,让“大众”在震惊和痛苦之后孕育反抗的潜能。
除此之外,“文化工业”批判又给“大众”一词增加了一项新的语义——文化精英观照自身的镜像。阿多诺认为,艺术的基本功能就是反抗。而对法兰克福学派而言,反抗主要存在于艺术和审美领域,具体讲就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之中。在“文化工业”洪流肆虐泛滥、极权统治大幕徐徐降落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写实艺术已丧失了批判和反抗的功能,这一功能只能由卡夫卡、乔伊斯、贝克特、勋伯格所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来承担。“激进的现代主义之所以保留着艺术的固有禀性,就因为它让社会进入了自己的境遇,但只是借用一种隐蔽的方式,就好像一场梦。倘若艺术拒绝这样做,那它就会走向灭亡。”[5]在阿多诺的美学理论中,可以发现一系列对位:写实与变形、整一与碎片、标准化的同质与交流的拒绝、虚幻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幻等等。前者被统统赋予“文化工业”和它的消费者——“大众”,而在“大众”的负极,文化精英们显影出自己的图像。
三、英美文化批判传统中的“大众”
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相平行,英美理论界在20世纪也活跃着一支文化批判话语,其对“大众”一词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相近的使用,即在整合原先语义的基础上,建立起“大众”作为文化精英镜像的新语义。然而,不同的政治取向使“大众”一词在英美文化批判中呈现出许多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特征。
英美文化批判传统可上溯到19世纪中期,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给文化下了一个理想主义的定义:“文化即对完美的追求。”[6]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人物利维斯(F.R.Leavis)接受了阿诺德对文化的理想主义定义,并将文化理想态的对立面——文化的现实态称为“文明”。利维斯认为,文化和文明不仅区分了理想和现实,同时也对人群作出区分:前者属于少数精英,后者则属于“大众”。在这样的架构上,他完成了他的“大众文明和少数人文化”。
利维斯的“大众”一词同样呈现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三个层面的语义,但具体内涵与法兰克福学派有明显区别。心理学层面上,法兰克福学派强调“大众”个性的丧失与对文化支配权的认可,利维斯则强调“大众”趣味的低俗,及对传统尤其是英国文学传统的漠视;社会学层面上,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现代工业分工所造成的“单子效应”,利维斯则强调城市生活与传统有机社团的断裂;政治层面上,法兰克福学派强调“大众”对文化权力的认同,利维斯则强调“大众”对旧文化权力的反叛。不同的政治取向决定了“大众”一词的不同旨归:利维斯试图把“大众”引回到过去,回到那个社会秩序井井有条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时代;法兰克福学派则尝试把“大众”推向未来,一个“大众”自觉反抗资本主义总体性控制直至颠覆压抑性权力关系的全新世纪。
有趣的是,二者在整合“大众”一词后却赋予其相似的功能:以“大众”为文化精英观照自身的镜像。当然,利维斯心目中的文化精英完全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利维斯而言,文化精英就是能欣赏但丁、莎士比亚、邓恩、波多莱尔这样的传统经典作家的少数人,因为“在这少数人身上承载着我们从最卓越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的能力,他们令传统中最精微,也最易逝的部分得以存续”[7]。不同的精英路线却采取了相同的“大众”策略:先抹平“大众”一词中的一切差异,令“大众”成为一个完全同质化的整体,然后再把所有令人坐立不安的特征投身到这个整体上。然而,精英路线的致命弱点也正在于此:“大众”成了一个“空集”,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它来建构起自身的形象,包括“大众”自己。善于捕捉社会心理的“文化工业”绝不会放过这样的契机,“大众性”成为“文化工业”拓展新市场的逆向心理动因。精英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选择不可避免地被吸纳入“文化工业”中,被整编入他们所反抗的权力结构中。精英试图以“大众”建构自身,却走向自身的解构。
四、“后现代”语境中的“大众”
“大众”与“精英”间泾渭分明的区隔是“大众社会”的理论基石,而随着二者的合流与交融,“精英”退隐,“大众社会”也被时代所超越,“大众”不再是“精英”观照自身的镜像,它成为构建真实的“拟像”。
“拟像”是法国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概念。鲍德里亚认为,在一个“文化工业”的触角无所不在、从媒体到各种文化产品直至语言符号都已被权力牢牢控制的时代,人们已不可能再得到任何真实的影像,那怕是变形、虚假的影像。现时代的人们日日面对的是“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拟像”,是工业手段复制出来的备份,真实本身“是由模拟单元、数据矩阵、记忆库和指令模块制造出来的,有了这些手段,真实就可以被无限次复制”[8]。
在鲍德里亚极富科学幻想和哲学玄思的理论背后,是一幅真实的社会景象:“精英”和“大众”融合为一体,也可以说前者被后者吞并。“大众”这个词总是和虚幻、假象联系在一起,而真实、本质则是“精英”的专利。随着西方社会由“大众时代”进入“消费时代”,原有的“精英”与“大众”、“高雅”与“低俗”之间的分界不再有效,消费由实物形态的商品消费转向由欲望的无意识逻辑所支配的“符号消费”,资本主义经济也由商品经济体系转向符号经济体系。商品被编制成从高向低有序排列的体系,以全系列的整体出现在消费者面前,商品在物之序列中的位置成为消费者在人之序列中位置的的参照点,商品成为符号。商品序列形成的差异性符号体系将每一个社会成员编入其中,产生出一切话语的意义,而推动这一体系运转的原动力则是无意识的欲望。趣味、品质、深度、思想、传统这些用来区分“精英”与“大众”的标准在欲望的无意识逻辑中纷纷解体。
“精英”与“大众”、真实与虚幻、本质与假象的融合,也正是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杰姆逊总结出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特征,包括“拼凑”创作法大行其道、历史视野的退隐、精神分裂式的语言效果、歇斯底里式的崇高,以及批判距离的消失。[9]16-45导致这些特征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主体之死”,“文化病态的全面转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主体的异化已经由主体的瓦解所取代”。[9]14当然,分裂和瓦解只是针对“精英”主体而言,作为“精英”观照自身镜像的“大众”从来就没有被赋予主体性。主体的瓦解使现代主义式的“讽刺”蜕变成后现代主义式的“拼凑”,对真实的“模仿”成为构建真实的“拟像”。或许,杰姆逊心目中“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代言人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艺术家、时尚设计师。
五、中国语境中的“大众”
“大众”为谁?“大众”何在?对这些问题的追问最后竟把我们带到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答案面前:“大众”从来就没有实体性存在,“大众”是个飘浮在各种理论话语中的幽灵,是一个巨大的魅影。自“大众”一词出现以来,其语义的最基本要素是“同质”和“顺从”,无论它所顺从的是权欲熏心的“政治煽动家”,或是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或是无意识欲望驱动的差异性社会结构。权力果真实现了彻底的控制吗?支配性的社会结构同被支配的生活间果真已不存在任何张力了吗?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做的是重新界定“大众”。
英国著名文化批判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在界定“文化”一词时引入人类学视角:文化可以是一种理想,可以是有记录的作品和活动,但文化绝不仅在上述两种意义上存在,还“存在着文化的‘社会’定义,在这个定义里,文化是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10]。文化不仅有“精英文化”和“文化工业”对立的两极,还包括了二者间种种特殊生活方式,以及以那些方式生活着的人群。“大众”的解体也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大众”从未真实存在,那么假想中的对支配性文化的一致反应还存在吗?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解构流行》一文中说:“我们总是倾向于把文化形式想象成完整的、连贯的,要么腐败透顶,要么纯粹本真,危险也恰恰由此而生。文化形式中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它们也摆弄着那些矛盾,尤其当它们在‘流行’领域中发挥功用时。”[11]矛盾来自于受众的反应,文化权力总是倾向于把所有受众吸纳入某种文化形式中,把他们整合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大众”。虽然大多数受众并不具备充足的资源公开抵抗文化权力的整合,只能被动接受提供给他们的文化形式,但这种接受并不意味着完全顺从,他们总会以自己的方式改造那些文化形式,令它变色、变味、走样。这正是米哈依·巴赫金所展现的拉伯雷的“狂欢”世界。
在中国,“大众”一词有着全然不同于西方的语境。《大众电影》、《大众摄影》、《大众医学》、《大众科技》、《大众日报》、《大众证券报》,从这些报刊的名称可以窥见国人对“大众”一词的偏爱。“大众”一词在西方倍受鞑伐,在中国却大受追捧,似乎倒转了西方“大众文化”的逻辑:在这里,“大众”才是文化风尚和审美趣味的真正主宰。然而,当面对“大众为谁”、“大众何在”这样的问题时,“大众”一词同样显得空洞和苍白。地理上的水平分布、年龄上的垂直排列,再加上方言、民族因素,令“大众”在不同的环境、语境中呈现出不同的面目。我们的文化绝非在今天才走向多元化,我们一向就生存在多元化的文化之中。在使用“大众”、“大众文化”这样的词汇时,我们有意无意间已抹平了他人生存的特殊性,以此来建立起自己生存方式的合法性和支配权。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情况都是如此,区别无非是把自己圈在“大众”之内,还是“大众”之外。
或许,只有摒弃“大众”这样的称呼,真正开始尊重那些被称为“大众”的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才能走出“文化工业”的“邪恶循环”之路。
[1]滕尼斯.共同体和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M].涯鸿,宇声,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3]ADORNO T.Culture Industry Reconsidered[M]// Culture and Society:Contemporary Debat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275.
[4]ADORNO T.Essays on Music[M].Berk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438.
[5]ADORNO T.Aesthetic Theory[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321-322.
[6]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M].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8.
[7]LEAVIS F R.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 [M]//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 New Y ork:Prentice Hall,2006:13.
[8]BAUDRILLARD J.Selected Writings[M].Stand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167.
[9]JAMESON F.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3.
[10]WILLIAMS R.The Long Revolution[M].Peterborough:Broadview,2001:57.
[11]HALL S.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M]//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New Y ork: Prentice Hall,2006:461.
[责任编辑 文 俊]
G0
:A
:1009-1513(2010)03-0048-04
2010-03-25
杨建国(1974—),江苏南京人,博士研究生,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文化理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