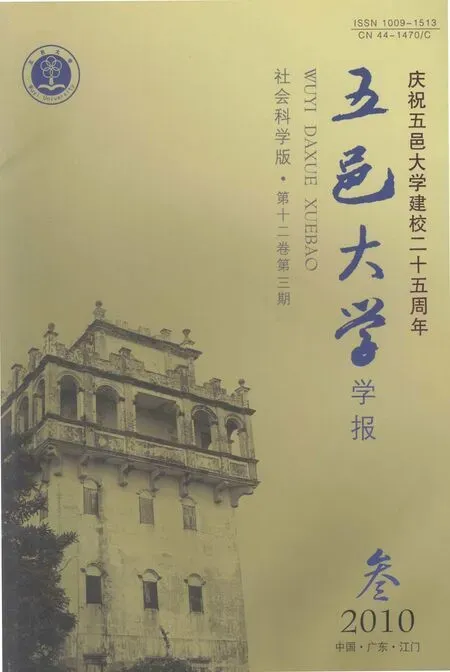《金山》:物象与历史重建
2010-03-21王则蒿
王则蒿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金山》:物象与历史重建
王则蒿
(五邑大学 文学院,广东 江门 529020)
物的形象(物象)的使用在文学本文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金山》通过碉楼及与其相关的物象,重建了华侨身份与侨乡史的叙事行为,展现出独特的叙事学、形象学意义,有助于海外华人对自身存在的反思与对家国观念的追索,以建构一种更加真诚的自我言说。
《金山》;物象;意义;嵌入;书写
……意义永远、处处穿越人和物体。[1]196
——罗兰·巴尔特
物,进入文学,是作为形象出现的,笔者称之为物的形象(即物象)。物永远具有意义,包括无意义的意义,而“意义永远是一种文化现象,一种文化产物,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文化现象不断被自然化,被言说恢复为自然,言语使我们相信物的一种纯及物的情境。我们以为自己处于一种由物体、功能、物体的完全控制等等现象所共同组成的实用世界中,但现实里我们也通过物体处于一种由意义、理由、借口所组成的世界中:功能产生了记号,但是这个记号又恢复为一种功能的戏剧化表现”[1]198。
文学,按从亚里士多德发展来的西方叙事理论,在于通过对一件有头有尾的事件的摹仿来再现世界。遍布于世的物,当然会以物象的形式遍布于“再现”之中。以“情感—表现论”为基底的东方诗学,建立在“比兴”的基础之上,而所谓比兴,正是通过可见的物的形象(兴象)来传递不可见的情感信息。历史书写更是离不开物的展示:人们通过考古发现堆栈历史的“物证”,以搭建“信史”,因为“物”比“人”更长久也更客观,“物证”自然也比“人证”更长久更可信。但是,人们常常有意或无意忽视掉的是,“意义永远、处处穿越人和物体”,有人类的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意义对于物件的利用。用于搭建历史的物证,说到底,也只是负载意义的物象。
文学写作展示正是“言语使我们相信物的纯及物情境”的过程。文学劫夺物的看似“物自体”的表象,将其呈现为能指,重新具备漂移性,组构“再现”或“表现”的世界。本文立意于分析碉楼及与其相关的物象在《金山》中的叙事学意义,从中找寻海外华人文学当代写作的形象学意义,而非小说本文的诗学品质。
一、童谣:女性目光下的物的亮相
《金山》以广东童谣开篇:“喜鹊喜,贺新年,阿爸金山去赚钱;赚得金银千万两,返来买房又买田。”它在正文中的“亮相”,是在第6章《金山缘》,亨得森太太去世之后,亨得森先生回家,听到锦河边给死者擦脸边哼唱的。
童谣的落脚点——意义实现点,在最后的物象上:房与田。田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农耕社群的经济命脉,房是生存赖以展开的基础和家族经济能力的标志,二者是中国宗法制社会千古不易的“恒产”。而碉楼,是“房”的具体形象,作为恒产及其文化意义的物象,是从形式到内容高度统一的用于“保护财产”与“看守财产”的建筑形象,而碉楼中的一切,都是恒产的组成部分,包括住在其中的女人。
女人有与物一致的功能性,即可使用性:用于繁殖后代、扩大产业(买房置地)、消费金钱以建树男性在乡里的地位与名声。女人又不同于一般的物,长了腿,有脑子,有欲望,会像六指一样在新婚之夜不合规范地小便,因在不该出门的时候出门而被土匪绑票(她爱“凑热闹”,忍不住要在野外方便,才给了绑匪以机会);还可能像锦绣一样,由于抛头露面,成为侵略者兽欲的牺牲品。她们必须比物更精心地封存:是以,此楼之名叫“得贤居”,贤是六指大名中的第三个字。
处在开放空间的“童谣”中的被述,没有女人,只有喜鹊、金山和阿爸,游移在盼望远人归家和催促劳力离家的意旨之间。金山与唱歌谣者既对立又合谋:它们既互相争夺又共同激励创造财富的男人。有被述就有叙述者,叙述者隐于歌唱的儿童之后。小说本文说,锦河是从母亲那里学来这首童谣的:母亲是叙事的隐形原创,她有一股俯视一切被述者与物象的目光。
童谣在中国文化中一向具有预言功能,近于卜辞:看似无所指而指涉一切。童谣原创乡村女秀才六指,碉楼“得贤居”兴衰系之于她,最终她死了,而碉楼成了无人居住的鬼宅。可以说,小说的核心情节就是她与碉楼在物的意义上同质化的过程:无人,是彻底的物化。小说本文就是要唤起这鬼宅的看似“物自体”一般的“历史”:使物化了的鬼魂还阳。
由此小说形成由《引子》、第8章之《金山故事》与《乡野传奇》以及《尾声》构成的均称布局,其节奏,一如童谣本身,四平八稳,徐缓悠长。小说的英文名字Gold Mountain Blues中, Blues(蓝调)源自黑人奴隶的艰苦生活,其突出特点就是节奏悠扬、徐缓,用于表达哀伤、忧郁的情绪。如果说蓝调是《金山》叙事的基调,那这哀歌的内部结构,则由两股目光构成“对位”。
第一股目光,来自女性社会学教授艾米·史密斯。在这条视线上,通向碉楼的路与碉楼一样残破而荒诞:不称职的方家后人、不会说广东方言的老年痴呆症患者方延龄用广东方言引领会中文的艾米,走上“清点”方家碉楼之路;另一股目光,来自当地的男性社会学教授、碉楼的研究者与保护者欧阳云安。
“当栗色头发棕色眼睛的艾米拨开喧嚷的人流,在那块写着‘方延龄女士’的牌子跟前站定时,接机的人吃了一惊,对看了一下,满眼都是问号,怎么来了个洋人?”[2]3从句突出的不是艾米作为方家后人的身份,而是她的“异”——她的长相。来者是当年歌谣作者和演绎者的后代,但她与碉楼及其背后的乡土格格不入。她的母亲要求她归入另一种文化,而她也成功归入。正是“异”,使她以挑衅而主动的姿态出现。欧阳云安显示出的,则是男性的乡土的宽容——他是方家几代人的启蒙者的后人,父性的启蒙(enlightenment,原义即“照亮”)在他身上,就是照亮缺失在记忆深处的“蒙尘的历史”。而缺失,是由于移民后代与原乡文化的隔断造成的。
但作为乡土传奇正牌解说人的本土男性对“蒙昧的历史”的“照亮”,一直没能脱离第一位出现在读者眼前的女性挑衅与质疑的目光,当然也无法摆脱那道自开篇就存在的俯视一切的鬼魂的目光,并随时被异质的女性目光扫描到的负载鬼魂言说的物的打扰,而这些物,则随着碉楼向女性目光的洞开,以物象的形式构成另一套编码系统——犹如童谣,它在“大历史”之下隐形书写,构成另一种历史。它们的编码者,居于男女两性之间、异域与乡土之间,给金山和碉楼的鬼魂敞开了还阳之路:介于本土与异域间的身份认同。
二、碉楼:物象与鬼魂丛生之地
当碉楼第一次在小说本文中高调亮相时,最打眼的就是它拼贴的任意性:“五层的水泥洋楼,楼的四面都贴了飞檐。窗极多,却极是细窄,又风化得走了形,便像是满墙炸开的炮弹孔。每一处门窗上都装了铁条……顶层的屋檐下立了一圈罗马式的小廊柱,柱身和窗框上都雕满了花纹……”[2]8这按男性、本土的社会学家解释,是受建筑设计者本人的知识结构、文化素质和欣赏水平所限。但对于有类似于叙事者身份的观光客,碉楼的意义肯定不止是美学的:“这些集碉堡和住宅为一体的特殊建筑群,是清末民初出洋捞生活的人们将一个一个铜墙铁壁板省出水来寄回家盖的,为了使他们留在乡里的女人和孩子们免受绑匪和洪涝之苦。”[2]3它是表征人对个体生存、家庭、社群、文化碰撞与交流的理解以及个体自我意识的符号,记录着百年中国历史与文化变迁,可用于重构乡野历史的“物象”:这任性的拼贴,展现的正是“乡土”与离散个体艰难的互证过程。
艾米·史密斯为清点方家“得贤居”而来,碉楼的意义自然要在“清点”完成之时显现:她要在这由她的太外公为其发妻建起的楼里完成自己的婚姻仪式,并且以它为基点完成家族碑铭——碉楼成了她身份认同的基点。
碉楼中的生活早已随着那几声不该响起的枪声终止,在变动不居的生活事件中保持着运动的义项也已经随之终止,留给前来“清点”与“交割”的人们,就如同一个沉默的文本——一座尘封的建筑和被时间淘洗后遗留给现在的附着物:
屋里的那几样旧物,只给窥探者显示了隐隐约约一个开头。像是一个貌似深邃的山洞,只探进去一个头,便跌入了无底的黑暗——是没有一点破绽的那种黑暗。这样的旧物,也许能挑起民俗学家的一点兴趣,可是艾米需要的,却不仅仅是这样的兴趣。艾米寻找的是历史。一句话。一片纸。一封可以把推测铁板钉钉地落到实处的信。一张可以把怀疑不容置疑地凝固为现实的照片。[2]117
人们总是能发现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发现确如艾米预期——历史随着信件的发现“落到了实处”。而那些原本不引起艾米兴趣的“旧物”,比她想要找的东西更富于言说的意味,从而使“信件”里的鬼魂“落到实处”。
引发和推动叙事灵感的物象,是铭刻记忆的符号,而记忆犹如鬼魂,如果没有这座仍然屹立于现实土地上的碉楼,这些物件就可能真正沦为孤魂野鬼,丧失叙事的能力。它们经由灵感触发才能“还阳”,而灵感就是反复出入于碉楼的艾米·史密斯的目光。
叙事是由她带动的。没有她的“归来”,就不存在叙事的必要,因此,物象出现的顺序和运动的节奏并不由“碉楼”本身决定,而由她的“触发”决定。随着她的急于离去的心情被尘封在碉楼中的“历史”的凝固状态所吸引,叙事也就从她与欧阳针锋相对的焦躁渐入舒缓:一杆烟枪缓慢地揭示方得法没能成为秀才而成了“金山伯”和“得贤居”建立的终极原因;只有当方得法娶到关淑贤这一事实被揭示之后,那些已经闪现过的物象——油漆剥落缺失的文字、颇显文字功力的对联和其他同类装饰物——才随着那柄载有六指手书的扇子释放出它们的光彩,得到细致地辨别、确认。
有的物象用于生活场景的“还原”,营造已死的生活的“真实感”,如脚踏车和由它引发的锦河的儿时记忆、反复出现的联结起金山与本土经济关系的金山箱、标识消费理念与财富积累的曼彻斯特银茶壶、被叫做“通天单”的美金做的墙纸等等;有的物象直接参与历史的搭建,因为它们是女主人公——叙事功能的主要承担者要找的东西,如旧唱片机和金山云的唱片、一双老旧不堪的千层底布鞋和鞋中塞着的布包里用毛笔小楷密密麻麻地写就的信,这些信是小说本文搭建起的历史的直接“物证”,其中的一封可与唱片与唱机互为解释;有的物象,却在可用于书写的物证历史之外闪现历史的另一副面目,如铺着床席的大床、绣着牡丹的对襟夹袄、夹袄中的丝袜,它们是叙事者目光所意欲“寻找”的东西。
另外,有些物象虽不来自碉楼,却是随着碉楼里的发现与历史时空的相互浸透被带出并参与讲述的,比如艾米展示给谢阿元看的从海外带回来的乡土的照片和保存在旧朱古力盒子中的碉楼里出生孩子的乳发。它们应被归于第二类:参与历史写作的“物证”。
那些最符合艾米预期的“物证”——“两地书”,使“得贤居”获得了叙事的合法性,也使“得贤居”里那些漂浮在空气中的鬼魂得以降落到地面上,得到还原并参与建构。因为它们不仅有物质载体,还负载着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言说”。
信件之所以藏在鞋里并置于楼梯凹陷处,显然与六指能做一手极佳的针线活(尤其是纳鞋底)有关。同时,这一收藏/呈现方式还与六指在新婚之夜用随手摸到的宣纸(本该用于书写的纸张)解决小便、随后将之揉成一团抛到隐蔽角落的秘史有关
—
—她有将“载有秘密”的纸张“塞藏”于隐秘处的“习惯”。
这是双重的“塞藏”。这里,笔者使用“塞藏”一词来呼应罗兰·巴尔特与福柯式语汇里的“嵌入”或“插入”。这一动作与用于嵌入的“鞋里”或“角落里”,都是对“书写”行为(对于没有掌握书写特权的女性而言,针线活和跟生殖活动紧密相关的排泄活动,也是书写的形式)的性意味的暗示。只是对于福柯和巴尔特,写作是纯然男性的行为。《金山》的叙事者却以一种近似荒诞的“塞藏”的方式,提示读者注意:书写或是男人的事业,而此本文以及它所收藏/呈现的记忆(鬼魂)的复活过程及其方式,都是女性书写的结果。否则,信件完全可以糊在墙里或者缝进棉衣里,而那双鞋也完全可以置于任何地方,它们能被其他人以同样偶然的方式发现,被付之一炬或者掉进河里被水淋湿以致无法解读。
同理,被发现的女性的衣服,不是厚实得不见女体的棉袄,而是曾经妖娆而新潮凸现女体的绣着牡丹的立领对襟夹袄,它也不用来“塞藏”可用于历史书写的信件,而是用于言说如同女体一样不可言说的秘史的“玻璃丝袜”。
三、充满言说和无言的“塞藏”
《金山》所“征用”的书写的物象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17个“信件本文”。其中比重最大的是方得法写给关淑贤的(8封),它们显然是鞋中的塞藏物;其次是关淑贤写给方得法(2封)及写给儿子们的(2封),它们可能来源自艾米的海外收藏;另一些信件是方得法与父母之间、锦河写给母亲以及为人代书的,它们应该出自于同一双鞋。方得法写给关淑贤的信件中,有一封分成两次出现,即最后一封家书,分别以在写作中及在解读中的信件形式出现,向六指阐明和确证唱片所表征的情感的移渡与归来的双重意义。此外,还有一封是锦山告知方得法死讯的信,没有以文本的形式出现,而是由墨斗转述。信件引用最多的章节是第4章《金山乱》(即它们被“发现”的那一章,共6封),其次是第6章《金山缘》(共4封),第1章《金山梦》、第3章《金山约》、第5章《金山迹》无信件,第2章《金山险》、第7章《金山阻》各2封,第8章《金山怨》3封。
作为“可信的家史”旁证的,是负载族群和世界性——公共场域和历史——话语的报刊资料(“洋番”的媒体、海外华人媒体及地方媒体),法律文书与契约之类的公共性本文,以及在叙事中直接引用的粤剧唱辞、歌曲、古诗文等文化本文。华工在异邦法庭上文书的离题的乡野式孤愤,少年经历与华埠骚乱的莫名叠映,邦国政要与小说人物的意外遭逢,艺术再现形式与现代化进程的相互渗透
……文件物象在多义含混的叙事空间里,创造出历史性、族群意识与厚度感的幻觉。
但是,即使以乡村女秀才之身嫁入金山伯之家的六指,也没有在小说本文中留下如男人一般多的“文件”,而历史叙事却由她塞藏。她部分地拥有叙事权(书写能力),叙事者却让她让渡了这个权利。与她相关的描述,除了“书写”(包括小部分“文件”、绘画与书法、教育子女等常规的言说活动),就是与身体直接相关的物象的呈示——床和夹袄,以及通过名号还原的消失了的那半截手指。
六指因那半载手指而与猫眼儿都有被书写直接贬为异物的生理基础:天生异相。她和猫眼儿还拥有沦为异物的文化基础——身份:六指因识文断字被目为“妇解分子”,而猫眼儿曾经为妓。这两个相异个体于是附在一组重叠的物象上显形——塞在对襟夹袄中的玻璃丝袜。
当艾米发现它们并将夹袄放在身上比划时,她看见镜子里的一对鬼魂式的黑眼睛,这是本文中真正“出鬼”的地方,仿佛鬼魂透过这物件凝视叙事的进行。它的主人,在艾米的想象中,是高挑丰满的六指,因为它们在艾米自己身上出奇地合体;它包裹的破了洞的丝袜的主人,却极有可能是猫眼儿——正是她在后文中演绎了丝袜的性文化。而它们,在空间上被塞藏于古老的衣橱中,离那张意义暧昧的床——六指塞藏不合时宜的排泄史以及完成“终身大事”的地方——最接近。
物在空间上将两个女人混合为无言的女体,这女体也包含了异域的桑丹斯、亨得森太太和她的养女,本土的麦氏、昌泰婶、锦绣、区氏、阿莲和介于本土与异域之间的总想把自己藏进某个洞中去的延龄。她曾经以为庄尼就是那个洞,这一想象对于物象“性征”的倒转方式(在男性写作中,用于嵌入的总是女体)具化了本文将历史写作“塞藏”进女性叙事的方式。
六指切割掉自己的六指,由此获得方家正室的特权,但六指的形象却如影随形,人们依然称她为“六指”或“六婆”。切割是六指生命的主题:切割腿肉,获得婆婆的让步;切割母子亲情,保存丈夫的思念;切割欲望,阻断与富于男性魅力的长工墨斗之间的欲望绮思。她一生都在与自己身上的多余之物——六指、个性、自我、文字、欲望、爱情
——做斗争,这与猫眼儿从性工具中挣扎而出、成为被使用于家庭的“良家妇女”的方法大同小异。
在不断自我抑制的过程中,她们与可书写的历史渐行渐远:六指在惊闻丈夫意欲携外室归乡的“喜讯”的同时得到他去世的噩耗,猫眼在伴随抑郁症默默发胖的中途死去。随着枪声,六指携带着所有女体及与这些女体关系密切的男性,沦为无言的鬼魂,附着在一件件物上。
从身体上切割下来最终变成“物”的六指,与本是“物”却成为女性身体一部分的玻璃丝袜相映成趣。这看似阻断实为召唤性欲的表征物,是现代化了的男性欲望对女性身体想象的嵌入,从物变成了女性身体的一部分,也是现代女性对欲望的合理认同、彰显自身存在和反抗性压抑的象征物。在用道德伦理拘禁身体和性欲的乡野中,这双丝袜曾是多么销魂,此时作为物象呈现在我们眼前,却是如此寒伧。它凝结着华族女性试图皈依又无所适从的身份认同的辛酸史,荒诞、滑稽、吊诡,看似完整而漏洞百出,一如被切割的第六指,个色、多余、悲壮。
破洞的玻璃丝袜和多余的手指将表面坚固的历史“物证”戳出了一个洞,漏洞之下是女性与漂移人群生存的吊诡,对历史书写的有意破坏与归化其中的企图的痛苦角力,形成整一性的、男性的、用书写搭建的、铁板一块的历史上残缺的、女性的、物象的背书。
对于男权世界,女性是异,是离散者;对于“大中华历史”,移民是异,是离散者。女性与移民,在此意义上同构:这些被迫漂零于正史之外的异类的身份,正是被切割却不能成功消失的自我意识和被抑制却暴露无遗的欲望的言说,是被“塞藏”在旧鞋里的书写与公开的文件无法深入的历史的真相。
四、金山:身份建构的第三度空间
由物象建构起来的“金山”,最终成为女性与移民同构的场域。移民的历史,是被塞藏于大历史之中的物的历史,正如女性的历史是被塞藏于人类历史中的物的历史。
《易经》中为山为艮卦,阳爻在上,由两组相同的各含三爻的符号重叠而成,而它们各含两个阴爻、一个阳爻。西方属金,也属阴。“金山”,纠结起两性的复杂关系。在现实的维度上,“金山”的现实化必须由女性体现,正因为她们,“金山”才具化为一片片广漠的稻田和一座座田园之上的碉楼。正文叙事之始,是麦氏以向一杆烟枪的妥协确保自己在一夜暴富的丈夫生命中的唯一合法性,造就家族第一代“金山伯”,由之而来的“得贤居”获得被讲述的特权(名正则言顺),则因与众不同的六指,而这一切若未经由女性后人身居“现实”的审视,也不会被真正嵌入这正面由男性书写、反面由女性背书的双重历史。
形象学意欲探讨异质形象在一种文化中生成的机制及其文化意义。《金山》的形象学意义,在于当它让一个异质的有缺损的女性的目光去修正一个乡土的整一的男性的目光时,具化为碉楼“得贤居”,它是为离散者回归乡土而建的意义丛生的异质空间。
作为对一个地域、一个族群想象性认同的家国观念的建构,不可能脱离参照物,正如离开镜子我们无法构造自己。在他者与我们的互映中,金山成为真正的可居住、可生发意义以及进行意义转换的场所。方家两代“金山伯”都在渴望与异域融合和坚持与乡土认同中将之转化为自我言说的部分,他们用自己的方言给异域更换名头,在亨得森夫妇、桑丹丝、排华分子、侵略者以及其他“非我族类”身上建构自我的现实存在,在与方家相对立并最终成为仇人的区家人、给方家人带去知识的欧阳家族和革命者身上建构自我的历史意义。在这多重镜像中,碉楼拼贴出他们有残损的尊严:方得法捐助维新变法者,方锦山偷父亲的钱捐助革命者,方锦河献出财产和生命在异域保家卫国。
“得贤居”沦为鬼屋,使移民身份建构史变成漂移的物象能指,叙事者又将这孤魂野鬼趋向解体的“意义”找补回来:方家的异域后人在碉楼这建筑在乡土上的“金山”上完成人生大事以及为家族立碑。立碑是对族谱的完成,族谱的完成意味着身份认同的圆足。“金山”这介于在场/现实与缺席/想象之间的名词化为“我”与“他”之间的“第三空间”。对它,不必皈依或反抗、向心或离心,只要承认它的存在,它就为漂移的离散者,敞开着多重身份建构的可能。
海华文学叙事的共同起点是海外华人近代百年的家国之憾,它们的意义不在于重构历史,而在于其对自身存在的反思与对家国观念的追索。它对中华文化的自我神化是体贴而猛烈的破坏,从而有助于建构一种更加真诚的自我言说。
[1]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历险[M].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张翎.金山[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文 俊]
I207.4
:A
:1009-1513(2010)03-0034-05
2010-04-18
王则蒿(1973—),女,四川自贡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