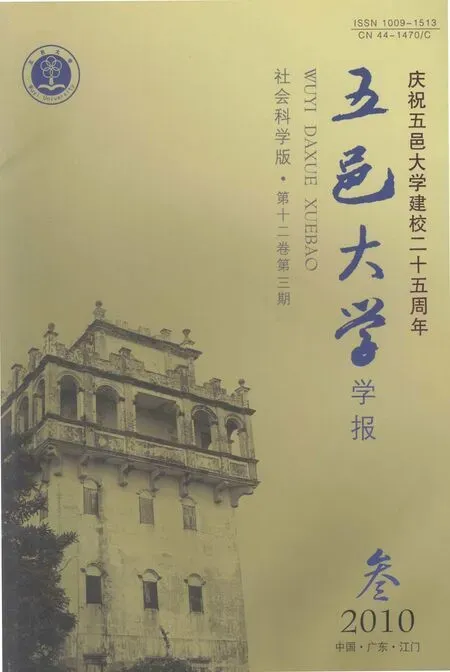试论康有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2010-03-21谢柳军
谢柳军
(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试论康有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
谢柳军
(暨南大学 历史系,广东 广州 510632)
康有为对中国民主革命持反对意见、怀担忧之情。他认为,中国当时的革命是“大义暗而不明”,骤行革命是“弊大于利”,在中国须行“大革命”,革命应该渐进而非激进。这些看法,由康有为的政治立场决定,也与当时历史背景的影响密切相关,对其看法应结合当时的国情予以理解、评价,才更为客观。
康有为;变法改良;中国革命;革命看法;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较早进行变革、谋求振兴的先行者之一,变法改良是他始终坚持的政治变革路线。康有为对当时的中国革命始终持怀疑、担忧态度,拒绝与革命派合作。然而,除“反对”外,他对中国革命还有何看法?他对革命持反对意见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探讨。
一、中国革命“大义暗而不明”
当时,中国革命派所热衷效仿的是美法等国的革命运动,即由革命走向共和。孙中山曾说:“吾主张共和政治,而必以革命为先导者。”[1]6康有为则认为,革命大义在欧美国家中为“革国为私有为国为公有”,即革命的目的是实现国家为人民公有,由全民共治。康说:“故百年来欧人号称革命者,实非专为革命也,专求国为公有云尔。”[2]664由此,康有为认为中国的革命在目标意义上比之欧美国家的革命相差甚远,甚至是一种误用,“若据今欧、日所译,而中国误用之”。这一看法在当时不能说全错。的确,欧美发达国家确是通过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国家富强,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公民社会。所以康有为认为欧美革命不只是进行单纯的暴力斗争,更重要的是建立全民共治的国家。他认为中国革命大义之不明还在于当时革命党人把推翻满清当成了革命之全部,“在今革者,则缘民族主义专用为排满兴汉之名词”,而这“改革之名词,古无可托,今无可译,于是大义暗而不明”。这种不明大义的后果不堪设想,“则朝野之间,为之大乱,而中国遂几于亡矣。”[2]665
除认为革命大义“暗而不明”外,康有为还认为,当时多数人对革命的目的很不明确,包括革命党人。首先,康有为认为欧人革命之目的是“求国为公有”,“由国为君为,革而为国为公有,此其政治大反至极也”,同样,中国革命也应“革数千年专制之命”,实现国为公有,这“比之革一朝之命,其重大逾千万矣”。[2]668而对此当时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呢?用时人的话说:“同盟会未尝深植其基础于民众,民众所接受者,仅三民主义中之狭义的民族主义耳。正惟‘排满’二字之口号,极简明切要,易于普遍全国,而弱点亦在于此。”[3]当时康有为对此也有洞察,实属可贵。他指出“革命之理至深且赜,而众人乃能以简单二字,妄视为救国不二之良方”[2]658,这种作法实在危险。因为在“万国竞争之日,列强群迫之时,而骤行人人所未经之涂,人人所未闻之事,此吾所深忧却顾,俯仰彷徨而不能自已也”[2]699。由此,他极力反对革命派的排满运动,强调要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就不止革一朝之命,而应“五族合轨,人心同趋”。这一点恰是革命党所缺乏的。对此后人也有论述:“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作他的后盾。至于革命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和习惯,只够作反动者的工具。”[4]因此,包括康有为在内的改良派对革命党之革命自然会嗤之以鼻了。
其次,革命的动机也尚未明确。康有为认为,革命党人中不免有投机而来者,企图以加入革命来谋取个人私利,“至于奸蠧丛生,则虽良法美意,反成巨害,不如不变之为愈矣”[5]。革命动机不明更在于革命者易受感情煽动,一受鼓舞便易忿怒盲从。他认为在当时已弱之中国,必不可“以一时得意于附和之多,借响应之众,因感情之误,固执至旧之论,拚掷万里之山河,四万万之人民,五千年之文明,听渔人之得利”[2]665。就是说,倘若革命者只出于感情之冲动而缺乏明确的革命动机,虽群起响应,后果也不堪设想,“革命不知所止而穷极之”,且“革命之说,一误行之,若群狂者操刀而舞,其不至于相杀至尽不止”[2]661。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及其政局是否如此?笔者在此并非把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混战归咎于辛亥革命,只想说明康有为当时所持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二、当前行革命于中国弊大于利
康有为认为当时国人对革命之大义“暗而不明”,因此,骤而行革命于中国不仅不能成功,还不免有亡国之虞。“大变如此,忧心如焚”,“以法国鉴之,革党必无成,以印度鉴之,中国必亡。”究竟革命之利与弊孰大孰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与康有为之辈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革命派认为革命行于中国可以推翻满清并建立共和国,是利大于弊的,“今欲求避祸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6]173,“吾主张共和政治,而必以革命为先导者……盖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苦痛”,“革命成,而他之问题悉迎刃而解矣”[1]6。康有为则认为,行革命于中国是弊大于利的,其弊有二:一是革命将使国家走向灭亡。其推论为:由革命而内乱,而分裂,而外国干涉。列国之干预最可怕,而国人却不深思之。“若熟念之,则外人即有借军械、助军饷而认革命军者,亦不过助其野心,借革命军之内乱自残,为彼除难耳。”[2]653二是革命将直接造成对劳苦大众的伤害。“今且勿论亡国,但述兵黩之祸,其别有三,如生计之败坏、盗贼之多、杀戮游离之惨。”[2]657更让康有为无法接受的,是革命派的“先破坏后建设”之说①。康有为指出:“夫天下事破坏则甚易,若建设,非累岁月不能成,又非安平无事不能奏动。”[2]656这也是康有为反对当时革命的最为关键的理由。其中是否有夸大之辞,一昧地诋毁革命,笔者以为不应作简单的评论。
康有为所以持“弊大于利”看法是有原因的:
首先,与他对欧美国家革命的认识有关。康有为流亡海外期间,对欧美以及亚洲国家的革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若言革命,必相攻杀,势之相迫,入于旋涡,无论何人,殆无能免者也”[2]656,“印度一起革命,死者二千万;德国一起革命,死者一千八百万。若吾国人多,若全国革命,死者当无量数。”[2]658显然,耽心牺牲过重成为康有为对中国革命看法的一个重要考量。在这种认识影响下,他认为革命弊大于利,自然难以接受革命。
其次,康有为认为革命还可能导致亡国。这与辛亥革命后康对中国形势的认识有关,即外有列国环视,且已在中国边疆地区蠢蠢欲动,尤其是沙俄。1911—1912年,沙皇俄国使用各种手段,对辛亥革命进行干涉,同时在长城以北展开大规模领土掠夺活动,带头掀起又一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7]西藏、新疆、东北均为列强觊觎瓜分之地,内乱之国不易伸展管治之权,因此,要变革中国,应以不乱为前提。对于革命倒满是否会引起列强干涉这一问题,孙中山也有考虑,更不敢否定:“事一发,则不能瞒欧人明眼之耳目也”,“欧洲联盟制我之事,或未必有,然不可不为之防。”而在如何防止俄国占我领土,孙中山认为利用列国间的矛盾关系可挟制俄国:“不幸欧洲有联之举,鄙意必行分立各省为自主之国(这正是康所忧虑的——笔者注),各请欧洲一国为保护,以散其盟;彼盟一散,然后我从而复合之”,“然后我得以利啖之,使专拒俄……俄势一孤,我可优游以图治”。但这一乐观看法,却不为当时大多数人所接受,譬如当时与孙中山交往密切的日人宫崎寅藏表示:“倘此事为俄主张,使独人(德国)先发手,则中国危矣。分割之机,或兆于此也。我辈为之奈何”,“机事不密,则害成者易之,大戒也”。[6]181-182这种担心革命可能会引起列国干涉而至亡国的看法,一定程度上与康有为的看法不谋而合。
正由于此,即使辛亥革命已成功,共和国也成立,“今共和告成数月矣,扫中国数千年专制之弊。不止革一朝之命,五族合轨,人心同趋矣”[8],而康有为对中国的革命仍不乐观,也终究没有转向革命阵营。其原因是,“今虽稍定,而伏莽于萧墙,狡启于强邻,岂遂靖乎?”“吾惧后患未已,顷二次革命,流血数省,人民生计益绝”[2]652。
三、中国的革命应是“大革命”
康有为曾对欧美的革命进行比较,认为革命有大小之分:“言立宪者,大革命也,革数千年国为君有之命。今号革命者,小革命也,仅革一朝一族之命而已,其为复汉人之权利则一也。”[2]668康有为把西方国家的革命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英国为例,通过君主立宪不仅革了专制统治的命,还实现了全民共治,使“君”与民同等,这种变革便是所谓的“大革命”;另一种是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暴力斗争,这种激进的革命以惨重杀戮为代价,是“革一朝之名”的“小革命”。而当时革命党人所热衷的用于推翻满人政权的正是所谓“小革命”。康认为这种革命行于中国意义不大:“革数千年专制之命,比之革一朝之命,其重大逾千万矣。”[2]665由此,实行君主立宪在康有为看来是一场“大革命”,是“革数千年国为君有之命”,而非“革一朝一族之命”,前者明显优于后者。因此,康不仅接受君主立宪,而且认为在封建专制统治长达数千年的中国,能够通过君主立宪达到全民共治国家之目的。
康有为认为君主立宪在有数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国是可行的,实行君主立宪是“大革命”,在中国就是要进行这种大革命,不但推翻满清王朝,更要推翻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推翻国为君有,实现国有公有、全民共治。“立宪国者,国为公为,君民共之”,“立宪之国,不论君主民主,要皆以国为国民之公有物,而君主虽稍贵异,不过全国中之一分子而已。”[2]662-663可见,康有为呼吁进行大革命就是要使“全民共治”理念实现于中国,改变数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国为君有”思想。而革命派之革命,在康看来,无非是汉人反抗满人并恢复汉族权利的斗争而已,与古代民族之间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区别。“今革命之名义,在中国用之,则专属征诛以为移朝易代之事。”[2]665康有为这种对大、小革命的判断,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对当时国内外革命运动的认识较为肤浅。然而,笔者以为对左右他这种判断的一些因素,还应该多作一些探讨——
首先,康有为认为革命党之“小革命”弊大于利,这在前段已有论说,此处不再累述。而立宪一事,康有为视为是变革中国的大革命,且可避免大弊祸:“此大事也,在中朝即俯而尊之,迫切而定之,苟上下能善行之,则君民无流血之祸,一国上下,可晏然无事,告厥成功。”[2]665康还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对于保存中国五千年之文明、四万万同胞之生命安全、国家不致分裂灭亡都是有利的,“故言立宪者,大革命也”。
其次,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在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中,出现了多个世界强国,譬如君主立宪的始祖英国成为雄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德国与日本也都通过君主立宪成为世界强国。无疑,君主立宪被视为一条成功之道已植根于康有为的变革思想中。相反,诸如美、法等民主共和制国家,在与欧美国家争斗中却屡试屡败、动乱不已,这也为康有为所识:“今共和政体之盛,莫若美洲,盖皆师法合众国政体之故,然除美国外,无一不乱者,在中南美间,无岁不见告也。”[2]681康同时认为,效仿美、法之革命与共和制,不是哪个国家都可以的,中国也如此:“夫各国政体,各有其历史风俗,各不相师,强而合之,必有乖,则足以致败矣。”[2]680由此,康有为不仅认为共和制不适于中国,且通往共和制的“小革命”方式也不可行。
四、革命应是渐进的而非急骤的
在中国政治变革过程中,康有为始终是主张变法改革的:“夫法之不能无弊,穷之不可不变,自然之势也。”[2]710但他同时主张,改造社会不能过于急躁,也不要急于一时以赴事功,渐进有序的革命对中国是极有利的:“今吾国人皆慕欧、美人之良法,……惟我海内同胞,无动于感情,无蔽于近见,慎择熟讲而后力行之,中国幸甚!”[2]694他认为革命若行之太急,不但难免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动乱发生,而且“革命极穷而不知止矣”,其后果也不堪设想。另外,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康有为认为,中国革命不应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应保护之以免遭革命之破害。这也是康主张中国革命宜行渐进方式的又一原因,即中国革命应以渐进为宜,才不致“拚掷万里之山河,四万万之人民,五千年之文明,听渔人之得利”[2]665。就是说,康有为关于中国变革的主张,从变法改良到渐进的革命,都体现着循序渐进、和平改革的思想,并以保国、保教为核心,以不乱为前提,以对外为重心。“夫重民者仁,重国者义,重民者对内,重国者对外。然重民者无所待于外,天下一统策也。重国者无不对于外,列国竞争策也。”[2]702“夫为国之道,先求不乱,而后求治。”[2]705
康有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为了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主张中国革命宜渐进有序地进行,这种考虑也不无其合理之处。首先,近代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民族危亡与国家复兴成了近代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作为大变局中积极倡导变革的康有为,同样抱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振兴民族之愿望。康有为始终认为民族矛盾是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列强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因此,中国之内,一则举国同心,一致对外;一则适时变革,强大中国:“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也”,“方今绝海棣通,列强邻迫,宜合举国之民地,以为对外之政策,不宜于一国民之内,示有异同”,“分则弱,合则强,治法之公理也”。他认为:“窃惟东西各国之所以致强者,在其举国君民,合为一体,无有二心也。夫合数千百万之人为一身,合数千百万人心为一心,其强大至矣。”[6]340-341所以,在外患日深的情况下,中国不仅要变革,还要做到举国同心和安定内治,才能使中国革命有保障、循序渐进地进行。
其次,康有为认为,暴力革命可能会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破坏。由此,他强调“求变法之不可骤”,在变革中应保护好传统文明。康借鉴西方国家如英、德以及亚洲日本的变革经验,认为中国革命也应该做到“温故与知新”。他指出:“英国之为治也,常新旧并行,其温故者操守极坚,其知新者进行不失,二者相牵相制,且前且却,各一步而一骤,而得其调和焉,故常守旧而能保俗,而又日更新以争时”;德美等国“则持重犹夫英也”;而邻国“日本亦师英,新旧并驰,是故进取而又能坚固也”。[2]710-711基于这种认识,康主张中国革命宜行渐进方式,以利于保护传统文化免遭革命之破坏。康认为中国革命应是渐进的而不是激变式的,说明他并没有完全否定与反对中国革命;同时也说明,革命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若革命“知进而不知退,知得而不知丧,知更新而不知守旧,轻佻浮动,一跃千里,而一败几于不可复振”[9]。即革命并非十全十美,因此,有必要加以积极引导乃至限制。康有为强调革命须渐进有序进行,是为了避免革命可能造成的破坏以及可能带来的其他激变。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仍有意义和价值。
综而观之,康有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是复杂的,这些看法又并非全无依据。当然不可否认,康有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有其保守的一面,这是由其政治立场决定的。不过,通过对康有为关于对中国革命看法的探讨,可以为认识中国近代革命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也可从中窥见中国近代革命具有的历史局限性,这同样反映在革命派身上,“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力量,但这种力量还没有突破历史的临界点”[10]。
注释:
①“先破坏后建设”说在革命党人如孙中山、宋教仁等人的讲话中多次谈到,如孙中山说“从前诸君,是求急切的破坏的;今日诸君,是要求急切的建设的”,“但破坏之后必须建设”等(参见中华书局1981年版《孙中山全集》第三卷1913-1916页),宋教仁说“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比及破坏告终,建设之事,不敢放置”等(参见郭汉民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宋教仁集》)。
[1]郝盛潮.孙中山集外集补编[G].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下册[G].北京:中华书局, 1981.
[3]胡汉民自传[G]//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近代史资料1981年2期(总45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60.
[4]蒋廷黼.中国近代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9: 87.
[5]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G].北京:中华书局, 1981:59.
[6]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孙中山全集:第一卷(1890—1911)[G].北京:中华书局,1981.
[7]余绳武.沙俄与辛亥革命[J].近代史研究,1981 (3):234-255.
[8]康有为.不忍杂志:1—3期[M].北京:文海出版社,1988:3.
[9]康有为.康南海文集[M].北京:文海出版社, 1972:19-20.
[10]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199.
[责任编辑 朱 涛]
K256
:A
:1009-1513(2010)03-0021-04
2010-05-08
谢柳军(1984-)男,广东茂名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