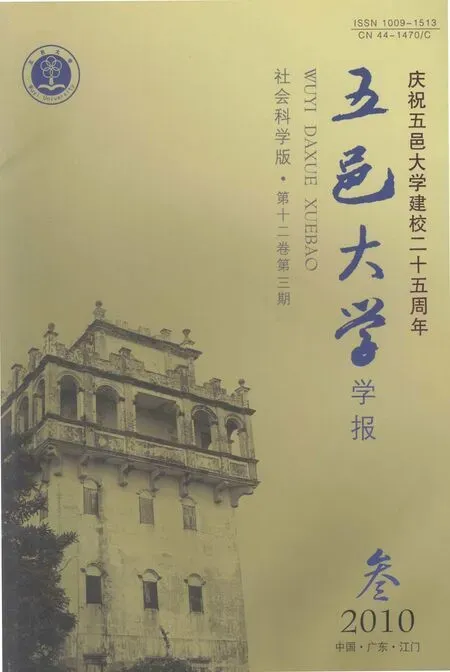论康有为对梁启超小说创作的影响
2010-03-21汪平秀汤克勤
汪平秀,汤克勤
(嘉应学院1.社科部2.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论康有为对梁启超小说创作的影响
汪平秀1,汤克勤2
(嘉应学院1.社科部2.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康有为对梁启超的小说创作有多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是:使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促成其投身于小说创作;消极影响是:使《新中国未来记》中途辍笔。从梁启超开始创作小说到最后放弃所写的小说,康有为在其中扮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
梁启超;康有为;小说创作;影响
一、康对梁小说创作的积极影响
1902年,梁启超作《三十自述》一文,写及初次拜见康有为的情景:
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师(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1]梁启超拜见康有为时年值18岁。他17岁中举,正少年得意。《三十自述》云:“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然而一见康有为,却被其深深折服,遂决然舍弃旧学,拜康为师学习新学。从此,梁启超的思想和人生发生了巨大转变。
1901年,梁启超曾作《南海康先生传》,提及自己师从的获益时说:“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2]确实,梁启超的学问根柢深受其师影响,而且他的人生道路也由其师引领,尤其在他的人生前期。秉承其师的政治改良思想,大力宣传维新救国主张,协助其师进行维新政治活动,成为梁启超早期的主要事业。“庶几南海先生之志,则启超愿鼓歌而道之,跪坐而进之,馨香而祝之。”[3]这句话是梁启超忠于其师、宣传其师思想的公开表白。梁启超的许多著作特别喜欢称引或者发挥康有为的说辞和文章。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问世后,梁启超作《读〈日本书目志〉书后》,一字不改地载录康的自序,可见他对康的极度尊重。他注意到康有为关于小说的论述,联系到维新宣传的实际需要,于是大力推崇师说。
实际上,梁启超对小说起初并无好感,这是他从小受的传统文化教育所致。戊戌变法以前,他的文学观基本上属于传统士大夫的正统文学观。1897年,他撰《万木草堂小学学记》,其中“学文”一门说:“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虽然,言之无文,行之而不远。说理论事,务求透达,亦当厝意。若夫骈俪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溺志。”[4]意即诗文是“溺志”之具,为了论道(“说理论事”)才留意于它;以之娱乐性情,只能偶尔为之,切忌“玩物丧志”。梁启超的这种重道轻文思想显然来自宋明理学的影响。对待文学的正宗——诗文尚且如此,更遑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小说了。但是,梁启超后来却留心小说、注重小说,这种转变明显是他接受了其师康有为的幼学思想和《日本书目志》的影响所致。
康有为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编行小说课本的启发,在《日本书目志》的识语中专门讲到幼学教育的重要性,还决心率弟子“编《幼学》一书”,确定其体例为十项,其中“幼学小说”一项说:“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5]梁启超在戊戌年前著《变法通议》,其中的《论幼学》将其师的幼学教育内容合并、更名,确定为七项,并没有超出康有为划定的范围。其“说部书”中,梁启超分析因“今人文字与语言离”而造成“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通俗小说“《水浒》、《三国》、《红楼》之类,读者反多于六经”的这一事实,提倡“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6]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希望用俚语写作小说,用来宣扬儒教,传达历史知识,激发爱国热情,介绍外国人情,改变社会恶俗。他们的这种小说观念,都是从小说的教育功用上着眼的。
1898年9月,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东渡日本避难。在接触日本的政治小说后,他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一文,提倡翻译“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的政治小说。从这篇文章看,梁启超受康有为的影响仍然明显。梁启超指出小说具有通俗性和娱乐性,读者众多,可以因势利导,借以用作社会教育的工具,这一认识,其实出自康有为的小说观念。此文用三分之一强的篇幅,引述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卷十四“小说门”中所写的识语:
易逮于民治,善入于愚俗,可增七略为八、四部为五,蔚为大国,直隶王风者,今日急务,其小说乎!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于文学之人少,而粗识“之”、“无”之人多。“六经”虽美,不通其义,不识其字,则如明珠夜投,按剑而怒矣。孔子失马,子贡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岂子贡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群,人各有等。以龙伯大人与侥僬语,则不闻也。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泰西尤隆小说学哉!日人尚未及是,其《通俗教育记》、《通俗政治记》亦其意矣。[7]
梁启超大段称引师说,并以“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作赞语,说明他完全赞同其师关于小说作为政治启蒙、开通民智工具可包容一切知识的观点。他又在其师的基础上进一步生发,承接在《变法通议·论幼学》中认定的旧小说“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的观点,再次批判旧小说:“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由此可见,梁启超的小说观念,既受其师的影响,又有自己的思考;既隐含士大夫历来轻视小说、以之为“诲盗诲淫”的旧传统,又蕴蓄“小说为国民之魂”,能“导愚氓”、使“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的新知识。受其师影响,梁启超终于抛弃了士大夫的偏见,提倡为下层民众写作白话小说,为“今日中国时局”翻译、写作小说。这种小说观,实是中国小说创作观念的一大进步。
梁启超因为对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等的翻译,参与到政治小说的写作中。这一体验,一方面使他切身体会到政治小说乃“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8],可以引起“希贤爱国之念”,提高国人的政治思想觉悟,于是他大声呼吁“译印政治小说”;另一方面,又使他萌发了亲自创作政治小说的愿望,以确实地“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他曾把这想法汇报给其师康有为,康有为认为小说“衿缨市井皆快睹,上达下达真妙音”。后康又因梁启超延搁时日未能动笔而遗憾地说:“去年卓如欲述作,荏苒不成失灵药。”[9]后来梁启超专门记录其师的诗说:“吾《未来记》果能成,此亦一影事也。”①由此可见,梁启超对其师的鞭策是相当重视的。“顾确信此类之书,于中国前途,大有裨助”,又加上其师的关注和督促,梁启超一直“夙夜志此不衰”,“五年于兹”,终于在“身兼数役,日无寸暇”[10]的状况下动笔创作起小说来。
应该说,在康有为影响下,梁启超的小说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梁启超亲自投身于小说创作,也与其师的鞭策不无关系。这是康有为对梁启超小说创作的积极影响。
二、康对梁小说创作的消极影响
康有为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梁启超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梁启超在构思、创作通俗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时,思想曾一度趋于激进,多与革命派人物接触,先后撰写了《破坏主义》、《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等文章,宣扬革命思想,认为革命是大势所趋、无可逃避的。后来辛亥革命胜利了,梁启超回顾这段岁月时说:“戊戌八月出亡,十月复在横滨开一《清议报》,明目张胆,以攻击政府,彼时最烈矣,而政府相疾亦至,严禁入口,驯至内地断绝发行机关,不得已停办。辛丑之冬,别办《新民丛报》,稍从灌输常识入手,而受社会之欢迎,乃出意外。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11]当时梁启超这一思想新动向,引起了康有为的警觉。康有为多次对他加以严厉斥责,并专门写下《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和《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②进行训戒。梁启超曾去信与他争论,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主张“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2]1902年10月,康有为又致信梁启超,要求他放弃革命言论,并以病危相要挟。梁启超“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13],于是“大改宗旨,极知革之不可行,且劝人勿言”[14]。然而他在1903年4月致友人信中仍声明:“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13]在康有为的横加干涉下,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复杂变化,此时所表现出的种种情绪,都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得到反映。《新中国未来记》第三回,主人公黄克强和李去病关于革命还是非革命进行了反复辩论,正是梁启超当时复杂思想的艺术再现。小说争论的结果是“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论占了上风。不过,李去病虽然承认黄克强的“非革命论”有道理,但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他说:“今日做革命成者不能,讲革命也是必要的”,“我们将来的目的不管他在共和还是在立宪,总之革命议论、革命思想在现时国中是万不可少的”。黄克强反对破坏的革命论,但也并不完全抛弃破坏手段,他的社会变革行动底线是:“但非万不得已,总不轻容易向那破坏一条路走罢了。”[15]这就是梁启超倾向革命的一种曲折表现。
梁启超在开始小说创作后不久的1903年2月,即被康有为授命代表保皇会去美洲,直到10月才返回日本。期间梁启超心甘情愿地放弃了革命论。在1903年8月19日《致蒋观云先生书》中,他说:“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16]当看到美国联邦共和制所暴露的弊病时,他醒悟到共和制其实并不适合于中国实情。他认为,国人不具有公民的责任心,不适合管理国家,“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因此悲观地说:“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无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雷厉风行,以铁以火,陶冶锻炼吾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7]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动情地说:“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共和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祖国;吾爱汝也,然不如其爱自由。吾祖国吾自由其终不能由他途以回复也,则天也。吾祖国吾自由而断送于汝之手也,则人也。呜呼!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点汝之美名,使后之论政体者,复添一左证焉以诅咒汝。吾与汝长别矣!”[18]梁启超的思想发生急剧变化,正是康有为所以派他出访美洲的初衷,因此康有为很愿意看到这一结果。于是,梁启超已变化的政治思想不再适合《新中国未来记》开篇所设定的结构框架了:
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
梁启超“不惮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18],抛弃他以前的共和政治主张是容易的,但是,若要合理地处理《新中国未来记》原定的人物形象和结构内容却难。梁启超此时已完全放弃了革命论,他该如何处理李去病这个重要的正面人物呢?原先规划的政治方案,其进行步骤、时间等,又该怎样得到合理地调整呢?这些矛盾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十分棘手。当时就有读者断言《新中国未来记》一定完成不了。孙宝瑄1903年写日记就说:“其书所出,不过五六回,方在黄、李自西伯里亚回国之时,吾不知其此后若何下笔也。吾恐其从此阁笔矣。何也?凡撰书,如演剧然,必密合于情理,然后读之有味。演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以今日为过渡时代。盖今日时势为未来时势之母也。然是母之断不能生是子,梁任公知之矣,而何能强其生乎?其生则出乎情理之外矣。是书何必作乎?何也?子可伪也,母不可伪也。梁任公,天资踔绝者也,岂肯为无情无理之著作乎?故吾料是书之必不成也。”[19]果然,《新中国未来记》写完五回就没有下文了。
梁启超曾说自己一生好变,其政治思想的改变,正是《新中国未来记》中途辍笔的根本原因。而梁启超的政治主张在1902年后从激进渐趋保守的这一变化,又与康有为对他的强烈干涉不无关系。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新中国未来记》的搁笔,康有为应负有一定责任。这是康有为对梁启超小说创作的消极影响。
三、几点结论
第一,康有为对梁启超小说创作的积极影响占主导地位,消极影响则处于次要地位。梁启超的小说观主要源于康有为的小说观,其动笔创作小说也与康有为的鼓励有一定关联,但梁启超小说的思想内容以及中途的辍笔,又与康有为的思想影响和强烈干涉不无关系。换一句话说,梁启超正是接受了康有为的理论昭引,才提出风行天下的“小说界革命”主张,并投身于小说创作;又正是康有为对梁启超的横加干涉,才间接导致了《新中国未来记》成为“断臂的维纳斯”。从梁启超开始创作小说到他最后放弃所写的小说,康有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其中扮演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
第二,梁启超继承和发展了康有为的小说观,并形成了自己的小说理论。康有为仅认识到小说的通俗性和教育功能,以小说包容一切知识来作为政治启蒙、开通民智的工具,而梁启超在他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改造旧小说,进行“小说界革命”,从而成了影响一个时代的理论主张。
第三,康有为对梁启超小说创作的影响,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折射出康有为对梁启超整个人生和思想的深刻影响。
注释:
①参见1903年9月《新小说》第7号《小说丛话》。该期杂志实为1904年1月以后出版。
②二文俱作于1902年,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后文曾节录刊于《新民丛报》第16号,题为《南海先生辨革命书》。
[1]梁启超.三十自述[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上海:中华书局,1936:16-17.
[2]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上海:中华书局,1936:62.
[3]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55.
[4]梁启超.万木草堂小学学记[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35.
[5]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十[M].上海:大同译书局,1897.
[6]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J].时务报,1897(8).
[7]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J].清议报:第1册, 1898(12).
[8]梁启超.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42.
[9]康有为.闻菽园欲为政变小说,诗以速之[J],清议报:第63册,1900(12).
[10]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J].新小说,1902(1).
[11]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上海:中华书局,1936:2-3.
[12]梁启超.与夫子大人书(1902年4月)[G]//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286.
[13]梁启超.与勉兄书(1903年4月15日)[G]//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20.
[14]高山.致康有为书(1903年2月16日)[G]//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18.
[15]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
[16]梁启超.致蒋观云先生书[G]//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328.
[17]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M]//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上海:中华书局,1936:124.
[18]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M]//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上海:中华书局,1936:68.
[19]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709.
[责任编辑 文 俊]
I206.5
:A
:1009-1513(2010)03-0013-04
2010-02-04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09YJC751034)的阶段性成果。
汪平秀(1976—),女,湖南祁东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