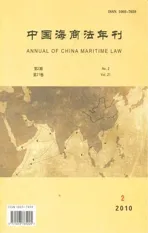《鹿特丹规则》视角内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之解析*
2010-02-15傅廷中
傅廷中
《鹿特丹规则》视角内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之解析*
傅廷中
以《鹿特丹规则》为视角,分析新型的制度建构对提单物权凭证功能的传承,并在新公约的语境下对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进行初步解析,指出在未来的海上运输法研究领域,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鹿特丹规则》;提单;物权凭证;控制权
在国际贸易和航运界,提单所具有的物权凭证功能已为人们所普遍认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近一个世纪以来,对提单功能(其中包括物权凭证功能)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截至目前,尚无人能够推翻此种结论。施米托夫在其所著的《出口贸易——国际贸易法律与实务》一书中即指出:“占有提单,在许多方面就等于占有货物,提单转让与货物转让具有同样效果。”[1]John Wilson也认为,占有提单可被视为占有提单项下的货物,占有提单的目的有三个:一是提单持有人有权在目的港请求交付货物;二是持有人在运输途中仅仅根据提单的背书,即可转让货物的所有权;三是可将提单作为债的担保。[2]透过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提单所具有的物权凭证功能毋庸置疑。另外,就有关提单的立法而言,在20世纪,《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先后出台,这三个公约也均未否认提单所具有的物权凭证功能。然而,自2009年《联合国全程或部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合同公约》(又称《鹿特丹规则》)通过以来,这个问题却使人们产生了一些困惑,从而再度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鹿特丹规则》有许多新型的制度建构,其中与提单有关的制度变革尤其值得注意,此种变革的特征有二:首先,公约中没有使用在业界已耳熟能详的“提单”的概念,而是代之以“运输单证”的称谓;其次,公约不再直接使用物权凭证的表述方式,而是单纯提及“运输合同的证明”和“货物收据”这两项功能。这种新的表述似乎要向人们传递两个信息:一是提单的概念将成为历史,且将被一种名为“运输单证”的新型货运文件所取代;二是《鹿特丹规则》语境中的运输单证将不再具有物权凭证的功能。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鹿特丹规则》关于运输合同的定义中缺少了承运人或履约方“保证凭以交付货物”的表述,因而使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弱化。[3]然而,笔者通过对规则的分析,得出以下三点初步的认识:第一,在《鹿特丹规则》的框架内,提单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第二,在新型的制度建构中,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依然存在,只不过是要区分具体情况而已;第三,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减损,但此种功能可通过其他制度建构得到补救。
一、《鹿特丹规则》框架内提单概念之寻踪
要研究在《鹿特丹规则》的语境之下提单是否还具有物权凭证的功能,其前提是要明确在新规则的框架之内,提单这种货运文件本身是否还会存在。
正如我们所知,在现行有效的三个公约当中,提单的概念均被直接而清晰地规定在相关的条款当中。例如,《海牙规则》第1条即规定,运输合同仅适用于提单或者与海上运输有关的任何类似的物权凭证所包含的运输合同。《维斯比规则》第5条也明确规定:“本公约各项规定,应适用于在两个不同国家港口之间与货物运输有关的每一提单。”《汉堡规则》第1条则不仅沿用了提单的称谓,而且还进一步地为提单确立了定义,即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由承运人接收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
相比之下,在《鹿特丹规则》当中,通篇不见提单的称谓,由此给人们的印象是:伴随着海上运输法的革命,提单将要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但笔者不以为然。首先,《鹿特丹规则》第1条(定义条款)在对“运输单证”确立定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运输单证区分为“可转让的运输单证”和“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两种形式,这与传统海商法中区分可转让的提单和不可转让的提单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而且,公约还就运输单证的签发、运输单证的内容、运输单证下的权利转让、运输单证的证据效力等问题分别作出具体的规定。很显然,这些内容在传统的海商法中均属于提单制度的范畴。其次,通过回顾和分析公约的制定过程,也可清楚地印证这一点。在有关《鹿特丹规则》(草案)的说明中,公约的起草者认为,在与“运输单证”有关的两项内容的定义中,第一项内容“将包括对承租人所签发的但并不证明运输合同,而仅起到货物收据作用的提单,以及在运输之前或转运期间所签发的某些种类的收据”;至于第二项内容,“将包括名副其实的提单及海运单”(A/CN.9/WG.III/WP.21第31段)。由此可见,《鹿特丹规则》并非要取消提单这种货运文件形式,而是要站在一个更高起点上,以一种总括性的概念来囊括包括提单在内的各种运输单证(包括电子运输单证),从而使公约调整的合同关系实现最大化。
二、《鹿特丹规则》语境中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之传承
从理论上讲,既然《鹿特丹规则》的制定者无意取消提单这种运输单证的形式,故提单所具有的物权凭证功能即可顺理成章地得以肯定,然而,规则的第1条(定义条款)第14项却只将运输单证界定为货物收据和运输合同的证明,由此会给人们留下一种深刻的印象,即在《鹿特丹规则》的语境之中,即使提单这种运输单证得以继续保留,也不再具有物权凭证的功能。笔者对此同样有相反的理解。以笔者之见,在《鹿特丹规则》当中,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并没有被否定,而是以一种隐性的特点得以传承。所谓隐性传承,就是指在公约当中不以明示的方式对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加以肯定,而是区分不同情况,将此种功能蕴含在相关的制度当中。
我们知道,海上运输所涉及的运输单证存在不同的种类,按照货物运输方式划分,可以分为班轮运输下签发的运输单证和在航次租船情况下依据租船合同而签发的运输单证;从提单流转的角度来划分,可分为可转让的运输单证和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如记名提单);从单证的制作形式来划分,又可分为纸质运输单证和电子运输单证。在上述的提单种类当中,区分可转让的运输单证与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对于考察提单有无物权凭证的功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在可转让的运输单证之下,只要提单的转让过程符合法定的程序,提单持有人即有权请求承运人交付提单项下的货物,虽然提单不同于票据法意义上的票据,但票据转让的无因性(即认单不认人的特性)在这里同样可以得到体现,因而使物权凭证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但是,在签发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之下,法律上所强调的是持单人的身份而不是单证本身(此即所谓的认人不认单),故物权凭证的功能在这里便不复存在。《汉堡规则》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简称《海商法》),由于未区分具体情况,笼统地赋予提单以物权凭证的功能,容易使人们误认为不论何种提单均具有物权凭证的功能,虽然通过理论研究也可以澄清这一点,但极易在航运和司法实践中导致混乱。时至今日,在业界还经常有学者强调,在签发记名提单的情况下也必须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之所以存在这种观点,正是由于法律规定不清晰所致。实际上,这是对提单物权凭证功能的一种片面的、机械的理解。
《鹿特丹规则》将物权凭证的功能从运输单证这一总括性的概念中剥离出来,而后再区分情况,将此种功能赋予可转让的提单,可以有效地避免司法实践中的混乱。虽然笔者无从考证此种制度设计的真正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鹿特丹规则》在区分运输单证的种类并以此确定单证持有人对货物有无物权的问题上,达到了现行三个公约所没有达到的客观效果。
笔者之所以认定在《鹿特丹规则》之下,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表现为一种隐性的传承,原因在于公约虽未直接使用物权凭证的概念,但却将此种功能隐含在相关的条款之中,通过分析公约的定义条款,即可看出这一点。《鹿特丹规则》第1条除了将运输单证区分为可以转让和不可转让的两种形式,而且还不惜笔墨地对可以转让的运输单证加以描述,将其定义为通过“凭指示”或“可转让”之类的措辞,或以该单证所适用的法律所承认的其他具有同等效力的措辞,表明货物应按照托运人或收货人或持单人的指示交付,而且其上没有标注“不可转让”或“不得转让”的字样。公约作出此种规定,其本意无非是要突出宣示可转让的运输单证所具有的物权凭证功能,否则,对运输单证加以区分将毫无意义。
三、《鹿特丹规则》框架内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之减损
在目前各国的海上货物运输法中,承运人必须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这已成为一个铁的规则,该项规则的确立同样根源于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对此无人否认。然而,在《鹿特丹规则》下,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虽然得到了隐性传承,然此种功能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公约中的另一种制度所减损,该项制度即是指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承认无单放货行为的合法性。
我们知道,在凭提单提取货物的问题上,理论和实践一直存在着矛盾。从法律上讲,提单作为物权凭证,承运人凭单交货乃天经地义,但在实践中,由于运输环节和国际支付方面的原因,若绝对地强调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又将会影响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因此,承运人出于提高效率方面的考虑,亦为了不影响收货人的利益,常常采取凭担保函交付货物的做法。长期以来,这种理论和实践相抵触的做法一直困扰着人们,虽有许多学者不厌其烦地对所谓的无单放货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亦有学者从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的角度探讨承运人无单放货的责任,但最终都没有从根本上使问题得到解决。
针对当前国际航运界所面临的这种矛盾的情况,《鹿特丹规则》的制定者们达成如下三点共识。
其一,现今大量存在的无单放货的现象与承运人凭单放货的法律义务产生了很大的偏离,因此,不能使其成为强制性的义务(A/CN.9WG.III/WP.21第161段)。
其二,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承运人不可能总是坚持要求在交付货物时将提单交出,也不能把在任何情况下的错误交付的责任都推给承运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提单项下的收货人或被背书人应保持警惕,争取货物在船舶到达时能够被交付;在以提单进行质押的情况下,银行也必须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并保持警惕,且在船舶到达时采取步骤(A/CN.9WG.III/WP.21第181段)。
其三,虽然承运人在无单放货时可以要求提供保函,但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保函本身并不能免除承运人无单放货的责任,因此,承运人在承担了无单放货的责任之后,凭借保函向保证人追偿损失的权利却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就客观原因而论,提单流转过程中的延误,实际上是由贸易中的问题所致,而与承运人无涉,故按照凭单放货的要求,令承运人承担无单放货的风险,对承运人而言有失公允(A/CN.9WG.III/WP.21第181段)。
基于上述反思,《鹿特丹规则》的制定者对凭单放货的问题设置了例外规定,即在特定的情况下,承认无单放货行为的合法化。《鹿特丹规则》第47条第2款规定:在签发可转让的运输单证或者可转让的电子运输记录的情况下,如果其上载明可以不提交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此时可在不影响第48条第1款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下列规则:一是如果货物未能交付是由于单证持有人接到了交付货物的通知而未在货物抵达目的地后于规定的时间或期限内请求提取货物,或因持有人未能适当证明其是公约第1条第10款第1项第1目所列的人(即在指示单证中被载明的托运人或收货人)之一而被承运人拒绝交付,或承运人经过合理的努力而无法确定持有人时,则承运人可以通知托运人就货物的交付发出指示;承运人经合理努力而无法确定托运人的,可以通知单证托运人,请求就货物的交付发出指示。二是承运人根据前项规定按照托运人或单证托运人的指示交付货物的,解除承运人在运输合同项下向持有人交付货物的义务,而不考虑是否已向承运人提交了可转让的运输单证,也不考虑依据可转让的电子运输记录主张提货的人是否已按第9条第1款规定的程序(即《规则》中规定的可转让的电子运输记录的使用程序)证明其为持有人。透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鹿特丹规则》虽然没有否定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并不绝对地坚持这一功能。具体而言,由于各种原因使提单的传递发生迟滞而晚于船舶到达目的港,或者有义务在合理的时间内提取货物的单证持有人没有提取货物时,承运人有权寻求货物控制权人或者托运人的指示而予以放货,并且免除此种情况下无单放货的责任,如果因此而发生损失,应由发出指示的人承担。《鹿特丹规则》第47条第2款第3项规定:“承运人根据本条第2款第5项对持有人负有赔偿责任的,根据本条第2款第1项发出指示的人应补偿承运人由此遭受到损失。”由于实行这样的例外规定,便将无单放货的责任转嫁到了托运人或单证托运人的身上。
透过上述对无单放货责任的例外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出,长期以来,在国际海上运输领域所固守的关于提单所具有的物权凭证功能的理论,在《鹿特丹规则》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减损。
此种制度设计对承运人而言体现了公平的原则,使其得以免除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的严格义务和法律责任,亦可有效地解决在某些情况下承运人不得不依据担保函交付货物而担保函又不具有法律效力的矛盾。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此种制度设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支付产生影响。在目前的国际贸易支付业务中,经常使用的结算方式是跟单信用证支付方式。在此种支付方式下,银行承担的是第一付款人的责任,然而,银行对卖方承担付款义务的前提条件是卖方要保证做到单证相符(即货运单证与信用证的要求相符)和单单相符(即信用证项下随附的各种货运单证相符)。银行之所以能够接受提单,正是基于提单所具有的物权凭证功能,因为掌握了提单就能控制住提单项下的货物。设想,如果在法律中承认无单放货行为的合法性,就意味着银行在接受提单时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显然,这不是银行所期望的后果。在《鹿特丹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曾有学者对承认无单放货合法化的做法提出质疑,理由是此种规定容易滋生欺诈行为。
另外,承运人只要找不到持单人即可要求向其他地方交付货物,或者不凭银行所持有的单证即可随意交付货物,无疑会使银行担保的效力大大降低(A/CN.9WG.III/WP.21第180段)。
四、《鹿特丹规则》中的货物控制权制度对提单物权凭证功能之补充
按照《鹿特丹规则》第1条(定义条款)的规定,所谓货物控制权,是指根据规则第十章按照运输合同向承运人发出有关货物的指示的权利。虽然公约关于货物控制权制度的定义的规定十分简单,然而,结合公约第十章的全部规定,笔者认为,可将货物控制权进一步定义为货物控制权人(通常是卖方)基于其所持有的运输单证所具有的物权凭证功能,在承运人的责任期间内,以不变更运输合同、不妨碍承运人的正常营运、不损害同一航次其他货主利益的前提下所享有的,向承运人发出变更目的地,或变更收货人,或停止交付的指示等各种权利的总和。
我们知道,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下的货物交付最终要通过运输环节来实现。然而,在国际海上运输中,当货物被装船之后,有时因不可抗力、买方违约或单证瑕疵等原因,卖方需要采取一些补救措施,此种措施的实施在现行的海上运输法体系中却找不到相应的依据。例如,在FOB价格条件下,买方负有租船或订舱的义务,故买方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当卖方将货物装上由买方派来的船舶并取得运输单证继而向银行申请支付货款时,如果银行发现单证上存有瑕疵便会拒绝支付。此时,若卖方以未收到货款为由请求承运人停止交付或变更提货地点或变更收货人,则承运人可以卖方并非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为由而拒绝执行其指示,由此便会造成卖方的经济损失。对于此类问题,在现行有效的三个公约中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有鉴于此,《鹿特丹规则》在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有关国家立法的基础上,确定了货物控制权制度。货物控制权的概念虽然出自运输合同法,但其本质却是向持有物权凭证的人(尽管此种人有时可能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提供的一种救济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货物控制权是基于物权凭证而不是基于运输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鹿特丹规则》第50条虽然赋予货物控制方就货物发出指示或修改指示的权利,但同时又规定,此种指示不构成对运输合同的更改。基于这种分析可以进一步认为,货物控制权是基于物权凭证而产生的一种纯粹的权利但不附带运输合同项下的义务,那种认为控制权人在向承运人发出关于货物控制权指示的同时还负有对需要特殊照管货物的告知义务的理论,实际上是将此种指示混同于运输合同项下的义务。换言之,是将货物控制权人的地位绝对地等同于运输合同的当事人。
《鹿特丹规则》第51条就控制方的识别和控制权的转让问题作出了详尽的规定,这些规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持单人的权利给予保护。虽然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并非是要论述控制权制度,但透过公约关于控制权的制度建构,笔者认为,货物控制权制度的确立从另一个层面上补救了由于公约关于凭单放货的例外规定而对提单物权凭证功能的减损,从而在另一个角度上实现了船货双方的利益均衡。
五、结论
笔者认为,在《鹿特丹规则》的语境之下,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提单的概念,但不能以此认定提单的概念从此在海上运输法中消失,只不过是由于公约所适用的合同范围被扩大化而将其覆盖在“运输单证”这一概念之中。此外,就提单所具有的物权凭证功能而言,由于《鹿特丹规则》将运输单证区分为“可转让的运输单证”和“不可转让的运输单证”,因而不能笼统地将运输单证称之为物权凭证,而是要区分不同的运输单证来加以认定。透过公约对可以转让的运输单证所做的规定可以看出,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并未消除,而是表现为一种隐性的传承。鉴于在当代海上运输中无法彻底根除无单放货的现象,公约允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不凭单交货,使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损。但是,在另一方面,公约又通过货物控制权制度的确立使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得到了适当的补救。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即使在《鹿特丹规则》的视角之内,在未来的海上运输法研究领域,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依然是有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References):
[1]SCHMITTHOFF.Export trade-the law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M].London:Sweet &Maxwell,2007:258.
[2]WILSON J F.Carriage of goods by sea[M].6th ed.London:Longman,2008:131.
[3]孙志勇.《鹿特丹规则》中几个法律问题的比较研究[J].青岛远洋船员学报,2009(1):3-5.
SUN Yong-zhi.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otterdam Rules[J].Journal of Qingdao Ocean Shipping Mariners College,2009(1):3-5.(in Chinese)
书 讯
《海事诉讼文书样式与范例》已由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大连海事法院副院长,大连海事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关正义主编,大连海事法院多名有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参与编写。
《海事诉讼文书样式与范例》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了海事诉讼文书的特点、作用和基本要求;第二部分以诉讼文书样式、实用范例和使用说明为编辑体例,收录了162种常用的海事诉讼文书(这些文书格式同样适用于涉外海事诉讼),其中包含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印发的《海事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的87种文书;第三部分简要介绍英国海事诉讼文书的类型和基本内容。
为了读者使用时的方便,本书对收录的《海事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中的文书样式未做任何改动,并在目录和正文中用“*”号标明。文书样式之后的范例均是根据文书样式的基本要求制作的范本。使用说明则主要强调文书样式要写明的基本内容、应当注意的事项,以及对相关不统一问题的看法等。本书的第一和第三部分主要用来从宏观方面帮助读者理解所选诉讼文书样式。
《海事诉讼文书样式与范例》是一本海事诉讼相关工作者的应备工具书,可供海事法官、律师、海商法专业师生以及海事诉讼当事人参考使用。
(供稿:姚文兵)
Analysis of the function of the document of title under the B/L at the visual angle of the Rotterdam Rules
FU Ting-zhong
In this paper,a study is made at the visual angle of Rotterdam Rules o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function of B/L and a prim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me is also made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convention.It is pointed that in the research area of the law of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in future,the function of the document of title of B/L shall still be one of the important subject to be conscientiously researched.
Rotterdam Rules;B/L;document of title;control right
DF961.9
A
1003-7659-(2010)02-0019-05
傅廷中.《鹿特丹规则》视角内提单的物权凭证功能之解析[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21(2):19-23.
2010-06-20
傅廷中(1953-),男,辽宁铁岭人,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lawftz@mail.tsinghua.edu.cn(北京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