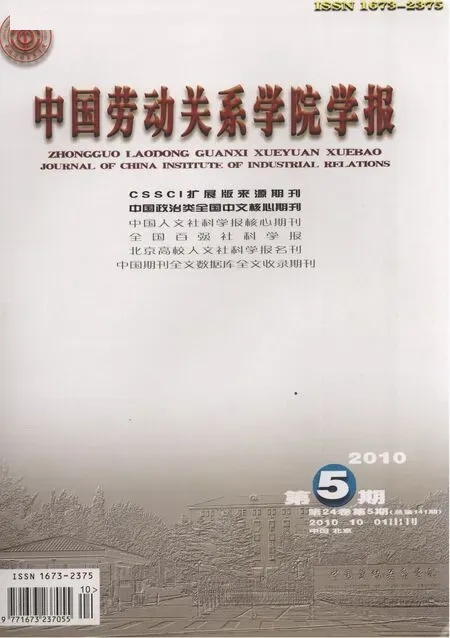寻找“世纪迁徙”中的数字路标*
——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前瞻
2010-02-15杨英新仝文瑶
杨英新,仝文瑶
(河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寻找“世纪迁徙”中的数字路标*
——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前瞻
杨英新,仝文瑶
(河北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0)
媒介素养赋予人们信息社会的生存之道,且关乎全民素质的提高。在媒介素养教育已在中国落地生根之时,身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双重边缘群体——农民工,也急需开启媒介素养教育之门,藉此找到信息社会的路标,有效利用大众媒介,推动自身继社会化进程。
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
一、媒介素养与农民工的“世纪迁徙”
“媒介素养”是人们对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自 20世纪 30年代英国学者提出媒介素养问题以来,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在许多发达国家普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在 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至今已形成一定规模。相比之下,媒介素养教育进入中国大陆较晚,90年代末被传播学者卜卫引入,但近年来,后发之势强劲。大家已经认识到,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里,公民素质亟待提升,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培育的重要方面,不可小视。从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来看,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多集中在青少年,针对弱势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刚刚起步,在中国,针对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更是处于空白。而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发展与和谐并重,且处于转型期的特殊社会语境下,在社会弱势群体中,开展包括媒介素养在内的全方位的素养教育尤为必要。
中国农民,正以每年 500万人的速度进城,加入到 1.2亿的打工大军中,演绎着一场规模空前的“世纪迁徙”,也形成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他们不远千里都市寻梦,成为地理和文化上的“双重移民”;他们多是中国农民中的精英,渴望通过辛勤劳动为城市认可,对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充满期待;与此同时,还要在新环境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可以说,农民工群体承受着适应与发展、经济与心理的多重压力。在“世纪迁徙”的大潮中,他们急需找到推动其完成顺畅的继社会化的能源,以及释放、缓解压力的渠道。根据笔者之前对河北省石家庄市农民工群体所做的调查,大众媒介已成为农民工城市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平均每天接触时间在 1—3小时的比例占到 37%,71%的人认为进城后的媒介接触总量增加。尽管受到诸多条件限制,大众传媒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影响力已不可小觑,且有扩大化的趋势。但调查也显示了与之对应的另一个事实——农民工媒介素养水平整体偏低。要知道,在媒介化的城市里,一个不善于“使用媒介”的人,就是一个与社会信息隔绝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实现进步的期望,不可能持续成长的倾向,不可能做好适应变迁的准备[1]。有意识地在农民工中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引导其找到信息社会的路标,有效利用大众媒介完成城市化进程,已迫在眉睫。
二、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先行者卜卫指出:“媒介素养教育应该特别尊重参与者的本土经验和地方知识,媒介素养教育不是自上而下,而应该是自下而上,需参照本来的知识和经验,以受众为中心,根据受众需要来探讨所要达到的目的。”[2]具体到农民工的媒介素养教育,结合其整体文化水平及实际需要,可重点强调如下层面。
(一)媒介认知
由于文化水平不高,生活范围狭小,农民工受众对大众传媒产生了极强的神秘感和崇拜感,神秘和崇拜极易带来盲从,同时也过大拉开了双方的距离。所以,对农民工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首先要提升其对媒介和媒介信息的认知。其中包括:
大众传媒的功能是什么?在诸多农民工眼中,媒介的功能更多是提供娱乐,他们通常忽视另一更加重要的功能,即提供信息。要知道,一个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信息性内容在媒介接触中是否占有足够比例。大众传媒功能的不平衡利用,必然阻碍农民工的个人现代化进程,同时加大其与市民群体的知沟差距。
信息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作为受众的农民工,有必要了解其中奥妙。了解谁是信息的制作者,制作流程是什么,如,新闻是记者采集、由编辑整理、经总编审定,还要经过新闻审查等。还可根据受众的接受度,适当介绍新闻业务的基础知识,如了解版面、栏目、节目等概念,了解报纸发行知识以及媒介经营运作。了解媒介产品常用的技术表现手段,如三维动画技术、计算机模拟技术、特技镜头,可以塑造逼真的荧幕效果。
媒介信息就是真实世界吗?任何媒介信息都不可能完全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总会或多或少掺杂传播者的主观意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不仅向我们提供了信息,也左右着我们对客观事实的感觉和判断。帮助农民工理解这个道理,使其成为清醒的媒介社会公民。
(二)媒介使用
要成为信息的主人,必须学会使用媒介,对农民工受众来说,要注意如下方面:
首先,广泛了解媒介接触渠道。笔者之前的访谈发现,一部分农民工之所以媒介接触频率较低,并非因缺乏媒介接触意识,而是不了解经济实惠、方便的媒介接触渠道。比如,有人认为书籍、杂志只可在书店、报刊亭买,而实际上,超市、图书批发市场、网络书店 (包括旧书网店)、旧书摊都可以买到经济实惠的书刊。同时,也有一些途径可免费获得媒介资源,如书报栏、社区图书馆、部分城市图书馆,还可主动联系一些捐赠书籍的公益组织。近年来,各地政府对公共媒介设施的投入不断加大,农民工要对此类信息多留意,熟悉公共媒体位置。
其次,掌握媒介的操作技巧。传统媒介操作简单,但网络和手机媒体对农民工来说却存在一定难度。很多人不会操作电脑,不会上网、浏览、发帖、邮件、聊天等基本技巧。手机的使用也往往限于打电话,更多功能并未开发利用,如收发短信、拍照、上网。
再次,能从媒介获取所需信息。对于农民工普遍关心的问题,如就业、个人技能提升、法制以及子女教育,还有进入城市后,引发的一系列心理问题该如何调试等,都可以在大众媒介找到指导。所以,要熟悉媒介资源,知道去哪里找、怎样找,及利用媒介实现自身发展目标。
(三)媒介“解毒”
海量的媒介信息鱼龙混杂,一些媒体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不讲社会责任,低俗信息泛滥,虚假信息匿身其中,一些新闻、影视片故意制造暴力、凶杀等故事作为“卖点”。在这类信息的“易感受众”中,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便是其中之一。所以,要让其具备识别、过滤信息的能力,做到批判地观看,认真地思考,减少媒介接触中的盲目和被动。比如,掌握识别虚假就业信息的方法和手段,识破虚假广告的惯用伎俩,揭露不良言论者的隐秘意图,防范网络交友中的陷阱等,在思想和方法上构筑起对负面媒介信息的“防火墙”。
另外,能够对媒介的偏见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以农民工群体自身来说,作为“城市移民”,这个人群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都与城市居民有着巨大的差距,特别二元户籍制度划分更为这一社会阶层贴上标签,单一个体的具体问题更被污名化为整个群体的共同问题,礼仪失当、行为怪异、道德弱化成为扭曲农民工媒介形象的三大“特征”[3]。这些内容,不仅型塑了城市人群对农民工群体的不良印象,对农民工群体自身也会带来消极影响,出现所谓的“自我刻板化”,即个体自认为某群体的成员时,把伴随此种身份的刻板印象加诸于自己身上。其结果是,产生对自我身份的抵触,自我贬低,自我沉沦。也有人因此萌生逆反情绪,误认为,媒体偏见代表了所有城市人的偏见,于是排斥憎恶城市人,甚至走向犯罪。培养农民工对媒介信息的批判思考能力,将会助其抵制负面信息的干扰和误导。
(四)媒介表达
通过媒介发声,是媒介素养的高层次要求,是一种从被动接受媒介信息,过渡到适当主动参与媒介信息的状态。农民工群体“缺乏参与传播活动的机会和手段,缺乏接近媒体的条件和能力,主要是被动地、无条件地接受来自大众传播媒介的信息和那些几乎无法得到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信息、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4]。培养农民工的媒介表达能力,就要使其做到:掌握与媒体联络的渠道,能提出对媒体信息的意见和要求并主动向媒体表达。利益被侵害后,主动希望媒体介入,清楚如何与媒体联系。能主动观察自己周围的环境,如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能积极向媒体反映。面对媒体时,能自如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自身的利益诉求等。在具体操作上,还要掌握给媒体投稿、热线联系、短信联系、写信的技巧等。
可喜的是,一部分农民工精英已经主动与媒介搭桥。农民工民间艺术团体在各地崭露头角,他们业余时间组织演出,展现农民工风貌,同时借媒体东风推进事业发展。以周述恒为代表的农民工作家创作的农民工题材小说、诗歌,在媒体的关注下反响卓著。从心理学角度看,无论哪种参与过程,都能提升农民工自信,使其找到自尊,同时还会带来某种控制感,而适度的控制感,又是维护心理健康之所需。参与媒介的社会意义在于,作为社群的一员,为社群在公共议题上发声,促进了跨族群、跨团体的对话。
三、农民工媒介素养教育的实施路径
(一)激活媒介素养意识
农民工身处城市社会边缘,长期的弱势地位导致他们在认识媒介与自身关系时,往往存在局限,即认为,大众传媒与我无关。这种意识,使得媒介资源大量浪费,也阻碍了媒介素养问题进入其兴趣视野。由此来看,媒介素养教育的第一步,就是要让农民工受众意识到,大众媒介以及媒介素养与生活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对媒介素养的宣传非常重要,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此时尤其要发挥作用,不仅应让媒介素养成为全民性话题,还要对农民工群体媒介生活多加报道,推出农民工媒介素养先进典型,让农民工直接感受到媒介素养的益处。
(二)加大公共媒介设施投入
只有媒介在使用者的生活中具有一定覆盖性和渗透性时,媒介素养教育才具有切实意义。政府应继续加强公共媒体的建设,推进诸如广播电视、社区文化站、电影放映、图书馆等文化惠民工程,还可定期发放免费上网卡,在农民工集中的工作生活地增设报刊栏,免费或减价向农民工提供报纸等,为他们接触媒介提供便利。只有将媒介接触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必然性,媒介素养的提升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可拓展的空间。
(三)推进多元化社会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整合社会资源,多个组织共同努力、相互配合,才能有效开展。
媒体应主动接近农民工受众,邀请他们走近媒体,参观报社、电台、电视台,讲解媒体如何运作。亦可开设特定栏目或媒介知识讲座,建立专门的媒介素养网站,构筑媒介素养教育基地。香港电台 (RTHK)已先行一步,在香港教育局的资助下,他们成功制作了多期传媒教育节目,反响良好。值得注意的是,手机媒体操作简单、价格便宜,在农民工群体中普及率很高,它集传统媒体优点于一身,兼具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特性。手机短信短小精悍、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更新快,是传播媒体素养知识的良好平台,还可实现线索收集、调查、意见反馈等多种功能,为农民工发出自己的声音,实现媒体表达提供便利,手机媒体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有着很大的开发空间。同时,媒体可拓展思路,适当提供给农民工亲自创作媒介信息的机会。曾经供职新华社、《南方周末》和《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周浩曾策划“厚街”民工自拍系列,将机器交给农民工,让他们亲自对自己的生存、工作环境做记录,不仅让农民工在实践中参与使用媒介,同时也成为他们自我身份表述,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媒体工作者还需提高自身媒介素养,充分考虑农民工受众特征,重视媒介产品质量,为培养其良好的媒介素养创造有利环境。
杜区在举办知识讲座、技能培训以及文化休闲活动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教育将成为居民全民性教育与终身教育的基本单位,成为学校正式教育的有力补充。以社区为单位,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是当前国际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新趋势。社区可与一些学术性、社会性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合作,邀请传媒专家、媒介从业人员以及教育学者针对社区农民工举办媒介素养讲座,推荐优秀媒介资源。
农民工所在的工作组织,以及农民工自发的集体互助组织,也可以组织媒介素养培训,邀请新闻院校的教师,以及媒体机构的编辑记者开办讲座、举办形式活泼的主题活动,对农民工进行媒介知识的普及。工作组织还可鼓励辅助农民工自办媒体,如职工内部报纸、职工宣传栏、职工广播等,让农民工在实践中培养媒介素养。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热心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民间公益组织,已经开展了成效显著的工作。以中国香港为例,“传媒教育协会”致力于推动和发展香港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年轻人媒介素养水平。“香港教育城”是由“品质教育基金”资助设立的一项大型教育基础设施,提供一系列开展专案式媒介素养学习的场所。“明光社”为社区、学校和教堂提供媒介素养讲座,制作教材,出版书籍和相关材料,组织传媒教育营,为青年工作者提供培训,该组织设立的传媒教育资源中心向公众开放。在中国大陆,这类组织远未形成规模,媒介素养教育事业需要民间有志之士的加入。
倡导大学生志愿者在教师的指导下,进入社区,以及农民工集中的工作组织,进行媒介素养教育。还可以征集被城市人淘汰,但仍可使用的媒介设备和媒介资源,赠送给经济困难的农民工使用。
(四)借力农民工“意见领袖”
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却依然在原有的关系网络中交换信息和资源,寻求支持与庇护,他们与城市人的联系极为有限。亲缘和地缘关系依然是把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在以信任为基础的交往和互动中,他们建构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群体中,已经涌现出部分思想先进的精英,以农民工精英为突破口,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树媒介素养教育品牌,更要使其发挥其意见领袖的作用,将媒介素养意识和媒介素养知识,通过人际传播传导出去,必将在分外信任和依赖内群体关系的农民工群体中产生连锁效应,营造起媒介素养的学习氛围。媒体亦可培养部分农民工通讯员,作为意见领袖,更架起农民工与大众传媒沟通的桥梁。
(五)加强文化基础素养培训
媒介素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基础素养,从听、说、读、写的技能,到批判思维的培养,无不与之相关。农民工学历以初中为主,整体文化程度偏低,只有对农民工进行补偿性的成人教育,让他们学习必要的文化知识,才能保证媒介素养教育顺利开展。
(六)与农村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形成合力
部分地区农村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已在酝酿之中,如果将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必将提升新一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基础,与成人媒介素养教育形成合力,达到更好的培养效果。早在上世纪60年代,英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就陆续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中小学的正规教育课程,中国可借鉴他们的先进经验,逐步在农村中小学开设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相关课程,通过组织学生记者团、支持学生办报、办广播等具体的实践活动提高农村学生的媒介素养水平。当媒介素养教育形成延续性,各阶段的媒介素养教育目标就可有所侧重,青少年时期可强调媒介认知与防御,成年之后则可侧重媒介使用与参与。
四、结语
传播学者麦克鲁汉在《理解媒介》中说,媒介文化已经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的过程,将每一个人都裹携其中。生活在媒介文化所制造的仪式和景观之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生存”。实际上,媒介素养不仅赋予我们信息社会的生存之道,还关乎全民素质的提高。在媒介素养教育已经逐步进入中国青少年的生活图景之时,身处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双重边缘群体——农民工,其实也急需开启媒介素养教育之门,即使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他们自己。但我们相信,在社会各方的推动下,不久的将来,“媒介素养”将不再为这个群体所陌生,农民工群体在艰辛的“新市民”之路上必将由此获益。
[1]冯恩大 .社会变迁中的农民工与现代化启蒙 [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5).
[2]卜卫 .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 [A].陆晔 .中国传播学评论 (第三辑)[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3]董宽 .传媒歧视遮蔽利益诉求——透视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媒介表达 [J].新闻三味,2006,(12).
[4]段京肃 .社会发展中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J].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A Preview of theM edia L iteracy ofM igrantWorkers
Yang Y ingxin,TongWenyao
(Hebei Nor m al University,Shijiazhuang050000,Hebei Province,China)
The media literacy gives people the way of existence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It also rela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overall quality of the nation’s population.As the marginal grou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migrantworkers need to open the door of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signs of information society,to effectively use the public media and to enhance the course of socialization for themselves.
migrantworkers;media literacy;education
F241.33
A
1673-2375(2010)05-0082-05
2010-08-10
杨英新 (1979—),女,河北承德人,硕士,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仝文瑶 (1963—),女,天津人,河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院长。
本文系河北师范大学科研基金项目相关成果。(项目编号:W2007Q44)。
[责任编辑:寸 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