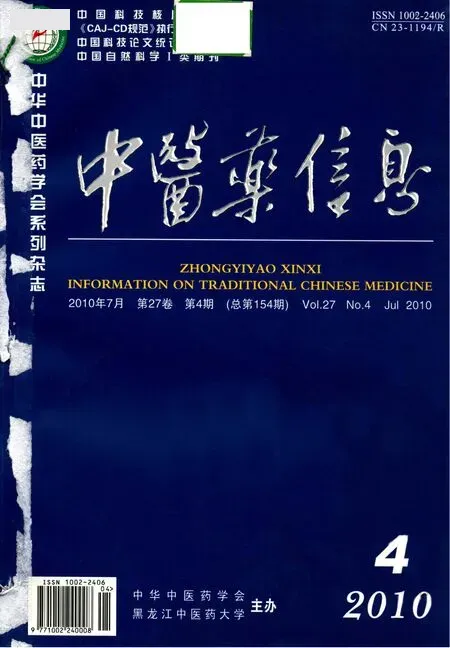近代中医教育的反废止努力——以课程教材建设为例
2010-02-09周鸿艳李志平李和伟
周鸿艳,李志平,李和伟
(1.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世界文明史中,“中国文明的连续性是不容忽视的,在疾病记载方面,在许多文明中,中国几乎是唯一的拥有连续性著述传统的国家”[1],中医学在古代中国乃至世界都是较为先进的。然而到了近代,伴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一统天下的地位被逐渐撼动。正如丁福保所说:鸦片战争以后,“西人东渐,余波憾荡,侵及医林,此又神农以后四千年以来,未有之奇变也”(丁福保历代医学目录表)。中医学是否还应该存在,能否继续传承下去,成为中医近代史上争论的核心问题。李约瑟所赞誉的“连续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此,中医的教育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有中医教育则中医兴,无中医教育则中医亡”。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一直是近代中医界反废止的主要内容。在争取中医教育合法化过程中,中医界除了重视加入学制外,更重视中医教育的内涵建设,尤其是在课程教材建设方面进行诸多尝试。
1 对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在清末颁布的壬寅癸卯学制中,壬寅学制没有规定医学的具体课程,也没有真正实行。在癸卯学制中医科又分医学及药学两门。医学门30门课程中只有1门中医学课程,而且没有分科、没有名称,只是笼统地称之为“中国医学”。药学门16门课程中只有1门中国药材。癸卯学制中医科虽有中医、中药内容,但分别仅有1门。之所以造成这一局面,固然和清末的改良派强调引进西学、模仿日本有关,同时也与中医学的课程教材建设欠完备不无关系。即使当时中医学能够加入学制,也很难像西医学那样列出完整的课程体系。因此,1904年,何廉臣在最早的中医杂志《医学报》上撰文说:“今日中医开智莫若仿欧美治科学之法,先编定教科书,将中医之缺者补以西法”。对于中医教育向近代的转型,当时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至民初壬子癸丑学制,大学医科课程51门,药学课程52门。已经完全没有中医、中药学方面的内容。壬子癸丑学制颁布后,引起了中医界的警觉,遂导致近代医学史上首次中医抗争救亡运动。北洋政府在各界舆论压力下,强调“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在事关中医教育的学制问题却说:“厘订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此语虽有搪塞之嫌,但以当时之条件,短时间内编订中医学课程,确实难度较大。1915年,丁甘仁为兴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书申请立案,虽获备案,但教育部批复中也特别指出“惟中医学校名称,不在学堂系统之内,本部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内,亦未定有中医各科课程”。内务部则强调“俟该校课程拟定后送部核查可也。”
由此可见,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私人办学,都没有较为完备的中医学课程体系,教材建设更是无从谈起。这一局面也是中医学被摒弃于学制之外的一个内在因素。认识到这一问题,中医界的有识之士开始重视中医学课程教材的建设,以期为中医教育的合法化奠定基础。
2 对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的不懈努力
希冀中医教育加入学制,一直是中医界反废止的重要内容,但每每功亏一篑。在这一过程中,中医界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中医教育若要加入学制,就必须改进和完善中医教育自身,使之规范化,符合近代教育模式。基于这一思路,从清末到民国,中医界在课程教材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2.1 清末对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的尝试
清末的中医社团往往附带有中医教育的功能。如周雪樵等人创办的“中国医学会”就附设医学讲习所,开列有解剖、生理等12门课程。并于1909年起陆续编写教材,《素灵讲义》即是该会公开发行使用的第一部中医教材。上海的另一中医社团“上海医务总会”也特别重视教育,在第一次议员会议上,编写中医教科书被列为首要任务。
2.2 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
由于中医界对壬子癸丑学制“漏列中医”的反抗,“北洋政府对中医基本上执行放任、观望政策”。从而给中医教育造成了一个较宽松的发展环境,兴办了多所私立的中医学校,为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的探索提供了平台。在课程建设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共开出生理、本草等18门课程。而地方兴办的山西医学传习所共开出内经、解剖等20多门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黄墙朱氏私立中国医药学校”教务主任的张山雷非常重视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撰写了《黄墙朱氏私立中国医药学校编制课程商榷意见书》,这是民国时期有关中医教材编写、课程建设的重要历史文献。在“意见书”中张山雷对于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与中医学的关系有较为正确的认识:“谨按吾华医学,未入耕堂,编制课程,茫无成法,向来俗尚,止有李氏《必读》、汪氏三书,似为学子问津之初步。此外则各不相谋,随意自择,从未有通行规则,以何者为必备之书,必由之道,此吾邦医学所以纷别淆杂而莫可究诘也。”[2]
鉴于1925年加入学制的再次失败,在1926年底至1927年初,李平书、夏应堂等人积极组织中医课本编辑馆,制定计划以求统一全国教材。由于条件所限,这一计划并未得以贯彻,但统一教材问题受到中医界的广泛认同。1928年,全国各地中医教育界人士齐集上海,研讨统一教材问题。各地代表提出自己不同的学术见解,因意见不统一,最终未能就课程、教材、学制等问题达成统一的意见。但神州医药总会委员蒋文芳提出的“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的理论,制为完善之学说”成为其后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的指导原则。
2.3 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
北洋政府对中医教育的不作为,唤醒了中医界的觉悟,遂有各种办学的努力和尝试。20年代末,各地中医学校已渐趋成熟。因而,为争取中医加入教育系统,迫切需要集合全国的力量,总结各地办学的经验教训,并采取务实积极的方针,首先统一全国的中医教材和课程。
1929年7月7日至7月15日,中医药界在上海召开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该次会议由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出面召集,到会者有上海中医专校、中国医学院等9所学校的教务负责人。均系我国近代中医教育界著名人物。这次会议上议定了中医学校入学资格、修业年限、学说采用标准,并确定了29门课程及教授时数。审定通过了五年全日制中医专门学校应开设的各门课程及教学时数和各年度的教学安排。这次的全国中医教材编辑会议,是近代中医教育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我国中医教育已经开始成熟,其对近代乃至现代的中医教育均有深远影响。
3 近代中医学课程教材建设的启示
课程与教材建设是近代中医学反废止、求生存努力的重要内容。以图通过自身符合近代教育规律的变革,能够加入学校系统得以存亡续绝。这显然是一种开创性工作,它不同于西医的课程教材可以直接从外国翻译借鉴,因此也就决定了中医学课程教材的建设需要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比较显现的矛盾就是如何处理好中西医的关系,包括中西医课程比例如何分配?教材中中西医内容如何体现等问题。应该说,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近代中医教育家们的做法还是较为恰当地。
如1928年的统一教材会议,中医界对教材编辑的指导思想意见分歧很大,《伤寒今释》作者陆渊雷先生与《包氏医宗》作者包识生先生各持一端,争论三日而不能决。陆渊雷是采用西医理论之激进派,包识生是力主中医体系保持完整之正统派。但最终还是达成了“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的理论,制为完善之学说”的基本原则。
近代中医课程教材建设的不断探索,主流是沟通中西。与西医对待中医的态度截然相反,中医药界的主流并没有拒绝西方医学。近代史上没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办教育时主张完全脱离西医,搞所谓的纯中医教育。中医名家谢利恒、恽铁樵、包识生、张山雷、蒋文芳、陆渊雷、时逸人等先生,大多参与了中医课程建设和教材编撰。在具体学术观点上,他们的认识可能有所不同,但在沟通中西医学上是一致的。
总之,近代中医界克服政府阻碍、办学经验不足等困难,先后兴办了70多所中医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普遍开设中、西医学课程;教材建设上,共编写170多种教材,并进行了统一教材的努力。中医教育通过自身的变革,逐渐接近近代的教育模式,为建国后中医药高等教育的迅速勃兴奠定了基础。
[1] 潘吉星.李约瑟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996.
[2] 张山雷.黄墙朱氏私立中国医药学校编制课程商榷意见书[J].中医教育,198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