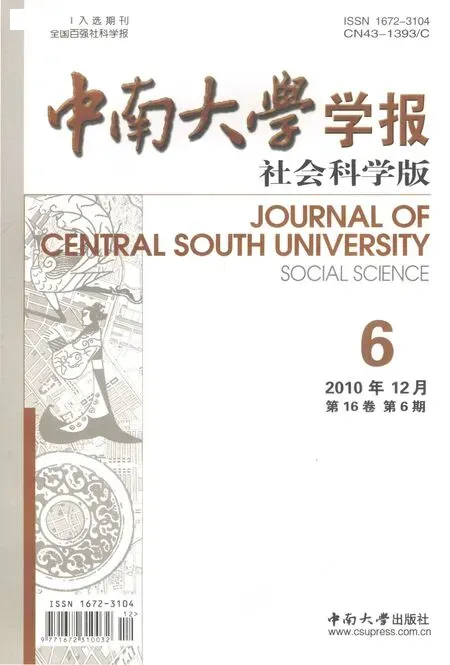坎普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
2010-02-09李霞
李霞
(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 南京,210093)
1964年,苏珊·桑塔格在发行量很小的杂志《党派评论》上发表了《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让她一夜成名,成为时代的偶像。因为敏感如她,感受到了60年代的文化新潮流,顺应了时代要求,愿意成为新文化代言人。另外,还因为桑塔格找到了一个适合自己的话题:坎普。两方面的结合,让桑塔格站在了时代潮流的尖峰上,尽情书写她对六十年代文化的理解和企盼。
坎普,在桑塔格眼中,已超越了其原有负面的狭隘含义,成为当代文化感受力的先锋和典型。她详尽地描绘了坎普丰富复杂、充满悖反的美学内涵。一方面,启发我们联想坎普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联想到坎普和现代主义的继承、超越之复杂关系。
一、坎普的美学内涵
《关于“坎普”的札记》开篇就非同一般,桑塔格写道:“世界上有许多事物还没有被命名;还有一些事物,尽管已经被命名,但从来没有被描述过。其中之一便是以‘坎普’这个时尚之名流传的那种感受力。”[1](320)但她接着又退一步,说克里斯托弗·伊斯特伍德在小说《夜晚的世界》中花了两页的篇幅对坎普粗粗勾勒,此外再无他人论述过。这即意味着,在坎普这块领地里,桑塔格是真正的领主。坎普又是什么呢?
“坎普(Camp)”,原本为同性恋圈子中的“黑话”,简单讲,就是“娘娘腔”,本为男人却举止温柔,故引申为举止行为故意夸张。无疑,坎普是和同性恋有联系的。坎普是小圈子里头秘密的东西,不能和公众交流,谈论坎普,就是出卖坎普,这是致使其长期无人描述的原因。桑塔格深知坎普和同性恋的关联,也知道谈论坎普会在世人心中引起怎样的微妙情感。但她克服了心理障碍,勇敢地触及了这一敏感话题,在勾连坎普和同性恋时,使坎普又超越了同性恋。“尽管不能说坎普趣味就是同性恋趣味,但无疑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别的契合和重叠之处。……并非所有的同性恋者都有坎普趣味。然而,总的说来,同性恋者构成了坎普的先锋 以及最清晰可辨的观众。”[1][337]同性恋者为使自身合法化,认为自身拥有不一般的、非世俗化的感受力和审美趣味——坎普。在最初的内蕴上,桑塔格进一步以58条札记的形式,细致地刻画了坎普所蕴含的审美趣味与当代文化思潮的复杂关系,将其演绎成一种当代先锋趣味和感受力的化身。
坎普包含怎样的美学内蕴,和当代文化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坎普坚持在审美层面上体验世界、感受生活,是唯美主义的极端表现,它尤其重视事物形式、技巧方面的因素,而对事物的实用性、功能性不予关注。桑塔格认为,自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成为坎普。坎普是“对夸张之物、对‘非本来’的热爱,是对处于非本身状态的事物的热爱。”[1](324)她指出,极好地展示坎普风格的是“新艺术”作品,该类作品通常将一种东西转化成另一种东西。比如,将灯具上盘绕个蛇,认为具有东方情调,并不为取悦他人;将房子设计成岩洞;将地铁口设计成了铁铸兰花柄的形状。坎普是将生活看成是戏剧的延伸,以审美的眼光打量一切,日常生活呈现审美化。坎普所代表的新式生活态度和审美趋势是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新涌现的社会现象。费瑟斯通指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科技不断创新,经济高速发展,商品得以过度生产;消费不再以商品使用价值为目标,而趋向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以显示自身所独有的审美品味和社会身份。坎普趣味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恰当描绘,成为涵盖生活风尚的关键之语。此词一出,立刻风靡全美,因为桑塔格改变了其旧有的含义,并赋予其新的内核,新旧在此融合,道出了六十年代新潮人物叛逆、喜新的复杂微妙的心理。
坎普以审美的眼光去感受世界,它一反惯常的实用标准和道德标准去评判事物,而是以审美的眼光去关注事物的形式、技巧,去体验、品味一切。因此,坎普对一切事物都平等对待,具有现代民主精神,超然地去面对一切,悬置评判。桑塔格指出,现代的坎普者和过去的贵族纨绔子虽然都属于自命不凡的鉴赏家,但二者又有本质的不同。她形象地描绘道:“老派的纨绔子厌恶粗俗,而新派的纨绔子,即坎普的热爱者,则欣赏粗俗。老派的纨绔子常常感到厌恶或者不胜厌倦的地方,坎普鉴赏家则常常感到愉悦、兴致盎然。老派的纨绔子用洒了香水的手绢捂着鼻子,而且很容易昏厥,坎普鉴赏家则吸着去嗅那些恶臭,而且为自己坚强的神经而洋洋得意。”[1](336−337)过去的纨绔子寻找那些稀有的、高档的物品;而现代的坎普者,却能欣赏大众化的、普通的东西。老派纨绔子是精英文化的鉴赏家,鄙视大众文化;而现代的坎普者却是大众文化的热爱者。
面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坎普趣味并不判定谁高谁低,谁好谁坏,而是平静地欣赏一切,接受一切。坎普爱好者从不融入事物,而是隔着远远的距离谛视事物,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相参与。它倡导一种游戏精神,玩笑式、不真诚地看待事物,废黜严肃。坎普的许多范例都是过去糟糕的艺术、失败的艺术,而不是当时就获得成功的作品。之所以能成为坎普,是因为我们与其不再有任何瓜葛,不再为其失败所困惑,而能以审美的、非功利的眼光审视它、欣赏它。“人们可以以严肃的方式对待轻浮之事,也可以轻浮的方式对待严肃之事。”[1](335)所以坎普是游戏式地对待一切,显得宽容而慈爱,认同于它所品味的东西,缺乏悲剧意识。
基于坎普是审美地、游戏式地对待事物,注重事物的技巧和形式审美,可以推知,坎普是无关道德的。坎普“体现了 ‘风格’对‘内容’、‘美学’对‘道德’的胜利,体现了反讽对悲剧的胜利。”[1](334)坎普提倡感受、体验艺术、悬置道德评价。坎普对待艺术的方式是与六十年代美国的新兴文化精神相合拍的。
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坛,新兴艺术层出不穷,每天都有新艺术诞生。这些新兴艺术,打破了以前的艺术常规,突破了传统艺术形式(如小说、戏剧),在艺术型态、媒介等方面有所超越;所用的材料和手段耀人眼目,从科学技术到人的主观幻想,从现成的艺术品到日常的生活用品,甚至生活垃圾,都可被用于艺术中。艺术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去表现爱情、战争这些崇高的主题,而是表现“人们熨衣服、梳头、洗头、晃腿,他们微笑、睡觉、抽烟、看电影、打发观众去看电影、打牌、看报、理发、玩跳房子游戏、打球、溜冰,他们做爱,也做饭”。[2](152)艺术表现平常的生活,不再教育、启迪大众。这遭到了老派艺术家的诟骂,认为新兴艺术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垃圾艺术、大众艺术,不能担负引领人们走向真、善、美的重任,应予以清理。此时,需要一种新的审美趣味来为新兴艺术寻找合法化依据。而坎普趣味就是代表着一种新的审美标准,切合了美国六十年代新兴文化的要求。
坎普所倡导的游戏式地对待事物和艺术,平等地欣赏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就是在消费社会背景下对待新兴大众文化的方式:艺术也仅仅是消费品,不再关注其道德意义,只注重其形式带给人的愉悦和感官刺激,仅此而已。坎普倡导悬置道德评价,平等、民主地对待一切,其实是用多元化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给新兴艺术留下了发展空间。于是,新兴的大众化艺术在坎普大旗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引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革命。
二、坎普和后现代主义
迈克•费瑟斯通在《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一词流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纽约。当时,桑塔格、哈桑、凯奇等一批年轻的艺术家用该词特指一场反对已被体制化、凝固化的现代主义的超越运动。他还分析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相关特征:“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被消弥了;人们沉溺于折衷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性特征衰微了,还有仅存的一个假设:艺术不过是重复。”[2](9)管窥费瑟斯通的分析,可以得知,不仅桑塔格和后现代的兴起有密切关系,而且坎普的美学内涵与后现代艺术也不谋而合。
坎普的内涵在许多方面都暗暗切合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一切,或可以这样说,正是有了坎普美学的助推力,后现代主义美学才大张旗鼓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坎普和后现代主义的关联不容置疑,是后现代主义在艺术上的一个翻版。
首先,坎普主张审美地对待一切,悬置道德评判,这和无深度、娱乐化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消费精神相吻合。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中,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而与各阶段对应的文化分别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杰姆逊认为,现实主义文学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文化表现,“金钱”是其叙事的关键符码,关注现实和社会;现代主义文学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表现,“时间”是其话语的关键符码,关注人的内心和心理;后现代主义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表现,“空间”体验是其叙事的主要特征,一切都空间化,去中心化,一切皆成为消费品,包括艺术,艺术成为消费品,变成一种娱乐的对象。
桑塔格认为,依据人们对艺术感受力的不同,可以将历史上的艺术分为三类。“第一种感受力,即高级文化的感受力,基本上是道德性的。第二种感受力,即体现于当代众多‘先锋派’ 艺术中的那种极端状态的感受力,依靠道德激情与审美激情之间的一种张力来获得感染力。第三种感受力,即坎普,纯粹是审美的。”[1](344)不言而喻,第一种感受力是传统艺术所追求的,偏重道德审美,认为艺术应是承载真、善、美的工具,其道德功能大于审美功能。第二种感受力是以现代主义、先锋派的艺术为代表,注重形式的不断翻新,作品因而显得深奥难解,对观众持疏远态度,对社会持批判和否定态度。因而审美激情和道德激情始终处于矛盾状态,读者欣赏时的感情是紧张、痛苦和喜悦并掺。第三种感受力——坎普,是审美的、轻松的、愉悦的,欣赏者抛弃了道德上的重负,只是沉浸于艺术带来的感官愉悦、感官刺激当中,超然于事物的道德和功能之外。
可见,桑塔格的坎普感受力是和杰姆逊所说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反对艺术承载道德,反对赋予艺术的深度意义,只注重艺术审美及审美愉悦,艺术已和其他消耗品一样,变成提供娱乐、刺激之一种。
其次,坎普致力于消除高级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这和后现代主义狂欢化地对待各类艺术是相通的。后现代主义著名学者菲德勒有句名言:“跨越边界,填平鸿沟”,说的就是要打破雅俗之间的分界。现代主义运动从19世纪五十年代始,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式微,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现代主义非常严格地区分出各门艺术的媒介特质和边界区域,各门艺术有其自身的不可替代的特征,彼此不能逾越。如绘画和雕塑,同为美术,但绘画是平面的、二维的艺术,雕塑是立体的、三维的艺术,二者各有特征,不可取代。而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兴的艺术不断涌现,如电影、多媒体声光节目、摇滚乐;同时,艺术媒介的常规也在不断被打破。从工业技术到私人的主观幻想,从现成的艺术作品到日常的生活用品,甚至生活垃圾,都可以被用作艺术的原材料。艺术和非艺术的界限被打破,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消失,新兴的后现代艺术是个混杂的艺术,完全不同于纯净的、界限分明的现代艺术。艺术为何会朝这方面发展? 周宪在《审美现代性批判》中指出,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媒介、形式、技巧已经发挥到极致,没有再发展的潜力;若要推进艺术,必须让艺术在混杂和蒙太奇中寻找新的支点。[3](334)后现代的艺术是一个去分化、没有边界的、众声喧哗的综合体,正如杰姆逊所说,“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距离正在消失。”[4](129)
坎普是桑塔格面对六十年代的新兴艺术而提出的新审美标准,以对抗于以道德为准绳的传统审美标准。坎普不对事物作任何道德评判、好坏评价,只是审美地远距离欣赏。这击碎了高级艺术所具有的道德优越感,使之能和通俗艺术站在同一平台。坎普所具有的平等、民主精神,就是不敌视大众艺术,以一种多元共生的心态让大众艺术拥有发展的空间和可能。坎普之物就是些边缘化的、曾经失败的艺术品,开始并非为高雅文化所认可;坎普欣赏者却懂得欣赏它的美,不为主流文化标准所左右,这足以显示其与高雅文化相抗衡的心态。更为明显的对抗是坎普之物的表现方式,它青睐滑稽模仿、仿拟、戏剧性,以此篡改经典作品,给欣赏者带来的是反常、滑稽,可笑的感觉,这与强调个性、原创性和崇高的现代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高级文化被从神庙下拉下来,和通俗文化一起构造了艺术的狂欢世界,成为娱乐品,是各种刺激的来源物。
第三,坎普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这与后现代主义的“小叙事”精神是相通的。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指出,现代主义主要是宏大叙事、元叙事,比如解放人类、理性这样的启蒙叙事;而后现代主义是对元叙事的质疑和解构。现代强调总体性、统一性、普遍性,而后现代强调差异性、不确定性、局部性、多元化。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在《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中说:“后现代告别了近代的现代的基本要求:统一的梦想。这些统一的梦想从普遍数学模式的构想经过世界史哲学的规划一直打到社会乌托邦的全球性计划。后现代的彻底的多元性与这些统一的限制一刀两断,因为它们指望一种整体,而这种整体毕竟只会兑现为极权主义。”[5](316)后现代主义基于反思现代主义宏大叙事所导致极权主义等重大历史问题,一直强调小叙事,避免宏大叙事。后现代主义关注日常生活、解构崇高、在琐碎中发现即时的美,反对本质主义。而后现代文化以视觉性、愉悦性、当下性、震惊感代替了对艺术的反思。
坎普主张消解道德、审美地看待一切,注重事物的技巧、形式、风格,及时发现它们给人类感官所带来的感受,反对将艺术作为教导人类迈向真善美的路标。坎普爱好者关注生活中的日常事务,如一个门把手的美、一个灯具之美、一部电影带来的愉悦等,认为日常事物自有其美所在。他们已成为生活和艺术中轻松的游戏者、旁观者,而不是批判者和沉思者。可见,坎普和后现代主义都关注“小叙事”,发现和认同日常生活之美,反对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失去了启蒙精神所留下的批判现实精神。
显而易见,坎普和后现代主义在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二者的关联不容置疑。确切地说,桑塔格的坎普趣味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急先锋,在她的带领下,后现代主义这杆大旗终于插入了当代文化的腹地。
三、坎普与现代主义
众所周知,1993年,60岁的桑塔格亲赴萨拉热窝,支持他们的正义之战;2001年的 9·11事件,全美全世界都在声讨恐怖主义,她却站出来指出美国政府的极权和愚民政策。可见,桑塔格不是一个“什么都行的”后现代主义式虚无主义者,而是一个追求正义和真理的现代主义者。桑塔格在一次采访当中明确地说,她并不觉得后现代这个词有什么用,并不喜欢自己和后现代扯在一起。[6]难道桑塔格后期转变立场了吗?
其实,桑塔格一直心怀现代主义的启蒙、叛逆的救世精神,现代主义从未远离过她。现代主义的精神在她早期作品所描绘的“坎普”中就已存在。坎普与后现代主义关联显而易见,而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则比较隐晦。在《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中,桑塔格有好多看似矛盾的、似是而非的话语,在这些话语中就蕴含着坎普与现代主义精神无法割裂的脐带关系。
首先,坎普和现代主义一样,都重视艺术作品的形式审美,认为形式是艺术的本体。现代主义艺术追求新奇,关注作品形式的花样翻新,形式是现代主义的生命。现代主义反对现实主义,因为在现代主义者看来,现实主义的写法是对现存社会的认同,是对现实的拙劣模仿,已失去了批判力。若要批判现实,必须用艺术的形式,区别于现实的维度,来对抗现实。马尔库塞认为,正是艺术形式使艺术内容超越了现实,使其不同于现实的维度,它是艺术真理的美的显现;是形式,使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得以表现出来。形式的性质,否定那些压抑人的质料,具有对抗现实的力量。
坎普坚持在审美层面上体验世界,尤其重视形式、技巧方面的因素。坎普趣味要求艺术偏重形式的审美,丢弃道德的重负。坎普要求用形式取代内容,桑塔格认为:“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从来就不只是某些思想或道德情感的表达。它首要地是一个更新我们的意识和感受力、改变滋养一切特定的思想和情感的那种腐殖质的构成的物品。”[1](348)而新的艺术形式是更新、改变人的感受力的主要来源。当代新兴艺术运用各种媒介创造新艺术,就是在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眼光和思维,拓展人的感受力。这也是反思社会的途径。坎普注重形式,和现代主义者注重形式的初衷和目标是一致的,都将形式视为艺术的本质,并希望通过艺术形式来对抗现实和社会。
其次,坎普和现代主义一样,都批判和质疑启蒙现代性,对抗工具理性主义。众所周知,现代主义兴起之初,是站在社会的对立面来批判启蒙现代性。现代主义强调艺术自律,强调艺术和生活之间的距离,来对抗生活中盛行的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但随着资本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吸纳和消化,现代主义愈益成为资本主义艺术体制的一部分,成为维护现存体制的帮凶,与其初衷日益相悖。比格尔曾论述过制度化的现代主义在当时的文坛所起的规范他者的负作用:“它发展形成一种审美符号,起到反对其他文学实践的边界功能;它宣称具有某种无限的有效性(这就是一种制度,它决定了在特定时期什么才被视为文学)。……它决定了生产者的行为模式,又规定了接受的行为模式。”[7](281)足见,此时的现代主义已经远离了它最初具有的批判质疑的精神,成为体制中的顺从者和获益者。
但现代主义批判质疑的精神并没有死亡,由桑塔格倡导的坎普趣味就是对体制化的现代主义的反抗,继续点燃现代主义批判质疑的精神之火。现代主义强调艺术自律,严格区分生活和艺术之间的界限,严格限定艺术之间的等级区分;而坎普则将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生活中的日常用品、甚至垃圾也可以转化为艺术品,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的区分已没有任何意义。坎普就是针对现代主义的条条框框而来的。现代主义是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颠覆,是对资本主义体制的质疑,自身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但当它成为体制的获益者时,也就违背了其最初的目标。坎普趣味等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主义的又一次反叛,是对现代主义批判精神的又一次实践。虽然坎普欣赏大众化、通俗化的东西,但坎普和现代主义在精神本质上是相通的:批判、质疑现存体制。
利奥塔曾说过,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初期,并不是其末期。他也是从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共有的批判精神看到二者的共通性,才有此结论。坎普趣味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先锋,自然也逃脱不了她和现代主义之间的既叛逆又亲近的关系。
足见,桑塔格倡导的坎普趣味,并不如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断然割裂了和现代主义的关系,并向其发起攻击。坎普和现代主义,二者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集中表现在二者对现存体制的反思和质疑。理解了这些,我们也就懂得了桑塔格为何后来会转向政治的激进之旅,因为她本人自始至终都具有现代主义的批判现实精神。
四、小结
桑塔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坎普趣味,作为一种新的审美感受力,是为了给新兴的当代艺术张本,为其合理性建立理论依据。坎普感受力,为当代通俗文化、新兴文化的发展扫除了理论障碍,促进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蓬勃开展,并最终在当代文坛占据主流地位。坎普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先锋,是它响应了时代的要求并为其代言。
坎普和后现代主义的关联,早有论者指出,但它和现代主义的关系,则很少有人论述。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所致。其一,坎普和后现代的渊源更深厚一些;其二,随着坎普所代表的后现代艺术的发展,它们离现代主义的批判、质疑的精神也渐行渐远。坎普主张审美的生活,具有反抗工具理性的意义,但意义已经非常有限。毕竟,审美地生活必须建立在丰裕的物质基础之上。另外,当代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和现实共谋,融入市场,失去了批评的立场。再有,坎普趣味不会关乎艺术的内容及意义,也就失去了对社会的重新审视和批判的机会,留下的是对现实的认可、妥协。启蒙运动所留下的人文精神这一宝贵遗产已经丧失殆尽。
[1]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M].程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2]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上海: 译林出版社,2000.
[3]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4]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5]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A].周宪.《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C].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陈耀成.苏珊·桑塔格访谈录: 反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他[EB].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331287/,2006−12−14
[7]萨利·贝恩斯.1963年格林威治村 先锋派表演和欢乐的身体[M].华明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