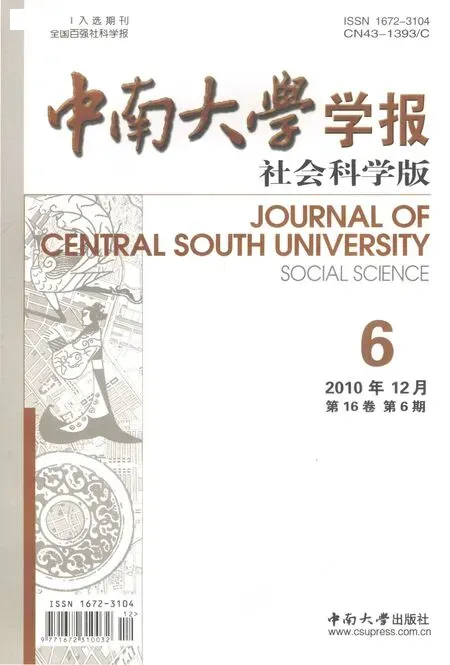翻译与共谋——后殖民主义视野中的译者主体性透析
2010-02-09屠国元朱献珑
屠国元,朱献珑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后殖民主义以殖民时代之“后”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文化权力和话语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身份等问题为研究课题,是一种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判思潮。后殖民主义涵盖了哲学、历史、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同时摄取了多种理论批评方法,如女性主义、解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因此几乎无法把后殖民主义界定为某一“理论”或“主义”。正是由于理论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后殖民主义成为各种思潮和学说的融汇交锋之地,迸发出强劲的理论活力。后殖民主义译论是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之后的重要理论纬度,深刻揭示了翻译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功能,为译者主体性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考视角。
一、作为共谋者的翻译
在后殖民主义著述中,翻译频频登台亮相,成为不同文化、种族之间权力交织的矛盾集合体。按照罗宾逊的看法,翻译在三个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在殖民化过程中充当殖民主义建构主体性的工具;②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之后,成为维护文化等级秩序的“避雷针”(lightning rod);③在解殖民化(decolonization)过程中,成为被殖民者摆脱殖民枷锁、削弱文化霸权的工具。[1](31)殖民者借助翻译在潜移默化之中完成了主体性和殖民话语的塑造,并逐渐为被殖民者所认同和接受。翻译成为殖民主义借以维护文化等级秩序和不对称权力关系的重要途径,翻译俨然成了“帝国的殖民工具”。在长期的殖民化统治下,被殖民者不得不在殖民者虚构的镜像中来解读和关照自身的生存境况,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等级秩序——前者高雅后者庸俗、前者文明后者野蛮,前者聪慧后者愚笨等等——进而造成了被殖民者“我不如人”的强烈自卑感甚至走向自我殖民,殖民者正是通过这种不平等的话语等级体系来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在赤裸裸的殖民统治结束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之后,殖民主义改头换面,通过大众传媒、学术交流、经济扩张等更加隐蔽的形式实施其文化殖民的战略。
尼兰贾娜在《为翻译定位》一书中通过考察印度殖民时期古典作品英译史,揭示了翻译与殖民主义的共谋关系,“殖民基业里所隐含的驯服/主体化(subjection/subjectification)的行径,并非仅仅是通过帝国的强制机器得以实施的,它们同时也借哲学、历史学、人类学、语文学、语言学以及文学阐释这种种话语得以推行。……作为一种实践,翻译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力关系。”[2](117)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以“实在、再现和知识”等在场形而上学概念体系为基础,知识就是对实在的再现。再现式的翻译可以创造出通顺的、透明的、超越的文本,并通过哲学、史学、传记等不同话语形式参与到殖民文化的构建和定型过程中,遮蔽殖民主体构建过程中的暴力,达到延续和强化殖民统治的目的。翻译通过再现“他者”的某些模式,呈现出另一种形态的“他者”,并藉此制定出“遏制”他者的策略。在殖民文化语境下,这种再现式的翻译渗透到殖民统治的霸权机制之中,在再现被殖民者的过程中,抹杀其中的权力关系和历史性,“翻译强化了对被殖民者所作的统识性描述,促成其取得爱德华·萨伊德称之为再现或无历史之客体的地位。”[2](118)尼兰贾娜以琼斯的翻译活动为例,“琼斯著作里最富意味之处包括:1)由于土著民对其自身的法律和文化的阐释不足为信,所以必需由欧洲人来作翻译;2)极想做一个立法者,给印度人制定他们‘自己的’法律;3)极欲‘净化’印度文化并代为其言。”[2](126)经过琼斯文本加工之后的印度人成为“一付懒懒散散、逆来顺受的样子,整个民族无法品味自由的果实,却祈盼被专制独裁所统治,且深深地沉溺在古老宗教的神话里”。[2](126)殖民者通过翻译抹杀了隐藏殖民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历史和权力等因素,遮蔽了殖民主体构建过程中的暴力行径。翻译研究“所忽略的似乎不仅是贯穿于翻译里的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而且还有译本的历史性或效应史(historicity or effective history)”。[2](170)翻译沦为殖民者构建其主体身份的工具,成为不同语言、文化、种族之间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载体。后殖民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要解除这种殖民主义话语,即所谓“解殖民化”,“解除殖民化的不良影响的渐进过程,尤其是指解除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结……由于无法完全消除殖民化的历史痕迹,在现实意义上,解殖民化意味着在发展中逐步超越殖民主义的精神遗存,并将其融入到转型后的文化之中”。[1](115)解除殖民化必须首先在还原殖民主体建构过程的基础上,揭穿殖民主义话语的谎言,还文本生成以本来面目,让深藏其中的权力差异显露出来。在后殖民语境下,翻译再次成为“工具”——成为处于文化边缘的弱势族群抵制文化霸权、重塑文化身份的工具。
二、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翻译策略
后殖民主义译论完全抛弃传统的内部研究,将翻译纳入更为宏大的后殖民话语体系之中,揭示文本生产中的历史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因素以及隐藏其中的不对称权力关系,借助翻译所具备的建构文化主体身份的功能,消解殖民话语、抵制文化霸权,实现“解殖民化”的历史使命。综合起来看,解殖民化的主要途径有三:杂合化、食人主义以及抵抗式翻译(异化策略)。
(一)杂合化策略
霍米·巴巴(Homi Bhabha)在《文化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e)一书中指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定位既不能以普遍性为旨归,也不可以将文化差异规范化或标准化,更不能走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只存在于不同文明接触的边缘和疆界处或是一种边界协商,与之伴随的是居间的、杂糅的“多种声音”。巴巴正是借助这种独特的杂糅策略向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发起挑战,进而尝试营造文化多样性的格局,文化的杂糅(或杂合)也成为后殖民主义研究者的共识。巴巴认为,“杂合化”(hybridization)是不同种族、文化、语言、意识形态彼此混杂的过程,是殖民地和弱势文化颠覆和瓦解文化霸权的一种抵抗性策略。基于此,巴巴创造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以“挑战文化的历史认同感”,瓦解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不存在原创的、“纯洁”的文化体系,文化之间亦不存在高低贵贱,所有文化的身份只有在这个矛盾的、模糊的阐释空间中才能得以构建,“在自由地在断裂的、暂时的互文性文化差异中通过翻译和协商来显示自己的文化身份”。[3]第三空间所具备的模糊性、矛盾性和无意识性能够去除文化的原始统一性和固定性,文化的差异性得以留存,文化间的冲突得以化解,从中衍生出一种“非我非他”的文化的杂糅话语形式。杂糅化既可以帮助弱势文化或边缘族群摆脱身份压迫和文化遏制,还可以让强势文化意识到自身文化语言的异质性,丢掉普遍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幻想。巴巴引入了文化翻译(cultural translation)的概念来构建自己对文化观,“在文化翻译过程中,会打开一片‘间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一种间隙的时间性,既反对回到一种原初的‘本质主义’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4]在传统民族疆界消失、中心坍塌之后,文化成为一种翻译式的、边界协商式的意义生产过程,而巴巴就是要利用这种杂糅的空间或方式来喻说一种“翻译式”的世界主义。
翻译成为塑造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成为一种不同文化差异性的商讨和协调过程。译者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协调者或斡旋者的角色,两种文化和语言在译者的引领下进入“第三空间”进行协商、交流、碰撞和融合。徘徊于目的语与源语文化之间的译者本身的行为也具备了相当的杂糅性,他的文化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目的语文化对源语文化的态度,尽管他主观上努力采取抹去自身痕迹的异化策略,或者采取抹去原作异质性的归化策略,但读者在最终的译本中总是既可以看到语言文化的“异域性”或“新颖性”,又可看到本土文化的印迹和译者自身的介入,译本因此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充满不同声音的杂合体。与其他后殖民主义学者一样,尼兰贾娜倡导将翻译视为“抵抗与变革的阵地”(a site for resistance and transformation),主张运用杂合化的策略来抵抗殖民话语和文化霸权。尼兰贾娜提倡重译印度及其他旧殖民地的文本,但她并不主张彻底抹去殖民者印迹的极端民主主义或本土主义(nationalism and nativism),或呈现所谓的普遍主义的元叙述局面(meta-narrative of global homogenization),而是要以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方式消解不同文化间的对抗性。她借鉴了德里达的引用性(citationality)理论,将翻译视为一种重读/重写历史的过程,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重新解读和翻译印度和其他殖民地文本,通过“引用”(cite)或“引证”(quote)殖民者的话语实现文化的重新转换。尼兰贾娜赞同本雅明为显现“纯语言”而倡导的直译,“‘引用’或‘引证’近似于翻译中的直译(literalness)。对本雅明而言,直译意味着翻译单位不应是句子而是单词,‘翻译不应该用以传达信息,而是用以反映原文的句法’”。[5]尼兰贾娜的重译理论是杂合化策略的一种体现,杂合化是“指向一种新的翻译实践的同时又颠覆了本质主义阅读模式的一种后殖民理论的标志”。[2](154)除尼兰贾娜以外,梅勒兹(Samia Mehrez)、谢莉•西蒙(Sherry Simon)、拉菲尔(Vicente L.Rafael)等学者都着力运用杂合化翻译策略消解文化中心主义和普遍主义,凸显文化的差异和多元,从不同侧面继续推进杂合化的研究。
(二)巴西的食人主义
在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之后,巴西人民开始反思自身的文化发展模式,并逐渐意识到在获得政治独立的同时,还存在着与欧洲严重的文化依附关系,文化身份变得越来越模糊。1928年,巴西现代主义者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Oswald de Andrade)发表了《食人主义宣言》,主张只有“吞食”欧洲文化,才能摆脱文化上的依附、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继而在权力关系网络中争取主动。食人主义源自巴西土著部落的一种仪式,食人是怀着敬意和有特殊用意的:食人是为了获取力量,精神的或肉体的,或兼而有之。食人主义者只吞食三类人: 强壮的人、有权势而且受人尊敬的人、通灵通神的人。[6]“吞食”意味着背离,同时还包含着对被食者的尊敬。在巴西理论界,食人主义思想逐渐内化为一种共同的精神信念。20世纪60年代,德坎波斯兄弟(Haroldo & Augusto de Campos)将食人主义引入翻译研究领域,同时借鉴了解构主义思想,建构起了一种后现代的、非欧洲中心主义的(non-Eurocentric)食人主义译论。德坎波斯兄弟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侵越(transgression),或弑父的行为(a form of patricide),他们拒斥对原作的任何预先设定以及亦步亦趋的复制和再现。在德坎波斯看来,翻译并不是将原文强行占有,而是一种让原文得以解放的方式,通过吞食原文、汲取原文的精华,摆脱原文的束缚获得自由。因此,翻译成为一种汲取力量的行为(empowering act)、摄取营养的行为(a nourishing act)和具有认同功能的行为(act of affirmative play),原语文本通过翻译获得了重生,延续了自身的生命历程,译作成为原作的“来世”(afterlife),这种理念与本雅明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一脉相承。[7]在翻译实践层面,德坎波斯兄弟翻译了大量东西方文学经典,如《荷马史诗》、希伯来语的《圣经》、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甚至还将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进行二度翻译,带着“爱与尊敬”(love and reverence),将异域的文学经典咀嚼、消化,为巴西文化输入新鲜的血液。翻译总是意味着创作和超越,异域文本进入本土文化必然意味着变形,即以本土文化框架为依归肢解和重组原文,从而使译文呈现出一种全新的面貌,因此食人主义通常采用类似于“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可以基于本土文化的诉求改造、移植甚至挪用原作中的异质成分。德坎波斯兄弟的食人主义思想在翻译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并根据所译文本的主题或意像创造出一套独特的术语,如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提出了“再度想像”(reimagination),在翻译《神曲》时提出了“移转光明” (translumination)、“移转天堂”(transparadisation),在翻译《浮士德》时提出了跨越文本(transtextualization)、再次创造(transcreation)、移植魔鬼(transluciferation),在翻译的《伊利亚特》时提出了移植海伦 (transhelenization),在翻译《圣经》时提出了“重谱诗歌乐曲”(poetic reorchestration),此外还有去除弑父记忆(a patricidal dis-memory)等术语。[8]在后殖民语境下,食人主义思想既可以摆脱殖民主义的文化同化和文化渗透,又可以有效规避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倾向,因此它对弱势文化族群解除殖民化、削弱文化霸权、重塑文化身份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三)韦努蒂的抵抗式翻译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将传统的归化、异化翻译策略植入后殖民语境之中,赋予其强烈的权力和政治色彩,视翻译为一种“文化政治实践”。韦努蒂通过考察17世纪以来的英美翻译史发现,其间的译者大多以本土的语言文化价值观为基点,采取归化式的翻译策略改写外国文学作品。译本通顺易懂、自然流畅,甚至看不出翻译的痕迹,也寻不见译者的踪迹(invisible);在原作的选择以及内容的增删等方面均以英美文化审美偏好为依归,如庞德的《华夏集》便采用了归化的策略,无视其中特有的文学和文化元素,将中国古典诗歌改造为意象派诗歌,译本因为迎合了目的语文化的口味获得了极大成功。然而,这种透明的翻译背后却隐藏着民族中心主义和英美霸权主义的价值观,通顺、易懂的译本隐含了欧美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制以及不对称的权力关系。“流畅译法的目的在于不让译者介入外语文本之中,译者主动地用另一语言重写原文,再让译文在另一种文化里流传。但这一过程带来的却是自我毁灭,最终把今日的译者挤到文化边缘,……流畅译法也抹掉了外语文本在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这种重写使译作以透明易懂的译语的主流文化为依归,甚至不可避免地表达了译语的价值观、信念和社会楷模,把翻译牵连到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里去……在这种重写过程中,流畅策略就担任了一项文化移入的工作,把外语文本归化,使译语读者不但明了熟识文章意义,并且从中满足自恋情怀,在他方文化里认出自己的文化。这样,一场帝国主义扩张话剧又在上演着,他方的意识形态通过‘透明’译法扩充了它的版图,进入了另一个文化领域里去。”[9](241)韦努蒂称之为翻译“最大的丑闻”,“不对称、不对等、占有与依附的关系在翻译行为中屡见不鲜,原语文化不得不俯首听命于译语文化。译者成了剥削异域文本和文化的共谋”。[10]归化的翻译成为殖民者的“帮凶”,弱势文化不得不听命于英美强势文化的摆弄,归化的翻译成了殖民者进行文化殖民和强化殖民意识形态的共谋,它不仅帮助殖民者撒播话语权力,实施文化侵吞,而且在被殖民一方的意识中不断强化他们自我他者身份的认同。对译入英美文化的外国文本所采取的归化的翻译策略所作的本质揭示,使归化策略在后殖民主义翻译批评中遭到了译论家们的指责和唾弃。[11]韦努蒂呼吁创立一种“存异伦理”,主张运用“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在翻译过程中采用背离本土语言文化规范的混杂文体,向读者呈现充满文化异质性的外国文本,读者面对译本不应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而是陌生感甚至疏远感,文化的差异由此才得以体现。“抵抗式的策略可以生成既陌生又怪异的译文,有助于保留异域文本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性。如此就可以划清译入语文化主流价值标准的界限,还可以阻止这些标准把他者文化纳入译入语帝国的疆域之内。”[9](250)异化策略成为抵制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文化自恋情结、重塑“他者”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
三、结语
“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了文化、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等语言之外的世界之中,翻译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功能得到史无前例地高扬,透明式的、再现式的翻译忠实观被彻底抛弃,原作/译作、作者/译者的二元对立被拆解,原作者的权威及文本意义的普适性消解于译者的积极介入和意义的无限延异之中。透过纷繁庞杂的后殖民主义译论,追问“身份”成为共同的诉求,体现现出强烈的“身份焦虑”(the anxiety of identity),引发了改变自身弱势或边缘地位的反叛和抵抗。被殖民者和弱势文化族群在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的压制下陷入失语的境地,文化身份的日益边缘化和模糊化。“身份”对他们而言,不是本质主义模式下面各种属性的集合,而是一种文化的建构或话语的建构。他们一方面质疑被传统翻译观念和翻译实践所固化的等级二元,另一方面将翻译作为一种行为性(performative)的话语实践,来服务于议定文化身份的动态过程。[12]后殖民主义将翻译视为解殖民化的工具,翻译本身就成为一种政治行为,通过翻译的杂合化策略去除文化的普遍性和同一性,借助抵抗式的异化策略凸显文化的差异性,甚至将强势文化直接“吃掉”来获得文化身份的认同。后殖民主义译论将译者推向了权力网络的中心,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译者及其翻译实践成为重塑身份、彰显差异的最为重要的一环,或者说,译者本身就是话语,翻译成为译者表达自身及其所属群体文化诉求、重塑文化身份的载体或工具。
[1]Robinson,Douglas.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M].Manchester: St.Jerome Publishing,1997.
[2]许宝强,袁 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Bhabha,Homi K.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4.
[4]Bhabha,Homi K.The Post- 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Divided Horizons [M].London: Routledge,1996.
[5]Niranjana, Tejaswini,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M].Berkele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6]蒋骁华.巴西的翻译:“吃人”翻译理论与实践及其文化内涵[J].外国语,2003,(1): 63−67.
[7]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8]Bassnett,Susan & Trivedi,Harish.Post-Colonial Translation:Theory and Practice [C].London: Routledge,1999.
[9]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M].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10]Venuti,Lawrence.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
[11]葛校琴.当前归化/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J].中国翻译,2005,(5):32−35.
[12]曾记.“忠实”的嬗变: 翻译伦理的多元定位[J].外语研究,2008,(6): 7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