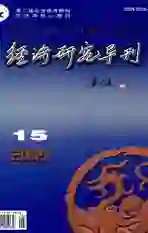周作人:“平民文学”对通俗文学的超越
2009-09-30封兰
封 兰
摘要:周作人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以人性的二元为基础,以个人为本位。他倡导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正是从人的文学出发,周作人发现了通俗文学的不足,故加以否定。但周作人又清醒地意识到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并进一步肯定其巨大的影响。正是看到了通俗文学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看到了其平民精神的光辉,只是由于其“文学价值的缺失”,周作人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文学类型——平民文学,借以阐发他的“人的文学”的主张。
关键词:周作人;通俗文学;平民文学
中图分类号:I1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5-0211-02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现代知名作家。从事过文学翻译,诗歌创作,散文创作。在现代文坛上,周作人以“人的文学”的首倡而开始了文学批评的重要历程。
一、对通俗文学价值的否定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实际上一直处于纯文学之维,畅谈人的文学和人生的文学。周作人应该说是很自觉维护纯文学的,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相反,从其字里行间,我们会感觉到他对通俗文学的不屑一顾,甚至是否定。周作人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以人性的二元为基础,以个人为本位。他倡导人的文学,“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的文学,便谓之人的文学。周作人的这一文学思想,有这样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人的文学是以发扬人性为目的的文学;第二,人的文学是个性和人类性的统一。”[1]正是从人的文学出发,周作人发现了通俗文学的不足,故加以否定。
周作人认为应该拿文学当做一件艺术品而去创作或作为一件艺术品而对它加以鉴赏,然而通俗文学往往“流行于中等以下的社会,其中虽间有佳作,当得起文学名称的东西,大多是迎合下层社会心理而作,所以千篇一律,少有特色。”对通俗文学而言,其创作者的地位不高,多是些“低级的文人”,“仿佛同画工或是说书的一样,他们也自称作戏作者”。他们往往“单依文学为谋生之具”,“如专依卖文糊口,则一想创作,先须想到这作品的销路,想到出版者欢迎与否,社会上欢迎与否,更须有官厅方面的禁止与否,和其他种种的顾虑”,“作书的目的,不过是供娱乐,或当教训”。因而,创作出来的通俗文学作品俨然成了“低级的东西”,“都不是正路的文学,而是来自偏路的”。这样的创作不是源于作者的个性和自由,而是舍弃了个性去迎合大多数的心理,这显然是周作人最瞧不起的,所以他有“到处得到欢迎的《礼拜六》派的小册子,其文学价值仍然可以等于零”的评价。
他说:“文学家虽希望民众能了解自己的艺术,却不必强将自己的艺术去迁就民众:因为据我的意见,文艺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现,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现在倘若舍己从人,去求大多数的了解,结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学的标本,不是他真的自己的表现了。”[2]
这样,在周作人眼里,通俗文学的诟病正是舍弃个性,迎合大多数,尽管受到一时大众的欢迎,其文学价值微乎其微。周作人认为,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应当独立自由的表现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不能听命于别的个体,甚至也不能听命于来自社会和民众的要求。“应命、应声都不能创造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反言之,通俗文学缺乏文学价值,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
二、对通俗文学影响的肯定
尽管对通俗文学有着“文学贵族”与生俱来的偏见,周作人仍然是一位宽容的批评家。
文学是什么?周作人所下的定义是,“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3]他解释说,“这‘愉快是有些爽快的意思在内,正如我们身上生了疮,用刀割过之后,疼是免不了的,然而却觉得痛快,这意思金圣叹也曾说过,他说生了疮时,关了门自己用热水烫洗一下,‘不亦快哉。这也便是我的所谓愉快。当然这愉快不是指哈哈一笑而言。”“在我们的皮肤作痒的时候,我们用手去搔那痒处,这时候是觉得愉快的,但用力稍过,便常将皮肤抓破便又不免觉得痛苦了。在文学方面,情形也正相同。”“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体操”。“欲使文学有用也可以,但那样也是变相的文学了。椅子原是作为座位用的,墨盒原是为写字用的,然而,以前的议员们岂不是在打架时作为武器用过么?在打架的时候,椅子墨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却终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处。文学亦然。”
从以上大意看,作为文学只是个人情绪的张扬和宣泄,也即《诗序》上说的;“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是为言其心志。那么什么人需要文学呢?他说:“文学,仿佛只有在社会上失败的弱者才需要,在际遇好,没有不满足的人们,他们任何时任何事既都能随心所欲,文学自然没有必要。而在一般的弱者,在他们心中感到苦闷,或遇到了人力无能为的生死问题时,则多半用文学把这时的感触发挥出去。”[4]
周作人将文学分为了三个层次:原始文学,通俗文学,纯文学。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他极公正地确认了通俗文学在文学中的地位。他将文学的全部视作一座山,他孜孜以求的纯粹文学仅是山顶上的一小部分。纯文学以下是原始文学和通俗文学。原始文学是“由民间自己创作出来,供他们自己歌咏欣赏的一部分”。而通俗文学是“比较原始文学进步一些”,“受了纯文学的影响”而创作出来的。他说:“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纯粹文学,而是道教(不是老庄的道家)和通俗文学。因此,研究中国文学,更不能置通俗文学于不顾。”[5]这里,周作人清醒的意识到通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并进一步肯定其巨大的影响。
三、文学价值与影响的结合——平民文学
既然研究文学不能置通俗文学于不顾,那么对文学这座大山研究时,周作人发现高高在上的纯文学显然具有贵族文学的性质。“在文艺不能维持生活的时代”,“只有那些贵族或中产阶级才能去弄文学”,这样的文学“大抵偏于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或游戏的”,可以假定其具有一种如尼采所说之求胜意志的贵族精神,它“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几乎有点出世了”。于是,相对贵族文学,周作人提出了“平民文学”的主张。
“平民的文学正与贵族的文学相反。但这两样名词,也不可十分拘泥。我们说的贵族的与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6]
所以“平民文学应该着重,与贵族文学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我们不必记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因为英雄豪杰才子佳人,是世上不常见的人;普通的男女是大多数,我们也便是其中的一人,所以其事更为普遍,也更为切己。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
同样,周作人假定平民文学具有如淑本好耳所说之求生意志的平民精神,它是入世的,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周作人认为,仅有求生意志,没有超越现实的精神,只能陷入现世利禄的自我满足之中。周作人所言平民精神,实际上也正是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元代的戏剧中所宣扬的功名妻妾的团圆思想,正是乐天派的自我满足的体现。
周作人的结论是“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或从文艺上说来,最好的事,是平民的贵族化——凡人的超人化,因为凡人如不想化为超人,便要成为末人了。”
这样,平民文学成了又较通俗文学进步的文学。所以周作人说“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7]
有些人认为平民文学是单纯的通俗文学,是写给平民的文学。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解释过“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周作人提倡的“平民文学”较之陈独秀所说的“国民文学”、 “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具有更加明确清晰的内涵。
正是看到了通俗文学的巨大影响,同时也看到了其平民精神的光辉,只是由于其“文学价值的缺失”,周作人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找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文学类型——平民文学,借以阐发他的“人的文学”的主张。于是,我们不妨视之为对通俗文学的某种程度的超越,也许周作人本人并没有这样清晰的认识,然而旁观者清。事实上,平民文学确实较通俗文学进步,更趋近于人的文学。
参考文献:
[1]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5):6.
[2]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散文集)[M].北京:北京晨报社,1923.
[3]尚飞.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观[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2,(4).
[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北京:人文书店,1932.
[5]权绘锦.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6]张伟.论周作人“人的文学”观[J].安徽文学:评论研究,2008,(10).
[7]梁白瑜.从“人”的文学到人的“文学”——论周作人的“人的文学”观[J].枣庄学院学报,2007,(3).
[责任编辑陈凤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