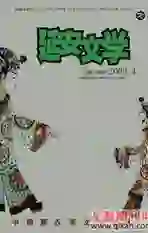新诗典:吉狄马加诗歌近作选读
2009-09-08
吉狄马加,彝族,1961年6月生于四川凉山,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2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现为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第十届政协委员,一级作家。
迄今已在国内外出版的文学专著、诗集有《初恋的歌》(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一个彝人的梦想》(199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罗马的太阳》(1991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吉狄马加诗选译》(彝文版,199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遗忘的词》(1998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吉狄马加短诗选》(2003年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吉狄马加的诗》(2004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涯海角》(意大利文版,2005年4月罗马伊姆普罗特出版社出版,翻译:维尔玛·科斯坦蒂尼)、《时间》(英汉对照版,200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吉狄马加的诗与文》(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秋天的眼睛》(马其顿文版,2006年3月马其顿共和国斯科普里学院出版社出版,翻译:特拉扬·彼得洛夫斯基)、《“睡”的和弦》(保加利亚文版,2006年10月保加利亚国家作家出版社出版,翻译:卡拉斯拉沃夫)、《吉狄马加诗歌选集》(塞尔维亚文版,2006年10月“斯姆德雷沃诗歌之秋”国际诗歌节出版社出版,翻译:德拉根·德拉格伊洛维奇)、《彝人之歌》(德文版,2007年德国波鸿项目出版社出版,翻译:彼得·霍夫曼)、《时间》(法文版,2007年法国友丰出版社出版,翻译:亚历山大·桑德里娜)、《时间》(西班牙文版,2008年委内瑞拉卡斯塔利亚出版社出版,翻译:何塞·曼努埃尔·布里塞尼)、诗集《神秘的土地》(波兰文版,2007年波兰埃德玛萨雷克出版社出版,翻译:马雷克·瓦夫凯维奇、彼特·陶巴瓦)等三十余部。
吉狄马加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少数民族代表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诗人,多次荣获中国国家文学奖和国际文学组织机构的奖励,其中诗集《初恋的歌》获中国第三届新诗奖;组诗《自画像及其他》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诗歌奖最高奖;组诗《吉狄马加诗十二首》获中国四川省文学奖;诗集《一个彝人的梦想》获中国第四届民族文学诗歌奖;1994年获庄重文文学奖;2006年5月22日被俄罗斯作家协会授予肖洛霍夫文学纪念奖章和证书;2006年10月9日,保加利亚作家协会为表彰他在诗歌领域的杰出贡献,特别颁发证书,证书的题词为“保加利亚作家协会授予诗集《“睡”的和弦》作者吉狄马加证书,因其作品使世界更亲近、人民更智慧、生活更美好”。其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西班牙文、罗马尼亚文、德文、塞尔维亚文、波兰文等多国文字,曾多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和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国际活动。2007年,创立首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并出任诗歌节组委会主任。
自画像
风在黄昏的山岗上悄悄对孩子说话,风走了,远方有一个童话等着它。
孩子留下你的名字吧,在这块土地上,因为有一天你会自豪的死去。
——题记
我是这片土地上用彝文写下的历史
是一个剪不断脐带的女人的婴儿
我痛苦的名字
我美丽的名字
我希望的名字
那是一个纺线女人
千百年来孕育着的
一首属于男人的诗
我传统的父亲
是男人中的男人
人们都叫他支呷阿鲁
我不老的母亲
是土地上的歌手
一条深沉的河流
我永恒的情人
是美人中的美人
人们都叫她呷玛阿妞
我是一千次死去
永远朝着左睡的男人
我是一千次死去
永远朝着右睡的女人
我是一千次葬礼开始后
那来自远方的友情
我是一千次葬礼高潮时
母亲喉头发颤的辅音
这一切虽然都包含了我
其实我是千百年来
正义和邪恶的抗争
其实我是千百年来
爱情和梦幻的儿孙
其实我是千百年来
一次没有完的婚礼
其实我是千百年来
一切背叛
一切忠诚
一切生
一切死
啊,世界,请听我回答
我—是—彝—人
回答
你还记得
那条通向吉勒布特的小路吗?
一个流蜜的黄昏
她对我说:
我的绣花针丢了
快来帮我寻找
(我找遍了那条小路)
你还记得
那条通向吉勒布特的小路吗?
一个沉重的黄昏
我对她说:
那深深插在我心上的
不就是你的绣花针吗
(她感动地哭了)
注:吉勒布特——凉山彝族腹心地带地名。
彝人谈火
给我们血液,给我们土地
你比人类古老的历史还要漫长
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慰藉
让子孙在冥冥中,看见祖先的模样
你施以温情,你抚爱生命
让我们感受仁慈,理解善良
你保护着我们的自尊
免遭他人的伤害
你是禁忌,你是召唤,你是梦想
给我们无限的欢乐
让我们尽情地歌唱
当我们离开这个人世
你不会流露出丝毫的悲伤
然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
你都会为我们的灵魂
穿上永恒的衣裳
口弦的自白
我是口弦
永远挂在她的胸前
从美妙的少女时光
到寂寞的老年
我是口弦
命运让我
睡在我心房的旁边
她通过我
把忧伤和欢乐
倾诉给黑暗
我是口弦
要是她真的
溘然离开这个人世
我也要陪伴着她
最终把自己的一切
拌合在冰冷的泥土里面
但是——兄弟啊——在漆黑的夜半
如果你感受到了
这块土地的悲哀
那就是我还在思念
老去的斗牛
——大凉山斗牛的故事之一
它站在那里
站在夕阳下
一动也不动
低垂着衰老的头
它的整个身躯
像被海浪啃咬过的
礁石
它那双伤痕斑斑的角
像狼的断齿
它站在那里
站在夕阳下
紧闭着一只
还剩下的独眼
任一群苍蝇
围着自己的头颅飞旋
任一些大胆牛虻
爬满自己的脸
它的主人不知到何处去了
它站在那里
站在夕阳下
这时它梦见了壮年的时候
想起火把节的早晨
它好像又听见头上的角发出动人的声响
它好像又听见鼻孔里发出远山的歌唱
它好像又嗅到了斗牛场
那熟悉而又潮湿的气息
它好像又感到一阵狂野的冲动
从那黑色的土地上升起
它好像又感到
奔流着的血潮正涌向全身
每一根牛毛都像坚硬的钢丝一般
它好像又听到了人们欢呼的声音
在夏日阳光的原野上
像一只只金色的鹿
欢快着奔跑着跳跃着
它好像又看见那年轻的主人牵着它
红色的彩带挂在了头顶
在高高的山岗
它的锐角挑着一轮太阳
红得就像鲜血一样
它站在那里
站在夕阳下
有时会睁开那一只独眼
望着昔日的斗牛场
发出一声悲哀的吼叫
于是那一身
枯黄的毛皮
便像一团火
在那里疯狂地燃烧
母亲们的手
彝人的母亲死了,在火葬的时候,她的身子
永远是侧向右睡的,听人说那是因为,她还要用
自己的左手,到神灵世界去纺线。
——题记
就这样向右悄悄地睡去
睡成一条长长的河流
睡成一架绵绵的山脉
许多人都看见了
她睡在那里
于是山的女儿和山的儿子们
便走向那看不见海的岸
岸上有一条美人鱼
当液态的土地沉下去
身后立起一块沉默的礁石
这时独有一只古老的歌曲
拖着一弯最纯洁的月牙
就这样向右悄悄地睡去
在清清的风中
在濛濛的雨里
让淡淡的雾笼罩
让白白的云萦绕
无论是在静静的黎明
还是在迷人的黄昏
一切都成了冰冷的雕像
只有她的左手还漂浮着
皮肤上一定用温度
血管里一定有血流
就这样向右悄悄地睡去
多么像一条美人鱼
多么像一弯纯洁的月牙
多么像一块沉默的礁石
她睡在土地和天空之间
她睡在死亡和生命的高处
因此江河才在她身下照样流着
因此森林才在她身下照样长着
因此山岩才在她身下照样站着
因此我苦难而又甜蜜的民族
才这样哭着,才这样喊着,才这样唱着
就这样向右悄悄地睡去
世间的一切都要消失
在浩瀚的苍穹中
在不死的记忆里
只有她的左手还漂浮着
那么温柔,那么美丽,那么自由
黑色的河流
我了解葬礼,
我了解大山里彝人古老的葬礼。
(在一条黑色的河流上,
人性的眼睛闪着黄金的光。)
我看见人的河流,正从山谷中悄悄穿过。
我看见人的河流,正漾起那悲哀的微波。
沉沉地穿越这冷暖的人间,
沉沉地穿越这神奇的世界。
我看见人的河流,汇聚成海洋,
在死亡的身边喧响,祖先的图腾被幻想在天上。
我看见送葬的人,灵魂像梦一样,
在那火枪的召唤声里,幻化出原始美的衣裳。
我看见死去的人,像大山那样安祥,
在一千双手的爱抚下,听友情歌唱忧伤。
我了解葬礼,
我了解大山里彝人古老的葬礼。
(在一条黑色的河流上,
人性的眼睛闪着黄金的光。)
头巾
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
送给了他相爱的女人
这个女人真是幸运
因为她总算和这个
她真心相爱的男人结了婚
朝也爱
暮也爱
岁月悄悄流去
只要一看见那头巾
总有那么多甜蜜的回忆
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
送给了他相爱的女人
可这个女人的父母
却硬把她嫁给了一个
她从不认识的人
从此她的泪很多
从此她的梦很多
于是她只好用那头巾
去擦梦里的灰尘
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
送给了他相爱的女人
或许由于风
或许由于雨
或许由于一次特大的山洪
彼此再没有消息
于是不知过了多少年
在一个赶集的路口
这个女人突然又遇见了那个男人
彼此都默默无语
谁也不愿说起过去
两个人的手中
都牵着各自的孩子
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
送给他相爱的女人
可能是一次远方的雷声
可能是一次初夏的寒冷
这个女人和一个外乡人走了
她想等到盛夏的傍晚就回来
可是回来已是冬天的早晨
从此她只好在那有月光的晚上
偷偷地数那头巾上的花格
有一个男人把一块头巾
送给了他相爱的女人
但为了一个永恒的等待
天说要背叛
地说要背叛
其实那是两条相望的海岸
尽管也曾有过船
醒着也呢喃
睡着也呢喃
最后有一天
这个女人死了
送葬的人
才从她珍藏的遗物中
发现这条头巾
可谁也没有对它发生兴趣
可谁也不会知道它的历史
于是人们索性就用这头巾
盖住死者那苍白的脸
连同那蜷曲的身躯
在那山野里烧成灰烬
彝人之歌
我曾一千次
守望过天空,
那是因为我在等待
雄鹰的出现。
我曾一千次
守望过群山,
那是因为我知道
我是鹰的后代。
啊,从大小凉山
到金沙江畔,
从乌蒙山脉
到红河两岸,
妈妈的乳汁像蜂蜜一样甘甜,
故乡的炊烟湿润了我的双眼。
我曾一千次
守望过天空,
那是因为我在期盼
民族的未来。
我曾一千次
守望过群山,
那是因为我还保存着
我无法忘记的爱。
啊,从大小凉山
到金沙江畔,
从乌蒙山脉
到红河两岸,
妈妈的乳汁像蜂蜜一样甘甜,
故乡的炊烟湿润了我的双眼。
失去的传统
好像一根
被遗弃的竹笛
当山风吹来的时候
它会呜呜地哭泣
又像一束星光
闪耀在云层的深处
可在它的眼里
却含有悲哀的气息
其实它更像
一团白色的雾霭
沿着山岗慢慢地离去
没有一点声音
但弥漫着回忆
黑色狂想曲
在死亡和生命相连的梦想之间
在河流和土地的幽会之处
当星星以睡眠的姿态
在蓝色的夜空静默
当歌手忧郁的嘴唇失去柔软
木门不再响动,石磨不再歌唱
摇篮曲的最后一个音符跳跃成萤火
所有疲倦的母亲都已进入梦乡
而在远方,在云的后面
在那山岩的最高点
沉睡的鹰爪踏着梦想的边缘
死亡在那个遥远的地方紧闭着眼
而在远方,在这土地上
千百条河流在月光下游动
它们的影子走向虚无
而在远方,在那森林里
在松针诱惑的枕头旁
残酷的豹忘记了吞食身边的岩羊
在这寂静的时刻
啊,古里拉达峡谷中没有名字的河流
请给我你血液的节奏
让我的口腔成为你的声带
大凉山男性的乌抛山
快去拥抱小凉山女性的阿呷居木山
让我的躯体再一次成为你们的胚胎
让我在你腹中发育
让那已经消失的记忆重新膨胀
在这寂静的时刻
啊,黑色的梦想,你快覆盖我,笼罩我
让我在你情人般的抚摸中消失吧
让我成为空气,成为阳光
成为岩石,成为水银,成为女贞子
让我成为铁,成为铜
成为云母,成为石棉,成为磷火
啊,黑色的梦想,你快吞没我,溶化我
让我在你仁慈的保护下消失吧
让我成为草原,成为牛羊
成为獐子,成为云雀,成为细鳞鱼
让我成为火镰,成为马鞍
成为口弦,成为马布,成为卡谢着尔
啊,黑色的梦想,就在我消失的时候
请为我弹响悲哀和死亡之琴吧
让吉狄马加这个痛苦而又沉重的名字
在子夜时分也染上太阳神秘的色彩
让我的每一句话,每一支歌
都是这土地灵魂里最真实的回音
让我的每一句诗,每一个标点
都是从这土地蓝色的血管里流出
啊,黑色的梦想,就在我消失的时候
请让我对着一块巨大的岩石说话
身后是我苦难而又崇高的人民
我深信这千年的孤独和悲哀呵
要是岩石听懂了也会淌出泪来
啊,黑色的梦想,就在我消失的时候
请为我的民族升起明亮而又温暖的星星吧
啊,黑色的梦想,让我伴随着你
最后进入那死亡之乡
注:口弦、马布、卡谢着尔——均为彝族的原始乐器。
苦荞麦
荞麦啊,你无声无息
你是大地的容器
你在吮吸星辰的乳汁
你在回忆白昼炽热的光
荞麦啊,你把自己根植于
土地生殖力最强的部位
你是原始的隐喻和象征
你是高原滚动不安的太阳
荞麦啊,你充满了灵性
你是我们命运中注定的方向
你是古老的语言
你的倦意是徐徐来临的梦想
只有通过你的祈祷
我们才能把祝愿之辞
送到神灵和先辈的身边
荞麦啊,你看不见的手臂
温柔而修长,我们
渴望你的抚摸,我们歌唱你
就如同歌唱自己的母亲一样
被埋葬的词
我要寻找
被埋葬的词
你们知道
它是母腹的水
黑暗中闪光的鱼类
我要寻找的词
是夜空宝石般的星星
在它的身后
占卜者的双眸
含有飞鸟的影子
我要寻找的词
是祭司梦幻的火
它能召唤逝去的先辈
它能感应万物的灵魂
我要寻找
被埋葬的词
它是一个山地民族
通过母语,传授给子孙的
那些最隐秘的符号
看不见的人
在一个神秘的地点
有人在喊我的名字
但我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
我想把它的声音带走
可是听来却十分生疏
我敢肯定
在我的朋友中
没有一个人曾这样喊叫我
在一个神秘的地点
有人在写我的名字
但我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
我想在梦中找到它的字迹
可是醒来总还是遗忘
我敢肯定
在我的朋友中
没有一个人曾这样写信给我
在一个神秘的地点
有人在等待我
但我不知道
这个人是谁?
我想透视一下它的影子
可是除了虚无什么也没有
我敢肯定
在我的朋友中
没有一个人曾这样跟随我
毕摩的声音
——献给彝人的祭司之二
你听见它的时候
它就在梦幻之上
如同一缕淡淡的青烟
为什么群山在这样的时候
才充满着永恒的寂静
这是谁的声音?它漂浮在人鬼之间
似乎已经远离了人的躯体
然而它却在真实与虚无中
同时用人和神的口说出了
生命与死亡的赞歌
当它呼喊太阳、星辰、河流和英雄的祖先
召唤神灵与超现实的力量
死去的生命便开始了复活!
星回节的祝愿
我祝愿蜜蜂
我祝愿金竹,我祝愿大山
我祝愿活着的人们
避开不幸的灾难
长眠的祖先
到另一个世界平安
我祝愿这片土地
它是母亲的身躯
哪怕就是烂醉如泥
我也无法忘记
我祝愿凡是种下的玉米
都能生出美丽的珍珠
我祝愿每一头绵羊
都像约呷哈且那样勇敢
我祝愿每一只公鸡
都像瓦补多几那样雄健
我祝愿每一匹赛马
都像达里阿左那样驰名
我祝愿太阳永远不灭
火塘更加温暖
我祝愿森林中的獐子
我祝愿江河里的游鱼
神灵啊,我祝愿
因为你不会不知道
这是彝人最真实的情感
注: 彝族传说,约呷哈且是一头领头的绵羊。瓦补多几是一只雄健的公鸡。达里阿左是一匹驰名的赛马。
回望二十世纪
——献给纳尔逊·曼德拉
站在时间的岸边
站在一个属于精神的高地
我在回望二十世纪
此时我没有眼泪
欢乐和痛苦都变得陌生
我好像站在另一个空间
在审视人类一段奇特的历史
其实这一百年
战争与和平从未离开过我们
而对暴力的控诉也未曾停止
有人歌唱过自由
也有人献身于民主
但人类经历得最多的还是专制和迫害
其实这一百年
诞生过无数伟大的幻想
但灾难却也接踵而至
其实这一百年
多种族的人类,把文明又一次推向了顶峰
我们都曾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
悄悄地流下过感激的泪水
二十世纪
你让一部分人欢呼和平的时候
却让另一部分人的两眼布满仇恨的影子
你让黑人在大街上祈求人权
却让残杀和暴力出现在他们家中
你让我们认识卡尔•马克思的同时
也让我们见到了尼采
你让我们看见爱因斯坦是怎样提出了相对论
你同时又让我们目睹这个人最后成为基督徒
你曾把许多巨人的思想变得虚无
你也曾把某个无名者的话语铅印成真理
你散布过阿尔夫•希特勒的法西斯主张
你宣扬过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义
你让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获得成功
同时你又让国际工人运动处于了低潮
在诞生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年代
你推崇过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
你为了马丁•路德•金闻名全世界
却让这个人以被别人枪杀为代价
你在非洲产生过博卡萨这样可以吃人肉的独裁者
同样你也在非洲养育了人类的骄子纳尔逊•曼德
拉
你叫柏林墙在一夜之间倒塌
你却又叫车臣人和俄罗斯人产生仇恨
还没有等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真正和解
你又在科索沃引发了新的危机和冲突
你让人类在极度纵欲的欢娱之后
最后却要承受艾滋病的痛苦和折磨
你的确让人类看到了遗传工程的好处
却又让人类的精神在工业文明的泥沼中异化而亡
你把信息时代的技术
传播到了拉丁美洲最边远的部落
你却又让一种文化在没有硝烟的地方
消灭另一种文化
你在欧洲降下人们渴望已久的冬雪
你却又在哥伦比亚暴雨如注
使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庄毁灭于山洪
你让我们在月球上遥望美丽的地球
使我们相信每一个民族都是兄弟
可你又让我们因宗教而产生分歧与离异
在巴尔干和耶路撒冷相互屠杀
你让高科技移植我们需要的器官
你又让这些器官感受到核武器的恐惧
在纽约人们关心更多的是股市的涨跌
但在非洲饥饿和瘟疫却时刻威胁着人类
是的,二十世纪
当我真的回望你的时候
我才发现你是如此的神秘
你是必然,又是偶然
你仿佛证明的是过去
似乎预示着的又是未来
你好像是上帝在无意间
遗失的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
注:纳尔逊·曼德拉——南非黑人民权领袖。
想念青春
——献给西南民族大学
我曾经遥望过时间
她就像迷雾中的晨星
闪烁着依稀的光芒
久远的事物是不是都已被遗忘
然而现实却又告诉我
她近在咫尺,这一切就像刚发生
褪色的记忆如同一条空谷
不知是谁的声音,又在
图书馆的门前喊我的名字
这是一个诗人的圣经
在阿赫玛托娃预言的漫长冬季
我曾经为了希望而等待
不知道那条树阴覆盖的小路
是不是早已爬满了寂寞的苔藓
那个时代诗歌代表着良心
为此我曾大声的告诉这个世界
“我是彝人”
命运让我选择了崇尚自由
懂得了为什么要捍卫生命和人的权利
我相信,一个民族深沉的悲伤
注定要让我的诗歌成为人民的记忆
因为当所有的岩石还在沉睡
是我从源头啜饮了
我们种族黑色魂灵的乳汁
而我的生命从那一刻开始
就已经奉献给了不朽和神奇
沿着时间的旅途而行
我嗒嗒的马蹄之声
不知还要经过多少个驿站
当疲惫来临的时候,我的梦告诉我
一次又一次地想念青春吧
因为只有她的灿烂和美丽
才让那逝去的一切变成了永恒!
时间
在我的故乡
我无法见证
一道土墙的全部历史
那是因为在一个瞬间
我无法亲历
一粒尘埃
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
哦,时间!
是谁用无形的剪刀
在距离和速度的平台
把你剪成了碎片
其实我们
不用问时间的起源
因为它从来
就没有所谓的开始
同样,我们也不用问
它的归宿在哪里?
因为在浩瀚的宇宙
它等同于无限
时间是黑暗中的心脏
它的每一次跳动
都如同一道闪电
它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
请相信,这并非上帝的意志
仿佛是绝对的真理
当时间离开了我们
它便永远不再回头
所有的生命、思想和遗产
都栖居在时间的圣殿
哦,时间!
最为公平的法官
它审判谎言
同时它也伸张正义
是它在最终的时刻
改变了一切精神和物质的
存在形式
它永远在死亡中诞生
又永远在诞生中死亡
它包含了一切
它又在一切之外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东西真正的不朽
我敢肯定地说:那就是时间!
献给1987
祭司告诉我
那只雁鹅是洁白的
它就是你死去的父亲
憩息在故乡吉勒布特的沼泽
它的姿态高贵, 眼睛里的纯真
一览无余, 让人犹生感动
它的起飞来自永恒的寂静
仿佛被一种古老的记忆唤醒
当炊烟升起的时候,像梦一样
飞过山岗之上的剪影
那无与伦比的美丽,如同
一支箭镞,在瞬间穿过了
我们民族不朽灵魂的门扉
其实我早已知道,在大凉山
一个生命消失的那一刻
它就已经在另一种形式中再生!
我听说……
我听说
在南美安第斯山的丛林中
蜻蜓翅膀的一次震颤
能引发太平洋上空的
一场暴雨
我不知道
在我的故乡大凉山吉勒布特
一只绵羊的死亡
会不会惊醒东非原野上的猎豹
虽然我没有在一个瞬间
看见过这样的奇迹
但我却相信,这个世界的万物
一定隐藏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我曾经追悼过一种消逝的语言
没有别的原因
仅仅因为它是一个种族的记忆
是人类创造的符号
今天站在摩天大楼的最高处
已经很难找到印第安人的村落
那间诞生并养育了史诗的小屋
只能出现在漂泊者的梦中
我为失去土地和家园的人们
感到过悲伤和不幸
那是因为当他们面对
钢筋和水泥的陌生世界
却只能有一个残酷的选择
那就是—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