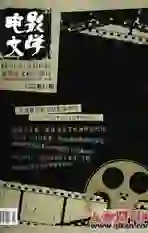再读《唐璜》:戴假面具的“真理”
2009-07-14刘杨
刘 杨
[摘要]长期以来,人们得到一个共识即拜伦的鸿篇巨著《唐璜》之所以具有特殊魅力就在于其包罗万象(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等等)。然而,笔者认为,《唐璜》不仅包罗万象、内涵丰富,而且更是将“真理”之二元对立项(bmary opposition)“真——假”进行了彻底的解构,从而预见了“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
[关键词]真理,解构;后结构主义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的长篇讽刺叙事诗《唐璜》对大多数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这部作品之所以流芳百世和经久不衰就在于其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涉及文学、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等等)。然而,本文作者认为,《唐璜》不仅包罗万象、内涵丰富,而且更是将“真理”之二元对立项(binaryopposition)“真——假”进行了彻底的解构(即:解构了“二元对立”之逻各斯中心主义),从而这部作品也一定程度上预见了“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
一
浪漫主义诗歌最初衡量自身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严肃性。所谓“严肃性”,即诗歌中的“言说者”(speaker)与它所叙述的“物”(matter)之间存在着一种很紧密的联系。这种密切的联系体现了“言说者”对这个“物”的真实的、严肃的感受。这就是浪漫主义诗歌的“严肃性”的含义。那么,这种真实严肃的感受即是浪漫主义诗歌的“真理”。
众所周知,“虚伪”是“严肃”的对立面。一个人可以一方面表现得很“真诚”,很“严肃”;而另一方面却在模棱两可的言说。而这恰恰是在说明其“两面性”。故而,此人会被认为缺乏一个真诚严肃的人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诚实。那么就浪漫主义诗歌而言,其承载的内容应该是严肃、真诚的,而不容许有任何虚假的成分的存在。其所寻求的是一个完美、真实和纯净的世界。因此它应该规避任何修辞和表现自我的成分的发挥和使用。因为修辞性的诗歌,就其思想的诺境而言,似乎是不尊重“真理”和“知识”的。因为此时“虚伪性”会有出现的可能,特别是当话语对象(包括诗歌话语)被有意指向读者的时候。当浪漫主义诗歌转向讽刺诗(通常以向读者大众“对话”的方式展开)的那一瞬间也同时将自身置于“真诚”的对立面:“虚伪”。
而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就是一部典型的讽刺诗,故而拜伦也将其推向了“虚伪”的一方。众所周知,拜伦是一位被其同时代的很多人所指责和控诉的诗人。而他的鸿篇巨制《唐璜》也被指责为“虚伪的诗歌”。这就很自然地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拜伦和他的诗歌坚持了“修辞”的特色。尽管为此招来了无数的骂名和指责,拜伦依然坚守自己的创作风格和信仰。“虚伪性”可以被看做是拜伦作品重要性的标准。“虚伪性”,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严肃性”的双胞胎姐妹,在拜伦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事实上,这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它们是对立和矛盾的。对立性(冲突)恰恰就隐藏在浪漫主义诗歌的自我完整性之中。正如拜伦在《唐璜》中如是说:
假如人人都不免于自相矛盾,
我怎能避免冲撞他们每一位?
甚至违背我自己?——但这是瞎说,
我从不否定自己,将来也不会。
凡怀疑一切的什么也不会否定,
真理之源固清,但下流就污秽,
而且要越过“矛盾”的许多运河,
以至它常常要藉“虚构”而通过。
这些诗行表明了“对立性”的存在。显然,拜伦既承认同时又否认了自己的“真实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矛盾”与“对立”。我们可以通过细读(closingreading)拜伦的《唐璜》来揭示更多的诸如此类的“对立面”。拜伦正是通过这种与读者的“对话”,来实现其“虚伪性”的存在,来阐明二元对立项(真实与虚伪)之同时存在(即:解构了“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当然,这也可以被视为拜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创作策略,即“二者兼有”(both…and)的写作策略。拜伦在《唐璜》中写到:
还请注意:像伟大的考克勋爵
但一个作家若是前后一致,
那怎能期望他写出现存的事实?
二
在拜伦作为一个诗人的职业生涯中,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必须提及(虽然这篇文章不是拜伦自己所撰写,但却是他所激发或者说导致的)。这篇文章就是亨利·布鲁额姆(Henry Brougham)(以下简称布氏)所撰写的一篇针对拜伦早期作品《闲散的时光》(1808)的批评文章。
这篇文章对拜伦的《闲》进行了非常“认真”的细读(closing reading)。布氏严厉批评了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矫揉造作”和“充满虚荣心”等等。尤为重要的是,布氏特别指出了拜伦的《闲》有意识地强调了其贵族身份以及“年纪尚轻”。他怀疑拜伦在有意识的“设计”作品的读者群。布氏认为:“或许……他提到自己‘年轻的目的就在于唤起我们的好奇心,而不是为了从我们这里博得同情和怜悯等。”布氏的上述批评现在看来的确是有失公允;但是他的评论也至少说明了一点,即拜伦的作品确实是有其读者群之针对性的。拜伦的确达到了目的:控制读者(布氏也在其中)。换句话说,布氏是一个极为认真的读者,因为他发现了拜伦作品中的一个“秘密”,即作品中所隐藏的“算计”和“虚伪性”。
《英格兰诗人和苏格兰评论家》(1809)是接下来拜伦针对布氏苛评的强有力的回击。拜伦在其中反驳道:自己不是布氏所说的那种装模作样的诗人,而是一个严肃的诗人。拜伦在《英》中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诚实,尽管作为一个作家和普通人也有失误之处,但是比那些将会在其作品中遭到其鞭挞的对象(如布氏等)更加的坦白和勇敢。拜伦在《英》一文中的回击一方面为自己报了“一剑之仇”另一方面,也更加深了他本人对于“控制读者”策略的更进一步和更深层次的理解。而布氏的那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拜伦在其作品中的“控制读者”方面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后,拜伦的作品在这个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并且这种策略的使用也越来越趋于成熟和老练。布氏指控拜伦的作品缺乏“严肃性”,而拜伦却在《英》中用一种很严肃的风格进行了回击。在这其中,拜伦并没有否认而是勇敢的承认了自己的缺点,这恰恰变成了证明自己“严肃”的强有力的佐证。这一点正是布氏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因此他中了拜伦的圈套。
拜伦的“读者控制”策略实际上就是通过与读者进行“对话”(与读者“交流”)来得以实施的。这种“与读者的对话(交流)”的策略也逐渐成为其一生的创作策略。拜伦的作品一直都保持着与读者的直接的“交流与对话”(例如,直呼读者的名字或姓氏),同时回应读者对其诗歌的评论。其读者可以是“言说者”,也可以是“听众”。在《唐璜》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与读者对话”的片段:
汝应皈依弥尔顿,屈来顿,蒲柏,
勿从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
……
像什么都行;——我写的这一堆比喻,
就为的请您选择;也许您高兴
把她比作石碑上刻出的女性。
下面是拜伦对当时的读者对其作品的评论后的回应:
人们攻击我——请想想:我!您目前
这篇诗的作者!——不知怎的,说我
意图嘲弄人类的良知和德行,
以及诸如此类的可怕的罪过;
而且用的语言非常粗暴,天哪!
我真不知道他们还想干什么!
……
这些诗节让我们看到了它们与其他的浪漫主义诗歌的不同。在这里“写作行为”已经完全将“想象活动”这一领域物质化和社会化了。我们目睹了诗歌与人的活动(事件)是如此惊人的相似。诗歌反映出在不同对象之间进行着的充满动态的交流。可见,拜伦对于读者的“在场”是如此的敏感和关注。事实上,其写作行为就是一种“想象很多读者在场”并与之进行“对话和交流”的行为。在《唐璜》的第一章中,讲述了伊内兹与其丈夫约塞之间的婚姻问题。事实上,这却是暗指了拜伦与其妻子之间的婚姻问题。这才是拜伦真正的写作意图。
伊内兹找来一些医生,想证明
她的亲爱的夫君得了神经病,
她只说,是对上帝和人的职责
使她来控告的,——这可有点奇特。
当然,拜伦在此所指向的读者既包括“知情人”,也包括普通的“不知情人”。但是,他更多的可能还是指向当时的“知情人”。拜伦的好朋友霍布豪斯(Hobhouse)读了上述诗节后曾经不止一次的奉劝拜伦“笔下留情”,因为它们实在是“太明显了”。但是拜伦却不以为然,相反却强调自己并没有在诗歌中有所指。显然,拜伦是不够坦白的。在这节诗中,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拜伦将自己的妻子、霍布豪斯以及其他的亲朋好友等都置于其诗歌的想象的读者群中。这些人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解读这些诗行,从而得到不同的理解。这恰恰就是拜伦所期望的。不同的人读后会有不同的理解,这就会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不以为然,而有些人就会非常愤怒,因为他们认为拜伦在诗歌中影射自己,尽管拜伦自己一再声称并非如此。是非难辨。真实与虚假混合在一起,实难辨别。也许拜伦已经知道什么读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看来很自信自己“控制读者”的能力,相信自己能让读者沿着自己设计的“轨道”来阅读和理解这些文字。无论如何,拜伦是一个如此“精明”的诗人,因为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这就是拜伦的《唐璜*留给我们的悬念与困惑。伴随着诗歌的发展,
“严肃性”也逐渐退出舞台。诗歌通过逐渐发展一种新的“真理”之理论回应了这种状况。这个理论就是“带假面具的真理”。
话又说回来,什么是谎言?那只是
真理在化妆跳舞。我要质问一声
史家,英雄,要人,律师和教士们,
谁能拿出事实而不用谎言弥缝?
哦,谎言万岁!一切说谎的人万岁!
现在,谁再说的缪斯愤世嫉俗?
……
《唐璜》就是“戴面具的真理”的真实写照,因为这部作品的六卷的出版都是在“匿名”的情况下出版的。拜伦自己的名字从未出现在这部作品中的任何注释和文本中。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作品的作者是谁,而拜伦也没有刻意去隐瞒,但是他又显得有些模棱两可。正如他的回应:
就《唐璜》而言,我既不会否认也不会承认是它的作者——每个人都可以各抒己见……
可见,拜伦没有直接承认自己是《唐璜》的作者,其目的就是让其作为一个“面具”来发挥作用。将“面具”作为一个原点,从这个原点可以辐射出各种各样的意义,从而丰富作品的思想内容。而这个光荣伟大的任务就交给了读者,由读者去填补意义的空间。所采取的方式就是“与读者的对话(交流)”。
当然,这个“戴面具的真理”本身充满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正如我们所着到的,解构了诗歌“真理”之逻各斯中心主义。一种构建在“矛盾(冲突)”之上的新的“真理”出现了。正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冲突与矛盾,才让诗歌得以构建新的“真理”之理论。其目的不是存在于解决(回答)问题,而是在于对问题的“设置”。《唐璜》第十七章如是说:
我把它留作疑团吧(世事皆然)。
……
《唐璜》的终极目标就是测试它自身到底能够发挥想象到什么程度,并且进一步用一个想象“对抗”另一个想象,从而来实施这些测试。整部作品始终都在实施这种想象:在谎言中想象真理,在真理中想象谬误。而这一切,正是通过“与读者的对话”来得以实现。《唐璜》对于其读者要说的一切是如此的“感兴趣”,读者所说的一切正是其发挥想象空间的一个最好的媒介(工具)。拜伦的“用心良苦”是如此显而易见。可见他对读者的控制能力是相当强的。而他所创设的这种写作模式(both…and)又是如此的明显:
但大事起于细因:您可会想到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能把
男人和女人带到毁灭之边沿的
危险的感情,起因竟如此浮泛?
……
上述诗节是“叙述者”用一种逗笑的方式讲述了阿德琳与唐璜之间关系可能带来的后果。拜伦借此暗指了发生在其生活中的一件真实事件,即:1813年拜伦与弗朗西斯女士玩一种牌类游戏的事件。但事实上,那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牌类游戏,而更是卜种情感游戏。弗朗西斯女士与拜伦演绎了一段“面具背后的真理”:他俩并非是在打牌,而是在做爱。请看下面这段拜伦对另一位女士(墨尔本女士)的精彩的描述:
我们玩着打牌(biIllards)的游戏,却没有考虑到其“危险性”……
拜伦给读者预设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拜伦与那个女人的确是在打牌,但同时他二人又似乎不是真的在打牌,而是在做别的“什么事”。换句话说,这里的文本包含了双重含义:他们二人既是在玩牌类游戏,又是在玩情人间的追逐游戏。读者的“参与”在这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有了读者的参与想象,才使得文本意义得到了丰富。让我们试想一下弗朗西斯女士读到这一段时作何感想,而她丈夫读到时又会有什么反应,又或者拜伦的任何一个亲友读到时又会有什么想法等等。当然,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和理解这些文字。这或许正是拜伦所期待的。
拜伦的这种“二者兼有”
(both…and)的创作策略在《唐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和使用。这种策略彻底解构了“真——假”之二元对立项。鉴于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拜伦的《唐璜》在一定程度上预见了“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那么,读者就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阅读拜伦的《唐璜》及其其他作品。这种阅读方式即是:解构阅读。“解构阅读是一种‘增值‘增添,但它是本文自身解构造成的意义播撒……”可以说,在《唐璜》的解读中,读者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读者积极的参与其中才使得文本意义得到了广泛的“播撒”。此时,读者与作者没有严格的区分,他们实际上共同具有读者与作者的双重性。作者面对自己的作品并没有优先性和权威性,他(她)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因为作品并非是意图的产物,而读者也并非是被动的,当读者阅读文本时,也是在与作者共同创作,这就是所谓的“阅读中的读与写双重活动”。这样一来,传统阅读所读出的确定意义就不存在了。此时阅读作品变成了一种游戏,一种想象的游戏,它摆脱了表达真理的包袱,从而走向了“文本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