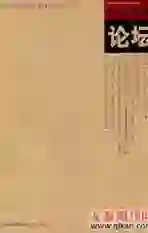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批判
2009-06-17简军波丁冬汉
简军波 丁冬汉
[内容摘要] 现代合法性理论发展至今,已经分化为自由主义及其批判两大范式。前者宣扬合法性主要来源于“法律、合法性信念和宪政民主”,而批判理论认为,这些要素虽然重要,但最终需经真理的检验,以使权力体系重新合法化。批判理论主要来自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但也来自自由主义阵营内部。这两类合法性理论的存在,为当代政治实践提供了较全面的检查视界和参考依据。
[关 键 词] 自由主义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左派理论。
[作者简介] 简军波,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问题研究中心讲师。
丁冬汉,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部讲师。
前言
合法性(legitimacy)是所有政治权力所要面对的问题。权力拥有合法性,便可获得权力对象的认可或拥护而得以长存;而长期缺乏合法性,权力一般会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甚至将遭到颠覆。由于合法性对权力如此重要,在学术领域,它便逐渐成为“政治科学的核心概念”①,“至少从霍布斯和洛克时代以来,国内政府的合法性就成为政治理论的核心焦点”②。
因其重要性,国内外学者对合法性问题的论述便显得相当丰富,但基本上没有以自由主义为基准进行分类与阐述,本文便试图从自由主义角度对合法性理论进行概括和总结,从而更准确、清晰地梳理和厘清现代社会合法性的概念和理论脉络,并为其他关于合法性问题的学术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
一、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基本内涵
作为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进行理解。经济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相对立,上承亚当·斯密,中继哈耶克、弗里德曼,下秉当代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则与政治含义上的资本主义相联系,而与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相对立。无论如何,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代议民主及现代性(modernity)密切相关,本文所指自由主义便是内在于中性意义上的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政治范畴之中的。
1.法律合法性。在自由主义合法性论述的知识份子群体中,马克斯·韦伯是最先系统地致力于这一研究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将合法性最终简约为合法律性(legality)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视合法性为权力对既定制度的遵守,以及被统治者对权力关系的首肯,他解除了价值在政治权力合法性中的地位,合法律性或实证法被抬高为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权力不能以灵活性来掩饰权力的滥用,所依据的只能是法律与制度,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情感选择③。这一观点得到卡尔·施密特的继承,并且在二战后得到了重新肯定和强化,如卢曼认为权力系统需在建立起绝对肯定的法律秩序内活动④。
2.合法性信念。马丁·李普塞特在论述合法性危机时指出,判断合法性丰裕与否的依据来自于群体的认可程度。他认为,任何政治系统,若具有能力形成并维护一种使其成员确信现行制度对于该社会最为适当的信念,便具有统治合法性⑤。这一将合法性与合法性信念相联系的观点被帕森斯、阿尔蒙德和戴维·伊斯顿等政治社会学家所认同。例如阿尔蒙德认为:“如果某一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种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⑥
大众的合法性信念来源在于权力对他们功能性需求的满足。李普塞特认为,在政治变革过程中,若权力不能满足特定社会群体的要求,便无法获得合法性。他举例说,20世纪初期的新兴阶层是殖民地精英,他们坚持要求掌握本民族政治体系,若这些要求遭拒,殖民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革命冲击⑦。可以说,功能主义与合法信信念的直接相关性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论述中是很常见的。
3.民主作为合法性的基础。自由主义合法性学说都脱离不了另一个假定,即现代政治合法性必定是民主合法性(democratic legitimacy)。政治民主对权力主体进行了法制规范,也对服从主体即权力对象提供了合法性信念依据。这一合法性观念表明,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既是法律合法性的体现和保障,也是建构服从者合法性信念的基础。因此,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内核也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民主合法性。
二、对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的批判
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自诞生后就开始遭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左派学说的批判,他们从反叛资本主义本质和各种弊端入手,对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给予了最深刻的批判。
1.新(旧)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批判人所共知。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资产阶级法权关系使处于不同阶级归属的人事实上保持不平等状态,因而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方式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及其社会,最终建立起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观念在俄国演变为激进革命理论,在列宁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政党在沙俄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通过实践埋葬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合法性。
可见,经典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自由主义合法性的所有论证和辩护,宣告一切基于(资产阶级)民主、法律和信念等为基础合法性,在没有剔除资本主义外壳的前提下是无法成立的。
而新马克思主义主要关注晚期资本主义,从技术发展与人的普遍生存状态、官僚机构和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危机等角度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缺陷。“法兰克福学派”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为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批判的典型。
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对晚期资本主义技术发展对人类批判精神的抑制做了最系统分析。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乃至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阶段,人具有两个“向度”,既具有肯定现实世界的一面,也具有反思、批判和超越现实世界的一面。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即发达工业社会已蜕变成新型极权主义社会,它压制人内心的否定精神、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使社会成为单向度(one-dimension)的社会,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人⑧。
马尔库塞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一体化和极权主义倾向的痛诉代表了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性批判,和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表达的是对自由民主合法性的坚定否认。
然而,马尔库塞从科学技术角度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方式缺乏强劲的力度,这使“法兰克福学派”的新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等人找到了新的批判视角⑨。哈贝马斯从危机概念着手,从三个方面(经济、行政与合法性)考察过晚期资本主义的体系危机,在谈到合法性危机时,他认为,由于市场机制在政府干预下逐渐虚弱,资产阶级的公平交易观念行将崩溃,政府不再是竞争性生产过程的守护者而是直接干预者,在此情形下,政府干预行为应合法化。由于这一问题在资产阶级广为接受的意识形态中获得了解决,即通过民主完成,但他依然认为,这暴露了行政干预下的社会生产与生产的私人化要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只有在行政体系足够独立的前提下才可以实现⑩。
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韦伯式的“合法性信念就退缩成为一种正当性信念(Legalitt),满足于诉诸做出一种决定的正当程序。但是,在合法性信念依赖真理的情况下,仅仅依赖于国家根据系统的合理规则所建立起来的立法垄断和执法垄断,显然是不够的。相反,程序本身就受到要求合法化的压力”{11}。
哈贝马斯不但批判了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对政治权力的理解(认为法律是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也批判了以信念作为判断合法性是否丰裕的标准。在他看来,群众对于权力机构的合法性认知存在盲区,群众并不完全了解权力系统的合法性状况,那种合法性信念从真理角度而言并不可靠。合法律性只有在经过法律制度体系背后的价值性评估后才可以真正合法化,即“法律不仅要求得到承认,而且要求值得承认”{12}。
不过哈贝马斯对自由主义合法性的批判存在重要缺陷——容易导致乌托邦式的论述,价值的绝对主义嫌疑会使合法性观念缺乏历史的和多元文化的视野,即使哈贝马斯试图对自由主义合法性和自己所持有的观点进行调和,然而终究“语焉不详,高深莫测”{13}。
2.其他左派学者的批评。约翰·基恩在《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表达了对自由主义合法性论述的报怨,他认为这样的合法性概念与许多早期的现代政治词汇命运一样,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原有意义{14}。
他将批判对准了所有自由主义合法性概念,认为在所有这些论述中(包括韦伯的),将一个政权怎样才能被视为合法的各种原则问题混在了一起,它们未能分别探讨这个政权的被统治群体的信念、他们的统治者提出的要求及上台掌权的程序的合法性。“‘合法性意味着取得了群众的同意,也可以设想这是某种想象不到的、天生似的机制在起作用,分析家看不清其中的狡诈”{15}。总之,基恩表达对合法性信念与真理相脱离的现象的不满,这一点与哈贝马斯的观点相似。
当代法国学者让-马克·库克也对自由主义合法性进行过批判。他认为,不通过规范的检验而直接将合法性定位于合法律性的行为不足以带来真正的合法性,合法性需要将规范与法律统一起来(他所指规范即价值){16}。在阐释合法性含义时他提到,合法性的基本要求首先是被统治者的首肯;其次是遵循与满足社会的价值;第三是要将价值升华为具体的法律和制度{17}。
让-马克·库克还探讨了与合法性相关的要素。比如,他声称在消除阶层差异和权力垄断的弊端前,代表制(间接民主制)并没有解决合法性诉求,因为代表也成为了一个阶层,不能完全代表被统治者。因此,这要求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不间断地进行检验。对权力而言,保持其合法性的重要努力表现为承担公共责任,而那些谋求私利的领袖会很快消耗其合法性资源{18}。
结语
自由主义合法性理论及其批判表明现代合法性理论存在两种不同的发展向度,以及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内在冲突。而这些发展和冲突为我们理解、审视和指导人类政治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现代政治的发展要求各国权力体系必须满足自由主义理论所阐述的核心要求(法治、人民的合法性信念和宪政民主),同时权力体系的作为不能到此为止,它还必须时刻面临来自真理方面的诉求,即来自质疑权力本身是否符合现代主流价值的外部压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理论的共同观点。对所有政府和权力体系而言,这两方面的要求都同等重要。
(本文系复旦大学金苗资助项目“现代合法性与美国霸权的困境”课题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YH3056043)
注释:
①M. Stephen Weatherford, Measur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6, No.1, March, 1992, p.194.
②Daniel Bodansky,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 Coming Challenge f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93, No.3, Jul., 1999, p.596.
③Max Weber, Legitimacy,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William Connolly,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First published in 1984 by Basic Blackwell Publisher Ltd,.
④{13}转引自胡伟:“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其意义”,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
⑤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 London: Heinemann, 1969.
⑥[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第35-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⑦见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 London: Heinemann, 1969.
⑧[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第3页,张 峰、吕世平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
⑨[德]于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赵鑫珊摘译,载《哲学论丛》1978年第5期。
⑩Jurgen Habermas, What Does a Legitimation Crisis Mean Today? Legitimation Problems in Late Capitalism, William Connolly,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Baisic Blackwell Publisher,1984, pp.135-155.
{11}{12}[德]于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第128、133页,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15}[英]约翰·基恩:《公共生活与晚期资本主义》第284、28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6}Jean-Marc Coicaud, Legitimacy and Politic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
{17}[法]让-马克·库克:《合法性与政治》中译本序,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18}Jean-Marc Coicaud, Legitimacy and Politic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