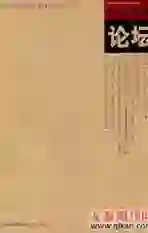生命的自然与自然的生命
2009-06-17尹秋雯聂庆璞
尹秋雯 聂庆璞
[内容摘要] 庄子哲学的核心问题是生命问题,在这一母题下理解庄子的自然审美,可以发现庄子的自然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然,它是属于生命的自然,而庄子文本中的“自然”本身也仅仅是出于生命考虑,以主体精神构造出来的审美乌托邦。庄子关于生命与自然合一的思想早已为人论述多遍,但是庄子的生命并非人们所说的逍遥的生命,而是一种受难的生命。从这一视角出发,庄子美学将得到一种新的解析。
[关 键 词] 庄子;自然审美;受难生命;超越。
[作者简介] 尹秋雯,就学于中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和网络传播研究。
聂庆璞,中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和文艺美学研究。
一、生命的主题
在一些注释者看来庄子哲学的核心在于:探索在乱世中如何保全生命与超越生命困境的问题。这种对生命重视、对生命意识进行哲学自觉反省的精神尤其贯穿于《庄子》的内七篇。王博就认为:内七篇不同于外篇和杂篇,它是自成体系的,而且“内七篇很明显地是围绕一个主题——生命的主题——展开的”①。并且内七篇对于生命的体系性认识,被庄子后学零散又时而不乏深刻地继承了。如此看来,如何对待生命确乎应成为庄学的核心问题——“庄子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即生命问题”②。
同时代的思想家一般把政治秩序当成中心议题,而庄子的思考重心倾斜于生命在乱世中的安顿。庄子学派把忽视生命的思想家们评点为“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天下》)当时流行的儒家、墨家都把生命当成外在道德的附庸,主张“杀身成仁”或者“自苦以为天下”等,以惠施为代表的名家在万物中唯独忽略了人本身,而法家、纵横家更是鄙视人的生命,把生命看作追逐功利的纯粹工具。庄学认为,这些执着于外在世界而忽视生命本身“逐万物而不返”的态度和行为会让“内圣外王之道”(《天下》)暗而不明。至于纯粹的自然世界,就更不能引起庄子的注意了,庄子主张“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齐物论》)。只有人的存在才是庄子最关心的问题,关乎生存的哲学在时代乱世中成为庄子的思考主题。
二、生命的困境
王博把《人间世》看作解读庄子哲学的“首篇”,因为《人间世》代表着庄子对世界的一般看法,可以被看作庄子哲学产生的个体感受化了的“时代背景”。在其中,庄子把他生活的时代描述为一个生命受到极大威胁的时代。“回闻卫君,其年壮,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民其无如矣!”(《人间世》)可见,卫国君不仅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而且“其年壮”,这就暗示了浓黑悲凉的“非人间”世界还会延续下去。“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周围尸横遍野,朝中君主嗜杀成性,在权力世界中人们进退维谷。被分配了出使任务的叶公子高就清楚地意识到“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人间世》)。身体损伤(“人道之患”)与精神损害(“阴阳之患”),两者必得其一。在生命时刻受到威胁,人的精神状态,生命的质量便可想而知了。叶公子高受命后“内热”的感受就代表着当时多数人(尤其是士人)的普遍感受。成玄英说:这种内热就是“怖惧忧愁,内心燻酌”③。严酷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人的戕害让人变得煌煌不可终日。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孟子·梁惠王上》)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悲惨的生命境遇。庄子更是把人的存在称为“与物相刃相糜”的过程,把人生在世比喻为处于神射手的靶心,即“游于羿之彀中”(《德充符》),“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惶恐又不可逃遁,这就是庄子面对的最无奈的困境。
在这种生命困境的逼迫下,庄子开始对生命问题的思考从具体的境遇上升为普遍的对生命的反思。在脆弱短暂的生命过程中,人们要遭遇外物的束缚和压制。即使生命得到保全,那么这浑浑噩噩的生命之意义又何在。故庄子首先提出肯定生命,持一种贵生论的态度:“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大宗师》)其次,他主张要在“苦”的生命中寻求一条超越之路,让生命摆脱一切社会的、情欲的、功利的束缚,实现自由和重现生机,即“无待”的“逍遥游”。前者更多地被道教继承,后者更多地被中国传统文人继承。正是通过后者,庄子极大地影响了民族的心理—文化结构,并且影响了中国的艺术精神和美学系统,这正是我们所要考察的。
三、超越天人分裂
在庄子“非人间”的天人对立、天人分裂的严酷事实下,天(外部世界)作为一种强大的异己力量残害、蹂躏生命主体的自由和尊严。庄子敏感地意识到这点并改变了思考向度,他并不像儒墨学派利用政治和社会秩序使天人达到和谐,而是把天人和谐的理想状态内在化。孔子的“吾与点也”是理想社会的写照,而庄子的“与物为春”则是绝对的内在态度,它与社会、与他人毫无关系。即每个人都可以实现其自身生命的意义,祛除暴虐的天,重回真正的属人的天,但这种状态能否实现取决于心灵,而非外物。
虽然这个世界是野蛮的、残暴的、荒谬的,但是“我”的生命却是可贵的。在庄子看来,“审美”成为了一种善待生命、实现生命意义的人生态度和一处受难生命的栖息之地。与孔荀“文质彬彬”(《论语·雍也》)、“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荀子·修身》的态度不同,庄子对当时社会政治大抵是极度失望的,他认为社会政治与美无关,真正的美是属于心灵的。在《德充符》中,庄子描述了很多身体畸形和残废的人,但是他们都是有“德”之人,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充分理解庄子的经典隐喻:形体的残疾表征着生命经受着天人分裂的苦楚,而内心的充盈则表征了人可以在苦难的生命中找到一种超越的价值,生命因这种价值而充实了自身。同时,这个隐喻的意义可以解读为两方面:一是生命的脆弱,容易受到摧残;二是人的内心才是生命的本质所在,心灵优于形体,可以超越形体,超越形体也便超越了苦难的人生。为了实现生命的意义,庄子找到了生命最根本的立足点——人的心灵。这个立足点向外投射便生成了自然之美,自由心灵的外在寄托是生命本质的外化、投射。
四、改写自然
“面对压抑人性的现实,庄子向往原始的自然生活,回归‘至德之世就是要回到自然,以自然为至美,自然主义也是庄子审美生存的源头”。④庄子对政治的失望导致他对自然的崇拜,社会政治把自然的生命变成了异化的生命,反抗社会对个体生命的残害、压迫,就应该回归自然。于是自然崇拜的原始遗俗被庄子复活了,并被抬高为“至美”的属人之境。庄子笔下的自然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自自然然,不事人为;二是指自然环境、山水花鸟。⑤后者作为实体性的自然不只是对前者的逻辑演绎,更是范畴升华。庄子笔下的大自然并非纯粹的自然,它是主体精神的一种象征,代表着生命的超越之维,显然比“无为”包含着更多内容。
庄子笔下的大自然祛除了强大异己力量的一面,没有了天人对立的灾难叙事。这无疑是有悖常理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然看作人的异己力量和改造对象才应该是最基本常识。在远古神话中,大自然的同义词是洪水猛兽,根本就不是那种可以诗意栖居的环境。庄子对大自然做了诗意改写,让自然表征生命,去对抗当时社会对生命的异化。这是一种在生命现实困境下生发出来的绝望,这种绝望催生了构造乌托邦的欲望。庄子笔下的“神人”大都是在自然界中自由遨游的人物,这象征着生命力的自由释放和无限扩展。同时还默含着一种审美之境,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人与万物相互交感,人与大道神秘契合,张扬着恒久的生命活力,隐秘地歌颂着生命的狂热: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苦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疡而年谷熟……(《逍遥游》)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齐物论》)
“神人”是什么样的人?从低端来说,他们仅仅是免于被戕害的生命,“不能热”“不能寒”“死生无变于己”,庄子并不能忘怀生命所承受的苦难和恐惧,这种悲剧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这里的自然界应该被看成心灵虚构出来的生命升华之境,它通过理想生命外化的径程达到了一种文学的乌托邦效应。审美在这里被恐惧和欲望俘获,但是它又具有一种超越本能,轻轻松松地超越了沉重的悲剧感,并走向了“乐感文化”的终极层面——最高境界。
五、自然的生命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人间世》),审美是超越的,但是超越的动机却在于生命遇到了无可奈何的困局。庄子没有放弃对生命的追求,他理想的生命状态在于:自然的生命。任其自然,而免于人为的残害、荼毒。这种愿望导致了庄子对自然的崇拜,自然在这里也被一厢情愿地假想为善的和美的。大自然的壮丽、广阔、灵动仅仅是困境下生命一种源自本能的自发构造。人心特有的这种构造功能给超越现实预留了一种可能。
审美境界是实现生命超越所获得的最高乐趣,与其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激情,不如说这是现实黑暗之下的深刻无奈。但是无奈者却深深眷恋“此岸”,并且在其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和乐趣——“作为庄子的最高人格理想和生命境地的审美快乐,不止是一种心理的快乐事实,更重要的是一种超越的本体论态度”⑥。自然审美是主体借助客体达到的一种形上境界,可以看作是对生命不得自然发展的补偿。当然,除了补偿以外,因为有了这种超越之维,生命的价值才能远远超过一般有“成心”的生命,变得充满乐趣和意义丰满。
审美是从属于“自然的生命”这一诉求的,审美虽然不是功利性的,但又有服从于某种人生目的的合目的性。庄子后学洞悉了这点,他(们)明确表示:“圣人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知北游》)。天地之美并非是纯粹的自然之美,这种自然只是因为显现了主体的寄托和意志,才变成可以“游”,可以“体道”的美丽自然。圣人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达万物之理”。庄子学派不同意“逐万物而不返”,因此这里的“万物之理”当是指与人及其生命密切相关的神圣真理。
六、生命的自然
庄子认为人的乱作为造成了生命困局,这不仅直接伤害生命,还造成了生命的“内热”,让它变得充满忧愁和恐惧。而生命的理想境地就是去除这种人为,让生命自由展现、自由发展,让生命任其自然。因为对抗和失望,庄子把注意力转向了人为世界的对立面——自然。庄子的大自然是人主体愿望和主体意志外化形成的产物,它的作用在于能够烘托出主体生命的自由,证明主体与道为一的精神能力。“大自然”之所以能烘托出生命的自由,就在于这种自然是一种被改写、被去势、被阉割了的自然,它丧失了狂暴的异己本质,变成了一种被动的、安详的、无为的适合生命栖息的理想姿态,它任由主体去刻写、去流连、去抚玩。它不仅不像现实社会那样残害人,反而成了主体刻写自己精神本质的优秀对象。这种自然显然成了属于生命的自然。
庄子提出的超越是向内的功夫。他认为,只要掌握了这种功夫就能让心灵保持和乐的状态、摆脱外界束缚从而实现生命价值。向内的超越要求主体要经过“坐忘”“外天下—外物—外生—朝彻—见独—无古今—入于不死不生”(《大宗师》)等步骤才可以达到对“道”的观照。这些步骤以“忘”为根本特征,这就印证了庄子试图达到人生初始状态,即自然的生命的努力。能够实现对道的观照,就能得到“至美至乐”⑦。“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田子方》)。代表庄子自然审美核心概念的“游”,应该被看成主体自我修养的结果,这种修养让生命忘却一切苦难、固执,达到“自然”的理想状态。“游”是对修养的自觉操练、审美印证,是收获主体生命活动的外在成果。被移情化了的、被皆着我之生命理想的“自然”,甚至可以看成是生命意识的自我观照。大自然不是纯粹的客体,而是一个沟通物我的中介,但是美感却被滞留在这个中介上了,以显示出美感客观化的过程。因此,大自然在庄子的语境中不仅表现着宇宙本体,更表现着自我生命理想。庄子所谓的“天地之大美”因此也应纳入生命范围。
七、解牛神话的生命透视
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人与万物相互感应,人与大道神秘契合,大自然用庄子的文学语言隐秘地歌颂着生命的热狂。庄子自然审美观的本质其实是自我生命理想的感性呈现。庄子塑造出的一系列工匠艺术家形象可以看作这种观点的例证:如“痀偻者承蜩”“津人操舟若神”等等,这些“艺术家”们在各自的领域自由嬉戏,自由展现着生命创造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应该是“庖丁解牛”(《大宗师》):庖丁杀牛的过程不仅具有“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的艺术元素,其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高超的“行为艺术”。“官知止而神欲行”,这种合目的与合规律的统一便是美的创造。“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则是一种因为创造力得以升华,而呈现出的一种精神享受,它超越了物质功利,超越了一切庸俗的感官快乐。这种“道也,进乎技矣”的生命快感是感性快乐和形而上学的本体快感的合体,庄子审美境界的形成“是由于人的自由得以显现,人的实践创造的力量得到肯定获得的一种精神的满足和愉悦”⑧。生命在这里以“道”的名义展现了自身令人愉悦的创造力、活力,达到了审美生存的最高境界。
“庖丁解牛”在庄子美学中的意义也许还没有充分地被发掘出来。在笔者看来,“庖丁解牛”其实体现受难生命更急切的欲求。它是一则描写“屠杀”艺术的故事。如前所言,庄子生于乱世,生命困境最直接地来源于杀戮,但庄子却把屠杀上升为一种“艺术”的体道活动,这似乎是一种反讽,他嘲笑了社会统治者连屠杀都属于“月更刀”“岁更刀”的“族庖”,永远不能体道。这无疑是利用“恶搞”来排解恐惧的惯用手法。从弗洛伊德学说看,向外的屠杀代表着一种施虐的本能快感。编故事者往往给自己在故事中留一个或多或少类似于自己的人物形象,无疑,庖丁身上肯定有庄子的影子。受压抑的生命往往更需要强烈地释放生命的潜能,但是庄子却用审美的方式把生命中被压抑了的潜能升华了出来。“庖丁解牛”以寓言方式暗示着庄子整个美学体系的生成动力和生成过程。同时,“乐感文化”那种以理控情,以情入理的姿态,在这里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个生命被蹂躏的世界中,对外发泄生命力无疑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生命的母题在这里,是如此的明显,如此的急迫。庄子的自然审美、庄子的美学在这一母题之下似乎可以得到更好的阐释。
注释:
①②王 博:《庄子哲学》第142、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第12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时晓丽:《庄子审美生存思想研究》第39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⑤⑥李泽厚:《美学三书》第280、271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⑦⑧叶 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第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