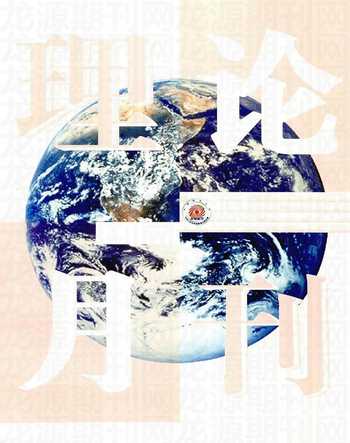论唐代对受贿犯罪的惩治
2009-04-29秦文
秦 文
摘要:唐律作为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以其完善的立法思想、高超的立法技术闻名于世,尤其是针对官吏受贿犯罪的法律设计严谨周密,尽管现在去古甚远,然而其中许多合理化的法律制度对我们现今的刑法完善有许多借鉴意义。
关键词:赃罪;惩治;比较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12-0119-04
西晋张斐注《泰始律》时解说:“赃”: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唐代在总结前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对官吏赃罪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于唐律中首次确立“六赃”的概念,对官吏赃罪的认定和惩罚更加具体和细密。六赃罪分别于唐律首篇《名例》卷第四《彼此俱罪之赃》、《以赃入罪》条以及《杂律》“坐赃致罪”条,分别为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六类经济犯罪。其中除“强盗”罪与官吏犯赃无涉外,其余五赃之窃盗(其中“监守自盗”条)、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坐赃均涉及官吏受贿犯罪。下文将对唐代惩治官吏受贿犯罪法律的主要特点进行阐述,并进而与现代刑法加以比较,期望对现法律的完善提供理论上的帮助。
一、官吏受贿犯罪成立要件范围较宽
六赃中将受贿分为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唐律138条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此外,即使不是受财,获取其他的非物质利益,同样可以认定为赃罪。例如性贿赂行为,唐律186条,对于监临官特别规定:“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为亲属娶者,亦同。行求者各减二等。各离之。”甚至对于接受馈赠借贷财物等一类行为也要受到惩处。唐律141条——148条,均涉及到对接受馈赠、乞娶、借贷、私自役使等行为的惩处。由此可以看出,唐律不仅对于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行为严厉打击,而且对于监临官变相接受财物,以及利用各种名目聚敛财物的行为,甚至是借钱借物等现在看来不值一提的行为,一律视为犯赃,并给予有力打击。这些规定,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可细细想来,唐律的制定者立法意图在于要求官员洁身自好、防微杜渐。从小事着眼,处处严防死守,不给行贿人留下任何空隙,从而做到为官清正廉洁。
就现代刑法而言,首先,受贿罪构成要件中强调“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事实上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较大财物的行为显然具有社会危害性,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古今对比,不难看出,唐律赃罪刻意强调官吏利用职权的“受财”行为,无论是否枉法,本质都是行为人对职务权力运用的廉洁性的破坏。从而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而且大批受贿者可以以此为借口。堂而皇之接受各种感情投资、礼品馈赠,从而逃避法律的制裁。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如日本、韩国、德国、泰国、奥地利、丹麦、美国及我国港、台地区都没有将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成立的构成要件。其次,应当逐步摒弃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物质利益”观念,将贿赂对象向某些非物质利益延伸。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财物扩大解释为财产和财产性利益,不能以金钱估算的其他利益均不能认定为贿赂范围。而《公约》则将贿赂的对象明确表述为“不正当好处(利益)”,其他相关的地区性或者国际公约对贿赂对象的表述均与此一致。从世界各国、地区的立法来看,除奥地利、俄罗斯、西班牙等少数国家的刑法规定贿赂仅限于“财产上的利益”外,其他多数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刑法均规定,能满足人的欲望或者需要的一切利益,都是贿赂。较为典型的是,日本刑法典甚至将接受很可能升值的股票以及超出实际质量和功能的评价引发的误导性接受赠与物也视为构成受贿罪。就我国社会生活的实情看,给予、接受、索取非财产性利益已成为腐败的一种重要手段,而且对于贿赂犯罪,《公约》第15条是采取“各缔约国均应当……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这种强制性而非任择性条款来规定的。将贿赂规定为“不正当好处”,是《公约》的强制性要求。而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与《公约》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二、官吏贪污受贿起刑点极低
唐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138条)汉代“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唐代丈量单位与汉代差异不大,幅宽一尺八寸,长四丈为匹。15匹约60丈。60丈锦绢的价值究竟有多大?有人做过一个相对的比较:唐律规定庸人代役。日庸钱为3尺锦绢,那么60丈锦绢就等于200个普通劳动日值。据此推算,今天一个普通劳动日值约30~40元人民币,200个普通劳动日值大约在6000-8000元之间。唐律规定监临官受财枉法200个劳动日值即要判处死刑,也就是说监临官贪赃枉法约相当于今天6000-8000元人民币的价值就要判处绞刑。对于受财不枉法,唐律规定赃满30匹即贪赃达400个劳动日值的钱物,虽然没枉法也要判处绞刑。而对于一般盗窃,唐律《贼盗律》(总282条)规定,“窃盗,不得财,笞五十;得财,一尺杖六十,一匹加一等;五匹徒一年。五匹加一等,五十匹加役流。”可见,一般盗窃罪无死罪。
现代刑法有关受贿犯罪起刑点,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规定一般为2000元,1997年《刑法》修订后规定一般为5000元。而有资料显示,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目前在实际办案中,一般情况是,受贿金额5万元以上的才立案。而盗窃罪则规定“1000元以上不满2500元的,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六个月或单处罚金”,起刑点远低于受贿罪。从刑罚的一般配刑原则来讲。对职务犯罪的处罚要重于非职务犯罪。前者所造成的犯罪后果远重于后者。而且。过于明确的数额标准使得刑罚空间过于僵硬,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一定数额之内的受贿是允许的。于是造成相当大的法律漏洞,对惩治腐败十分不利。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从性质上进行区分,受贿即使数额很小,也构成刑事犯罪。加拿大、英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刑法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的相关刑事规范,均无关于受贿罪数额的明文规定。司法者应当通过考察除数额外的其他情节,结合贿赂对象以及行为人所追求的不正当利益,综合平衡确定是否构成犯罪,进而选择量刑。
三、根据官员不同身份实行同罪异罚
1对监临官受贿处刑极为严厉。《名例律》第54条专门对监临和主守官做了界定:“统摄案验为监临。”疏议:“统摄者,谓内外诸司长官统摄所部者。案验,谓诸司判官判断其事者是也。”“躬亲保典为主守,虽职非统典。临时监主亦是。”疏议:“‘主守,谓行案典吏,专主掌其事及守当仓库、狱囚、杂物之类。”监临官就是政府各部门的长官和主管官吏,主守官就是专门负责掌管某一事
务的官吏。对于这类官员受贿一律严惩不贷。《贼盗律》第283条:“诸监临主守自盗及盗所监临财物,加凡盗二等,三十匹绞。”疏议:“假有左藏库物,则太府卿、丞为监临。左藏令、丞为监事,见守库者为主守,而自盗库物者,为‘监临主守自盗。对于监临主司受贿行为,唐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监临官接受监临人(即下属)财物,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对于送钱物者,也要给予减监临五等处罚。但对送物之人的处罚,只能限制于杖刑,杖数不能过百。而一般的赃罪,即对于非监临主司因事受财的情况,唐律(杂律)中规定:“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与者减五等。”对于监临主守特别是刺史和县令贪污、受贿,采取加重惩处的措施。如德宗贞元六年十一月敕:“自今以后,太守、县令有犯赃者,宜加常式一等。”唐律一如既往地从重处罚受财枉法的官吏,犯此罪者可以处以死刑。为了警示贪官污吏,对个别犯赃的五品以上高官更采取“集众”公开处死的特殊行刑手段,杀一儆百。《资治通鉴》卷记载的沧州刺史席辩赃污案、《旧唐书·代宗本纪》记载的宣州刺史李佚坐赃案,是其显例。唐朝统治者之所以对亲民之官和国家司法人员犯法行为从严惩治,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政教的推行和封建法律的权威,从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稳定。
2区分“有禄”官与“无禄”官。唐律138条。对于监临主司受财枉法或不枉法条,其中规定:“无禄者,各减一等;枉法者二十匹绞,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按照唐代禄令规定,官员从正一品到从九品,一年禄米从700石到52石有差,唐禄分春、夏、秋、冬四季。唐律根据官员是否有禄,作为区分刑事责任的依据之一,其思想出发点当是高薪养廉,享受高薪俸禄者理应为廉政的表率,因此,一旦涉及赃罪,必定要受到比无禄者更重的惩罚。如玄宗天宝十一载十二月敕:“牧宰自人。所寄尤重,至于禄料,颇亦优丰,自宜饬躬励节,以肃官吏。如闻或犯赃私,深紊纲纪。今后刺史犯赃宜加常式一等。”后世律典继承了这一思想。明代学者王肯堂《读律笺释》云:“官吏俱指见任见役者。受财虽同,而枉法不枉法则异,财之受,法之枉不枉虽同,而人之有禄无禄则异。”
现代刑法理论强调同罪同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受贿罪中,不同的犯罪主体其罪行所产生的后果恶劣程度是不同的。上述这类人受赃枉法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危害特别大,因此,对其惩罚也理应特别严厉。若严格按照同罪同罚的刑罚理论,就其后果而言,势必有失公允。我国目前受贿犯罪处罚的规定太笼统,不利于贯彻区别对待的法律精神。因此,在处罚上对国家工作人员与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普通公务员与特殊公务员,收受贿赂与索取贿赂的行为,还有情节严重与情节特别严重等情况区别对待,以保证司法机关定罪量刑的准确性,从而更好地贯彻罪刑均衡的原则。
四、官吏赃罪处罚实行连坐
唐律一般规定公罪连坐,贪贿属私罪范畴,但为了严惩和预防官吏贪污受贿犯罪,唐代法律也规定了相关的连坐措施。
1亲属连坐。《职制律》规定:“诸去官而受旧官属,士庶馈与,若乞取、借贷之属,各减在官时三等…‘家人受所属吏民馈送及借贷、役使、经商牟利等,减官人罪二等论处,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减家人罪五等;执法官吏犯赃,从重处罪。”越一法律规定带有连坐性质,而连坐又是被后人所诟病的古代法律最主要的弊端之一。但唐律规定监临官家人犯赃连坐则应有其道理,因为家人广纳坐贿,数额甚至达数百千万,当官者难道会一点都不知情吗?此外,唐律在这一法律规定方面的连坐,对确不知情的监临官本人虽有惩罚,但惩罚较轻,即减监临官本人犯赃七等论罪,最多不过是笞刑之类。当然一旦对监临官本人治了罪,其仕途升迁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故从影响仕途的角度看,连坐惩罚足以威慑监临官,他们不但要严格要求自己,也要严格要求家人不涉足任何贪赃受贿之类的勾当。而从今日腐败很大一部分属于当官者的家人犯罪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不认为唐律所规定的家人犯赃监临官本人连坐的惩罚确有其允当之处。
2职务连坐。唐律当中没有规定同职犯私罪连坐,但是为了严厉打击官吏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在司法实践中,下级官吏犯赃罪,要连坐上级长官。其目的就是为了加强上级官员的监督管理,杜绝犯赃行为发生。如玄宗时,韦凑任河南尹。开元10年,河南府洛阳县主簿王钧因受贿被杖杀。玄宗下诏:“两台御史、河南尹纵吏侵渔,《春秋》重责帅,其出(韦)凑曹州刺史,侍御史张洽通州司马”。根据《唐会要》所载,不难得知肃宗、宜宗朝都有下级官吏犯赃连坐长官的例子。反之,长官犯赃罪,有时也会连坐僚属。天宝6年3月,岭南五府经略采访使兼南海太守彭果坐赃被决杖、长流溱溪郡。“会果坐赃,连累僚佐”,岭南五府经略采访使判官郑日户因此被贬为光化尉。现代刑法原则强调罪责自负,然而就受贿罪本身而言,往往涉案人员不只是直接负责的官员,上级官员没有有效的监督、防范或故意放任,甚至官官相护、利益均分,由此所破坏的不仅仅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而且污风蔓延,严重影响了国家公权力的形象,造成民众的信任危机,影响国家行政体制的正常运作。当然,时过境迁,如果一味盲从古人的做法,恢复连坐体制,无疑与现代法治文明精神相悖,然而严于治吏、强化监督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五、刑罚与行政处分一体化,对犯赃官员实行资格刑
唐律规定(18条):“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犯奸、盗、略人若受财而枉法者,亦除名;狱成会赦者,免所居官。(会降者,同免官法。)”这也就是规定,官吏犯有受财枉法等罪名,在接受刑罚的同时,必须受撤销其所有官职和爵位的惩罚,即使是刑案判决后上报遇赦的,也要被撤去现任官职。(遇降级处刑的,依免官法处理)除此之外,从唐令以及唐代皇帝发布的诏敕和司法、行政实践的史料记载,可以看出,对于贪赃官员多实行禁锢和追告身的惩罚。禁锢就是禁止官员再叙官,终身绝仕宦之途。这种形式经常被称为“永不齿录”。如太和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中书门下奏,县令“犯赃在一百贯以下者,举主量削阶秩,一百贯以上者,移守僻远小郡,观察使望委中书门下听奏进止,所举人中,如有两人善政,一人犯赃,亦得赎矣,其犯赃官,永不齿录”。追告身是指追夺官员做官的证明文书,包括追夺历任告身和现任告身之一或两种都追回。唐代开元七年令规定:“食禄之官,若犯私罪,考在下中以下,犯公罪考在下下,解所伍,……追告身。”告身既是做官的证明文件,同时又是可以折抵刑罚的特权,失去告身往往意味着被解除官职,失去了应有的权利,因此其实是一种很重的资格刑。刑罚与行政处分一体化,从而使得撤免官爵有了法律的监督和保障。这种惩处办法,无论是单独适用还是附加适用,对于官
吏的震慑力是很强的。
根据权力寻租理论,任何官员在进行贪赃犯罪时,肯定要对犯罪成本与犯罪收益进行计算,当犯罪成本大大超过犯罪收益时,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受贿行为。因为他们不得不考虑由于贪欲酿成的犯罪所需支付的犯罪成本过高,因为一旦涉罪,轻则要受囹圄劳役之苦,重则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对于这些饱读诗书礼义的士大夫而言,名誉重于利益,一旦犯赃被查处,会被弄得名誉扫地、颜面全无,不仅本人前途尽毁,甚至会使子孙后代仕途受阻,对于身负光宗耀祖重任的他们,这种代价实在太大了。因此,制度设计本身在于警示官吏洁身自好、廉洁自律,以免以身试法,身败名裂,从而保证国家官僚体制的有序运转。
唐律严惩贪赃犯罪的做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效。后世评价贞观时期的吏治:“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后妃之家,大姓豪滑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袭细人”。王船山认为,唐太宗时期“义明而法正,奸顽不轨者恶足以恣行而无忌,即有之,亦隐伏于须臾,而终必败。”
我国刑法并不缺乏资格刑,但在贪污贿赂罪中,除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被当然剥夺包括上述权利的政治权利外,对其他罪犯并不必然附加资格刑,这将导致刑法预防、打击犯罪力度的降低。从世界范围看,多数国家都规定对贪污贿赂犯罪除判处自由刑以外,附加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如意大利刑法第317条之2“附加刑”规定,因贪污贿赂犯罪受到处罚将被褫夺公职终身。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有类似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其犯罪成本,遏制贪利欲望,从而实现有效遏制腐败的目的。
综上,通过对唐律惩贪肃贿相关法律惩处措施与现代刑法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优秀法典,在惩治受贿方面精细的设计。其中重惩犯赃官吏、维护廉政体制的思想,十分值得借鉴。一部唐律445条,其中有233条罪名与官吏职务犯罪相关,足见统治者对吏治的重视,正所谓“明主治吏不治民”。与我们现代的刑法相比,有许多思想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目前反腐成为全球之势,惩治腐败的刑罚呈多样化、严厉化的特点。我国在设计反腐相关的法律时,也努力与国际接轨。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就有关官员身边人受贿的相关法律问题作了界定,与国际反腐公约保持一致。继续进行追溯,其实唐律中已有这方面的相关规定。因此,虽然我们已经距古甚远,然而许多宝贵的思想不仅是古今相通,而且是中西相通。当然,不可否认,作为一部封建法律,其中的糟粕性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唐律第186条,为避免监临官员因亲枉法,不许监临官员娶所管辖区的百姓女儿,尽管主旨是预防腐败,现在实行未免不合时宜。既不符合现代人员流动频繁的现实。也违反婚姻自由的原则。因此,对于传统法律,我们也要仔细甄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