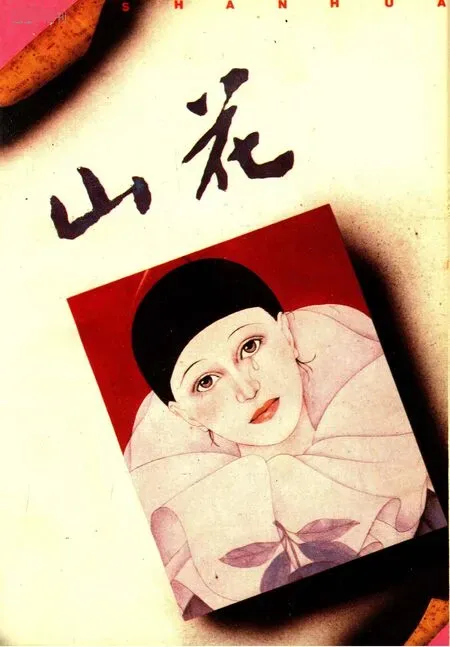婚变
2005-04-29赖榆
赖 榆
已经过了立冬,雨还是一下就七八天,整天淫雨连绵晦气沉沉。说来也怪,今天一大早,突然停了。之后,灰潆潆的天上怪怪地凸现一个毛绒绒的太阳。
方洲的头发就像一顶帽子,盖在他的浓眉大眼的脸上活像个猫头鹰,这是鞍山铁西区那个漂亮理发师的杰作。幸好他那双眼珠子儿圆瞪瞪的,显得很有精神。当兵出操搞惯了,他在公园里走路也是挺胸收腹甩着膝盖操正步,雨水淋过的落叶湿漉漉的,打湿了他的鞋子和裤脚。有两个环卫工人在用竹丫扫把清扫林荫道,干干净净的黑灰色水泥路面正一段一段清清爽爽地显亮出来。
三三两两的游客陆陆续续踱进公园大门,拐向飘逸的林中小路,可是华美一直没有出现。她怎么了?方洲想,不是已经说好了的嘛,莫非还会突然发生什么变化?
方洲是从单位直接来的,出差回来正轮到他值夜班,来之前专门给华美打了电话,约她回家一趟,华美斩钉截铁说永远不愿意回到那个让她伤心的地方。方洲说那我到你那里去好不好?华美说没必要,你如果同意了,我们约个时间直接上街道办事处办手续。方洲说又不是听音乐会,那么大的事情,总有些细节要谈吧。华美说看来你已经想好了?方洲说就算是吧。
后来说定,十点半在公园见面,一进公园大门右手有个茶室,格调幽雅,还可以点菜,那是他俩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方洲是个守时的人,他提前到达,不知道她今天是不是会准时。反正这种关键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迟到,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这次约会,无论对他,或是对她来说,都至关重要,关系到第二次婚姻存在还是消亡的重大问题。自从华美提出离婚,他就找不到机会与她好好地谈一谈。
方洲很顾面子。他在部队就是正团级干部,现在是集团公司的工会主席,属于副地厅级干部。他离过一次婚,前妻不喜欢当兵的人,可又偏偏嫁给当兵的人,那些年的事情真是说不清楚。后来,不知怎样与她的老同学联系上了。那同学是个经济学博士,在美国的一所大学当教授,没过多久,前妻提出与他离婚,嫁到美国去了,还要把女儿带过去,说是让女儿在美国读书深造。当时方洲刚刚转业,一切都得重打锣鼓另开张,只得让前妻把女儿带走,说只要女儿愿意你就带她走吧。女儿刚上高中,一听说要去美国,高兴得梦里都在手舞足蹈,哪有不愿意的道理!
那时候方洲已经四十多岁了,厂里正在搞改革,搞公司制改造,由军品转产民品,他又要工作又要进修,忙得一塌糊涂,根本没心思考虑重新结婚的问题。奇怪的是亲戚朋友实在是太主动太热情,整天把他的婚姻挂在嘴上,不是这家设局,就是那家请客,几经介绍,他就认识了华美。华美有一米六五高的个子,胸部很丰满,腰肢却纤细,穿着一件紧身体恤,配上短包裙,显得线条分明,身段相当动人。长方型的脸盘子长得很清秀,眉毛比画过的还要均称,头发又黑又亮,眼睛像一泓纯净的泉水,鼻梁笔挺得像是经美容院加工过的,嘴巴稍大了一点儿,但是很耐看。反正,算得上一个美人。介绍人是厂里保卫处的徐处长,他事前就给方洲讲过华美在本市名气很大的私立远志中学当音乐老师,歌唱得不错,还获得过黄果树杯优秀歌手银奖。现在见了面,方洲在心里赞赏说没错,是个搞艺术的。
这种近似于互相“面试”的场合已经有好几次了,方洲一直没找到感觉,那晚见了华美却有种莫名的冲动,他抽空把老徐扯到一旁要求给个机会与华美单独谈谈。老徐眼睛一亮,说那就行了,华老师也是这个意思;看来你俩有缘。
应该说,方洲跟华美的确还是有缘的,他第一次打电话约她到这家茶室见面她就没拒绝。那是个周末,时值初秋,就像今天一样雨后初晴。天并不凉,可是华美从公园大门那边款款走到方洲面前时他居然觉得浑身在哆嗦。方洲结过婚,可是活到43岁他还是第一次这样跟女人约会,不知道如何进入角色。殊不知就是这副手足失措的模样让华美作出了选择。
第一次约会,两人居然在一起呆了一整天。华美不喜欢说话,方洲没完没了地说西藏的风光,说他在部队上的事,她听得津津有味。时而惊讶,时而叹息。两人爬到山顶,又回到湖边,在那里看到一个照相摊子,方洲灵机一动,试探着问华美:允许我跟你一起照张相吗?
华美定定地看了方洲好一阵,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啊……
没多久,方洲就成了华美家的常客。华美家就是她姑姑家,华美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她来自北方的一座中等城市,她说她不喜欢那座北方的城市,所以她才来到了南方,她有一个姑姑,就在这座城市里,是和姑父随着南下部队来的。为什么不喜欢那座城市呢?华美说她在那里结婚后与丈夫过不到一块儿,丈夫气大如牛,对她又打又骂,根本就不把她放在眼里。最后,她毅然与丈夫离了婚,从北方乘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来到遥远的南方投靠自己的姑姑。
姑妈非常喜欢方洲,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儿子一样,说方洲有文化,聪明,人也长得精神。一点也不摆领导干部的架子,还知道体贴人。说华美找到他是福份。俗话说结二次婚是“一台新婚事,两套旧家什”,可方洲不愿意。那时候他刚分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新住宅,他花了三个月时间把它装修得设施齐备又漂漂亮亮,家具也全是新的。华美说你完全不必如此奢侈,方洲说不对!要是有钱,我愿意让你像公主一样做我的新娘。
还公主呢,华美说,都二班老太婆了!
和华美刚认识的时候,华美问起过他为什么离婚的问题,他说得相当详尽。方洲是个头脑清醒的男人,说起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尽管主要责任在前妻,他还是毫不留情地把自己批评得体无完肤:结婚几年了,我都没能给她一个“家”。连她生孩子我都不在她身边,你说,这算啥男人?
他也问过华美以前的事情,可华美就不愿意说。一提,她就没好脸色,求你不要问了,她说。那些破事想起来就伤心,不说也罢。
为什么不说呢?方洲想,当然要说,互相都要说,如果不说,怎么会有信赖?没有信赖,怎么能同床共枕,相伴下半辈子?这是基础,是夫妻之间赖以生存的感情基础啊。可华美,还有她姑妈就不这样想。有一次姑妈背着华美给方洲讲过,你别逼她了,既然她不想讲出来,说明她的确有她的苦衷,女人有女人的难处,如果你老是追问还可能逼着她扯谎。你应该允许你的妻子有自己的秘密,这是做女人的基本权利,如果你不准许一个女人保留个人的秘密,就是侵犯了她的基本权利,就是对她的极端不尊重。你们这一代应该不会比我们更封建吧?如果她什么时候想通了,她会讲给你听的。
离过婚的男人不想第二次离婚,但是,也不怕第二次离婚;离过婚的女人呢?大概也是,谁不想过平平安安稳稳定定的家庭生活呢?华美是一个才结了半年就离婚的女人,她没有孩子,不担忧子女今后的抚养问题。她与方洲结婚还不到五年,他们都曾经有第一次离婚的解脱和痛苦,教训和经验,都实实在在地想在第二次结婚之后好好地稳稳当当地生活下去。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在结婚五年之后还是走到
离婚的边缘。
直接影响他和她婚姻关系的导火线是生孩子的问题。
按照有关的规定,华美没生育过,可以生一个孩子,她才三十出头,完全可以要一个孩子。方洲虽然有一个孩子,可孩子不在身边,在遥远的美国。现在他一想起孩子,就会想起他的第一次失败的婚姻,失败的自我,贫乏无味的生活。他告诉华美,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如果身边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该有多好。我们会更加幸福,夫妻生活就会更加协调,更加稳定,我们会找到更好更新的感觉。
请你不要提孩子的事情,华美说,我这辈子最不喜欢的就是孩子,如果我喜欢孩子,我早就要了,如果我要了孩子,那么,孩子早就已经成为我第一次离婚的障碍,我现在就不可能会与你生活在一起。中国的人口这么多,都成灾了,你还是个大干部,环保意识都没有。
关环保意识什么事?方洲很惊讶,要个孩子主要是为你好啊。在他心目中华美是个好女人,如果有个孩子那就简直是完美了,这个家也就完美无缺了。可华美坚决不要,以后每当他一提到再生一个孩子时,她就会反感,就会出现夫妻的争执、红脸,双方都会唇枪舌剑把积累在肚子里的怨气乱出一通。然后华美一赌气就回她姑姑家去住,几天几夜也不回家,每次都要等他去接她,她才勉强回来。
方洲这套住宅就在公司新征拨到的一片宿舍区里,周围都是熟人,结婚那天大家送给夫妻俩的吉利话就是“今天喝喜酒,明年吃红蛋”。说了也就丢了,没人问他为啥新娶个媳妇回家老没生孩子。可是华美却觉得左邻右舍都在用一种鄙夷的眼光瞧着她,人家与她说话的口气稍微重一点,她就觉得人家与她故意过不去,故意刁难她,故意给她出难题,她觉得看什么人都不顺眼,说什么话都不顺口,办什么事都不顺心,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导致她和方洲大吵一架。
终于有一次,华美临出门时硬邦邦甩下一句:离婚!
这一句“离婚”打得方洲差点背过气去。结婚五年了,他现在才觉得完全不了解华美。早上,两人一起走出家门去上班;中午大家都不回家吃饭,随便在外头买个盒饭或者吃碗面就对付过去了;晚上,两人也经常不在家吃饭,华美办了个声乐班,差不多天天晚上有课。他自己厂里的事情也忙,有时很晚才回来,一天见面的时间就那么点,再加上有些话不便再提,两人之间话越来越少,越来越陌生,只不过是因为有一张在街道办事处打的暗红色结婚证把他们这符合结婚条件的一男一女拴在一起,让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合法地同居。
尽管情绪沮丧,他还是如同以前那样去接她,华美说你不要再来了,说破天我也不会回去。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到办事处去登记离婚;如果你不同意,我只好到法院去起诉。
看得出来,她说话算话,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华美已经好几个月没回家了。
国庆节前方洲奉命到长春参加一个企业文化建设交流会,想给华美说一声,打电话过去,她没在,是姑妈接电话;听说方洲要去东北,姑妈赶忙交待说那你无论如何应该绕道到鞍山去看看你岳母,还让方洲记一下华美她妈妈的地址。方洲说我记下了,如果有时间我一定会去。
这本是客套,可那会议实在没多少意思,主要是游览,游哈尔滨,游长白山,还说要到这些地方就得在这个季节,夏天来没特色。方洲在西藏当了那么多年兵,冰天雪地见多了,没多少兴趣,心里又烦,就没去,却去了鞍山,找到了华美她妈妈。
岳母比姑妈还小几岁,可比姑妈衰老得太多了,方洲叫了一声“妈”,把她吓了一跳,方洲说我是您女婿,是华美的丈夫。老人家一听,老泪哗的就下来了。
方洲这一辈子公差私差出了无数次,只有这一趟让他感到“值”。在那座北方城市里,他总算读懂了跟他同床共枕了五年却依然陌生的妻子。
华美本来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要不然她父亲也不会给她单名一个“美”。可是她父亲在一次意外事故中死了,那时,她刚上小学。妈妈年轻时长得很漂亮,父亲死后没多久就有人上门说亲了,后来,她就有了一个继父。继父对她和她母亲都十分粗暴,经常打骂她和她的母亲,继父刚认识母亲的时候装得像个人似的,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母亲嫁过去之后,才知道继父彻头彻尾是个混蛋。他是个奸商,很能挣钱,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经常去娱乐场所泡小姐。有一天,华美她母亲到姥姥家去了,继父喝多了酒,凌晨一点过钟才回家。一看华美她母亲不在,就趁她熟睡的时候把她强奸了,那时华美还不到十六岁。继父做了坏事还威胁她说你要是敢告诉你妈老子就让你们三娘母滚出去!后来,母亲发现了华美生理上的变化,拿着木条子逼问,华美才说出这事。母亲大叫一声“天哪!这个畜生!”站起来就把家里砸得稀巴烂,然后把继父告上法庭。
后来去翠湖医院,医生责备母亲说为啥不早一点来?老几十岁了,你不知道现在来刮有多伤人?华美其实很聪明,读书又用功,在班上总名列前几名,但是无论她个人的情况还是家里的条件都不允许她向往大学了。就在那年,她报考了市里刚创办的幼师,毕业后不久就胡乱找了个对象匆匆出嫁。新婚之夜丈夫说她不是处女,不容分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之后断然提出离婚。
华美是在新婚之夜遍体鳞伤地回到母亲家里的。离婚手续还没办妥,她就开始先兆流产。又去翠湖医院,还是那位姓欧阳的大夫,她检查了一下,长叹一口气说还是先保胎吧,尽管很难,但是值得试一试,要是再做一次人流,以后恐怕就怀不上了。
母亲还在犹豫,华美一咬牙说不管了!大夫,请你给我做掉!就这样,华美离开了那座生她养她的城市,离开了她那辛苦了一辈子的可怜的老母亲,从遥远的北方躲藏到了南方,想把彻骨的伤痛隐藏到灵魂深处,慢慢地把那些不愿意提及的不愉快的事情遗忘。
老岳母一边说,一边擤鼻涕,方洲听得怒火中烧,坐都坐不住,他在岳母身边急促地转来转去,把指关节捏得嘎叭嘎叭响。
那个老畜牲!方洲问,他现在在哪里?
岳母摇摇头说抓进去后才知道他有前科,几项流氓罪一起判的,也不知在哪里劳改。事后方洲想,幸好岳母不知道,也幸好他在鞍山转了两天还是没查到那个老畜牲的下落,要不他恐怕会杀人。
华美终于来了,低垂着头,脸上挂着愁云,松弛的面肌透着烦懑,显得心情非常沉重。她的步子迈得很慢,像在数着那些一半埋在水泥地里的鹅卵石。方洲迎上去,她说,对不起,我来迟了,万分抱歉。没事的,多等一会儿也没啥。方洲微微一笑,又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说好了要来我就一定会来,华美说,好歹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你应该了解我的德性。
方洲说当然了解,如果我到现在都还不了解你,那恐怕到世界末日也没人了解你了。
那么,你把那个带来了?
什么带来了?
离婚报告!你电话里不是说想清楚了吗。
我没说呀?你是不是弄糊涂了。
骗子!
华美说完,转身就要走。方洲赶紧拦住她说别走别走,带着呢。我们还是在老地方吃顿饭吧,边吃边
谈。
华美说那好吧,就算吃一餐散伙饭。
行。方洲说着,伸手揽住华美的手臂往茶轩走。华美肩头一甩,说别碰我!
茶室里一个客人也没有,方洲要了蔷薇轩,好久没来了,这个小包间还是老样子,靠落地窗放着一张红木茶几,两边各放一张双人沙发,墙头上还是挂着那幅墨竹。进了包间,华美在右手边那张沙发中间坐下,方洲想跟她坐在一起,华美手放在衣兜里,用下颌指指对面说坐那边去。
点了菜,华美说拿出来!方洲问,什么拿出来?华美道:你说是什么嘛!
方洲笑笑,抬起手像要掏荷包,手臂一抬,却抹抹头发,说,你看我这头剃得咋样?
华美看着窗外头也不回说,马桶盖。
我还以为你没注意到呢,我倒觉得——像个猫头鹰。
华美嘴角露出淡淡一笑,依然看着窗外。
气氛有所缓和,方洲点上一根烟,长长地抽了一口,说,你们鞍山的那些理发师手艺真是太差。
华美猛地转过头来警惕地问道,你说什么?鞍山?
是呀,我这头就是你们鞍山铁西区一个漂亮理发师的杰作。
你到那里去干啥?
去看我岳母,舅爷,还有欧阳大夫。
欧阳大夫!我妈都跟你说什么了?
都说了,你小时候的事,你第一次结婚的事,华美……
你——华美尖叫了一声骂道,你太卑鄙了!
华美站起来就要冲出包间,方洲赶紧把她摁坐到沙发上,说,我想好了,这婚我们不能离。
不听不听!闪开,闪开!!你让不让!
华美使劲去推方洲,却扑在他怀里,方洲紧紧抱住她,把脸颊贴在她头发上,轻轻地说,你可以骂我,我不该背着你去打听你过去的私生活。可是我看到你成天闷闷不乐的,我心里急啊……我是你男人,你心中有苦为啥不让我分担一点呢?华美……我想好了,我们不离婚,说什么也不离。我已经答应你妈要好好疼你。生不了孩子就不生,我们不要孩子,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
说到这里,方洲脑海浮现少女华美在那个横遭强暴的夜晚无力抵抗又无所救助的惨状,想起欧阳大夫描述十六岁少女华美在手术台上发出的那种已经不像人声的惨叫,心里一阵阵刺痛。
华美抵在方洲胸前的那只手慢慢地没劲了,方洲感觉到她在抽泣,有泪水从垂着的眼睑底下溢出。方洲吮着那泪水,吻着华美滚烫的嘴唇,喃喃地说,我们不离,嗯?嗯?不离,跟我回家,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来欺负你,永远不会……
华美任方洲吻着,抽泣从无声到有声,声音越来越大。
一个小伙端着盘子进来了,见了眼前的情景有些尴尬,问道,先生,需要帮忙吗y
不用,谢谢,我妻子她……把项链弄丢了。
小伙子一离开,华美再也压抑不住,放肆地哭起来。
作者简介:
赖榆,本名赖梁盟,现任贵州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当代法学论坛》和《当代法学论坛》丛书主编。1985年在《山花》发表小说处女作《银狗》,曾在《中国作家》、《延安文学》、《花溪》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多万字。1991年加入贵州省作家协会。中短篇小说集《背金子的老人》获全国第四届金剑文化工程金剑文学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