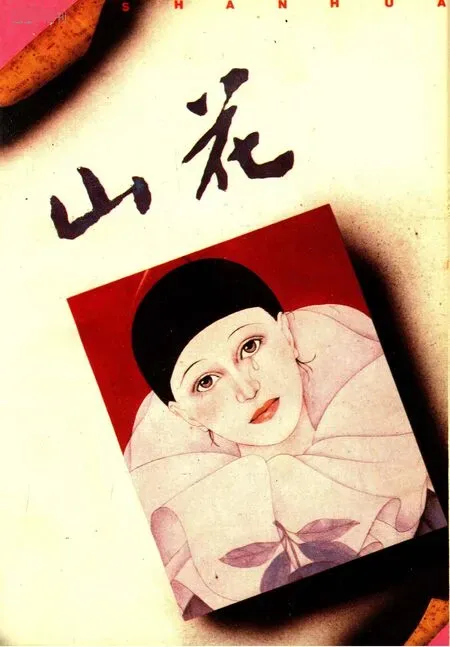豁达智性和幽默艺术的融合
2005-04-29张清芳
孙绍振先生当年以“三个崛起”而崛起于中国文坛,在相当长时期内,他是中国先锋诗论的头面人物,与谢冕先生一道,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年代冲锋陷阵。那些年孙绍振先生意气风发,激扬文字,纵论天下文学,“文学创作论”显示了他对“创作”的精湛领悟。90年代以后,孙绍振先生对幽默感兴趣,那是因为他本人就极富幽默感,据他的学生们说,他的口才无人能敌,讲课妙不可言。他研究幽默理论,那是顺理成章的事。出手几本书,他就成为这个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他对幽默的研究与他的散文写作揉在一起,把幽默理论融入小品散文的创作实践,创作了许多妙趣横生的幽默散文,在中国大陆文坛上独树一帜。《美女危险论》是他的第一部幽默散文集,收录了近五十篇的散文,内容题材涉及面极其广泛,大而言之有对历史文化和人性的批判和反思,小而言之又有对日常生活和婚姻恋爱的具体认识和理解。他的散文中沉重的忧患意识,比张承志、余秋雨等人“文化散文”中的愤世嫉俗、激烈批判多了几分豁达与宽容;同时又比专注于写身边琐事的抒情散文视角广阔,在其中引入对历史文化中某些普遍现象的睿智剖析,具有智者的大气和雍容。《美女危险论》在散文文坛上的独特性还表现在语言和形式上,作者把幽默作为重要的艺术技巧和创作手法,并将之融合进作品中去,形成总体风格上的戏谑感,但又用理性和睿智加以控制,使之避免堕入滑稽和讽刺,而是升华为富有情趣的幽默,同时这又形成了散文手法的多样化,孙绍振把幽默由一种理论变成了真正的活生生的散文艺术实践。以上这些特点构成了这部幽默散文集的魂灵,亦使它变得血肉丰满,成为豁达智性和幽默艺术融合的典范。
虽然身为学院派的理论家,孙绍振先生没有采取主流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而是采用了类似柏杨的“非贵族知识分子”的立场1,把自己放在和平民世俗社会几乎平等的位置上,在散文集中所选取的素材也有些类似,把主要的关注点落实到对女性、爱情婚姻和日常人生的体验上,并以此为切入点。但他对人性和中西历史文化也不乏睿智的剖析和认识,只是弱化了鲁迅式的强烈讽刺批判的锋芒,从而形成了一种含蓄内敛、雍容大度的软性幽默风格。
《美女独立论》、《美女危险论》、《美女荒谬论》和《美女是个“好东西”论》这“美女四论”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作者对女性、人性的独特认识和理解。女性,尤其是风情万种的美女,魅力和威力是巨大的,她们的最富杀伤性的武器是“带电的目光,尤其是带笑、带磁性的目光”。美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并非只有福音,对美的争夺和占有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使“城墙自动崩溃”,国家社稷倾颓。美女因为自身的千娇百媚,而“男性好色者众”,这样就使危险由此而生。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女危险”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美女不好“男色”,不计较男人的丑陋外貌和年老,因为这可以通过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势得到补偿,这是女性,乃至全人类共有的弱点。“女性是水做的”这个中国传统观念受到了质疑,这是作者对传统女性柔弱、无主见的所谓“美德”的批判。作者提出了现代社会中的“美女”的标准:独立自主的选择,坚定的意志,理智冷静的思考,不为男性的“如狗”“如狐狸”的目光所迷惑,也没有对男性色鬼的依附性。这既是美女之为美的标准,又是对女性,尤其是现代社会女性独立自主的人格的倡导和赞扬。
作者在更多的篇章中涉及到对爱情的探索和分析。“爱情就是感情生了怪病”,(《“谈恋爱”的“谈”》)这是每一个正常的人类都要得的病,无法依靠理性逻辑来分析和控制。爱情的特点在于它的伪装性,它是“躲躲闪闪的”,是自我折磨也同时折磨对方。所以爱情的逻辑是超越了理性的怪异的逻辑,属于“情感的逻辑”。女性的逻辑特点加剧了爱情的曲折和无规律性。因为女性的思维方式不同于男性,而是偏向于感性冲动,尤其当女性陷入爱情后,她的逻辑更加荒谬,“要情不要命”,为爱情可以付出一切,喜欢一个人时,偏偏喊他“杀千刀”的,发脾气闹别扭,只为以表示出“无限的爱”(《美女荒谬论》);恋爱还需要“谈”和“搞”,只有“尝尽了酸甜苦辣的滋味,青春才没白过,人生才够过瘾”。爱情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现代人格建构的必然成分,作者以此为出发点,对“历史上最纯洁的男人”柳下惠的存在提出了疑问,实际上是从另一角度对爱情的肯定。这是饱经沧桑的作者通过对人性和生活的睿智观察得出的结论,有坚实的生活基础,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
散文中对传统政治历史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同样呈现出与大陆主流的“学者散文”不同的特点。“学者散文”的代表作家余秋雨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专注于“人文山水”,写出了历史长河中知识分子的沧桑命运,充满了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沉重喟叹;张承志怀着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悲叹现代社会中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借历史人物寻找“清洁的精神”,对抗世俗的现代社会以拯救世人的灵魂。从这个角度说,他更像一个一厢情愿地试图拯救世界的教父。而孙绍振则明智平和地接受了现代世俗社会,并以此为背景,从柏杨似的世俗文化批判视角出发,以“谈话风”的风格侃侃而谈,把庞大抽象的历史文化具体化为历史和现实中的某一具体现象和事例,然后加以针砭和批判,试图建构一种和现实社会密切关联的文化批评和文明批评。他的散文少了一些愤世嫉俗的火气,多了一些林语堂、梁实秋式的宽容和豁达,但并不缺乏批判的敏锐和深刻。这代表了精英知识分子关注现实的另一种方式。
作者经常选取从美女和爱情的角度来切入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反而可能更切近历史的真相。他清醒地认识到“争夺美女和政权成为人类生活地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国封建社会宫闱之变的主要原因是妃嫔之间的争夺,表面的原因是后宫美女为得封建帝王的宠爱争风吃醋,而潜在的、深层的原因则是政治权利的争夺,这是“政治的赌博,是冰冷的铁与血红的铁的对抗”(《美女不独立论》),美色、爱情和政治对抗的结果往往是失败。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无性的文化”(《解构花木兰和武松》)。传统文化所推崇的英雄,都是反男性感觉的,武松的英雄气概不是表现在杀死老虎上,而是因为他是“海吃海喝”的肚皮文化代表,更重要的是他拒绝和杀死了潘金莲,表现出了对性欲的蔑视和压抑,符合“伟大的英雄就必须无性”的传统文化标准。在这种排斥正常人性的文化中,爱情和婚姻自然无地位和重要性可言。更可怕的是,这种“无性的文化”并没有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即使在现代社会,它仍旧是笼罩在人们头上的阴影。一个九岁的小女孩也以“无性”为傲,而对异性和异性正常的好感感到恶心,患有“恐惧症”(《德国男孩的“爱情”》)。正是这种不正常、不健康的“无性”文化孕育了畸形的人格和变态的社会现象,是需要警醒和改变的。
作为文革的亲历者和受害者,孙绍振在剖析文
革的罪恶时,并没有声泪俱下地控诉其野蛮和荒谬,而是幽默冷静,甚至略带俏皮地呈现出:文革变本加厉地复制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样板戏是中国传统“无性的文化”的集大成,它完全扭曲和扼杀了正常的人性和人情。文革浩劫的另一个原因是对“闹革命”精神的盲目崇拜,汉字“搞”蕴含了传统文化中对人性和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欲望和对暴力的崇拜。并且革命和“无性的文化”互相勾结互为表里,“革命越是发展,无性繁殖必然越是繁荣昌盛”(《解构花木兰和武松》)。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这个结论确实也符合某一阶段的历史状况,体现出作者对文革暴力革命的睿智洞察。
作者并非总是在审视历史文化,他还有温情的一面,更常常以温和宽容的目光回眸成长的琐事,津津乐道于具体的生活趣事和人生感悟,因为嘴馋而掉一颗门牙(《门牙的故事》),因好说俏皮话而获得“铁嘴”绰号(《铁嘴沉浮记》),还幽默地回忆自己在挨整时,“惊险而成功地扮演了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悬崖上走钢丝的角色,天可怜见,总算没有一回失足。”(《木炭炉子和革命化的春节》)。虽然充满辛酸,但也不乏自我调侃和饱经沧桑后的乐天知命,颇有些杨绛的《干校六记》的风味。
作者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也很关注,更多的是赞扬和期许。倔强而又执着追求个人致富的泉州人,精明能干的“阿拉”上海人,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具体化形象和象征。还有一些散文是谈中国的学校教育、中西文化差异和分析幽默的生成原因,同样和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感悟相系,洋洋洒洒,不乏精妙见解。
把幽默融入散文中,并非是孙绍振的首创,,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就出现了林语堂、梁实秋、钱钟书、王力等人的幽默小品文,《雅舍小品》和《写在人生边上》是其中的精品。但在这些幽默小品文中,幽默实际上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仅是顺手拈来偶尔为之,目的为表现一种超脱的士大夫心态,谈不上是一种特意为之的语言特色,幽默更非是构成散文的艺术手法和形式结构。在这一点上,孙绍振超越了前人。在他的散文中,幽默不仅作为艺术形式的重要构成因素,而且是一种支撑起散文框架的结构。同时在幽默中体现出深刻的睿智和精致的情趣,使之脱离了会“失之油滑”的滑稽和钱钟书式的尖刻讽刺,而升华成了一种真正的,富有生命活力的艺术形式。并且,孙绍振紧紧抓住“幽默是一种情感交流”,在散文中运用各种方法和技巧产生幽默,以达到与读者的感情交流和共鸣,亦使每一篇散文有自己的独特形式,很少雷同。幽默散文集《美女危险论》成为产生幽默感的各种艺术手法的荟萃和群展,充分成功地实践了孙绍振的《幽默五十论》中的方法论。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散文史上,孙绍振是真正把幽默作为幽默小品文第一要素的第一人。
在散文集中,每一篇散文不仅通过不同的方法技巧产生各式各样的幽默,而且在每篇中幽默出现的频率并不一样,有的散文几乎通篇,甚至每一段都运用了构成幽默的艺术方法,有的则只有一二处幽默,而更多抒情描写和描述。这正是作者深得幽默真谛的地方,因为幽默是一种超越了常规理性逻辑控制的情感,以戏谑性为其主要特征,它使用的素材应该距离当下现实生活非常遥远,最好是发生于古代的材料,距离现实生活越远,与作者和读者就越无利害冲突,容易产生无功利的审美:又可运用奇特丰富的想象加以夸张,与常情常理产生巨大的反差,而且由于预想的期待落空而产生一种失落感,导致某种怪异感甚至荒诞感出现,这就产生了笑,正如叔本华所说过的,笑不过是人们突然发现在他所联想到的实际事物与某一概念之间缺乏一致的现象。而这还是浅层次的幽默,只有在表面的滑稽和讽刺下隐藏着对现实生活和常规理性的深刻睿智的认识,也就是说,必须包含着一定的智慧,才能升华为真正的幽默。在阅读中,读者才能体会到一种放松的、包含智力快乐的高雅感情。幽默感就是这样由作者和读者通过作品交流而产生的。
所以,幽默最密集的篇什是那些有关中西古代政治文化的散文。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女不独立论》和《解构花木兰和武松》等作品。
《美女不独立论》开篇就设了一个玄虚的、可怕的悬念,绝世美女的作用“是对人类作出了贡献,还是带来了灾难,至今仍是千古之谜。”表面上被夸大的严重后果与实际上的微不足道构成了巨大的反差,这是幽默中的故作玄虚法的第一个环节。孙绍振紧接着为这个悬念寻找巧妙的解释:首先是因为只有女人,尤其是美丽的女人,才能激发男人的创造力,男人在本性上也离不开女人。其次是因为美女威力惊人,她的武器远远高过男英雄们用的刀枪剑戟,“就是带电的目光,尤其是带笑,带磁性的目光,无形无声,如带巧克力水果味的x光”,这些歪曲的、带调笑性质的话构成了故作玄虚法的第二个环节,幽默感由此产生。也显示出作者的狡黠、智慧和情趣。作者接着用偷换概念法把美女的“目击”歪曲为威力无穷的子弹和大炮,“她只要掉转目光,回头一看,城墙就自动崩溃了”;而把古典诗歌中的“一顾倾入城,再顾倾入国”诗句与女性破坏性的无穷美丽和魅力联系起来,用的是歪曲经典法。这两种方法都巧妙地应用了汉语的表层意思,以偏概全,反而产生了超越常规逻辑观念的幽默逻辑。
“天生丽质难自弃”本是唐代诗歌《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美貌的夸赞,而作者认为这是诗人白居易发现的“规律”,用的是庄词谐用法。因为“规律”的本义是指普遍性的客观存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而美与丑只是人类的主观感觉。把主观变化的感觉和客观严谨的规律混淆在一起,这二者有巨大的逻辑空白,就在这空白中产生了幽默感。作者还运用模仿反讽法把“英雄难逃美人关”改为“老头难逃美人关,更比英雄难”,这是柏格森所谓的“走样的移置”产生的幽默效果。
作者把美女的悲剧根源归纳为三个原因:女性“长得太美”,“不好男色”和没有独立性。从理性逻辑来分析,这三个原因并不直接导致美女的必然悲剧和灾难性后果,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同样的原因可以产生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果,犯了逻辑不严密的大忌。但是从某一角度来说,这种因果关系也是成立的,尽管有失偏颇。这种幽默方法属于歪解包袱法,既有表面的戏谑性,又有深层次的睿智思考,包含着作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中“后宫争宠”现象的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
在《解构花木兰和武松》中,作者同样用了很多幽默手法。作品在讨论“英雄”时,就用了偷换概念法。“英,花之谓也”,而英雄必须是雄性,否则就是“英雌”,是英雄的变性,“像泰国的人妖,不男不女,半男半女”。作者把从伦理价值上进行判断的“英雄”,偷换成只是从字面意思和性别身份推论出的一个概念,从中得出结论:“花木兰是雌的,所以她不是英雄。”同时从整个推论过程来看,作者用的又是歪解包袱法,为“花木兰不是英雄”找出了独特的原因。
作者继续讨论武松是否是英雄和他成为英雄的
条件与原因。武松是雄性,这仅仅是成为英雄的前提,他是通过杀老虎,特别是杀漂亮的母老虎——女人,才成其为真正的英雄。这个理由很荒唐和荒谬,然而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更荒谬的一个结论:“伟大革命要求伟大英雄,伟大英雄就必须无性。”这种连锁性的歪曲推理,产生的谐趣相应地层层放大,就容易产生幽默。同时也是一种歪打正着法,即原因是歪曲荒谬的,但是它的推导结论则是严肃理性的,甚至很尖锐地指出了中国文化的痼疾:中国文化是“无性的文化”。强化了幽默的攻击性和批判性,有些硬性幽默的色彩。
在描写现实社会现象和中西文化差异的散文中,因和作者自身距离较近,所以使用的幽默方法就少多了。《上课打瞌睡利大于弊》用了同枝异花法来写一个调皮学生的两次脸红。在《论“谈恋爱”的“谈”》和《论“搞恋爱”的“搞”》中,利用汉字的结构多次用歪解汉字法和偷换概念法,而《“阿拉”的命运》用谐音产生“滑头哥洗袜”类的滑稽,展示的不是幽默的智慧,而是强调了幽默的“调解情绪”的作用。《中国牛和英国牛的对话》、《论中国的狗和西方的狗》应用了偷换概念法来阐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人类破坏自然和屠杀动物的劣行。
在一些与作者自身联系非常密切的回忆性散文中,包括《中学生活记趣》、《没处可藏的礼品》、《厦门奇遇记》、《“铁嘴”沉浮记》、《五香豆的故事》和《爱滋病虚惊的故事》等作品,作者自然应用自我调侃法最多。这是一种嘲弄自己的幽默方式,甚至在《木炭炉子和革命化的春节》中,作者用黑色幽默来制造一种含泪的笑,把自我调侃推向极端。在它产生的戏谑性中,显示出作者本人真诚、天真的美好品质,引起读者的同情和共鸣,而产生一种精致幽默的感情,形成幽默。
如果说在美学领域中,孙绍振是“交错美学”的开创者,那么在散文领域中,他的幽默散文集《美女危险论》则是各种幽默艺术技巧的大全,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也是一个开创者。孙绍振的幽默散文既是对林语堂、梁实秋等人创作的幽默小品文传统的继承,又不逾矩地加以超越,同时提高了大陆幽默散文的创作质量,使大陆的幽默散文能与台湾的柏杨、李敖等人的散文并峙,也为“审丑”的幽默散文在抒情散文的主流中争得一席之位。
作者简介:
张清芳,生于1973年12月,山东人。山东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注释:
1.陈晓明著《世俗批判的现代性意义》选自《柏杨文学史学思想》第230页,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