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维诗歌中的落花意象论“言有尽而意无穷”
2025-02-24孙闻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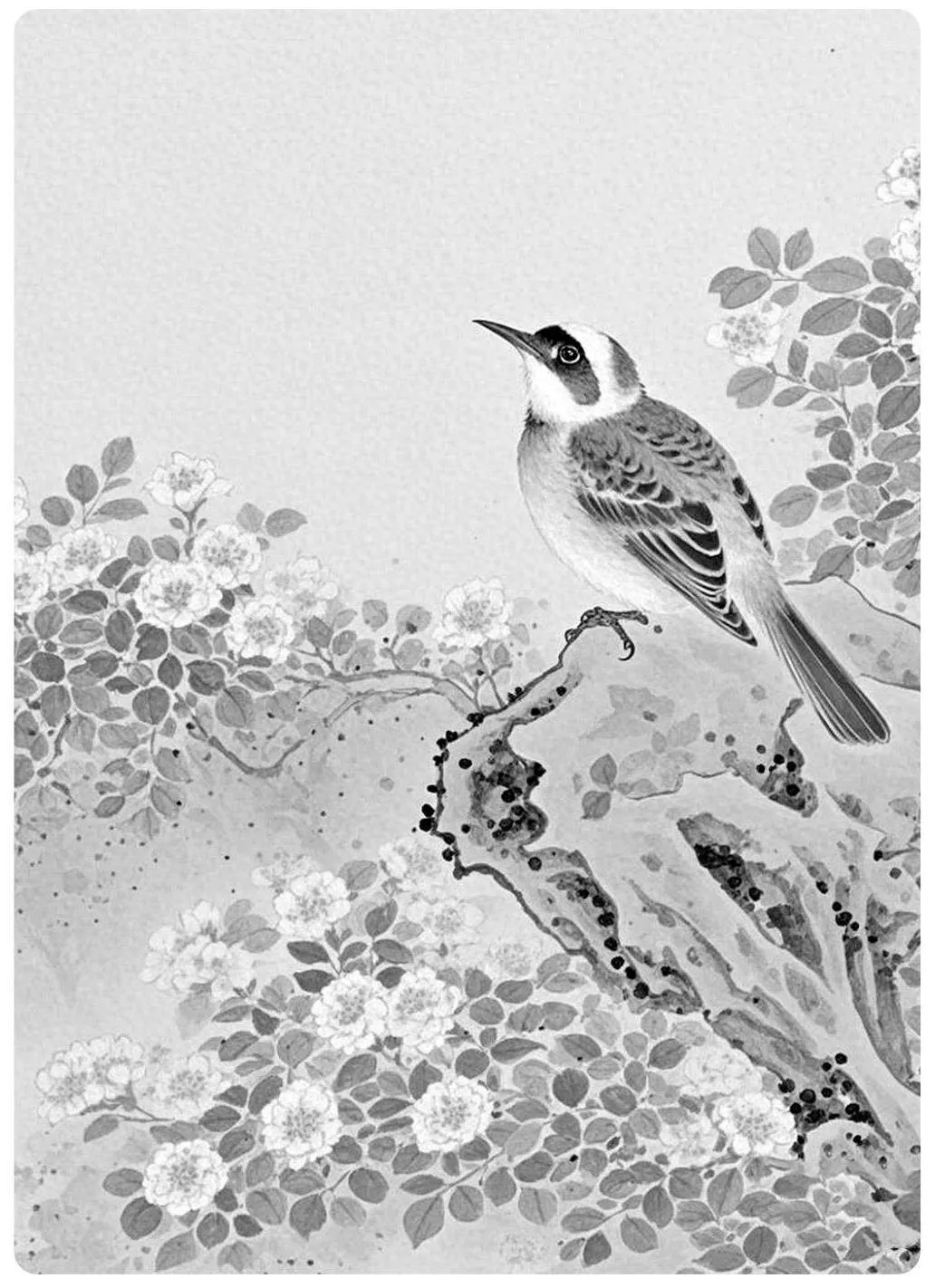

无论《诗经》还是《楚辞》,其中都氤氲着花的芬芳。“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都可以纳入‘花’这一短小的缩写之中。因之它的每一过程,每一遭遇,都极易唤起人类共鸣的感应。”(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花卉意象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元素,不仅象征着自然循环与生命变迁,更是深层次地反映着文人对于自身存在状态的认知与感悟。而“落花”这一形象更是超越了一般静物表层视觉美感与表意内涵,成为触发情感共鸣与思索哲理的关键媒介。正是因为花的娇艳,依照季节开放凋谢,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等诸多特点,使得文人骚客面对“落花”尤为怜惜。而“落花”作为另一种生命形态的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与“花开”有所不同的审美意趣。其他诗人笔下的“落花”,多半是伤春惜时的象征,但在王维的诗中,“落花”因为浸染着冷静悠远的禅思而显得蕴藉玲珑,进而需要读者走进诗人构造的透彻境界,对诗歌进行再加工,自觉或不自觉地延长对诗歌的情感体验,从而构成了“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的美学体悟。而这样的架构,在外在看来,体现了目击与神遇后的有无相生;在内在层面,则展现了禅宗对自然与生命的深切关怀,以及瞬间即永恒的澄澈境界。
一、目击与神遇
从外在表现来看,王维诗歌中的落花意象并非象征着同时代诗人笔下的“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刘希夷《代悲白头翁》)对红颜易老的悲叹,也并非“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李白《闻王昌龄左前龙标遥有此寄》)的离别之苦。以上皆是诗人睹物而自然生发出的思绪,“落花”在诗歌中只是作为现实存在,是引发诗人们思考的物质前提,其所造之境是“有我之境”,而王维诗中的“落花”似花非花,是经由诗人目击并对其进行艺术加工后的呈现。“落花”在其笔下蜕变为一种高度凝练的美学符号,作者、读者与宇宙之间借“落花”达成了某种有效连接,这种美的表达已远远超越了前人面对自然变迁的感性反应,成了王维营造“无我之境”的媒介。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目击”并非现实意义上的视觉结果,而是“神遇”的一个手段。朱立元教授在《美学》中阐述了“神遇”的概念,即“神遇不是感官感知,也不是言辩和思考,而是主体在无意识状态下不断解除感性和理性的束缚,来达到对主客两方面的直觉体验,并进而获得高层次美感的心理过程”。他同时也肯定了自唐宋以来,庄子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与禅宗思想中“妙悟”进行了融合互渗。这一理论同样可以视为《沧浪诗话》中“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另一个侧面解读。
目击与神遇在王维的诗中通过有无相生得以表达,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鸟鸣涧》)。王维只用了几个短小有限的“拙语”,却能带给读者无限的遐想。《沧浪诗话》中严羽评道:“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王维的诗即是如此,他的语言从不过分精巧雕琢,却圆融玲珑,首先因为他忠实于自己的文字,深切地观照自身及自然万物,并真挚地叙述于诗歌之中。王维不刻意追求辞藻的华丽,而是直接将自己的情感与观察诉诸笔端。无论是描写桂花飘落的宁静,还是春山静谧的空旷,他都力求保持一种原始的纯真,避免过多修饰带来的矫饰感。正是这种对纯净文字的坚持,使得王维的诗歌拥有了超越表象的力量,让读者在简约直白之中体会到含蕴丰富的情感与哲理。
其次是禅宗“空”的思想,文字终究可以穷尽,而所需要表达的心绪却是无穷的,于是,王维的诗句在有无、虚实、动静之间形成了无限的张力。那么,诗人以何等的静穆去捕捉桂花飘落的瞬间?又是如何听到空山之中一片花瓣坠落的声音呢?其答案正是因为人闲心定。故而可得,“桂花落”是诗人的“目击”,而“春山空”则是他的“神遇”,前者是外在的具象,后者则是内在的感悟,它们共同传递出诗人对“有”与“无”的深邃认知。在其诗句之中一切物象已然被剥去了善与恶、美与丑、感性与理性,一切的“有”最终归于“无”。
正是因为“落花”的精微意象,才能最大地发挥出诗歌中言语的力量,使得花落之扑簌,朦胧了山的存在,王维在有无的思考中漫游于天地,在动静之间俯拾得禅心,将意境混融于天地之间,引导读者同步迈进他所建构起的无限宇宙中去。
二、自然与自我
前文提到过,王维深切地关心自然,忠诚地将“目击”转化为“神遇”。如果我们对此种外在表现进行追根溯源,大抵要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再到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最后再到世尊的“拈花微笑”。整体来看,“无论易、庄、禅(或儒、道、禅),中国哲学的趋向和顶峰不是宗教,而是美学”(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也就是说,儒、道、禅的共通之处在于其哲学追求的终点是美学的而非宗教的、虚幻的,而是以真切之心关怀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物我合一”的境地。
禅宗“不立文字”的传统极大地解放了参禅者的思想枷锁,鼓励他们超越教条,关切个体自身的“悟”,直接从个体经验和直观感知中汲取真理。这种精神导向催生了禅宗独特的修行方法,即着重于内在体验而非外在形式,强调个体对自然界的细微观察,以期在与万物的亲密接触中获得顿悟。在这一过程中,自然界的每一分子,无论是一草一木,抑或一花一叶,都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同时,佛教本就主张万物皆藏有佛性,这意味着世间万物在本质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和关怀。这一信念进一步强化了修行者对自然界的敬畏之情,促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持谦逊与慈悲之心,视万物为平等的生命伙伴。这种思想在王维的诗中大量出现,如“流水如有意,暮禽相与还”(《归嵩山作》),以及“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积雨辋川庄作》)等。
而作为“花”这种娇艳却转瞬即逝的意象,自然而然地使诗人以我之思寄以“落花”之飘零,可以说“落花”寄寓着诗人独特的生命美学思想,既有对死亡,衰老这一永恒课题的忧愁,又有浑然淡泊的禅宗思想,同时也蕴含着盛唐特有的“哀而不伤”与悠游。由此“落花”成了王维与自然沟通的一帆舟楫,“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严羽《沧浪诗话》)。
王维在《秋夜独坐》中写道:“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果是花的另一种状态,山果不仅与诗人当前的人生状态有所暗合,皆是青春(花)走向成熟乃至衰败(果)的结果。同时,这两联蕴含的生命意识自“落”与“鸣”中自然地流露而出。秋夜独坐令人倍感凄苦,鬓已微霜则更添惆怅,但正是因为山果坠落的细微声响,秋虫鸣叫的热烈挣扎,生命的意味便破诗而出。王维并不多言,其“神妙”留予读者在诗境之外去捕获,由此可见王维对生命与美的感触之深刻。
王维的另一首诗《山居即事》中,诗人在创作“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时,自觉地将稚嫩的“绿竹”与半衰的“红莲”作对比。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中,始终弥漫着一种静美,并非一片了无生气的死寂,而是在纷扰表象背后流露出的纯粹的生命之音,这又何尝不是诗人以自我观照自然,又从自然获得妙悟的证据呢?自然生生不息,周而复始,衰微的紧依着新生,而萌发的接续着败落,这是一种无目的性、无意识的“大道”,于此就越发增添了诗人对生命的讶异与欢欣,以及静谧的哲学禅思。
三、瞬间即永恒
“落花”这一形态极为短暂,自枝头纷纷扬扬飘落至地面不过一瞬,但这一时间上的瞬刻,却能包容整个人生与宇宙的永恒与浩渺。从禅学的视角来看,参禅在本质上是一种瞬刻的直觉感触。在这一瞬刻,人不再将自身与万物相割裂,而是与宇宙浑然一体。所有感性层面的感官限制以及理性层面的思维框架的束缚都荡然无存,时间与空间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不清,难以分辨。这一过程就像是从有尽的“点”向着无尽的“空”发生转变,进而达到了南禅宗所极力推崇的“顿悟”境界。而这种“顿悟”境界与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阐述的“妙悟”的含义大体上是一致的。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王维早年因为家庭原因主要信奉北禅宗,后经过一系列社会变动,仕途的起伏等诸多因素,王维开始接触南禅宗,并且将南禅宗的“空幻”“顿悟”等思想融入自己的诗中,进而促成了王维诗歌中“瞬间即永恒”的禅思,完成了由“有尽”向“无穷”的深刻转换。
王维经常以画家的绘心去捕捉瞬刻的画面,在他的诗里有广袤绿田蓦地飞过的几只白鹭,也有被月光一寸寸照过的青苔,但“落花”因为自身便隐含着由开到落,由动到静等诸多意趣,使其成了王维表达禅思的更优之选。花朵的生命本就无比短暂,从盛开到飘散成泥不过一阵风雨,短暂到无法与世间坚韧物作对比,而其散落的飘飘洒洒中又洋溢着生的欢欣与死之静美。“落花”入诗后,是由死的刹那抵达至生的永恒,而附着在其上的禅思便越发廖远含蕴,如梦似幻。
王维在《辛夷坞》中写山中盛放又凋零的辛夷花,“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山花生空谷,从不因无人欣赏便失去颜色与芳香,它热烈地将自己的生命力展现给整个山谷,这是花的本性。于是,在无数次花开花落的瞬间里,王维仿佛触摸到了花的内在本性。他从目击到的花开花落这一现象出发,凭借神思与之相遇,从而由实在的景象得到虚灵的感悟,从动态的表象触及静态的本质,穿透了纷繁复杂的“幻象”,进而见到了常住不灭的永恒。在这个过程中,诗人自身的存在仿佛逐渐变得稀薄起来,宛如化作了溪涧中的一滴水,或者花蕊上的一粒花粉,弥散、融入这永恒的无尽之中,诗歌的意境也因此变得更加广博开阔,充满了宁静祥和的气息,这正是南禅宗“瞬刻即永恒”的思想在王维诗歌创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
但在王维的诗歌中,“瞬刻即永恒”这一境界的宗教性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学性质所让步。王维诗中的落花意象,是诗人将情感与景色、目击与神遇、主体与客体相互融合之后所产生的直觉感悟,最终指向的是“美”而非“佛”,是介于“学术境界”的“真”,和“宗教境界”的“神”之间的“美”的“艺术境界”。于是,在王维的诗中,“有尽”向“无穷”一次又一次进行突破,在“瞬间”中完成对“永恒”的构建。
于是,在其他盛唐诗人或为花谢花飞而伤春自怜,或为分离而忧伤,或为红颜易陨而叹惋时,王维则以诗人的忠实、画家的敏锐、僧人的空寂去观照这些“落花”,这些纷乱的花儿经由王维的“神遇”而超越了自身有限的绚烂生命,在王维的诗歌中获得了永恒。也正是因为王维极为关注周遭的一切,带着对感性认知的全面肯定以及对世间万物的同等尊敬,才能将无限的情思、意蕴、禅趣融于有限的文字之中,寥寥数笔,就将这样淡泊、宁远的心绪,与人生、宇宙相连,营造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意蕴。可以说,在王维的诗中,“落花”已成了读者们神驰的一个锚点,即便不参禅,不知佛理,读者亦能在其有限的诗行中体会到静穆永恒的空寂之美,这正是“落花”这一可亲可感意象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