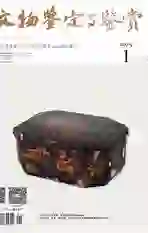明州妙智院与丰氏家族
2025-02-13沈芳漪
摘 要:《明州妙智院记碑》详细记载了妙智院自五代始建至北宋元祐间的历史,有多位丰氏家族成员参与记事树碑,且均与北宋著名官员丰稷关系密切。文献记载丰稷曾请妙智院为功德院,并归葬附近。基于已有的宋代功德寺研究,结合丰稷生平经历,推测他可能在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间(1100—1101)请妙智院为功德院,以守护祖先坟域。后因被列入“元祐党籍”,丰稷被除名夺职,丰氏家族后继无人,使得妙智院从家族私有之功德寺最终转变为一般寺院。
关键词:丰稷;妙智院;明州;功德寺;元祐党籍
DOI:10.20005/j.cnki.issn.1674-8697.2025.01.024
0 引言
《明州妙智院记碑》书于宋元祐六年(1091),此碑圭首高160厘米,阔83厘米。据民国《鄞通志馆碑碣搨本目》①及《鄞县通志》载,碑原存宁波鄞县妙智寺②,现疑不存。目前仅见当时鄞县通志馆所拓、后移增于天一阁③之拓片(图1)。
1 《明州妙智院记碑》概况
此碑碑文正书,见存十九行,满行三十五字。虽然“拓片磨泐过甚,石花斑驳错杂,碑字多有泐失,撰者及书者衔名残缺”④,恰有明末清初《敬止录》及清康熙、乾隆及同治《鄞县志》等,均载《明州妙智院记》一文,或详或略,可据此补充拓本所缺。
依据天一阁所藏拓片,并参考前人著录,经文献考证与字迹比对,移录碑文如下⑤:
明州妙智院记
苏州吴县主簿郭受撰
太平州繁昌县尉丰大常书并题额
钱氏之有吴越日,凡二浙之间山水奇秀者,皆许建刹摩以安僧焉。兹地始得僧师贤,不知何许人,一日束钵朅然戾止,目其峰峦峭拔,涧壑清激,翛然可爱,乃诛茅建庵而居之,未几倏然而化去。复有天台僧行昭来似续之,昭即天台国师之门人也,以其久参得旨,大为时辈之所钦。一日,有邑民梁阶等请献地以广其基,即太平兴国七年也。栋宇日渐隆备,乃以古观音像而名之。
仁宗享位,以天圣改元,至十年有诏许以存留。治平元年十有一月,国家将有事于明堂,复诏天下有未系锡名者,皆例赐其额,兹院始革为“妙智”。然上栋下宇皆鼎新其制,此主院子和勠力之绩。和师以无私为洁己,以无党为董众,故缁俗无远近班白,皆悉心而归之。虽一院粗完,而中所阙者,惟大殿耳。夫释氏之宫,苟宝殿不立,亦犹国家七庙不设,则祖宗之茂绩、昭穆之景铄,无得而讲焉,讵可而不立乎?乃竭志于蚤夜而力图之,裒众获财计一千缗,起熙宁四年春,市材召工,建成大殿,使来者瞻其宝构,则圆觉伽蓝之说炳然目前,不烦概举。岂比夫高甍大楹,崇基广厦,然后谓之壮观哉?则知和师自利兼人之功德,不可聊尔而论。呜呼!和师之往有年矣,今少师宝生欲其师之名不坠,故命予以纪其迹,庶乎来者之观,可以见其心之所存焉。元祐六年五月望日记。
陈承禄,徐世良、世昌、世安,京兆丰知常同立石。
徒弟僧义山、前住沙门宝生、住持沙门(下缺)
2 妙智院的历史沿革
目前关于妙智院的最早文献记载见于南宋宝庆《四明志》中。然而其中有两座“妙智院”:一属三十六座甲乙律院之一,位于“县西南七十里,旧号观音庵。后汉乾祐二年建。皇朝治平元年赐今额。常住田一百亩,山无”⑥。另一属二十二座禅院之一,位于大慈山,为史丞相府功德院。结合碑文内容看,前者与之相符,尽管方志记载较为简略,但写明了寺院位置、始建时间及当时的寺产情况。
方志载妙智院位于“县西南七十里”⑦处,清黄宗羲《四明山志》提及此寺在黄观岭⑧。民国《鄞县通志》记载此寺位于“七区鹳岭乡童君庙侧”,当时鹳岭乡有三座童君庙,其中有一童君庙位于“鹳岭乡大路沿妙智寺侧”⑨。按《鄞县通志》所附地图《鄞城分图辛》,妙智院约在今海曙区龙观乡大路村龙溪线以北。
妙智院建于后汉乾祐二年(949),正值吴越国王钱俶在位、大兴佛教时,僧人师贤最先于此建庵修行。后有僧人行昭来此,他是吴越国后期著名僧人、被钱俶奉为国师的天台德韶之百余门人之一,因“久参得旨”,亦为时辈所钦。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邑民梁階等请献其地,规模日渐扩大,乃以古观音像命名为“观音庵”。由于是无官方赐额的私建庵堂,随时有被取缔或拆毁的可能⑩,天圣十年(1032)得诏幸以存留,直至治平元年(1064)赐额“妙智”,正式获得了被官方认可的合法身份。这一时期,住持子和为营建寺院颇费心力,并于熙宁四年(1071)重建佛殿。继任住持宝生请人作记以纪子和之功,即此《明州妙智院记》,详细记载了妙智院自始建至元祐六年(1091)间一百四十余年的历史。
北宋后期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即丰稷请此院为功德院。丰稷(1033—1107)为明州鄞县人,是活跃于北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的著名官员,《宋史》有传k。他以刚正不阿、直言不讳而闻名,官至尚书,后因得罪蔡京被列入“元祐党籍”,死后追谥“清敏”。四明丰氏亦兴起于丰稷,成为两宋时期甬上四大望族之一。全祖望曾赞誉“丰氏为清敏公之裔,吾乡南宋四姓之一,而名德以丰为最”l。
而丰稷请功德院的相关记载最早见于明成化《宁波郡志》:“妙智讲寺……宋治平元年,尚书丰稷请为功德院,赐今额。”m但乾隆、同治《鄞县志》均对丰稷请功德院的时间提出疑义,理由有三:一是南宋宝庆《四明志》、元延祐《四明志》均未载此事;二是《明州妙智院记》明确记载治平元年赐额“妙智”的原因是“国家将有事于明堂,复诏天下有未系锡名者,皆例赐其额”,而与丰稷无关n;三是治平元年时,丰稷尚处低职,未为尚书,并进一步指出丰稷请院应在熙宁以后o。由此可见,丰稷请功德院是妙智院历史上的一个未解谜团。
此后妙智寺历经多次兴建,文献记载相对简略:南宋建炎间,僧人无量重建观音阁。元至正年间(1341—1368)寺毁p。明永乐时,妙智寺僧被并入城内的宝云讲寺q。正统十年(1445)r,住持弘亮重建。清康熙间,岳祖重建s,至民国时仍存t。20世纪70年代因建造鄞县化工二厂而拆除u,现已不存。
3 妙智院与丰氏家族的关系
功德院又称功德寺,起源于唐,盛行于宋,是由朝廷赐额专供少数贵族和官僚群体祭祀祖先、供奉香火、乞求冥福的寺院v。如黄敏枝、汪圣铎等学者,对宋代功德寺的设立制度、功能、特权及其与主家的关系等问题已有深入的研究。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将从两个层面来探讨丰稷请功德寺的问题:一是丰稷请功德寺是否确有其事?二是此事若真,丰稷请功德寺的大致年代是何时?
3.1 丰稷请功德寺的可能性
功德寺在唐代原为皇家专有,包括皇帝、皇子、公主、妃嫔及外戚等皇室成员w。发展至宋,这一特权群体扩展至品级较高的少数官僚,并随着仁宗及神宗时相关诏令的颁布,逐步确定了范围,成为一种规范化、合法化的制度。加之功德寺享有一系列宗教及经济特权,因此符合资格的官僚纷纷请立功德寺,以此作为他们地位和权势的象征x,如据黄敏枝统计,南宋四明史氏一族即拥有十所功德寺y。这也由上至下地带动了民间建立坟庵的热潮。在这种普遍盛行的社会风气影响下,丰稷请立功德寺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且丰稷喜好老释之说,多与释僧交游。他虽然以儒学著称,亦精通佛理。神宗曾问丰稷“闻卿知佛教理,如何?”丰稷答曰:“佛者,觉也。觉则无所不了。”丰稷被谪官后居于建州时,就携孙侄一二人居于佛寺中,不问世间政事,寻得一方清净。“燕坐阅《华严合论》,抄其要为百卷”,“怡然自得,与衲子辈游。”“学佛者宗师如善本辈,皆机语相契。”z善本亦为当时的名僧,曾住婺州双林寺、杭州净慈等名寺,为浙东僧俗所崇,神宗赐号曰大通禅师。
就妙智寺本身而言,从《明州妙智院记碑》即可窥见它与丰氏家族的密切关系。
《明州妙智院记碑》碑文由郭受撰于北宋元祐六年(1091)五月。据《敬止录》记载,郭受时为“吴县主簿”,吴县属苏州。为何作为吴县地方官的郭受会为万里之外的一座明州佛寺撰记呢?因为郭受还有另一重特殊身份,他是丰稷次女之夫婿。据建炎三年(1129)陈瓘所撰《宋礼部尚书叙复朝请郎提举亳州太清宫丰公墓志》(下文简称为《丰稷墓志》)记载,丰稷次女“适奉议郎郭受”。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中关于郭受的记载最为详细,载:“郭受,贯河南府,官至奉议郎,终于长沙判官。宋建炎间,其子维徙居于此,以北学教授诸生,从者如云,葬于西湖之原,榜曰‘郭先生墓’。其先以易学四世登科,两尚主,有官历尚书及国子博士。”
书丹题额者似为丰稷次子丰大常,时任太平州繁昌县尉,为明清《太平府志》及《繁昌县志》所不载,《丰稷墓志》仅提及其为“寿州寿春县主簿”。此外立石者中丰知常应为丰稷之侄,即与丰稷子丰安常、大常同辈。据清《黄堂丰氏宗谱》载,丰知常为丰稷兄丰稠之子。京兆应为丰氏家族郡望,如丰稷族兄丰称墓志铭中称其为“京兆丰君”。
此三位参与妙智院树碑记事者均为丰氏家族成员,且与丰稷都有比较亲近的关系,其背后指向的就是丰稷与妙智院的直接联系。据《丰稷墓志》,大观三年(1109)丰稷归葬于“鄞县通远乡银山妙智之原”,明确指出丰稷墓位于妙智院附近,这样的择址应当不是巧合。
尽管丰稷请立功德寺一事并未为两宋文献直接记载,但笔者认为妙智院应属于功德寺中数量较多的坟寺,位于主家坟墓附近,承担着守护坟域的职责。明嘉靖《宁波府志》载“清敏公丰稷墓,在县西南六十里环村”,清同治《鄞县志》亦引《鹳岭寺志》,载丰稷墓“在澍河桓村之南,俗名丰家河”。“环村”即“桓村”,因避宋钦宗赵桓名讳而改,宋时即属通远乡,至今地名仍存。丰家河即今穿桓村而过的中溪。此地于1983年还出土过丰稷族兄丰称的墓志铭,可知丰称于熙宁八年(1075)“葬于鄞县通远乡银山管金谷里”。笔者由此猜测丰氏家族的墓地即位于桓村附近,有待更多考古发现证实。
此外,就官僚请立功德寺的方式来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自己出资新建寺院,然后向朝廷请求赐额;二是指射已有寺院,再向朝廷请求敕额,最终由朝廷经程序认可后发放敕牒,作为寺院合法身份的证明。寺院也往往将敕牒以及赐额镌刻在石碑上,示之于世。如天一阁馆藏拓片《赵大资府状起置宝庆显忠禅寺尚书省敕牒碑》记载了赵与懽为其父赵希言请建功德寺、朝廷赐额“宝庆显忠禅寺”之事,《宋敕赐寿国宁亲禅寺额碑》是史岩之为其父史弥忠所建功德寺获朝廷敕额后所立之碑。
而追溯妙智院的历史,它始建于五代吴越时,非丰氏家族出资新建;院额“妙智”为治平元年(1064)朝廷统一敕赐,与丰稷请院无关;宋时并无高僧大德住山,声名不显。因此,笔者认为丰稷选择妙智寺作为功德寺的主要原因是其所处位置靠近家族墓地。像丰稷这样长期流转各地做官的官员,无法经常回乡照看祖坟,请立功德寺后即可以将保护祖先坟域的职责委托于寺院僧人。
3.2 丰稷请院的大致年代
针对官僚奏请设立功德寺的热潮,仁宗、神宗时分别发布诏令,正式规定了请立功德寺群体的范围。一是仁宗嘉祐四年(1059)六月,仁宗下诏“诏应乞坟寺名额,非亲王、长公主及见任中书、枢密院并入内内侍省都知、押班,毋得施行”。二是熙宁五年(1072),神宗下诏“定应见任两府、亲王、长公主、入内都知押班,许陈乞守坟寺等额,许十年内依见在例,仍两经圣节与度行者一名”。汪圣铎等分析认为,这一群体涵盖亲王、长公主、两府大臣、宰执大臣及皇帝内侍等,在宋代基本没有大的变动。因此,从丰稷个人的任职经历,可推测其请立功德寺的大致年代。
丰稷于嘉祐四年(1059)进士及第。初为地方官,历任亳州蒙城县主簿、真州六合县主簿、襄州谷城县令,为当地官民所称。因母去世服丁忧后,任宁海军节度推官、知越州山阴县丞,未赴。后作为安焘的属官,受其器重,于元丰元年(1078),由校书郎充书状官,随安焘出使高丽,表现出色。回国后“循两资”,迁著作佐郎、知开封府封丘县。元丰三年(1080),因“清修俭直”被荐为御史,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元丰改制后,易为通直郎、监察御史。尽管被神宗赞为“论事最诚实”,但因“弹劾不避权要”,如批评王安石之弟王安礼、不理会章惇请托事等,遂于元丰五年(1082)任秘书省著作佐郎,擢为吏部员外郎,后因王安礼升任右丞,丰稷便乞避出任利州路提点刑狱。
元祐元年(1086)哲宗即位后,丰稷迁承议郎,任成都路提点邢狱。元祐二年(1087)再入京中为官,召为工部员外郎,除殿中侍御史,不久迁右司谏,转朝奉郎。元祐三年(1088),因谏言荆、杨二亲王生活奢靡,而徙国子司业,元祐五年(1090)为起居舍人,后为中书舍人。元祐六年(1091)正月为太常少卿,后任国子祭酒,转朝散郎,十月哲宗幸太学,命丰稷讲《尚书·无逸》,因其博学多闻,遂赐金紫并兼侍讲,成为天下儒生的榜样。元祐七年(1092)迁权刑部侍郎。
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后,丰稷乞外郡,遂以集贤院学士知颍州、知江宁府。后入朝拜龙图阁待制,知广州,充广东经略安抚使,因丰稷为官“中立不倚”,哲宗试图以吏部侍郎之位辞留,但丰稷仍恳求外官,遂以龙图阁待制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而这正落入了章惇的圈套,他希望将丰稷“困以道路”,因此“连岁亟徙六州”:先移知郓州京东西路安抚使,复知西京。绍圣二年(1095),移知成德军兼真定路安抚使,转朝请郎,改知颍昌府、京西北路安抚使,徙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复知西京,又知南京。元符元年(1098),丰稷以眩疾乞知湖州,元符二年(1099)三月,徙知杭州浙西兵马钤辖,转朝奉大夫。
徽宗即位,丰稷转朝散大夫,元符三年(1100)四月召拜左谏议大夫,未至阙即改御史中丞。因丰稷“自下召还以来,无不誉元祐而毁熙丰”,多次替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美言,引发了徽宗的不满。其间他还弹劾章惇、蔡京、蔡卞等人擅权作威,使“京贬、惇黜”,虽然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丰稷也成了这些官员的“眼中钉”。十月曾布拜相,“首罢丰稷御史中丞”,遂改工部尚书兼侍读。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权礼部尚书,七月为礼部尚书。十一月被罢,以枢密直学士知苏州。崇宁元年(1102),曾布进言“丰稷助元祐之人,可见朋比”,再加上旧敌蔡京得势为相,丰稷开始遭遇轮番的政治报复:一是被列入“元祐党籍”,后经徽宗御书刻石立碑树于端礼门及各路、州、军等处,以示万世。二是不断被贬谪外地,先改越州浙东兵马钤辖,降授宝文阁待制,知明州,又落待制,知常州,贬海州安置、道州别驾、台州安置,最终被除去官籍,移建州居住、婺州居住。至崇宁四至五年(1105—1106)因徽宗诏追复元祐党人、毁元祐党籍石刻,才得以叙复朝请郎、提举亳州太清宫,后归乡居住。
丰稷历经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期间“三进三出”,因卷入党争之中,其政治生涯跌宕起伏。虽然未官至宰执,但担任过尚书省工部尚书、礼部尚书等,主管一部之事,亦属高品级的两府大臣之列,由此推测应是元符三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100—1101)间请立功德寺。
3.3 丰氏家族的变迁对妙智院的影响
功德寺不同于普通的寺院,因它属于某人或某家所有,所以主家与功德寺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例如,主家拥有延请名僧担任住持的权利,也可以为寺院出资建造供奉、提供田产、购买佛教典籍等,有助于寺院兴盛,但也会出现主家干预寺院田产、随意差遣僧人等问题,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就丰氏家族与妙智院而言,尽管因丰稷位极人臣,妙智院被请为功德寺,但随着他被列入“元祐党籍”,其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甚至被夺职除籍,这份荣光没有持续很久。
崇宁四年(1105)七月,徽宗下诏“罢元祐奸党所建坟寺”,“吕大防、韩维、司马光、韩忠彦、傅尧俞、孙固、郑雍、曾布、胡宗愈、黄履、蒋之奇、陆佃、文彦博、吕公著、李清臣、王丛叟、苏辙、张商英、刘挚十九人所管坟寺,诏本身所乞寺额持免毁拆,不得充本家功德院,并改赐敕额为寿宁禅院,别召僧住持”。尽管丰稷不在曾任宰执的十九人名单中,但作为“元祐奸党”,他所请立的功德寺也应在被波及的范围内。而且丰稷性格谨慎缜密,“平生章奏,随手焚稿,晚陷钩党,有旨搜取,只字不留”,这可能也是丰稷请功德寺一事为史志所不载的另一原因。
列入“元祐党籍”,无疑对丰稷家族后代也有巨大影响,“凡名在两籍者,皆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至近甸”。再加上丰稷长子丰安常、次子丰大常皆早逝,幼子希仁仅为承奉郎,其他孙辈亦未能像楼氏或史氏那样接连出现在朝中为政的官员。此外,两宋交替之际,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也导致了丰氏家族的分崩离析。绍兴三年(1133)的《寻访子孙札子》提及孙丰济“不知存亡”、丰治“建炎三年死于金贼,其妻子见在明州居住,孤弱失所”。希望明、广两州官员能协助寻访到丰稷直系的亲孙或曾孙,此等境遇不禁令人唏嘘。
4 结语
两宋时期,四明地区佛教发展极为蓬勃,佛寺数量众多,且高僧大德辈出,与日本、高丽等国交流亦盛。而佛教的勃兴与文人士大夫的崇佛风尚、世家大族兴建寺院的行为均有一定关系。从两宋时期四明地区功德寺的兴建情况来看,自仁宗、神宗正式确立功德寺设立制度后,丰稷是目前所见此地最早且是唯一一位请立功德寺的高级官员,不仅通过科举任官实现了个人阶层的跃升,也为家族前后三代带来了封官的荣荫及逝后的安宁。
可惜的是,受“元祐党籍”事件影响,丰氏家族在北宋末南宋初的衰落与迁离,未能给予妙智院长期稳定的支持,此院可能就此又转变成一般寺院。因此丰稷请立功德寺一事成为妙智寺史上的一段插曲,但这也是丰氏家族最辉煌时刻的历史见证。
注释
①鄞县文献展览会.鄞县文献展览会出品目录[M].[出版者不详],1936:142.
②⑨t陈训正,马瀛.鄞县通志[M].张传保,汪焕章,修.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
③骆兆平,谢典勋.天一阁碑帖目录汇编[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83.
④章国庆.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⑤为便于阅读,释文统一改为规范简体字。原碑泐失字样,如有按相关文献或经考证补缺者,外加方框。
⑥罗浚.(宝庆)四明志[M].胡榘,修.刻本.1854(清咸丰四年).
⑦历代方志多数记载为“县西南七十里”,仅有乾隆《鄞县志》引延祐《四明志》误作“县西南六十里”。
⑧黄宗羲.四明山志:卷2[M].刻本.1701(清康熙四十年):叶22a.
⑩刘毅力.宋代的佛教寺院管理政策[J].中国宗教,2022(3):70-71.
k脱脱.宋史:卷321[M].武英殿校刻本.1739(清乾隆四年):叶7-10.
l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7[M].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景清姚江借树山房刻本.1919(民国八年):叶1a.
mr杨寔.宁波郡志:卷9[M].张瓒,修.刻本.1468(明成化四年):叶23a.
n钱大昕.鄞县志:卷30[M].钱维乔,修.刻本.1788(清乾隆五十三年):叶12.
o董沛,等.鄞县志[M].戴枚,修.刻本.1877(清光绪三年).
ps闻性道.鄞县志:卷21[M].汪源泽,修.刻本.1686(清康熙二十五年):叶53b.
q高宇泰.敬止录:册8[M].清徐时栋校本:叶9a-10a.
u陈建国.龙观乡志[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vx钟强.宋代功德寺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8.
w陈瑞霞.唐代皇家功德寺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1.
y黄敏枝.南宋四明史氏家族与佛教的关系[C]//漆侠.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547.
z李朴.丰清敏公遗事[M].金山钱氏重刻小万卷楼从书本.1878(清光绪四年).
佚名.续补高僧传[M].卍字续藏本:卷14.[出版信息不详].
其子维即郭维,为丰稷外孙。据李朴《丰清敏公遗事》所载丰稷之孙丰渐语,“公之遗事久而湮没,……,赖外兄颍昌郭维,以儒学修谨,侍清敏公左右最久,能摭其本末,历历如数一二”。丰稷生平详尽的历史记载得益于郭维的讲述。
冯福京.昌国州图志:卷6[M].宋元四明六志本.1854(清咸丰四年):叶3.明嘉靖《宁波府志》、清雍正《浙江通志》误作郭贯。
佚名.黄堂丰氏宗谱:卷1[M].仁让堂木活字本.1822(清道光二年):叶13a.关于丰氏家族的家谱及其文献价值,王镇宇在《家族与地域之间:宋明之际四明丰氏家族研究》中已有所研究及评判,尽管清代族谱依旧谱而修订,但只能反映唐宋时期家族繁衍大体状况,具体而言有不少错漏。详见:王镇宇.家族与地域之间:宋明之际四明丰氏家族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5:18-19.
张时彻.宁波府志:卷17[M].周希哲,修.刻本.1560(明嘉靖三十九年):叶2a.
桓村位于鄞江上游,与丰氏家族故居处相距不远。明嘉靖《宁波府志》载丰氏家族原居于“小溪镇之蕙江”,丰稷致仕归乡后才徙居于“县西南五里董母墓北”。清全祖望亦有“宋丰清敏公则蕙江其故居也”“宋尚书丰清敏公之故居在桓溪,既贵后,在月湖”“丰氏本自马湖来,清敏公始居于西湖”等语。小溪镇位于“城南门折行四十五里”处,自宋以来属句章乡,即今鄞江镇。“蕙江”为鄞江上流的别名,指的是它山堰后过百梁桥至奉化江相接的这一段。“马湖”位于县南五十里,今属洞桥镇,仍存马湖桥、马湖山等地名。可见在丰稷致仕、迁居城内月湖前,主要聚居于城西南句章乡马湖一带。
汪圣铎.佛、道为孝道服务的体现:功德寺观[C]//姜锡东,李华瑞.宋史研究论丛:第10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29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浙江书局刻本.1881(清光绪七年).
张津.四明图经:卷2[M].宋元四明六志本.1854(清咸丰四年):叶14b.
程俱.麟台故事:卷2[M].清乾隆武英殿木活字武英殿聚珍版书本:叶10a.
[佚名].宋史全文续通鉴:卷13[M].明刻本:叶22a.
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M].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8[M].民国二至六年乌程张氏刻适园从书本:叶35a.
陈均.皇朝编年备要:卷26[M].清抄本:叶20b.
陈次升.谠论集:卷3[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叶19b.
秦缃业,黄以周辑.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19[M].浙江书局刻本.1883(清光绪九年):叶16a.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6[M].民国东方学会排印六经堪丛书本:叶12b.
王称.东都事略:卷110[M].席氏扫叶山房刻本.1798(清嘉庆三年):叶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