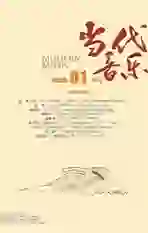论歌唱语言与歌唱发声状态的关系
2025-01-18李雪薇赵丽娟
[摘 要] 在声乐艺术创作以及声乐艺术实践中,歌唱语言审美是一项普遍存在的审美现象,基于人类对歌唱语言美学特征的不断总结,体现出声乐这门艺术的特殊性。歌唱语言和歌唱发声状态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歌唱者关注的焦点,如何实现歌唱语言艺术性与良好发声状态间的平衡也是困扰歌唱者的一大难题。文章从歌唱语言的特殊性和审美特征入手,分析歌唱语言与歌唱发声状态之间的关系。并从咬字吐字,歌唱语言表现元素的运用,装饰音演唱,声音稳定性与松弛度,歌唱弹性状态与表现力五大方面阐述歌唱语言在歌唱中的运用与表现。
[关键词] 歌唱语言;发声状态;语言审美;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 J616"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25)01-0148-03
歌唱有着圆润、饱满等审美要求,从本质上来看,歌唱是语言在音乐旋律上延伸、嬗变、扩展与升华的过程,歌唱语言是歌唱艺术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歌唱艺术生命活力的源泉,古今中外的歌唱大师和优秀的声乐作品无一不突出歌唱语言的重要性。然而在歌唱艺术实践当中,一部分歌唱者却存在重视歌唱技巧而忽视歌唱语言的问题,为了达到更加良好的歌唱发声状态不得不牺牲清晰、圆润的歌唱语言表现方式。实际上,歌唱语言与歌唱发声状态并非是对立存在的,而是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在歌唱艺术实践中实现歌唱语言与歌唱发声状态之间的平衡可以帮助歌唱者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
一、歌唱语言概述
歌唱是音乐与语言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歌唱语言可谓是歌唱艺术的灵魂所在。从概念层面来看,歌唱语言是“咬字与发音完美结合的产物”,在形式上体现出两种属性,一方面表现为声学形式,以母语本体语言整体性和发声技巧为基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特征。我国汉语字音由声母、韵母和音调构成,通过字音与语调的高低、强弱、唱段、节奏等,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歌唱语言表现形式。我国历代声乐家都表现出对歌唱语言的高度重视,也在长期的歌唱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字正腔圆,明朗清晰”的歌唱语言审美标准。如明代魏良辅在他所著的《曲律》中指出:“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我国当代作曲家、歌唱家应尚能也在《以字行腔》中强调我国歌唱语言艺术的精髓在于“以字行腔”“字领腔行”“字正腔圆”,歌唱语言是否准确,是否符合中国汉语的发音规则,是否体现出语调的变化,将直接影响歌唱表现力的高低;另一方面表现为内容形式。歌唱艺术与其他门类的艺术相同,都具有审美、娱乐、教化等功能,歌唱者运用歌唱语言的过程便是与听众进行深度交流的过程。从此种层面来看,歌唱语言是歌唱者对作品的“二度创作”,歌唱者对歌唱语言的处理方式不同,带给听众的审美感受也不同。优秀的歌唱者能够实现音乐与歌唱语言的完美结合,让歌唱语言伴随着音乐不断延伸、扩展和升华,并且在其中注入真挚、细腻的情感,引发听众的共鸣,让听众沉浸在音乐之中,充分地接收到歌唱者通过歌唱语言所传递的思想、情感、意志、愿望等内涵,在此过程中歌唱者与听众在歌唱语言这一媒介的支持下实现了融合,歌唱艺术的价值也在真正意义上得到了体现。综合而言,歌唱语言是咬字与发音、形式与内容融合后的结果,是歌唱艺术中不可或缺的要素[1]。
二、歌唱语言与歌唱发声状态的关系
在我国歌唱艺术审美语境下,歌唱语言与歌唱发声状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字正腔圆”来概括。歌唱发声状态是生理状态和心理状态相互作用后产生的结果,在歌唱艺术实践中,声带振动以发声,辅之歌唱技巧对自然声音加以美化、修饰,运用唇、舌、齿、牙、喉等语言发声器官控制、调整歌唱语言中的重音、字音、强弱变化、语调语势,讲求语言声调的准确性以及歌唱语言的抑扬顿挫。“字正”是对歌唱语言的基本要求,“腔圆”是对歌唱发声状态的基本要求,两者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字正”是“腔圆”的前提条件,注重跟随音乐的发展、律动以及变化将每个字音发准确、咬清楚;“腔圆”是“字正”的延伸,在歌唱时如果歌唱者过度关注咬字的清晰准确,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歌唱语言要素的表现上,很容易出现将字“咬死”的情况,这时候声带过于紧张,声带闭合的情况下对气息的阻力也明显增加,气息不连贯、不充足、不稳定则会导致声音虚实不定、苍白无力,歌唱发声状态变差,容易出现艰涩、紧促的声音;如果歌唱者过于注重“腔圆”,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共鸣腔体的调动、运用之上,则会导致歌唱语言的发音含糊不清,听众只能够感受到音乐的旋律、节奏,而难以体会到作品的内容和内涵。由此可见,在歌唱艺术实践中歌唱语言与歌唱发声状态相互影响、相互支撑,关键在于歌唱者如何看待歌唱语言的地位及其对歌唱发声状态的决定性作用,如果歌唱者追求歌唱语言和歌唱发声状态之间的相互平衡,能够灵活自如地应对歌唱语言的变化并调整好自己的歌唱生理状态、心理状态,便能够在清晰表达歌唱语言的同时,让声音具有共鸣的美感,反之亦然[2]。
三、歌唱语言在歌唱中的运用与表现
(一)咬字吐字
咬字吐字是一项基础性的歌唱语言技巧,在歌唱艺术实践中,歌唱者的咬字吐字方式会直接影响歌唱的状态,如果咬字吐字方式不当,很容易因咬字过紧、音节衔接缓慢而出现拖节奏,音量较低等现象,虽然歌唱者一直保持歌唱发声状态,但咬字吐字动作不正确、方法不科学会导致声带疲劳,声音紧绷且缺乏灵活性。所以在歌唱中运用歌唱语言的前提在于把握好咬字吐字的技巧方法。首先,尽可能缩小咬字的动作幅度,根据我国汉语语音特点掌握咬字吐字的基本原则,即字头清、字腹响、字尾准。咬字头时将声母发清楚即可;字腹要突出歌唱语言的色彩,突出元音;字尾要干净利落,并且与下一个字的字头快速衔接。其次要控制好咬字的力度。在歌唱艺术实践中可以通过咬字来改变歌唱发声状态,尤其是咬字力度既可以强调歌唱语言的语气感,又能够帮助歌唱者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进而影响到歌唱发声状态。例如歌唱家常思思在演唱由刘聪和樊孝斌共同创作的艺术歌曲《鸟儿在风中歌唱》时采用了朗读中的歌唱语言处理方式,将每个字都唱得很清楚,咬字力度轻巧,突出了鸟儿的轻快活泼。
在声乐演唱中,要了解汉语语言的“韵辙”,吐字时根据“十三大辙”对每个字音的韵母部分进行“归韵”“依字行腔”。例如在歌唱“阴平字”时在发音后保持原来的音高,声音要平稳;歌唱“上声字”时咬准并唱出字头后声调由低到高,让歌唱语言的声调和旋律线条的走向相一致,并且保证字音、字义清晰,进入良好的歌唱发声状态之中[3]。
(二)歌唱语言表现元素的运用
歌唱语言是传情达意的载体,是形式美与内容美的有机结合,与自然语言相同,歌唱语言也由重音、轻声、停顿、节奏等元素构成,运用好这些歌唱语言元素不仅可以让声音更具有感染力、吸引力,而且能够更好地表达歌词的含义。一是重音的运用。歌唱语言中的重音有语法重音和逻辑重音之分,语法重音由歌唱语言的组成和结构形式所决定,逻辑重音则由语义内涵所决定。
重音的运用并非通过加强音量来实现,而是通过语调的变化来体现。例如:在李双江歌唱《北京颂歌》中“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一句时,对“升”“灿烂”“金色”等动词和形容词运用了重唱,连词、助词等运用了轻唱,唱出朝霞升起的动态感。歌唱语言中轻声起到突出、衬托的作用,除了助词、虚词等轻声歌唱之外,还可以根据作品的情感基调、情绪色彩等进行轻声处理。例如:《姑娘生来爱唱歌》是一首云南彝族民歌,常安在演唱这首歌曲“人人说我是布谷鸟”一句时,用委婉含蓄的情感表达了姑娘对歌唱的热爱之情,让“姑娘”的声音更加轻盈、悠扬。
停顿是歌唱语言间歇性的体现,既可以作为换气口缓解歌唱的疲劳感,让歌唱者进入良好的歌唱发声状态之中,又可以强调某种情感情绪。在歌唱中歌唱者可以结合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对停顿之处进行“二度创作”。例如:由歌唱家吴雁泽演唱的《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饱含着两岸血脉相连的情感,乐曲中“台湾同胞”歌词后无符号表示停顿,但演唱家在演唱时略停顿,突出后面的“骨肉兄弟”,为歌唱增添情感。根据作品的情感基调来处理歌唱语言的节奏,完整且深刻地表现出作品的内涵。
(三)装饰音演唱
歌唱语言的特殊性在于其是一种被旋律规范的,被乐音装饰过的语言。装饰音演唱是歌唱者必备的歌唱技巧,对歌唱者的歌唱功底和审美意识有着较高的要求。歌唱作品中的装饰音演唱有着圆滑流畅的基本审美要求,气息的运用以及对声音位置的控制是影响装饰音演唱效果的两大因素,即既需要将声音保持在高位,让声带充分振动,处于良好的歌唱发声状态之中,又需要通过对歌唱语言的处理让字音清晰明朗,让声音圆润饱满。很多歌唱作品中作曲家都运用了大量的装饰音,这是对歌唱者的考验,歌唱者需要提高自身对歌唱发声状态的控制能力,追求歌唱语言和歌唱发声状态的平衡。例如,赵元任艺术歌曲《也是微云》中第16小节的“偏”对应着快速六连音,音乐旋律整体向上发展,力度持续增强,为了唱出有质感且圆润的声音,歌唱者要延长声带的振动部分,将声音共鸣位置保持在眉心,用头腔共鸣展现出自身嗓音的特性,适当地提高声音的音量和穿透力。在此基础上要将快速六连音唱得轻快、圆滑、音色富于变化,在音色变化中还需要保持声音高位不动,避免挤压共鸣位置,调节好自己的心理状态,缓解自己身心的紧张感、疲劳感,整个歌唱过程以充足、连贯的气息来支撑,随着气息流速的加快,声音力度也持续增强,歌唱发声状态要保持良好,避免声音干涩、苍白,在18小节处气息渐渐平缓,在歌唱“来”时轻轻带过,实现前后乐句的衔接[4]。
(四)声音稳定性与松弛度
声音稳定性与松弛度是判断歌唱艺术性的重要标准,也是歌唱者所追求的理想歌唱发声状态。声音的稳定性与松弛度是指声带稳定振动,气息稳定,采用科学的发声方法,让声音松弛圆滑,体现出歌唱艺术的美感。从生理层面来看,声带和喉咙是歌唱语言运用和歌唱发声的生理基础,打开喉咙并保持喉头稳定,处理好气息和喉咙位置之间的关系才能够突出声音的稳定性和松弛度。在歌唱中打开喉咙对于歌唱者来说并非难事,但如何在气息变化之下保持喉头位置稳定则是歌唱者需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在无意识的呼吸方式下,气息的上提或下沉必然会对喉头的位置产生影响,为了让喉头稳定在有助于科学发声的位置,演唱者可以采用“半打哈欠”的方式,即让共鸣腔体张开但并非处于过度张开的状态,让喉头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跟随音高的变化始终保持在最有利于科学发声的位置,再辅以正确的咬字吐字方法、歌唱语言处理方式,让声音更加优美动听。例如:赵元任创作的另一首艺术歌曲《秋钟》是一部富有古典韵味的演唱作品,“似远似近,和那轰轰轰的风声,似有似绝”是乐曲中旋律起伏较大的一句,旋律音区从中声区提高到高声区,此时喉头位置也需要略微提高,可以更好地达到音高要求,同时要注意对歌唱语言的强弱处理,赋予声音以柔和之感,保持声音的明亮。虽然喉头位置的变化会挤压一部分的胸腔共鸣,但可以实现声音的稳定性,能够更好地通过歌唱语言来表现作品的内容与情感内涵[5]。
(五)歌唱弹性状态与表现力
歌唱的弹性状态是指根据音乐作品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歌唱发声状态。歌唱的表现力涉及情感、歌唱语言、音乐旋律等多个方面,需要歌唱者在保持歌唱弹性状态的同时通过对节奏、音色、声音动态等的灵活处理,对呼吸、发声、共鸣的正确调节来增强歌唱艺术的表现力。对此,歌唱者需要熟悉了解歌唱作品歌词的内涵,深入研究歌唱作品的歌唱语言特殊性与审美特征,透过歌词来感受作曲家以及“曲中人”的情感情绪,这样才能够在歌唱中更加灵活自如地调整好声音的色彩、质感以及歌唱语言的处理方式。例如《上山》也是赵元任根据胡适创作的新体诗创作的一首艺术歌曲,作品开篇的歌词:“努力,努力,努力往上跑,我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擦,拼命地爬上山去。”体现出攀登者的满腔热情、昂扬斗志,歌唱旋律的走向也和歌词的含义、情感变化相一致,在演唱这首歌曲时要突出声音的力量感,尤其是在歌唱两个重复的“努力”时,腹部要保持鼓起,气息集中到胸腹部后再均匀、有力地倾吐出来,保持富有弹性的歌唱发声状态,通过横膈膜与腹部的对抗为歌唱语言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后续歌词的歌唱中要一气呵成,通过气息的变化以产生一种跳跃但有力的声音质感,体现出歌唱弹性状态和歌唱语言之间的关系,更好地表现出攀登者的决心、勇气、信念。
结" "语
歌唱语言是歌唱艺术中的重要元素,也是歌唱声音状态的前提条件。歌唱语言和歌唱发声状态之间具有“字正”“腔圆”的关系,尤其是在歌唱我国歌唱作品时要把握好汉语字音的发声规则,运用好咬字吐字技巧,让歌唱语言的声调与音乐旋律的走向保持一致,体现出“依字行腔”的歌唱语言审美特质。同时要注重歌唱语言的重音、轻声、停顿、节奏等元素在歌唱中的运用,在保持良好歌唱发声状态的同时,通过对歌唱语言的灵活处理向听众传递更多的关于作品内涵、意蕴的信息,并且在歌唱艺术实践中要保持声音的稳定性、松弛度以及歌唱的弹性和表现力,追求歌唱语言与歌唱发声状态的平衡。
参考文献:
[1] 陈丽丽.对民族文化的理解在歌唱语言运用中的重要性[J].作家天地,2023(28):153-155.
[2] 赵媛.民族歌剧演唱中歌唱语言与情感的表达探析[J].中国文艺家,2023(04):88-90.
[3] 黄琪媛.歌唱语言训练与舞台表演技巧的探究——吴碧霞声乐公开课有感[J].黄河之声,2022(13):112-114.
[4] 潘小燕,张清华.声乐中的歌唱语言艺术——咬字、吐字[J].艺术品鉴,2022(17):174-177.
[5] 王晶.声乐歌唱语言与咬字的艺术处理[J].戏剧之家,2022(03):87-88.
(责任编辑:韩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