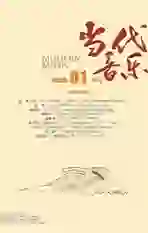音乐教育家费承铿对我国中小学音乐大纲研制的贡献
2025-01-18张华毅
[摘 要] 音乐教育家费承铿是本世纪“人教社”小学音乐教材主编、初中音乐教材副主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长期作为我国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起草、主笔人员(之一),先后参与我国第四份、第五份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本世纪音乐课程标准研制与修订工作。此外,基于教学大纲推行的研究,他提出“中国特色师范音乐教学法”理论,也是我国最早引进日本竖笛教学的专家之一。为了验证本世纪颁布的新课程标准,他躬行于小学一线进行教学实验,纠正了以往过分“淡化音乐知识技能”的做法,为我们音乐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费承铿;中小学音乐教育;音乐教学大纲
[中图分类号] J605"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233(2025)01-00199-03
费承铿先生是我国当代知名的音乐教育家。中国音乐教育协会会长谢嘉幸先生对其评价:费承铿的贡献“不亚于我主编的《国乐传承与创新丛书》中的音乐家(如李凌、施万春、董维松、耿生廉等)”[1]。我国新世纪音乐课程标准研制组负责人王安国先生评价其为我国“平民音乐教育家”,即基础音乐教育领域的音乐教育家,“堪称各级各类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楷模”,进而呼吁我们不要忘了他的贡献[2]。那么,费承铿先生有什么贡献值得我们记住他呢?本文仅就费先生参与、主笔我国音乐教学大纲(课程标准)方面的贡献进行评述。
一、参加国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起草
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是指导、检查、考评中小学音乐教学的规范性文件[3],对中小学音乐教学来说极为重要。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教学指导不是依据某些高深理论,而是对教学大纲的掌握来实施的。因此,参与制定国家音乐教学大纲的人既要有高深的教学理论知识也要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
费承铿先生从1986年便参与国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制定[4]。此后,费先生便一直从事国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起草、修订工作。1992年还是国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起草的主笔之一。2000年退休后,他仍是中小学音乐新课程标准研制组的重要成员(包括2011年的修订版)。本世纪音乐课标研制组组长王安国先生在纪念费先生的文章中,还特别描述了费先生参与研制新课标过程中的感人镜头:2000年末,《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在北京大兴起草,彼时电脑还未普及,在大家对文字输入都犯难时,63岁的费老自告奋勇利用课题组其他专家休息的时间,用“一指禅”的方式把字敲进电脑。当时寒气逼人,费先生仅裹着棉衣,手指冻得通红[5]。
二、参与制定第四、第五份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
制定国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集集体智慧于一体。如要说清楚费先生参与制定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具体贡献是很困难的。因此,笔者先笼统地进行分析。
费先生参与制定的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四份教学大纲。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颁布的第一份音乐教学大纲,基本是参照苏联的大纲而制定的,具有过渡性质[6]。1956年的第二份音乐教学大纲尽管有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内容,但小学仅是“唱歌教学大纲”,不仅规定太窄[7],而且还因为从该年度开始“美育”从教育方针中消失名存实亡。1979年制定的我国第三份音乐教学大纲尽管“结束了音乐教育的混乱局面”,但问题非常突出,主要是“概括性太宽”[8],即其内容规定的中小学界限模糊,尤其缺乏针对大多数学生、大多数地区这个对象[9],且内容本身仍然是以唱歌为中心的体系,缺乏创作、器乐的内容[10]。当时美育还没有回到教育方针中来,因此,这份国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某种程度来说也带有“过渡”性质。1985年我国进行了教育体制改革,美育在国家正式文件中开始重新出现。面对新的形势,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费先生参与的我国第四份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所负载的使命非常巨大,其鲜明的指向必须要具有“中国特色”。
以上当然是包括费先生在内的集体做出的贡献,费先生可确证的具体贡献是他进一步对此做出理论研究。
费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ZSY音乐教学法”[11],全名叫“中国特色师范音乐教学法”,其核心内容是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即既尊重音乐艺术规律也要强调其道德功能。费先生这一思想从他1984年发表的《音乐课的教材分析》[12]一文也能看出端倪。此原则在今天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甚至此前也有类似提法,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坚守这一理念是难能可贵的。新中国成立后,音乐教育的政治功能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80年代初美育还没有回到教育方针中时,一些学者对音乐教育的认识基本还是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占主导地位[13];也有学者提出要以“审美”为核心[14],尽管遭到其他学者的批判[15],21世纪的音乐新课程标准仍提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作为主导思想。音乐新课标课题组副组长此后声称新课标是以美国雷默提出的“以音乐审美为核心”作为主导思想的[16]。经过十多年的新课程实践,音乐新课程研制组总负责人王安国终于对新课标的哲学基础作出调整,在2011修订版的修订说明中特别提出新课程的哲学基础要回归中国传统,在强调“审美核心”原则时不能忽视德育[17]。如此看来,这基本上就是费先生思想的再现,费先生的主张显然更具有超前性、恒定性。从王安国的表态来看,费先生的主张真如其所说是“中国特色”。
不仅如此,费先生1986年开始受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中小学的音乐教学大纲,其后又编写了中师音乐教学大纲,我是主笔之一[18]。自此,费先生一直承担国家历次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研制与起草工作[19]。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国家第五份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特色是首次提出器乐进课堂,此后还进一步提出创作进课堂。自此,20世纪音乐新课程的所有教学领域(唱歌、器乐、创作等)几乎都已被开辟过了。要知道开辟一个新的领域不是那么容易的,新的音乐教学大纲必须从头做起,既要借鉴国外(如费先生1989年发表的关于日本音乐教材的文章《日本中小学音乐教材的启示》,这是他自学日语后翻译、研究日本音乐教育的系列文章之一[20]),又要开挖传统,进而还要作出创新性思考与表述,其学术含量与工作量可想而知。
器乐进课堂的一个突出标志是竖笛进课堂。费先生是我国最早引进竖笛教学的专家。早在1982年,费先生就借日本友人来其当时所在学校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访问交流之际,开始引进竖笛。他先是联系厂家生产,后引进课堂进行初期实验。在费先生2001年主编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音乐教材三(上)教参中写到:“我国从1985年开始将八孔竖笛引入中小学音乐课堂……”[21]。现在竖笛已成为国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中的首推乐器。1985年费先生在《上海歌声》11期发表他翻译的日文《创造性的竖笛教学》,这是我国最早介绍竖笛进入课堂教学的文章。该文介绍的方法几乎涵盖现今所有竖笛入门的教学方法。突出的特点是从“7(si)”这个音开始吹,而不是“1(do)”。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徐州师院工作期间,国家教育部还慕名来函拟调费先生去教育部为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培训竖笛,但鉴于徐州师院音乐系刚刚创办无法离开,因而推荐孙巍巍老师前往(见徐州师范学院文件1996年2号文《关于给予费承铿同志通报表扬的决定》)[22]。
三、参与本世纪音乐新课标的研制
2000年,国家启动新一轮课程改革,组建新的队伍来研制音乐课程标准。刘沛教授说,为了使得新课标能与旧的教学大纲相衔接,费先生虽然已经退休,但仍被邀参加音乐新课程标准研制[23],其贡献不言而喻。但费先生更为突出的贡献是他于2002年到徐州青年路小学义务任教一年,目的就是为了验证音乐新课标的科学性。跟费先生一起编教材的同事吴文漪的回忆文章《我心中永远的费老》写道,“为了了解学校实际的教学情况,费先生在课改前期到他家附近的小学校义务当了一个班(其实还有兴趣小组)一个学期(实际是一年)的音乐老师。一个大学教授义务从事最基础的音乐教育工作,不为名不为利,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啊!没有人要他这样去做,(他)完全是出于对音乐教育事业的责任心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24]。费先生的这次实验报告先后发表在《中国音乐教育》《儿童音乐》(见《前沿随记》,2004)两本杂志上。
音乐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王安国先生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费老师……自愿到一所小学……通过整学年的亲身实践,验证‘课标’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他……会从我国音乐教育实情出发……表达他的意见和建议,尤其对中小学音乐课失却学科本体的误区,直率地提出批评,极力主张摒弃表象热闹的浮华教风,倡导实施有效的音乐教育”[25]。
王先生提到的“失却学科本体”是指新课程标准实施开始提出的“淡化音乐知识技能”的做法。关于“知识技能”在中小学课程中的地位问题,教育界曾有王策三(2004)与钟启泉(2005)的持续论战。但音乐教育界似乎铁板一块,以至于从“淡化音乐知识技能”到“不要音乐知识技能”[26]。《中国音乐教育》杂志刊载的新课程专家对课标的解读(2002年第9期)甚至公开为一个音乐教师这样的教学进行辩护,此事源于该教师说一个学生听刘天华的名曲《空山鸟语》后,将其想象成“捉鸡”,并详解为老太太的鸡从鸡窝跑到院子里,她急着到处捉……该教师认为“不能用谁想象得好、差”来评价。某新课程研制组专家还对此特别评论道“音乐没有标准答案”,甚至站在该教师的立场批评以往教学的所谓“误区”[27]。这样的“解读”必然会带来不良影响,如果这样想象也可以的话,音乐听赏教学还需要老师教吗?谁不会自由遐想呢?对此,费先生不遗余力地进行宣讲,特别是他利用到全国各地进行音乐教材培训的机会对此类现象进行批驳。如2006年7月听过费先生宣讲的郝韶华老师在回忆文章《再回首回忆费教授》中提到,“作为一位伟大的音乐教育家,费教授对于课改,无疑是具有极强的前瞻性的。下面的一些激进的观点是2006年7月他在开封讲学时提到要注意的:1. 打破学科的桎梏。2. 淡化学科的知识体系。3. 在游戏和玩耍中轻松地学习。4. 重过程不重结果。5. 审美教育无需知识技能。6. 将有部分学生‘喜欢音乐而不喜欢上音乐课’的现象说成是全局性的。7. 一些杂志及报刊的文章进行了误导,例如《帕瓦罗帝也不识谱》《淡化双基》《在游戏中学习音乐》等。了解2012年音乐课标修正稿的人,就知道,这些观点印证了他对课改的前瞻性”[28]。
显然,费先生这种前瞻性不是凭空猜想来的。由于费先生在音乐教育界的影响力,经过费先生的建议,2011版新课标彻底改变了以往“淡化音乐知识技能”的提法,在原有基础上强调了“音乐知识技能教学”,王安国先生在修订意见中对此还加以特别的说明[29]。尽管这不能说是费先生一个人的力量取得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费先生的这种亲自实验的科学精神是很少见的。费先生这种科学精神哪来的呢?费先生是这样自述的:“张肖虎是一位全面了解中国国情、切实面向基础教育的音乐教育家,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如同他的人品一样宽厚而博大,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实践,厌恶空对空的理论。他多次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对那些不脚踏实地、不了解和研究实情,只会从理论上高谈阔论的所谓音乐教育家十分厌恶,指责他们‘只能起捣乱作用’。而他自己不仅多次参加了教育部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的制订工作,而且为了更好地编写教材,还亲自到中小学去听课,所以他对中小学生和中小学音乐教师的现状和需求了解得十分清楚......我在张先生的领导下一起编写大纲、教材和音乐教育改革的研究长达十年之久,曾戏称是他的‘嫡系部队’和‘不是研究生的研究生’,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的东西,尤其是刚直不阿的性格。”[30]
综上所述,费先生参与研制、起草、主笔国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工作具有引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基础音乐教育方向的作用。只不过,这“默默无闻”研制音乐教学大纲的行为不像署名的学术论文那样能被人所深入了解。希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学术界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刘双.儿时不喜欢音乐也能成为音乐教育家——《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读后[J].艺术评鉴,2017(13):12-13.
[2] 王安国.深切怀念费承铿老师[J].人民音乐,2013(08):60-61.
[3] 张肖虎.对义务教育《全日制音乐教学大纲》的理解[J].中国音乐教育,1989(03):10-12.
[4] 吴跃华.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3-221.
[5] 同[2].
[6] 金亚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学校音乐教育法规的建设[J].教育探究,2009(09):9-13.
[7] 许锐.建国后我国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D].中国音乐学院,2012:11.
[8] 廖家骅.对《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的一点意见[J].人民音乐,1982(07):49.
[9] 任传忠.初中音乐教学大纲、教材应面向两个多数[J].人民音乐,1984(07):46-48.
[10] 韦俊民.中学音乐教学大纲应当改一改了[J].上海教育科研,1983(03):35.
[11] 吴跃华.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92.
[12] 费承铿.音乐课的教材分析[J].江苏教育,1984(14):43-44.
[13] 吴跃华,闫辉.试论音乐教育要“以音乐审美为核心”[J].艺术探索,2006(S2):55-56,4.
[14] 姚思源.音乐审美教育应是学校音乐教育的核心[J].北京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04):73-74.
[15] 管建华.“审美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批评与音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建构[J].中国音乐,2005(04):6-16,30.
[16] 吴斌.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缅怀雷默先生[J].中国音乐教育,2014(10):4-5.
[17] 王安国.提炼“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对“音乐教育哲学”问题研讨的两点认识[J].人民音乐,2012(02):72-74,95-96.
[18] 吴跃华.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118.
[19] 吴跃华.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119.
[20] 费承铿.日本中小学音乐教材的启示[J].中国音乐,1989(01):35-36.
[21] 吴跃华.江苏师范大学音乐教育前史考释[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8:170.
[22] 吴跃华.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221.
[23] 同[18].
[24] 吴跃华.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18.
[25] 同[2].
[26] 吴跃华.论“音乐知识技能”教学[J].中国音乐教育,2005(12):4-6.
[27] 王安国,吴斌.音乐课程标准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6-49.
[28] 吴跃华.平民音乐教育家费承铿释传[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6:30.
[29] 王安国,王耀华.新的起点 新的高度——音乐课程标准几个重要内容的修订[J].基础教育课程,2012(02):131-134.
[30] 同[18].
(责任编辑:韩莹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