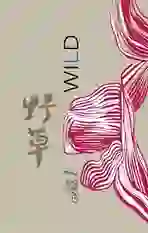“二千尺青铜老干横枝撑铁”
2025-01-14王自亮
我曾在《永远激荡的创造性流动》一文中这样写道:“洪迪诗歌早已达到了中国诗坛精神标杆的高度,他的重要诗篇放到一流诗人方阵一点也不逊色,他的代表作《超越存在》和长诗《长江》更是空前之作”,“即令低调地予以评价,洪迪诗歌也为百年中国新诗史奉献了一片并不显赫却独一无二的诗美天地。……他的诗歌风格深沉而幽微,同时拥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强烈的现实感,兼具宏大叙事的铺陈与玄奥奇妙的诗思运行。这些貌似对立的诗美建构方式和语言现象,在洪迪身上如此契合并高度融汇,浑然一体,形成极为独特的诗歌魅力”。
写下这些话之后,又过去十几年了。如果来一次“回头看”,我相信对洪迪先生这些评价是站得住脚的,能经受住时间检验。
而今,洪迪先生以93岁高龄,依然活跃在诗坛上,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文学批评。用“宝刀不老”或“常青树”来形容先生的精神状态,恐怕不够精准到位,也失之概念化。在我看来,他有点像晚年的歌德,在迈向“期颐之年”时仍保持了思想的活力,以及精神世界的丰茂。概括起来说,那就是“创造力不衰”。至今,洪迪先生仍将存在与时间、文学与人生、语言与事实,对历史本质与当下经济、社会状态,一如既往地作分析与省思,并得出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结论。令人钦佩的是,先生至今依然笔耕不辍,他的思想产品如此多样:诗歌、诗学和随想录,甚至哲学著作。不唯“追忆”,更有“批评与期待”:对未来,对人类,对这个令人不安的世界。
洪迪先生的世界,就是一个“思与诗”的世界。诗、诗人与诗学,是贯穿他一生的精神主线,倾注了心血、热忱和博大之思,更见出他的勇气和胆识。
在他看来,诗是情感时空与智力时空的统一,是“无解的斯芬克斯之谜”“旋转于多重怪圈中的豹子”,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体验、创造与超越,又是值得为之劳作一生的语言艺术。人之所以需要诗歌,“是为了从沉重的现实大地上腾起”,“愉悦自身,解脱自身,超越自身”,并使得我们进入“生命力高激发态”,获得最高意义上的“审美生命”。在先生看来,在人的全部创造物中,最富有创造性的是诗,因而诗又最具有神性。“诗的神性最根本的呈现,是诗美意蕴上人性的本真圆满与艺术语言上的气韵生动”。真正的诗人,就要投入“永远激荡的创造性流动”之中,写出更好的,更具原创性的作品。
而洪迪先生本人,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近年出版的皇皇巨作《诗学》以及新诗集《存在之轻》,就是他上述精神状态和写作姿态的产物。前者被诗人和批评家誉为“体大虑周、宏博精深的诗学著作,不但为新诗有史以来仅见,而且足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清人叶燮之《原诗》各擅其美,相映生辉”(唐晓渡语),“他发动我们的文心,似欲重启雕龙之业”(西川语)。著名诗人于坚,称洪迪先生为“这个时代的高人”。他的新诗集《存在之轻》,也获得众多好评。
在这里,我们向读者推介洪迪先生15首诗歌近作。
这些诗歌大多创作于2017年前后。按照先生自己的说法,自从出版总结性诗集《超越存在》之后,写诗的“习性难改,至今五六年间,偶尔经不住画上几笔,随便丢着”,大部分近作因为要出书,“几乎全被奕林惹出来的”,“好在肚皮里积着想写的不少,于是就天天赶工”。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洪迪先生已是87岁的老人了,我不知道“天天赶工”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宁可相信,诗歌是作者长期情感酝酿与语言积累的瞬间爆发。这种爆发是由一个饱经沧桑的长者完成的,应该是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幸运:目睹了一个真实的诗歌创作奇迹。
这些诗是怎么写出来,我在这里无法一一描述,但我坚信:这是意志、眼界和智慧的混合物,也是时间的作品。洪迪先生这些年身体方面有诸多问题,居住环境也甚为简陋,写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但短短时间内他还是奉献了上百首诗歌。他的沉静、耐心和坚持,完全是“热爱”的产物:对诗歌,对思考,对生命。据他自己说,不写诗不读书,“我是一日也过不下去的”。他是心中有大诗歌理念的人,是有诗学主张和美学信念的人,也是在创作中有诗歌“标准”的人,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数”。他是一个既随处寻找灵感,又让灵感自动降临的人。沉思,是洪迪先生诗歌创作的秘诀,而发生在内心的对话与碰撞(主观/客体、人/自然、自我/他者),则是他的诗歌之源。诗美创造,是他写作的动力。
于是,我们在读这些诗歌时,首先感受到的是诗人的思想活力,诗意激荡之际的想象力飞扬,诗美创造中的力与美之均衡,诗意运行过程的气韵生动。洪迪先生《立在地球边上》这首诗中,流淌着《创世记》般的力量与美感,同时又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源于性,金钱与权力”的毁灭,将其并置于大海/天空、鲲鱼/大鹏的背景下,赋予一种从内而外的激浊扬清的力量,而诗人“立于地球边上”,既是一种观察的角度,又是内心的景深。“我”与“眼前的一切浑然一体”,证实了诗人与大海、世界达到“物我两忘”境地,即“大海是我”。《白鸥》一诗则写出了生命的精义:“翔飞的自在”。一部生命的“奥义书”,既非动也非静,而是“常动的恒静”。而《石塘箬山天后宫》这首诗,非常耐人寻味。表面上是写东南沿海的一座天后宫(妈祖庙),一个佑护航行平安的神祇——“天后娘娘”妈祖:“民间女杜默。三神合一的天后妈祖/日夜立在山崖。护佑骇浪船舶平安”,实际上是写人,包含了人与神的关系,人性与神性,一种博大而永恒的爱,一份悲天悯人的心情。诗人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从海岸出发,通过无际的“汹汹大海”,洞开的“庄严的大门”,想到了三位与海洋、岛屿有关的“女神”:碧波蚌贝上裸体的维纳斯,她的“至美情爱”;宙斯后脑蹦出的甲胄雅典娜,她的勇武智慧;南海紫竹林中赤脚鱼篮观音,她的大慈大悲。跳跃的联想,超现实主义的跃升,主线自然是爱、死亡与悲悯,一种介于神性与人性之间的美。这种美飞翔并扎根于人心,具备了拯救的力量,再生的可能。
其次,我们在洪迪先生这些诗中,领受了介于幻美与“接地”的语言魅力,语言成为“存在之家”的例证。诺奖诗人米沃什曾经说过,作为一个诗人,他努力以骑鹅旅行记里的主人公那样,以两只不同的眼睛看世界,一只眼睛能看到恢宏的、开阔的远景,一只眼睛能识别细微的、近距离的事物。依我看来,诗人的语言也应该是双重的:一面是幻美的、迷蒙的、空灵的,另一面是真切的、坚实的、及物的。当然,卓越的诗人会时常将两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亦幻亦真、宏博而幽微的语言图景。洪迪先生的《海雾》就是这样的范例。诗很短,但可见一斑:
海雾从吹浪老鱼嘴上升起
隐而徐显。大队芭蕾舞女婆娑
变色龙的舞衣缥缈。飞天
绰约。晨曦渐成沉沉暮霭
便有依约箫音自远方缓缓趋近
非诉非泣。一种含铅的叹息
谁在叹息?不在海上或船中。落叶
纷飞。在那些补网的纤纤指尖
其中,远景是幻美的,近景是接地的。前者动感、情境和幻觉结合,后者则通过补网的手指,揭示了一种惆怅,一种悲凉之感。而“吹浪老鱼”则借用了李贺的意象,具备了语境上的奇异与幻灭感。而前面所提及的《立在地球边上》则是狂放的、远大的,也是有力的语流。
再次,超现实主义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这正是洪迪先生在《诗学》中的一个重要发现:“当代大诗人=超现实主义+本土文化”。他认为,诗的本性、本质是现实主义的,更是超现实主义的。好诗往往以超现实的形式,更美更深刻地掌握现实。当然,我们这里的“本土文化”是取其广义,包括地域文化、民族形式和心理积淀,甚至——集体无意识。洪迪先生近年的诗篇,有其抒情基点和飞扬高度,那就是在超现实氛围笼罩下的“地域文化”,是浙江东南沿海,特别是台州“山海之间”的文化元素,包括往昔游历、家族往事、个体命运和日常事物。洪迪先生的“本土文化”,是将现实主义的特质、日常性和奇异性,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赋予其神奇的超现实性,变形与嵌合,还带上某种程度的灵性与神秘。
故而在他的诗歌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既敦厚又灵动,既寻常又奇特的张力,给予我们“思与诗”的折射。“思”是沉思,“诗”是预言,都在感知与思考的框架里尽情舞蹈。他的《石塘箬山天后宫》《风帆》是这样的“超现实”,又动感十足,而他的《山海之间》则是一部诗歌的地方志,语言的山海指南,也是诗人的袖珍心灵史。这里有寒山、拾得和郑虔(广文)先生的逸事与传奇,也有儒释道三教创始者的懿言大德,奇异行状,更有山川地形和寻常事物,特别是底层的生存状态,编织成一个叙事框架,一个人世间“好的故事”。值得指出的是,洪迪先生在近期创作中,总是将自身生命历程嵌入叙述之中,并做了反讽、自嘲或旁白的处理,这是他早年创作中并不常见的。这一点在《山海之间》这首诗中尤为彰著,《头门港》也毫不逊色,在《天台云锦杜鹃》中也有别出心裁的体现,那句“二千尺青铜老干横枝撑铁”,就是一种自况,“夫子自道”是也。
最后,洪迪先生对历史题材的处理,体现了一种再现能力和深刻洞见,也展示了他将历史意识、现代性和戏剧性融合在一起的能力。即使是神话传说的诗性书写,也运用了鲁迅《故事新编》中穿越时空与赋予新意的手法,获得一种富于启迪性的穿透力。这些诗歌特质在《韩信》《樊哙》,特别是《逃浴》《庖丁解牛》中,都有很好的体现。于是,我们在《庖丁解牛》领受了诗意的哲学,隐性的思维,和充满巨匠意识的“元诗”:“噢!得告诉你一个猜想的小秘密/这位为文惠君表演的解牛庖丁/恐怕就是辅佐商汤得天下的伊尹/或者是跟黄帝探讨养生长寿的岐伯/或者即为骑青牛出函谷关的老聃”。在《逃浴》中,读者会感受到诗人对“帝俊薰衣草一样的娇妻”“天地间最仁慈的伟大母亲”如何“沐浴十个儿子”的故事,竭尽摹写之能事,不仅有画面感,还有感官上的渲染。最后笔锋一转:
个个逃避沐浴,一齐脏兮兮跑上天顶
各各耍出一副人莫予毒的霸王威势
海枯石崩。大地四处咧嘴砺牙
禾焦。木枯。猰凿齿九婴大鹏野猪毒蟒
死亡呈滔天洪水狂涛。浩浩汤汤
帝俊惊惶失色。赐神人或人神后羿
彤弓羽箭,去下界火速平乱
于是,后羿上射九日,下杀众凶于洞庭
桑林凶水之上或畴华之野。大地重归安宁
最终只剩下一个儿子,也就是唯一的太阳,“从此,尽心仁慈的羲和更加仁慈尽心/日日拉住遗下的唯一儿子清洗更清洗”,读到这里,我们都会发出会心一笑:从十个儿子逃浴,到“后羿上射九日”,原来这就是“太阳诞生记”。
洪迪先生漫长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之路,用他当年在《雨后新叶》里的话来说,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但愿多带上几双草鞋。”而今,我们看到他当年播下的愿望种子,都长成了参天大树。上面所分析的近期诗歌,则是收获之上的收获。因为我们在他的诗歌中,看到了他对茫茫人世的独特指证,对自我和他者毫不留情的解剖,对人性、灵魂和情感的揭示,以及穿透生与死、存在与虚无的巨大勇气,他的悲天悯人胸襟,这里有他的《无题》,也有《在一条熟悉的老街上》。他在《天台云锦杜鹃》中的结句,则是这一特质的确证:
水中月。我来几度,终归缘悭一面
不可即。即见着了,又当如何了结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