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如烟(外一篇)
2024-12-31郭彦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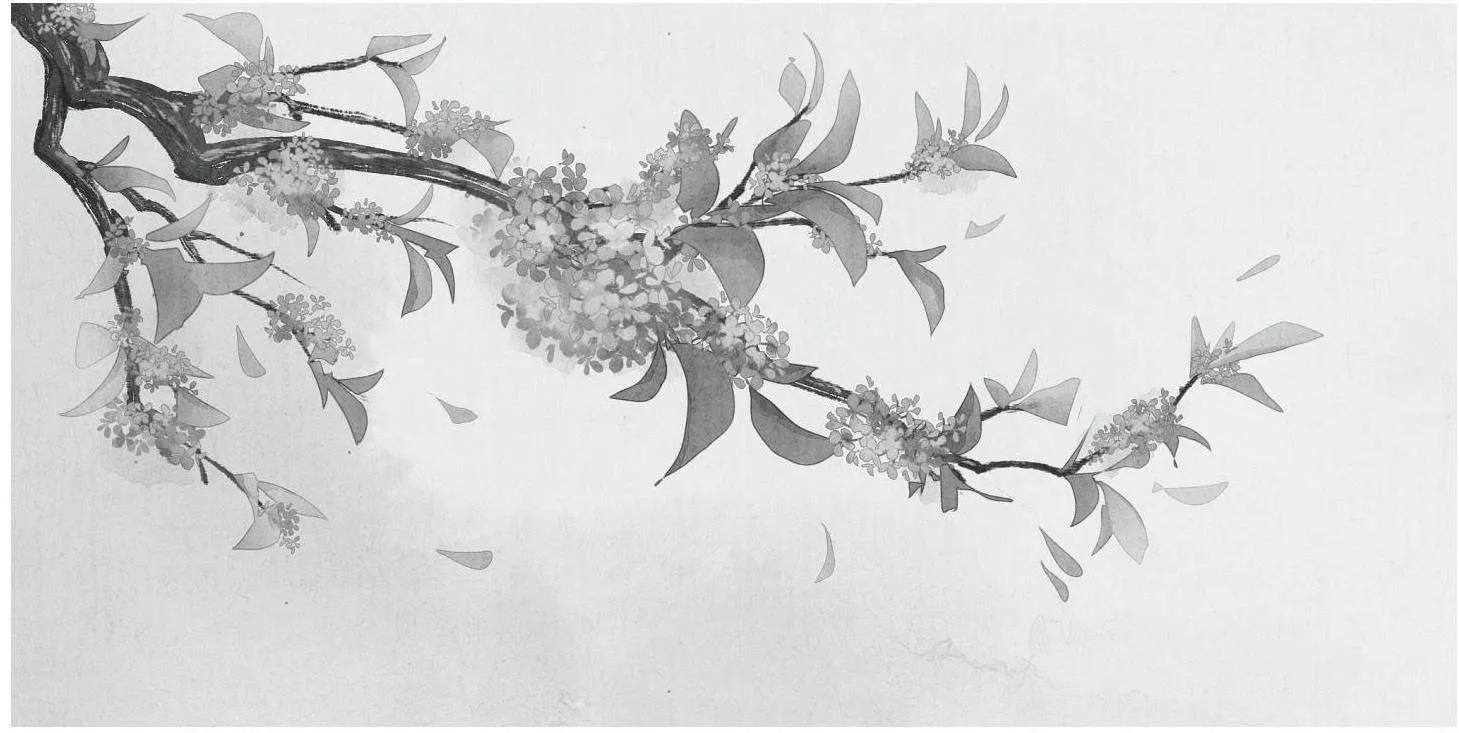
初二那年,我们班突然要和另一个学校的班级合并。这个学校离家七里多路,没有宿舍,需要每天早去晚回。
到了新班级,班主任韩老师第一堂课就宣布我做副班长,理由是我本来就是班长。韩老师宣布完了,也不管我愿不愿意,就晃着微驼的背开始讲课了。
两个班级合起来六十几个同学。关键是这边原班级有几个人高马大、满头白发的留级学生,初来乍到,他们一副足智多谋的派头,看着都打怵,还想让我在他们面前逞能,不知道班主任安的什么心?反正我是慌张的。
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有英语课程,对外语的认知也有限,英语课上,魏老师在上边挖空心思地讲,同学们在下边稀里糊涂地听。当挨个让大家站起来读单词短语时,结果都跟一根根木头似的竖在那里,啥也读不出。又瘦又矮的魏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犹如不认识自己的学生,两个无辜的大眼珠子使劲骨碌着,轮到我时,总算磕磕巴巴地读完坐下了。结果以后每堂课上,英语老师不再自找难堪,只喊我一个人起来读。时间长了,我觉得很没意思,有一次就拧巴起来,站在那里不肯读。课堂上顿时安静极了,大约过了一分钟或十分钟,从未有过的漫长后,魏老师又从讲台上走下来,在我身边站着,教室里依然安静。我低着头,不知道魏老师的大眼珠子是否又遭遇了不测,终于听见他叽里咕噜说了句什么,没宣布下课,然后自己走掉了。等我再抬头的时候,看到韩老师在窗外用恶毒的眼神瞅着我。
下午放学后,我就被叫去了办公室。韩老师倚在桌子那边用驼背对着我,英语老师正襟危坐在桌子这边,面前是摊开的英语课本。我知道今天不把英语课文读出来,是不会罢休的。就装模作样跟英语老师学了一会儿,然后读了课文……磨蹭够了,韩老师转过身来一边收拾东西一边面无表情地说,好,你可以回家了。以后没学会就来找魏老师补课……
生性懦弱的我,不敢对韩老师哼一句,只是偷偷地瞪了他一眼,然后咬牙切齿地把英语课本卷成筒状,紧紧攥住,巴巴地走出了办公室。下雨天,骑着自行车回家,路上滑腻腻的,眼睛被雨水浸得生疼,蹬着蹬着,忽然连人带车蹬到了路边沟里。水没到脚面,沟其实不深,但是又陡又滑,怎么也爬不出来。天色渐渐暗了,路边的苞米地里发出一阵阵奇怪的声响,就是没有行人路过,我像个失魂落魄的猎物,窜不出逃不得,就杵在泥水沟里呜呜地哭。
终于有人把手伸过来了,把我给拉出来,把自行车给拽出来,然后,甩甩手,大踏步走了。
是汲同学,我们班的。听说他几岁就没了亲妈,爸爸带着后妈去了东北,扔下他靠爷爷拉扯着。爷爷没有什么收入,身体也不好,爷儿俩的生活真是困难重重,可是,汲同学硬是撑住了。此时此刻,我很想知道,那一个个严寒酷暑或者狂风暴雨的日子,为啥都阻挡不了他上学的步伐?今天他又为啥也这么晚才回家?但是,我当时实在太窘了,啥也说不出口,只推着自行车抽抽噎噎地跟在后边。汲同学背着破旧不堪的书包走得飞快,一会儿就看不到了。
终于狼狈不堪地回到家时,家人们正等得焦急,我扔下车子和书包,哭得稀里哗啦……那时候大姐和我是我们家里的两个极端。除了父母,大姐对家庭的付出最大,脾气也最大,我在家里最小,最没用,可是最能哭,我不会声嘶力竭地那种哭,那样哭,我会晕过去,只是哼哼唧唧地哭,软硬不吃地哭。这次哭完以后,还是不过瘾,又没有其他法子,只有不理人、不上学的伎俩——随便别人怎样看吧,反正我是宣泄过了。
那时候还没有网游、旅游什么的概念,家里连电话都没有,家务活干不了,不上学也没啥好玩的,根本不开心。第三天,韩老师就来家了。我母亲四十好几的人,做了二十多年的妇女工作,好歹也有些知事晓理,那时却像个小学生似的被韩老师数落得面红耳赤。轮到跟我说话的时候,韩老师的口气软了一些,他说,脸皮子薄不要紧,就是别做“娇气鬼”……甚至把“娇气鬼”三个字轻飘飘地说了一次又一次,直把我说得心惊肉跳。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这样不留面子的揭底,第四天,我就灰溜溜地上学去了。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的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思想境界。他们比较信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或“行多少春风,下多少秋雨”等,但是行了春风却没有秋雨的时候,他们就用“吃亏人常在”之类理念聊以慰藉。那时候,生活上已经能够吃饱穿暖了,如果我们再安安稳稳地长大成人,他们就心满意足了。我的父亲还用他的一技之长加上他的宽厚仁慈,在当地成了彻头彻尾的大好人。总之,在那个风气拙朴的小地方,我们没有遇上什么牛鬼蛇神,父母活得很体面,我们也跟着无忧无虑。有个从大城市下放来的田老师,跟父亲成了至交。在昏黄的灯泡下或者静悄悄的天井里,他们总有聊不完的话题。我的大哥,生性顽劣,无缘无故就想逃学,父母说他,爱听不听,再说多了,就跑到我爷爷那里装可怜,我爷爷一手拉着孙子一手拽着拐杖来了,我爷爷不用说话,站在我家大门外,用眼神剜一下,事情就解决了。一来二去,我父亲就由我大哥去了。那个田老师却急了,经常满胡同找我大哥,找到了就设法把我大哥背去学校,连哄带吓让大哥留在课堂上,放学了再给背回来。
且说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那儿的学习氛围仍然松松垮垮的。上体育课时,我有时去操场应付一下,有时就跟几个同学跑到学校后边的树林里玩,老师也不当回事。师资配备不足,一个老师经常兼着好几门课程,我们班到期末时,史地生等课程只学到一半。中考时,有几个留级的,包括汲同学,勉强考上高中,应届生则全军覆没。我除了英语考得还行,其他的一塌糊涂。
都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慈父多败儿……这些道理,我后来终于信以为真。因为,我们家里兄弟姐妹几个,就大哥和我最没出息。
再后来,我那个打小就苦哈哈的汲同学终于一飞冲天,直到中纪委某大人物身边做事。他的爸爸在儿子功成名就之后,就带着汲同学的后妈回来了。汲同学此时既成大人,自有大量,不但厚待生父后妈,还对附近的父老乡亲恩惠有加。他每次荣归故里,因为身份特殊,都有地方部门款待,普通百姓无法见到了。
话说某日,我又被生活中的XYZ折腾得头昏脑涨,实在懒心断肠了,就跟一群狐朋狗友在微信群里胡诌八扯。明明就是一群乌合之众,穷酸道迩的群主,偏偏给群冠名“精英群”。一个昵称叫作“爱国者”的,风尘仆仆地进群了,点开老人家的头像去看,一张皱巴巴、黑乎乎的脸上贴着一枚鲜艳的五星红旗,他先噼里啪啦给“精英群”搬来了几个大链接,然后用沙哑得吓人的语音朗诵:“……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我们正聊得山穷水尽,终于有了新话题。老人说自己小时候当牛做马,吃不饱穿不暖,这条命都是新社会给的,可不敢蝇营狗苟,后来当兵在战场上九死一生……如今都土埋半截了,好歹攒了几万块钱,每年给贫困地区捐钱捐物……老人家的自我表白和表达能力,引出了一串串赞美的表情包,老人家又开始吭哧吭哧给我们普及爱国知识。我有些懵圈,心想,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嘛,我区区一个陋庸之辈,也配思考如此宏大之命题?老人家说,“爱国”,是一个动词,不是一个名词,是一种表现,不是一种形式……萎靡不振的群风好歹被激活了,有人甚至慷慨激昂,有人则说,这是一个和平的年代,虽然无须用肉躯堵住枪眼或用双手托起炸药,可是“爱国”还是“不爱国”,既不像勾三股四弦五那样边角分明,也无法用香农指数来判定是非,拿什么来证伪……
就这样七嘴八舌聊得天昏地暗之时,忽然有人加我微信,同意后才知道,对方竟然是韩老师!他说是从同学那儿找到我的微信。
我这个曾经被汲同学拉出泥泞的“娇气鬼”,当年中考失利,恨不能跟所有的老师、同学断绝来往,免得“一想起往事,梅花就落满了南山”,然后接受了营营役役的打工、因陋就简地活着的现实。通常,一个不争气的人,就约等于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在漫长的无聊的日子里,终于撞得皮糙肉厚之后,“娇气”自然就不了了之了……有一次自以为是去申请一个社会组织,人家要求提交个人资料,在学历一栏,我一时冲动填了“文盲”,结果可想而知。这个故事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后来偶有混得风生水起的同学再联系聚会,我酸溜溜地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开啥玩笑,咱是个文盲,哪来的同学……
现在想来,我的那些囧事儿在韩老师那儿应该不算什么。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迎来送往那么多学生,真正不负如来不负卿而修成正果的“桃李”,毕竟是少数。其实大多数“歪瓜裂枣”们,他们未必都是差等生,他们也曾开花,也曾有过鸿鹄之志,只不过,“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是吧——用这些虚头巴脑的碎碎念把自己哄骗了一番,然后鼓足勇气去跟韩老师聊天。
韩老师已经退休了,在省城儿子家居住。老了的韩老师更像一个老夫子,锋芒不露,慈悲有加,他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他说,想老家,想同学们,想春节回家时,看看我长什么样了……我一边喏喏地回应着,一边想象“韩老夫子”的模样,如若视频或者在老家这边见面了,那时,我又该如何面对他老人家……
这一天,忐忑着过去了。睡到半夜,梦见去考场的路上,遭遇各种磕绊,好不容易进考场了,做数学卷子时,不是钢笔坏了,就是把一道简单的完形填空填得乌七八糟……抓耳挠腮地就急醒了,然后躺在那儿辗转反侧……黑暗中,感觉世界真的是不动声色地把我挤了又挤……尤其那些我以为躲过了的往事,就像一颗早已出膛的子弹,兜兜转转,对我的追杀,终是没有放过。
又是中秋月圆时
又是一年中秋节。终于盼到了假期,收拾妥当准备启程回老家时,老同学忽然来电话,说是多年未见的一个发小从国外回来了,几个要好的朋友已经等在酒店,知道我不会开车,已经安排另一个朋友来接我。
一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从酒店回来,已是暮色四合,经过小区公园时,望见那轮明月,正挂在青幽幽的天上,月色溶溶,掠过高高低低的楼宇,透过香樟树的枝叶,斑驳倾洒着。就在这树影月色下,我发现怪老头一动不动地坐在香樟树下的长条椅上,椅子的另一头躺着他的胡琴。他花白的头发依稀可见。
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今年的秋天,时常阴雨绵绵,夏日的余温就在这一场场雨水之后很快离去。凉风瑟瑟,曾经热热闹闹的公园里,各种植物不再厚翠叠荫,遛弯闲聊的人也越来越少,只有这个怪老头,仍是风雨无阻天天来公园。怪老头曾经把一曲《赛马》拉得惊心动魄,可是今天,他没有要拉琴的样子,只是呆呆地坐在长条椅上。我经过他身边跟他打招呼,他甚至没反应。
怪老头在我们这个老居民区里是有些名声的。他是东北人,父母早逝,一个兄长在国外,老家里已经无牵无挂。在我们单位,他的业务能力超强,拿着普通员工的薪水,干着高级工程师的活儿。他还有个与众不同的地方:不肯使用智能手机,更不用说微博、微信、钉钉、支付宝、抖音等那些劳什子,一来二去就搞得有些孤立。本来姓“管”的老头儿,叫来叫去就被叫成了“怪老头”。新冠疫情时,别人都从网上抢购口罩、酒精、板蓝根等,怪老头家里啥也没有。儿子或朋友送给他几个,他也不用,好在他与老伴安然度过了。年末,怪老头索性办了病退告老归家。
赋闲在家的怪老头更加看淡一切了。小区里的大人孩子,他都能合得来,高兴的时候就像个嬉笑怒骂的老顽童,无聊了就半闭半睁着双眼将一把老胡琴拉得天昏地暗。怪老头的两个儿子先后考上名牌大学,大儿子毕业后随大伯去了国外,小儿子留在北京,有一张戴着博士帽的照片,跟大明星一样帅气风光,被怪老头揣在衣兜里,时常拿出来看。怪老头把他家某些美好的事情都归功于家里不用现代通信设备。
几年前,怪老头在北京的小儿子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怪老头更是乐得不行。怪老头的老伴被接去北京照顾孙子孙女,怪老头不习惯北京那边拮据的小蜗居,执意留在自己空敞的大房子里。生活上曾经完全依赖老伴的怪老头,忽然之间成了孤家寡人,平日的饮食起居就失去了平衡。没有了照顾,也没有了管束,早年因为身体原因被迫戒掉的烟酒又捡起来了,当他在小区公园里如痴如醉地拉《二泉映月》的时候,嘴里叼着的香烟就会随着曲子的高低上下摇摆……远在北京的老伴自然放心不下,每次打电话对老头儿千叮咛万嘱咐,老头儿嘴上答应着,并不照做。儿子儿媳们经常给老头邮寄一些吃穿用品甚至外卖快餐,老头自己用不完时,会分给左邻右舍。那年春节,孩子们因为疫情不能回家过年,据说怪老头从快递员手里接过他们寄来的大小包裹,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管大爷,管大爷”,我从老头儿身后转到他面前:“回家吧,这样坐着会着凉的。”我能猜出,此时此刻,他的宽敞的大房子里,除了堆着一些包裹,空无一人。
老头儿抱着双臂,还是没有吱声,朦胧中看不清他的表情。之前他的儿子想通过我微信跟老爸视频聊天,老头儿不接受。今天,中秋节,我不知道老头儿的儿孙们为何没有回家。我打开手机看他儿子朋友圈,看出来生活挺有滋有味的,也有可爱的双胞胎孩子的照片,我把手机凑到老头儿眼前,老头儿叹了口气,伸出手接过了手机。他戴上眼镜,把我手机里他的老伴、儿子、儿媳、孙子们的照片和视频,看了又看,还看了我老家发来的视频,我们一大家子老老少少,已经备好了一桌子饭菜等着我……我趁机鼓动老头儿把他儿子给他的手机装上应用,随时随地跟他远方的亲人视频聊天……老头儿不再固执,同意明天就让我帮他弄手机,然后拎起他的二胡,晃晃悠悠回家了。
这时候,我网约的出租车司机已经等得不耐烦,催促我尽快上车,他说干完这一单他就收工,他的老婆孩子正等着一起回他们的老家……
出租车穿过灯火阑珊的市区,上了高速路。归途漫漫,大大小小的车子形成一泻千里的车流,我们的车子忽而被裹挟着,忽而被堵住,司机师傅隐忍沉默着,他打开交通广播,让欢快的乐曲掩盖外边徒劳的鸣笛声。而天上那轮月亮,就那样光色迷离着,亦步亦趋地追着我们。它一定知道这漫长的路,来来回回已经发生的故事,它也知道,这漫长的路,还要反反复复发生更多的故事。我想,路的那头,那轮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永远清朗如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