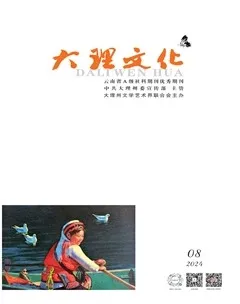祖母
2024-12-31修瑞


父亲意外过世五年后,母亲终于累了,一个人去了很远的地方,再没回来。母亲走后,当时只有5岁的我和长我3岁的哥哥搬去了祖母家里,与祖父母相依为命,一住就是18年。时至今日,我仍常常感慨,自己终究没有因为那18年,被日子的艰辛与难堪鞭打得怯懦自卑,也没有因此愤世嫉俗或者自甘碌碌,甚至可以始终坦然并微笑着与生活对视。之所以能够如此,因为有祖母在。她祖籍山东,因为闯关东比较早,几乎没有留下山东口音。她是小脚,在我的印象里,她的脚比我的手掌大不了多少,所以我怀疑她曾裹过小脚。她相貌普通,属于走在人群中很难被一眼认出来的那种,谈不上好看,但也绝不显丑。就是这样一个相貌普通且满口辽东方言的山东小脚老太太,硬是带着两个年幼的孙子,把苦日子过出了许多幸福的滋味,过出了一个又一个即便多年以后仍然值得回味和追思的温情。
一枚“戒指”
有一天,我在梦里梦见,原来那根稻草是一枚顶针。
那是一枚银灰色的顶针,是银制的,也或许是铝制的,但肯定不是钢制的,因为它可以被反复平展和卷曲而不折断,柔韧性很好,不像钢材那样宁折不弯。我对金属材料缺乏辨识力,就好像有脸盲症的人看谁都分不清记不住。拿一块磁铁可以轻易判断出一个物件是否是铁制的,这个道理我本是知道的。但磁铁无法分辨出一枚顶针究竟是银制还是铝制。我的理性告诉我,那枚顶针是铝制的可能性更大,或者基本可以确定。我实在无法想象,它的拥有者,一个清贫的女人,一辈子不曾拥有过一副银制手镯,或者项链,或者戒指,甚至是一枚银制耳钉,却肯买下一枚足以打造成一条项链或者几枚戒指的几乎没有审美价值没有浪漫气息的“银顶针”。但是,它应该是铝制的,我确定。
那枚铝制的顶针是祖母的。我见她右手中指上戴过它。她日常里是不戴它的,只在做针线活的时候才戴上。也不是做所有的针线活都会戴,比如缝纽扣或者补袜子就不戴,而是在做比较吃力的针线活的时候才戴上,比如缝被子或者做鞋子。它在她的手指上松紧刚好,轻轻箍在中指的第二根骨节上。其实它可以继续向下,滑落到第三根骨节上,那样看起来会更美观,更像是其他女人戴在手指上的戒指。但它没有继续下滑,她也没有允许它继续下滑。滑下去就成了戒指,停留住则是顶针。我猜想,对于一只勤劳了大半辈子,并且已经养成了勤劳习惯的手来说,一枚实用的顶针比一枚奢侈的戒指更有意义。她戴着它,用它周身均匀密布的圆形凹坑中的一个对准刺穿鞋底的穿有糙麻线一端的钢针,然后右手用力向前顶,左手捏着穿透鞋底的针尖一端使劲往外拽。多年以后,我操着针线缝补开了线的鞋子的时候才体会到,这一顶一拽,虽也费了不少力气,但终究比起单一的拉拽轻松了许多。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在农田里耕地,有时候牛来了脾气,任凭牵牛人如何拉拽,牛就是不往前拉犁,非得有人朝牛的屁股上拍上一巴掌,牛极不情愿地翻个白眼,才又继续往前拉犁。这和顶针的原理虽是两码事,但终究都是一顶一拽的事情,方向上形式上是相似的。
我对顶针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厌恶的,就好像我的密集恐惧症并不是天生的一样。至少在祖母戴着她的那枚铝制顶针给我做第一双千层底鞋的时候,我对它并不反感。我穿着祖母用巴掌丈量我的脚掌做好的鞋子,把玩那枚铝制顶针。它看起来是那样的粗笨,它套在我的中指上,径直滑落到了第三根骨节,就好像我身上总也套着的哥哥穿小了的衣服,松松垮垮。那些时候,日子是无聊的,村庄是无聊的,人在无聊的日子无聊的村庄里,习惯干着无聊的事情,并在那些无聊的事情里咂摸一些比无聊稍微有些滋味的东西。我盯着那枚铝制的顶针,一圈一圈数着上面的凹坑,数了三遍,三圈42个,三圈41个,总共249个凹坑。好险!如果再多出一个凹坑,就成了二百五。这差出来的一个凹坑,便成了我在无聊的日子无聊的村庄里咂摸出的比无聊稍微有些滋味的东西。我大约是唯一一个发现那枚铝制顶针制造者耍了那样一个数字小聪明的人。
祖母为我做好第一双千层底鞋之后,我除了发现那枚铝制顶针制造者耍了一个数字小聪明之外,还发现了顶针上有四个凹坑被钢针的屁股坐穿了。被撕裂的孔洞边缘参差不齐,向内翻出新鲜的金属茬口,像是被某种钝器戳开的伤口,血肉淋淋。我的确在一处孔洞边缘发现了一丝血迹。祖母用顶针用力顶刺穿鞋底的钢针的时候,有那么一次突然缩回了手,那种缩回完全是下意识的,嘴里发出的“嘶嘶”吸气声急促而响亮。少时,她用左手转动右手中指上的铝制顶针,换一个凹坑重新顶鞋底上的钢针,她鼻腔里传出“吭吭”发力声,头上的青筋凸起,手臂微微抖着。我想,那血迹应是她发出“嘶嘶”声的时候留下的。我不知道钢针坐穿顶针的凹坑并坐进祖母手指的时候,拔出钢针后的伤口是否也如顶针上留下的孔洞边缘一样,参差不齐中透着血红。那一定很疼吧?那伤口少说也要三五天才能愈合吧?可祖母只是“嘶嘶”了两声,几秒钟的时间,伤口似乎就愈合了,然后像是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一样,继续为我做鞋。
其实,那时候我不但不讨厌祖母那枚铝制的顶针,甚至还有些喜欢。我喜欢它,是因为喜欢祖母戴着它为我做的千层底鞋子。我穿着祖母为我做的第一双千层底鞋子去村子南面,比村子南面的铁匠铺还要以南的学校,我的鞋子在整个学前班的教室里独一无二,我在同学们或惊奇或艳羡的目光中高昂着头。
我是多年以后才开始厌恶那枚铝制顶针的。我厌恶它,是因为厌恶祖母戴着它为我做的我曾经引以为傲的千层底鞋子。那鞋子仍然独一无二,同样的款式,同样的材质,同样的缝制手法,无非是鞋码大了一些,它周身令人惊奇与艳羡的光环却不知从哪一天起消散得无影无踪,然后冷笑、调侃与讥讽像黑夜一寸一寸稀释日落后的天空一样,直到黑夜变得浓稠,稠得不再流动。有同学背地里给我的千层底鞋子起了个“豆包大傻鞋”的外号,继而又把“鞋”字去掉,称呼我“豆包大傻”。他们是背地里那样说的,但这种背地里,或许仅仅是背着我一个人。我讨厌那个外号的时候,便又对脚下的祖母做给我的鞋子生出了厌恶,一日胜过一日。它是那样的丑陋,没有别的颜色,没有一丝花纹,团团鼓鼓的,甚至左右脚不分,看上去还真像是一对豆包,连颜色都像。我厌恶那豆包一样的鞋子,于是又牵出了对祖母做鞋子的时候戴着的那枚铝制顶针的不满。是的,祖母每次做鞋子,都戴着那枚顶针。若不是因为有了那枚顶针,便不会有我脚下的千层底鞋子,也就不会有“豆包大傻鞋”和“豆包大傻”的外号。
我只记得那是一个周末晴好的下午,具体是哪一年哪一月已经记不清了,但肯定不是冬天,因为记得那天我在太阳底下出了一身的汗。那个下午,祖母在炕上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趁着祖母睡下的时候,偷拿了那枚铝制顶针,跑到离家100多米以外的村子西面的河边。跑出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几枚细铁钉,拎了一把小铁锤。我在河边找了一块大石头,把祖母的铝制顶针用力掰开,平展,然后一手捏着铁钉,将铁钉的钉尖顶在顶针的凹坑里,另一只手攥紧铁锤,一锤一锤敲击铁钉。我花了大半个小时的时间,终于把祖母的那枚铝制顶针打成了筛子。200多个被铁钉击穿的孔洞,密密麻麻,张牙舞爪,向着同一侧翻出新鲜而锋利的金属茬口,鲜血淋淋。
200多个孔洞密集在一块不足五厘米长、一厘米宽的铝片上,它们像聚在农村老式粪坑里的蝇蛆一样,朝着粪坑的上方张嘴呼吸。我在将平展开的被打成筛子的铝片重新复原成顶针的时候,胃液毫无征兆地突然上涌,绿的菠菜,白的豆腐,连同或整颗或嚼碎的米粒,中午吃下肚的饭被吐出了足有一大碗。
那天以后,祖母再没给我纳过千层底鞋子。她本可以再买一枚顶针,其实那枚被我打成筛子的顶针原本已经有了十几个孔洞,理应被淘汰掉了。可是祖母没有再买。大约也就是打那天的呕吐起,每次见到有密集特征的东西,总觉得头皮发麻,胃里翻江倒海。
多年过去了,我对顶针已经不再厌恶了。当初厌恶它,是因为厌恶祖母戴着它给我做的鞋子。后来祖母不做了,后来祖母走了,后来因为听一位歌者唱了一句“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便不再厌恶那双“豆包大傻鞋”。再后来专门逛了几家卖老北京布鞋的店,买过两双,踩在脚下,总觉得不比当年踏实。
从那以后,我曾在她生前用过的衣柜暗格里翻找过那枚铝制顶针。我知道她没有把它扔掉。自那次我把它打成了筛子以后,她就将它收在了那里,用一块白色绣了桃花的手帕包住。她喜欢桃花,之所以喜欢,因为桃花谢了,会结出桃子。可惜,祖母去世后,我的翻找一无所获,连那块白色绣了桃花的手帕也没有找到。许是家人收拾祖母生前用过的衣物时,将它一并烧掉了。只是,我更愿意相信,是祖母走时,将它一并带走了。那时候大家只顾守着躺在停尸冰柜里的她伤怀,却没有谁留意到,她的右手中指上戴着那枚被我用钉子和铁锤打成筛子的银灰色铝制顶针。她把它戴在了第三根骨节上,而不是第二根骨节。是的,戴在第三根骨节上,那顶针就成了戒指。
你光着脚,在我的梦里
去年盛夏的一个早晨,胸前突然起了一块钱硬币大小的一小片浅红色水泡。我以为是夜里被哪个不知名的虫子咬的,没怎么在意。到了下午,后背对应的位置也起了一小片同样的水泡,而且明显感觉整个左侧肩膀疼得厉害。
去医院检查,说是带状疱疹。
按照大夫的叮嘱,我每天都按时吃药。一天三顿,每顿都是一把西药加一碗中药,几乎再吃不下任何食物。可是连续服用了一周药,效果并不明显。到网上搜索相关病症,发现这种病竟然是由水痘等病毒引起的。我赶紧去中药店,买了些艾蒿回家煮水,然后用煮了艾蒿的水清洗病症处。不出三天,那些密集聚在一起的水泡都干瘪了,开始结痂。再过三天,便全然看不出那里曾有过什么异样。
我之所以会想到这样一个土办法,是因为忆起了我的祖母,忆起她曾用同样的办法,帮我治好了水痘。
我的老家地处辽宁省东北部山区,祖母曾是我们村子里的一名赤脚医生。祖母第一次跟我说起“赤脚医生”这个名词的时候,我是拧着眉毛在听的。这个陌生奇怪的名词,让我浮想联翩。一身白大褂,戴着白色的口罩和白色的帽子,手里拿着白色的注射器,却赤裸着双脚的医生。没有鞋子,也没穿袜子,是赤裸裸光着脚。那是怎样的一双脚啊?因为需要常年奔走在山野乡间的石子路上,厚厚的老茧,被岁月侵蚀开裂,透着血丝和每走一步都针刺在心眼儿里的疼。
那是一双女人的脚。
而事实上,我从未见过祖母赤着脚走路。她是穿鞋的,也穿袜子。那么既然穿鞋子,也穿袜子,为什么叫“赤脚医生”?多年以后,我从一本书中知道,“赤脚医生”是没有正式编制的土医生。那时,祖母是我们村唯一的医生。
曾听祖父说过,多年前,村里有一个患了严重肝病的人,县里的医院已经通知他回家准备料理后事了。后来他来找祖母,本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不想,祖母不知道去山里采了些什么药回来,竟用她的土办法,花了一个多月时间,给病人延续了五年寿命。
我本以为,祖父向来喜欢夸大其词,在祖母救治肝病晚期患者这件事情上,多半是有不实的,全当听传奇故事,不可当真。
不过,祖母常常进山采药却是真的。她有一本中草药书,里面有各种草药的彩图和草药习性及功效。她几乎认识书里所有的草药,她知道哪个时节适宜采摘哪种草药,她也知道去哪个地方采哪一味药能治哪一种病。
祖母常常拎着一个用杏树条编制的两尺多长、一尺余深的筐,筐里放一把手镐,再带上一壶新烧的热水,便出门进山去了。半日或者多半日,又满载一筐不知名的野草或者树根回来。祖母说,那些都是草药,能治不同的病。
祖母也自己种草药。她在房前屋后的园子里种了许多草药,我认得出的有龙胆草、细辛、黄芪、马兜铃和三七,还有七八种至今也叫不出名字。那是祖母的百草园。当然,我觉得其实村子四周的大山都是祖母的后花园。她知道哪里有哪种草药,她随时可以去取来,就像在自家的园子里摘菜一样的简单熟稔。
有一年冬天,我在结了冰的河面上玩,不小心掉进了冰窟窿里,湿透了全身。因为担心被祖父母责骂,我是悄悄溜回家的,换了一身衣服,把已经结了冰的湿透了的衣服泡在水盆里。祖母问我为什么刚穿了两天的衣服就要洗。我说走路的时候脚下一滑,刚好摔倒在了一坨新鲜牛粪上,弄脏了衣服。那是我拖着结了冰的湿透了的衣裤,在回家的路上想好的说辞。为了让这个说辞更逼真一些,我还故意守在河堤边的一个牛圈旁,等了将近半个小时,等到一头牛终于屙出一坨鲜牛粪,便赶忙用棍子挑起一些,趁牛粪冻结之前,抹在衣襟和裤子上。
因为穿着湿透了的衣服守在牛圈旁等牛排便等得久了,北方腊月的风怎么可能容许一个孩子对它的威严如此不屑一顾。是的,我被冻感冒了,很严重的那种。当天晚上,我便发烧了,烧得满脸通红,像一块烧红了的烙铁。邻家的孩子伸着胖乎乎的小手在我脸颊两侧,居然把我的脸当成火盆取暖。我也咳嗽,一声接着一声,咳得胸腔发疼。
祖母出了一趟门,不多久又回来了。她在厨房里生火,把火烧得很旺。很快,整铺炕都热了起来。我能感觉到热气从炕面坚硬如石的黄沙土里一丝丝一缕缕一片片地钻涌出来,带着一股焦糊味道。我贴在炕上的脚和屁股被烫得难以忍受,却仍然冷得发抖。我开始神情恍惚,我眼前的一切都仿佛在盛夏烈日炎炎之中,因为气浪对流,万物连同眼神和思想都在浮动和扭曲。
我神情恍惚的时候,祖母端给我一只沉甸甸的碗。那是家里最大的碗,大到几乎可以称其为盆。碗里盛满了黄色液体,碗底有些许细碎的沉渣。那些液体散发着一股奇怪的味道,那味道让我觉得想要呕吐。
祖母说,那些黄色的液体是泡了生姜的马兜铃水,能够驱寒止咳。
我神情恍惚,可是当我听到马兜铃这三个字的时候,突然就呕吐了出来。我清楚地记得,八六年版的《西游记》里曾有一个桥段,孙悟空就是用马兜铃给朱紫国国王治的病。而所谓的马兜铃,就是马尿。难怪那些液体呈现黄色,还带有一股难闻的怪味,可不就跟尿液一样。想到这里,忍不住又呕吐了起来。
祖母为了让我相信那些液体是草药泡出来的,而不是马的尿,去厨房取了刚刚用过的还湿着的马兜铃根给我看。我仔细闻着那些根的味道,大约确实和那些黄色液体的味道差不了许多。经不住祖母再三劝说,我闭着眼猛喝了一大口。一股浓郁得让人忍不住反胃的苦味迅速在口腔里扩散。我感觉鼻腔里呼出的气都带着苦味,甚至感觉到我血管里流着的每一滴血都捏着鼻子拧着脸,嫌弃那种苦味沾身。
我不想再喝,一看到那些黄色液体,就禁不住作呕。祖母大约早就猜到我会有那样的反应,提前准备好了勺子和白砂糖。她在我喝下第一口黄色液体之后,拧着眉毛坚决不肯再喝的时候,舀了一勺白砂糖进我的嘴里。这就好像两军交战,战场就是我的口腔。双方不断厮杀,不断消耗。白砂糖的甜中和了黄色液体的苦,苦中泛甜,甜中含苦。
虽然我不喜欢那种黄色液体的味道,但终究止住了呕吐。祖母舀好了一勺白砂糖,不停地敦促我趁热喝下剩下的黄色液体。那是多么难喝的东西啊!
我在神志恍惚的状态下,一口药一勺糖,喝掉了一整碗煮马兜铃水。祖母在热得发烫的炕上铺好了家里最厚实的被褥,让我钻进被窝里。我躲在被窝里,我能感觉到汗水从我的每一个毛孔里往外钻。它们相互簇拥着钻出来,然后汇成一片。我神情恍惚,看着头上的灯泡晕着光,然后慢慢睡去。
隔日醒来,高烧退了,也不咳嗽了,像是根本就没病过一样。祖母说,我的高烧是在后半夜的时候退去的。但即便是退了烧,也还是要再喝一碗那种黄色液体。于是,我捏着鼻子,一口气又灌下了一碗汤药,然后恶心了一整天。
祖母用两碗马尿一样的汤药治好了我的重感冒。不过在我的内心里仍然怀疑,大约是我自身的抗体战胜了疾病,跟祖母的土方子没有多大关系。
那次重感冒之后几年的一个秋天,那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有一天早上,班主任打电话叫来一个孩子的家长,让他把孩子带回家,原因是那个孩子的胳膊上起了几个水泡。班主任表情很凝重,如临大敌。他在那个孩子离开之后不久,拿来一瓶白醋在教室里喷洒,然后又给每个孩子都发了两颗白色的药片,看着大家吃下。
然而,那一瓶醋和那些药片似乎没能阻止事情的进一步恶化。当天下午,又有两个孩子的身上冒出了水泡,甚至其中一个孩子的脸上也起了水泡。
几天下来,班里有十几个孩子都进了医院。最早发病的那个孩子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星期,还没有出院。后来我知道,他们患的是一种叫水痘的传染病。
大约十天以后,我也被传染了水痘。
我和其他患水痘的孩子一样,被班主任“请”出了教室。我沮丧着脸回到家里,趴在炕上,头晕,所有的关节都在隐隐发疼,浑身的不自在。我的咳嗽吸引来了祖母的目光。她的目光是那样的睿智,一眼就看出了我的病症。她去到屋外,搬一把梯子架在房檐。爬上梯子,年近七旬的身子看上去是那样的轻飘,又那样的沉重。她在梯子上缓慢地向上爬行,梯子在她既轻又重的身子下,微微颤栗着。
祖母爬上屋檐,是为了给我取艾蒿。那些艾蒿是端午时候,祖母带着我去山里采回,放在屋檐上晾晒干的。祖母说那些干了的草能有大用途。我不以为然。一捆干草而已。
我趴在炕上,蜷缩成一团。用被子将自己紧紧裹着,头脑里昏昏沉沉,却又睡不着。
祖母从屋檐取下十几根艾蒿,回到厨房,还是用当年给我煮“马尿”的铁锅,煮了满满一大锅艾蒿水。她搬出家里的一口棕色陶缸,将热水倒进缸里,兑了少许冷水。她伸手试了试水温,确定不是很烫之后,让我进到缸里,把整个身子都浸泡在水下。没过多久,祖母又端了一盆新煮热的艾蒿水进屋。她把手伸进缸里试水温。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身子,避开祖母伸进缸里的手。祖母许是觉得水温不够,又添了些热水。我眼看着她用一只手从缸里捞起几根漂浮着的艾蒿,然后另一只手向我的肩膀伸过来。我慌张地躲开,我不知道祖母想要干什么。祖母再次伸手,按住了我的左肩膀。她笑,笑得那样的暖,像浸泡着我的水一样的暖。
她用手里的艾蒿轻轻给我搓着身子。搓一会儿,停下手来,用缸里的水把艾蒿浸湿,然后继续搓。
那天,我泡了一个小时的艾蒿水,祖母则用艾蒿帮我搓了一个小时的身子。我能感觉到她搓动的力道越来越小,她在搓了十几分钟后,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她老了,已经年近七旬,在给我搓身子之前,帮我搬来了水缸,又添了大半缸热水。她耗费了太多体力,已经没有了力气。我看见有汗珠从她额头的褶皱间渗透出来,我听见她的呼吸声越发急促。我说我可以自己搓,我想让她去休息。她笑,却仍然自顾自地帮我搓着身子,像一位收藏家在悉心擦拭着她珍藏的宝贝。
祖母帮我搓完身子,等我从缸里出来,她拿来水桶,处理那些我泡澡用的水。我乏了,我说等我稍微休息一下,自己来把那些水倒掉。但还没来得及穿上背心,就倒在炕上睡着了。等我睡醒,祖母已经把那些泡澡水全部倒掉了,连泡澡的水缸也搬回了屋外的仓房里。
我睡醒了。觉得身子轻松了许多,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觉得我轻得能飘起来。张开双臂,微闭着眼睛。觉得自己就是在飘浮,身下的土炕就是天上洁白的云。我飘浮在高空里,瞬时间就闻到了祖母做好的饭菜香。
隔日,我身上的水痘全然消失了。我撩起衣服,挽起袖子,那些前一天鼓起的水泡,一个都没有剩下,甚至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这太让人难以相信。我的那些患水痘的同学,有人十几天都没有痊愈,我却只用了一个晚上。
我曾一度觉得,祖母大字不识几个,连药品的说明都看不懂,作为一名曾经的赤脚医生,大约就是滥竽充数,为了混一口饭吃。然而,她用她的土方子,几次治愈了我的病,这必然不是巧合。而且,祖母曾用一种满身花纹的毒蛇治好了邻村一个老人的轻度血栓,用十几只蟾蜍治愈了外乡一个风湿多年的老头儿。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
祖母过世后,我在收拾她的遗物时候,曾试图寻找她的那本草药书,可惜没有找到。我想,那本书大约连同她脑子里的那些土方子都一并去了。记得祖母晚年时候,曾跟我说过一些土方子,她是希望我能记住的。我当时听了,不过只是装出个样子,并没有在意。我想既然祖母有兴致,终究不好扫她的兴。这是如何值得惋惜的一件事情。而今,偶尔在梦里回到过去,大多还是梦见祖母用艾蒿为我搓身子。她赤着脚,在笑,她的笑在透过窗子的阳光里无限光亮。
被一种温度灼烧
祖母出殡那天,我一直都在。我是看着祖母被推进炼火炉的。我从工作人员操作的小窗口看进去,那烧红了的炉膛里,活了几十年的祖母,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卸下了这一世的皮囊,连同她的爱和思想,终于化成一缕青烟,从连接火炉的耸入高空的烟囱里飘上了海蓝色的天空。
没过多久,有人端着一个钢制的方盘从火炉那边走过来。他用铁夹子挑拣着盘子里的碎骨头,并指着那些碎骨说,那就是我的祖母。我知道,那确实就是祖母。但在情感上,我无法接受。她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人,她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是笑着的,而不是眼前那些还带有火星的杂着焦糊味的碎骨。
家人用一块红布将祖母的骨灰包裹起来,然后将她捧上了车。中途,我从家人那里接过祖母。她很轻,轻得几乎就只剩一块红布的分量。但我的手臂却难以支撑如此轻的分量。她压得我的双臂酸痛,压得我抬不起头来。隔着一块红布,我感觉到了来自祖母的温度。那是发自她骨子里的热,那股热像火盆里烧得正旺的炭火,炙烤着我的双手,灼烧着我的内心。
我是在祖母过世后的第二天上午,从外地匆忙赶回老家的。家人在电话里只说让我尽快回去,说是祖母情况不是太好,却并没有告诉我,她已经离开了。所以,等我回到村子里,远远地就望见家门口立起了一根细木杆,上面挂了一长串的黄纸。
我的心咯噔一下,傻眼了。我才知道,与我一起生活近20年的祖母,走了。
祖母是在北方最热的七月份过世的。为了不让她的遗体腐败太快,家人租了一个专门冷冻遗体的冰柜,将祖母平整地放在了里面。她安静地躺着,没有表情,没有胸口的起伏,也没有一丝体温。我跪在她身边,紧紧握着她的手。她是那样的冰冷,冷得俨然就是一块冰。我想,她躺在那冰柜里,一定是冻坏了。我想用我的手给她取暖,就像当初她用她的怀温暖我冰冷的手一样。可是她的手实在是太冷了,冷得直到我的手也冰冷透了,还是没能让她暖和起来。
这让我想起了十七八年前的一个深冬,和以往的冬季差不了许多。或者大约更冷一些。
那年入冬起,祖母便开始咳嗽。起初只是偶尔轻咳一两声,听起来并不要紧。原本以为是祖母烧火煮饭的时候,被灶台里冒出的柴烟呛到了,咳嗽一两天就会好。所以,大家都没在意,包括她自己也是。不想,这咳嗽拖拖拉拉竟持续了两个多月。气温降到零下二十几度的时候,祖母终于病倒了,发着高烧,咳嗽声一声接着一声。那咳声里掺杂着嗓子的沙哑和带血丝的疼。
祖母找来一只玻璃制的小罐头瓶,洗净,里面垫些废纸,作为简易的痰盂。她咳了一整晚,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睡下。我趁她睡着的时候,拿起她的痰盂到屋后的厕所倒掉。我发现她咳出的痰液里杂着一丝一丝的红,是血。
我当时是惊慌得不知所措的。我呆呆站在原地,看着那些被我倒掉的带血的痰液,脑子里一片空白。祖母显然是病得不轻,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将来该怎么生活?我还能继续上学吗?或者我还能不能每天都有一口饱饭吃?我在惊慌中被一种前途未卜的情绪紧紧包围。
祖母终于听从了祖父和我的劝说,同意找大夫来给她瞧瞧。我穿上祖母给我缝制的麻布鞋,飞一样地跑去了村里唯一的一个小诊所,去请诊所里唯一的一位大夫。我去到诊所敲门的时候,大夫还睡着。虽然时间已经是早上七点多了,但在北方的农村,尤其是冬季,人们睡到八九点钟也很正常。
大夫被我持续的敲门声吵醒了,拿着听诊器,一脸不爽地跟我回了家。他用听诊器在祖母的胸口、脖子、腋下反复听了好几遍,但我们必须相信这个大夫,至少村子里没有其他人比他更懂得看病。更要紧的是,只有他手里有药。
大夫说祖母肺里发炎了,给祖母挂了两个吊瓶。他叮嘱短期内不能让祖母着凉,不能让她呛到冷风,不能让她劳累,她需要多休息。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那天是星期五,距离我期末考试还有不到两周时间。我的衣服实在是脏得连我自己都看不过去,有一个多月没有换洗了。以往我的脏衣服都是祖母帮我洗的。不过那时候祖母病着,我着实不忍心劳烦她拖着抱恙之躯,为我洗衣服。我衣服不多,唯一能用来替换的一套,刚穿上一天,就被溅上了牛粪。一个淘气的孩子将点燃的爆竹插在了路边的一坨鲜牛粪上,而我刚好经过。所以,我被溅了一身的牛粪。
那天放学回家,老远就听见祖母疲惫且虚弱的咳声,一声接着一声,咳得人心神不宁。我把暖壶里仅剩的一点热水倒给祖母,看着她把水喝完,然后扶她躺下。
祖母大约睡着的时候,我脱下已经满是汗臭味的衣服,丢进水盆里,舀了一盆凉水,披一件祖父的棉大衣,然后端着水盆出了屋子。我不敢在屋子里洗衣服,我知道我洗衣服的声音一定会吵醒祖母。她咳得那样的难受,难得可以小睡一会儿,若我把她吵醒,对她来说实在是太过残忍。所以,我必须到屋子外面去洗衣服,即便屋外的气温已是零下二十几度。
说来惭愧。我那时马上就要小学毕业了,竟然不会洗衣服,或者说从来没有洗过衣服。我看着水盆里自己的脏衣服,突然就觉得无地自容。洗衣服总是需要一把搓衣板吧。我想起祖母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大约都会用到那个东西。我悄悄潜进屋里,找到放在卧室门后的搓衣板和肥皂,再蹑手蹑脚回到屋外。天空里飘着三五片雪花,风吹得糊在门窗外的塑料布起起伏伏,像被擂动的战鼓,呼呼啦啦不停作响。
我看着水盆里泡在水下的衣服,犹豫该如何洗。我犹豫的时候,浸泡衣服的水结了冰晶。它们看起来是那样的锋利,它们在我第一次伸手进水盆的时候,毫无征兆地一拥而上,像成千上万根钢针刺痛我双手的每一寸骨肉。我下意识地缩回手,缩手的速度快过我对刺骨疼痛的感觉。我开始后悔不该在那样一个天气里洗衣服。我完全可以先烧一锅热水,然后再洗衣服。或者我再坚持一段时间,等祖母的病好了,再把脏衣服丢给祖母来洗。
可是祖母洗衣服,难道就不会觉得冻手吗?
祖母还在睡着。她在睡梦中轻轻咳了几声,声音有气无力地在屋子里撞了几下墙壁,就散了。
风依然在糊窗的塑料布上呼呼啦啦说着风凉话,它在讥笑我的愚笨和临难畏缩。它讥笑,它的讥笑声中,杂着祖母嘶哑疼痛的咳声。
我没去烧水,我怕烧水的声音会吵醒祖母。我深深地吸气,再长长地呼出。像是站在百米起跑线上准备起跑的运动员,紧张调整着呼吸,用大量吸入的氧气刺激自己的神经。我没有数过我做了多少次深呼吸,大约不会少于二三十次吧。我终于鼓起了勇气,将双手插入结了冰晶的水中,捞起泡在里面的衣服,在搓衣板上快速搓动了十几下,然后再一次缩回了双手。我的手在抖动,抖动的频率和心脏统一着步调。我能看见指尖上的肉在跳动,每跳动一次,都是一次剧烈的疼。
我双手煞白,脸色煞白,死死盯着将我冻得没有了血色和体温的结了冰的水盆,犹豫该如何继续搓洗水盆里脏了的衣服。我正犹豫的时候,被一道毫无征兆的霹雳般的声音震惊。我转头,祖母就站在身后。
“谁让你洗衣服的!”
祖母一只手扶着房门的门框,一只手拎着一只木制的半尺多高的板凳。她的身子是摇晃的,站不稳,病得还很重。她只说了一句话,那是使出了全部的力气,从丹田里运气,喊出来的。她呐喊着,却仍然有气无力。
她蹲下身子,将手里的板凳放在水盆边,然后坐下,用一只手掀开身上紧贴身子的棉袄,另一只手抓起我的双手,放在她的怀里。我冰冷的没有了温度的手紧紧贴着她怀中温暖的肌肤。她温暖的肌肤因为我冰冷的手的刺激而下意识地向内收缩,然后有热流不断传导到我的手掌,再从手掌传递到全身。
我的手渐渐有了知觉,我从祖母的怀里偷走了许多温度,我看见她连续打了几个寒颤。
祖母把我赶回屋里,让我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复习功课去。我进屋的时候,祖母端起水盆也跟进了屋里。屋里没有生火,虽然比起室外要暖和许多,但也不过只是零上几度。水盆里的水仍然是结着冰晶,冒着刺骨的冷气。
祖母从水盆里捞起一件衣服,擦了肥皂,然后在搓衣板上快速搓动着,动作是那样的熟练。是啊,她的双手在那张搓衣板上搓动了几十年,怎能不熟练呢。她熟悉那张板子上的每一道沟棱,她记得哪一处缺口是哪一年的哪一天造成的。她的手是那样的粗糙,结满了厚厚的茧。我觉得那些茧就像是穿在她身上的衣服,能够阻隔刺骨的寒。一定是这样的,不然祖母的手在冰水里泡了那么久,怎么可能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我躲在屋里,扒着门缝看祖母帮我洗衣服,我的手被祖母身上的温度灼烧。
隔年夏天,我去村子西边的河里洗澡。天气突变,我淋了一场急雨,然后就病倒了。我从小就体质弱,但凡淋雨,十有八九是要病一场。轻则感冒,重则肺炎。那时候哥哥已经在读中学了,我也即将小学毕业。家里除了最基本的日常开销,但凡有一毛钱,也都给我们哥俩读书用了。
没有钱看病,祖母就搬出她的土方子给我治。她曾是村里唯一的赤脚医生,曾帮很多人治好过病。
祖母翻箱倒柜,找了好半天,终于从厨房的米缸和菜缸缝隙间掏出一个吊瓶状的玻璃瓶。她打开盖子,用鼻子闻了闻,又倒出一些透明液体在手掌上,用火柴点燃。是酒精。那些燃烧的透明液体散发着浓烈的白酒的味道。
酒精在祖母的手掌上燃烧着,浅蓝色的火苗起起伏伏。我感到恐慌。我恐慌是因为祖母说要用燃烧着的酒精帮我搓背。让火焰在肌肤上跳跃,那是多么令人不安的一件事情,它随时可能将我灼伤,就像我偷别人家的鸭子,在远离村子的河滩上烧烤一样,烧焦的脂肪透着一股焦糊。
我觉得祖母的手已经透出焦味,她那浅蓝色火焰下的手已经被烧得像极了烧红的烙铁。她用两只手揉搓着燃烧的酒精,火苗在她的手里是那样温顺。那种温顺让我突然觉得把自己交给祖母,任由她发落,内心里是踏实的。
祖母开始用她被灼热的双手给我搓背。她用力按压着我的背,她粗糙的手掌在我后背的肌肤上反复搓动。我只觉得像是被火焰灼烧般的疼痛。久了便只剩下灼热,没有了疼痛。祖母不停地用力搓动着,酒精燃烧完了,她会再倒入一些到手掌上,点燃,然后继续在我背上揉搓。我在这样一种灼热状态下,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半夜醒来,自己躺在一床厚实的被子里。炕被烧得很热,热得我出了很多的汗。我觉得身子轻松了许多,相信我的病已经被祖母治好了。看着躺在身边的祖母,她的手红得有些肿胀。我轻轻抚摸着她那双粗糙的手,她的手掌还依旧滚烫着。
多年后,我考上了外地的一所大学。读大学第一年的冬天,寒假结束,我准备动身返校。祖母不到五点钟就起床了。我被祖母吵醒,略带埋怨口气说天还没亮,起那么早干嘛。祖母听出了我语气中的埋怨,回答说给我做些路上吃的干粮,然后放轻了脚步,甚至连呼吸声都在刻意压低。
我起床的时候,祖母已经蒸好了热腾腾的馒头,并且把我的衣服放在灶台前烘烤暖了。祖母递给我烘暖的衣服的时候,我突然就后悔了,后悔早上对祖母没好气地埋怨。
吃过早饭,祖母用一只铝饭盒装了两个热馒头,又装了我最喜欢吃的蕨菜炒肉。那是祖母刻意为我一个人做的,让我在路上吃。
我在路边等车的时候,祖母驼着背,脚步踉跄地踏着雪向我的方向加快脚步。我想她是有事情要叮嘱,于是上前去迎她。她穿了一双薄底的布鞋。那鞋子是那样的单薄,它在冰冷的雪地里瑟瑟发抖。
祖母从我手里拎着的塑料袋里取出那个饭盒。她说天气那样的冷,等我中午吃饭的时候,饭菜肯定早就冷透了。吃那样的冷饭,容易生病。说着,她转过身,解开系在腰间的麻绳,那是她的腰带。她从不舍得花,哪怕几块钱,给自己买一条真正的腰带。她觉得一根麻绳足以完成需要用钱购买的腰带的全部使命。我看见她把一只手伸进裤裆里,摸索了一番,掏出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把零钱。我知道,那些钱平时是祖母随身携带着的。它们就装在祖母贴身内裤的兜里。那是祖母特别缝在内裤上的一个布兜。或许她觉得把钱放在那里最安全,没有人能偷得走。
祖母把钱塞到我手里,让我在火车上买热乎的盒饭吃。她说我一个人在远离家乡的异地他乡实在不容易,用钱的地方也多,凡事别太为了钱而难为自己。我握着那些钱,那些一块、五块,最大面值不超过十块的钱,它们透着一股热度,那是祖母的体温,在我的手心里灼烧。
祖母系好她腰间的麻绳,她的双脚在雪地里交替抬起,再落下。她那样的矮小,那样的苍老,她佝偻的身子在冷风正劲的风口瑟瑟抖着。我望着她脚下的薄底布鞋,进而蹲下身子,把手指伸进鞋子里。
我被一种透彻的冷刺痛泪腺。
祖母过世那年,我读到一位诗人的一句“母亲还热着”的诗。那首诗的背景,是诗人捧着刚刚火化了的母亲的骨灰。一瞬间,我就想起了自己曾手捧着祖母的骨灰走过短暂却无比漫长的一段路。我相信那些灼疼我双手的温度来自祖母的身体,那是她对我,对生活深深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