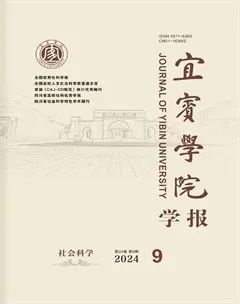自创生认知理论:BCI技术认知解释新进路
2024-12-31徐知知
摘要:脑机接口(BCI)技术的认知解释是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其中延展认知对BCI技术认知解释的争议最大。延展认知将认知范围不局限于头颅内部的观点与BCI技术对认知的实际影响是吻合的,但是缺乏透明度条件及没有脱离表征主义的认知框架是延展认知的解释始终无法脱离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BCI技术的认知解释应转向生成主义的认知,特别是自创生生成理论,它将认知系统视为一个更加广阔并赋有意义的网络,是BCI认知解释更加合理生动的新进路,
关键词:BCI;延展认知;生成认知;自创生理论
中图分类号:B80-0;TPIS
DOl:10.19504/j.cnki.issn1671-5365.2024.09.02
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 BCI)是一种新兴技术,通过交互设备使得大脑信号可以与外部世界进行交流。该技术在军事、医疗等领域被广泛运用,常见的应用形式有机械手、人工耳蜗以及其他疾病的治疗等。但是,自BCI技术研发与应用以来,学界对此的争议也尚未停止。其中,讨论的焦点之一便是此技术与认知,尤其是与“4E”相关的认知①的关系。本文将首先回顾国内外学者对于BCI技术的延展认知的争议。其次,分析BCI技术用以实现认知延展的两大困境,即无法满足透明度的要求和没有脱离表征主义认知框架。随后,本文将聚焦生成认知的特点,尤其是自主性和意义建构性这两大基石与BCI技术相联系,最后得出从延展认知转向自创生理论可以成为BCI技术的认知新范式的结论。
一、BCI 延展认知的争议
国外学者安德鲁·芬顿(Andrew Fenton)和谢里·阿尔珀特(Sheri Alpert)批判了行为主义拒绝使用任何非实体对象,如心理状态来解释动物或人类的认知的观点。行为主义将认知的产生完全归为刺激物,如看到天下雨,我就打开伞。但是,行为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刺激物与认知反应不是一一对应的。比如即使天没下雨,有人也会打开伞。反之,有人在倾盆大雨中也选择不打开伞。因此,芬顿和阿尔伯特选择支持安迪·克拉克(AndyClark)和尼尔·利维(Neil Levy)积极辩护的延展认知理论(extended mind),认为该理论可以更为合理地解释认知,并且促使人们重新看待传统记忆辅助工具的基本论点。延展认知理论将认知视为延展的,借助外部工具可以形成我们的认知,甚至扩大原有的认知范围。我们的内部认知与外部工具环境是耦合在一起的,而非单纯的内部现象或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因此,接受延展认知理论的人们更容易认可植入式或穿戴式技术取代或增强自然形成的神经认知结构,并将其视为个体认知过程基质的组成部分[1]。因此,作为延展理论支持者的芬顿和阿尔伯特坚信BCI技术的延展认知解释是合理的。此外,舍温(Susan Sherwin)将延展心智理论作为观察患者与BCI系统情况相加的透镜,“他们将该理论作为一个透镜,通过它我们学会重新审视人类与相关物理或社会环境的认知参与的特定方面”[2]。换言之,舍温将延展认知理论视作启发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BCI。除了国外学者,国内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也论证了延展认知对BCI技术解释的合理性。肖峰将BCI技术划分成治疗和增强两种功能,并将受益者分别称为“亚人”与“超人”。前者是丧失了部分正常感知功能的残障人士,而后者是原本具有正常感知功能的人借助BCI技术成为了具有超常能力的人[3]。肖峰认为二者都可以体现BCI技术的认知延展功能,且相较于一般的认知延展系统(如智能手机)而言,BCI技术对于人的认知可以有质的改变。在此基础上,认知完全是被延展的。只是认知延展能否被看作是延展认知主体有待商榷,因为这涉及延展心灵与延展认知关系的讨论。
与之相反,国外学者斯文·沃尔特(Sven Wal⁃ter)和理查德·赫斯明克(Richard Heersmink)尽管支持延展认知理论,但认为BCI技术并不是延展认知的案例。沃尔特认为芬顿和阿尔伯特的观点其实是将许多认知方法混淆在一起。因为在BCI技术的辅助下,认知只在“情境”的范畴中。换言之,认知只是被实施(enacted),而非被延展[4]。此外,生成主义代表者科斯罗(Miriam Kyselo)、豪斯明克(Richard Heersmink)等人也反对BCI的延展认知解释,他人认为BCI技术的出现恰恰对延展认知理论提出了挑战,许多现象,如最为经典的闭锁综合征(LIS)②就动摇了延展认知理论和具身认知的根基。除此之外,国内学者刘畅和叶斌通过分析BCI功能实现的机制,发现BCI技术的认知最为关键的是表征了大脑信号与行为者意图的关联,即如果BCI技术无法正确读取大脑信号,那么行为者也将无法与外部环境展开交互[5]。所以此技术的功能还只停留在传统的算法表征层面,认知的延展在算法机制下也就无法展开。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BCI技术认知解释的争议集中在是否可以用延展认知的观点进行解释的问题上。在下一节,本文将梳理和论述延展认知对BCI技术的解释,并提出它面临的挑战与质疑。
二、BCI 技术的延展认知解释及其困境
(一)延展认知对BCI 的解释
依据延展认知理论,人类的认知不仅局限于颅内,人类信息处理的“内容和方式”还必须考虑到外部环境及人类的各种物理、生理和心理特征。此观点也构成了具身认知和嵌入式认知的理论内容,延展认知可以视为这两种认知观的结合与延伸,因为它包含了这些观点的洞察力,同时也包含了个体身体外的某些事件或过程,作为个体认知过程的物理基础的构成要素[6]。克拉克通过经典的奥托与英伽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了认知是如何延展的:患有记忆失常症的奥托想要去大英博物馆,所以他借助记录详细地址的笔记本获取记忆信息,到达了目的地。正常人英伽通过搜寻大脑中的记忆便可获得相关信息,因此他也如愿到达了正确的地方。克拉克认为奥托借助笔记本的记忆与英伽大脑中自然的记忆并无实质性的差别。无论是奥托还是英伽,凭借笔记本或自身的记忆以及对于一定能到达正确地址的信念,他们的行动都产生了相同的因果效力,也都顺利地完成了目标。因而可以说,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对于认知而言,具有同等的地位,即对等性原则(prin⁃ciple of parity),这也是延展认知理论的核心。
克拉克认为事实上,我们的认知就是内部与外部工具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由各种人工制品和工具组成的世界,它们补充了我们生物大脑的能力,以便使我们更好地适应复杂的世界。这也意味我们会利用“超越大脑”的外部资源去帮助我们完成日常的生活及认知。在脑机交互的设想中也是如此。凭借BCI技术,大脑与机器的信息传递实现了一种双向流动。既可以从脑到机,将脑信号进行转换用于外部设备以实现功能增强,也可以从机到脑,将外部设备捕获的感觉信息传递至大脑。前者可实现认知功能的增强,后者可以运用于外部设备信息的捕获、提取、储存与应用。大脑中的神经元与电脑设备的信息流共同作用在一个认知网络中。对于功能失常的人来说,利用BCI技术,使得他们能够同正常人一样正常启动和保持通信,在建构的网络空间中与他人互动。如失去双手的患者可以借助机械臂操纵环境中的物体,以便同正常人一样顺利完成日常的动作。通过肢体与外界的接触,可以获取更多的感官信息,这些感官材料又可以向大脑提供更丰富的信息流,而大脑在接受这些信号后,又不断地给出反馈并发动相应的运动指令,使得身体这个“媒介”又能够收集更多的感官材料,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了更为广阔的认知网络。由此看来,延展认知对于BCI的解释似乎非常合理。
然而,如上述所言,延展认知的核心是对等性原则,而对等性原则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满足透明度的需求。接下来,我们会分析并发现,透明度将成为延展认知解释面临的困境之一。此外的另一大困境是延展认知其本质依然难逃表征主义的认知框架。
(二)延展认知面临的两大困境
透明度是实现延展认知的一个重要前提,它要求身体边界之外的任何东西如果要算作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则必须在身体与环境赋予意义的互动中“透明地”发挥作用。例如奥托在使用笔记本查询信息时并不需要深思熟虑,就如同英伽的生理回忆一样,是无意识的、快速的、易获得的一种状态。因此,笔记本在此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现象学意义上的透明设备(transparent equipment),所以笔记本既满足了对等性,与符合现象透明性需求,可以被称作实现了认知延展的功能。这就表明透明度的实现,要求足够熟练度的保证。想象一个熟练的木匠,他在使用锤子的时候,不会意识到锤子是一个独立的物体,除非锤子出现了故障。在此意义上,锤子对于木匠而言才算作是透明的。
然而,依据相关调查数据,现存的BCI技术很难轻易地被使用者操控,达到一种近似透明的状态。所谓“BCI 盲”(BCI illiteracy,又译“BCI 文盲”)就是一个典型案例[7]。他们由于某些功能缺陷,无法集中注意力于BCI技术的运用,无法熟练甚至正常的操作BCI。其次,BCI技术的使用熟练度极易受到干扰,诸如注意力水平的变化、心情低落或沮丧、缺乏良好的睡眠等因素都会影响BCI技术使用的熟练度,也就无法保证使用者维持在稳定的使用水平范围内。此外,实现认知的延展需要保证交互设备可以快速并且正确地识别大脑信号。为了满足此要求,使用者在佩戴BCI之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培训。但是在一般为期三个月至半年的培训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患者熟练地使用BCI依然是个难题。因为目前的BCI技术在实行信息转换时,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可识别的信号存在相当的局限性。因此,现有的BCI技术无法保证使用者足够的操纵的熟练度,也就无法满足现象透明度的要求,这也成为延展认知解释的棘手的问题。
除此之外,延展认知还面临另一解释困境,那就是表征主义。表征的观点是众多认知观的一种,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解释意识的“难问题”,即依靠混乱的、复杂的感官信息,我们如何感知真实的外部世界呢?表征的观点来自福多的(JerryFodor)计算机-表征理论,他将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方式运用在认知领域,认为认知就是输入-转译-输出的方式,我们的认知只能被动地、机械地接受来自外部的信息,认知也只是对外部世界的被动反映。延展认知的支持者是反对这种表征观的,他们将外部工具纳入了认知框架内,表明我们是可以通过这些工具和设备积极主动地影响认知的。换言之,我们的认知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依据身体、外部设备和行动主动地影响甚至改变认知的。尽管如此,延展认知的支持者,如安迪·克拉克认为认知还是无法脱离表征的,只不过这是一种基于环境的“选择性”表征以及以行动为导向的表征方式。国内学者叶斌认为基于表征机制,BCI技术还是得依靠算法运行,因为“认知仅仅是表征性的,由行为者的大脑信号表征他的行为意图。如果BCI无法正确读取大脑信号,那么行为者也将无法与外部环境展开交互。”
综上所言,由于延展认知面临无法解决的上述困境,本文认为或许生成认知中的自创生理论可以成为解释BCI认知的新进路。因为自创生理论支持者认为解释认知的关键是要回到人人互动的社会环境中,行为者积极地生成并维持自身,同时产生自身的价值与意义[8]。
三、BCI 认知新进路:自创生理论
生成主义的提出者吸取“正念觉知”的思想,调和了现象学“第一人称”研究方法和神经科学“第三人称”研究方法,并成功地将这种综合的“神经现象学”研究方法应用在测查癫痫病人发病先兆的实验中。这也为BCI技术的生成认知解释提供了经验支持。现阶段的生成论大致分为三种:自创生的(autopoietic)生成论、感觉运动的生成论(sensorimotor contingencies)及激进的生成论[9]。由于后两者存在较大争议,因此本文不予以讨论,而是关注自创生的生成论,因为它更强调自治和自创生的作用,关注环境、情境与认知的关系及意义的建构。
在自创生理论中,自治(Autonomy)和“ 自创生”(autopoeisis)及意义建构的概念是自创生生成论的核心。自治是与他治相反的,自治的定义是一个系统的操作和性质不是由外界设计者决定的,而是由内部之间互动而成的。“自创生”实际上是自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自创生中,系统的过程不仅产生自身,而且为系统增添了某些分子成分,增添的这些分子又反过来重构了系统的边界[10]。意义建构是又一核心概念。汤普森通过援引细菌与蔗糖关系的例子,强调了意义建构与有机体的繁衍是一体两面的[11]23-30。生物为了更好地生存,需要不断建构世界的意义,而赋予世界多样的意义之后,生物又可以更加热爱生命,提高生存的质量。本文认为,依据自创生理论的这两大基石可以解决延展认知无法解决的困境。
(一)对透明度问题的回应
有学者质疑自创生理论是否也面临透明度的困境。因为其代表人物科斯罗提出“身体对于认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置身于世界而不仅仅是神经的身体,就不可能有认知。”的观点,这是否表明身体对认知是构成性的,是否意味着身体边界之外的任何东西要算作认知系统的一部分,也就必须将透明度视作前提?本文认为这涉及透明度的强弱问题。
自创生理论强调认知是自治系统。它通过认知主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生成自身。同时,在与环境及感知的动态耦合过程中又丰富自身,扩大认知域。活细胞是自创生的典型案例。所有的活细胞都有一个半透膜,这样活细胞内部与外部环境之间就建立了一个边界。但是这个边界的存在,对活细胞自身并不意味是封闭的。相反,它要保持生命活力,维系自己的完整性与同一性,在结构上就必须是一种热力学开放的状态。换言之,在半透膜边界内部,暗含有一个新陈代谢网络,并与环境进行着持续的物质和能量交换,以便保持自身的生命力[12]。这就表明自创生理论对于透明度的要求是极低的,不涉及认知的结构性构成成分。我们的认知也是如此,内部与外部的界限在认知过程中非常模糊,且只是发挥某种作用,不属于认知的组成部分。不同于延展认知,认知的延展虽然将内部与外部共同编织在认知系统中,但内部与外部有着明确的区别,且必须发挥同等力量的作用,外部信息对此必须构成认知的一部分。这对透明度要求是极高的,想象一下我们在思考或回忆某些事时,这个过程往往是无意识进行的,我们很难察觉神经细胞是如何在其中运作的。这就要求我们借助的外部工具必须同自然认知一样,我们不会将“注意力”分配其中,除非出现异常。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至少目前阶段的BCI无法达到这样的要求。
除此之外,在构建外部世界意义的时候,活细胞会本能地表现出趋利避害的反应。它需要判断环境,调节自身的行动,这涉及认知的参与,对环境的认知评估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比如,“我”的认知本能告诉“我”黑暗是有恐怖意义的,它往往与生命受到威胁的场面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会倾向于离开漆黑的环境,目的是保存生命。在此意义上,透明度的满足并不是认知的充分必要条件,即使不满足透明度,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意义建构也不会停止,我们的认知也依然正常地进行,对环境不断评估,指导身体作出相应的行动。而延展认知只是单纯的构造认知,并未赋予其意义。通过外部工具,我们只是扩大了认知,获取了某些信息,但认知在延展理论中仅仅是“中性的”。比如我们使用BCI技术延伸了原有的认知范围,但这仅仅是出于BCI的功能解释,它与神经细胞一样,帮助我们形成认知。但它不会认为患者佩戴BCI,让他们有了对未来美好的期待,从而重新将生命看作是有价值和意义的事。因此,产生更为积极的认知能力。
综上所述,自创生理论中自治和意义建构的概念弱化了透明度的需求。尽管身体和外部工具在认知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相较于将外部环境视作认知的构成性部分的延展认知理论而言,透明度对于自创生理论既不是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因此,自创生理论可以解决透明度困境。
(二)对表征问题的回应
在表征问题上,自创生理论试图对表征主义的观点全盘否定。它融合现象学和以有机体为中心的生物学,试图重建一种“生命与心智连续”的生命观,充分体现生命与心智的自主性。
表征是指代某一事物的符号或符号集。在认知中,传统的表征理论就是外部世界在我们内部世界的反映。延展理论的代表克拉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表征观:以行动为导向的表征。然而,认知依然设定在表征范围内,就意味认知只能“推断”外部世界,不涉及意义的理解,我们是无法掌握真实的外部世界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康德的不可知论是一致的,延展认知的表征观实质在内部与外部预设了一道难以逾越的界限。依据自创生理论,认知主体不是被动地从其环境中接收信息并把信息转换成内在表征,而是通过自身行动直接参与意义的生成和建构,将物理世界转换为有意义的机体世界,从而支持主体生存与繁衍。
事实上,在许多生活案例中,对于外部世界我们不是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的,而是在与之互动中构建意义的。例如在一项有关左利手和右利手与“好”“坏”的概念关系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左利手的人更倾向于将“好”的物体摆在左边,而右利手的人则相反[13]。这充分显示了在行动与环境的交互中,人们是不断赋予世界意义的。因为对于左利手人而言,左边的物体似乎更加可控、熟悉及方便,因此会对左边的事物赋予积极地意义,反之亦然。因此,如果说延展认知论强调的是“上手实践”,那么生成认知论则是不断耦合生成的实践[14],生成认知彻底地清除了表征,以构建认知者与外部世界的意义为核心。而需要通过佩戴BCI设备的患者,他们也正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关联中找寻自身的价值,建构世界的意义,以此改善生存条件,更好地延续生命,而非只是实现认知功能。
通过佩戴BCI设备,患有功能障碍的人不再只是被动地困在受限的身体里,而是可以依据设想,主动地采取行动,获取期待或意外的感官材料来满足和丰富认知,从而继续维持或更新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通过与延展认知理论的比较,本文认为自创生的生成理论可以忽略透明度的影响,因为它并不要求外部工具构成认知的一部分,而是在与外部互动的过程中共同“涌现”的。同时,自创生理论不断提醒我们改变传统的将认知、感知及环境相分离的表征观,强调认知不是简单的对外部世界的反映,积极地投身于环境中并赋予其意义。只有这样,通过构建意义的方式真正理解外部世界,才能真正解决知觉的“难问题”。因此,自创生的生成认知论有望成为BCI的认知新范式。
结语
尽管自创生理论从认知论、本体论及方法论等方面彻底颠覆和超越了传统的认知观,并将意识、意向性、情感等非主流的元素纳入系统内,构成更为合理的解释框架,也不断地调和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认识差距。但是,它对BCI技术的解释也不是一劳永逸的。生成认知的范式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任何定论都为时过早。但无论如何,自创生理论强调行为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耦合,从而产生知觉经验并建构意义。这种心、身、世一体的整体论认知观相较于延展认知观,为BCI技术提供更为合理的认知解释。
注释:
① 第二代认知科学已经演变为“4E”认知,即具身认知(embodied)、嵌入认知(embedded)、延展认知(extended)和生成认知(enactive)。这个术语首次出现于2006年7月在加迪夫大学举行的一个关于具身心灵的研讨会上。次年,肖恩·加拉格尔在中佛罗里达大学组织了一次“4E”认知会议,正式开启了“4E”认知新纪元。具身认知强调身体在认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嵌入认知认为认知过程是对颅外过程的依赖,强调了认知主体对环境的依赖性;延展认知将认知视为部分地由身体以外的过程构成;生成认知将有机体与环境间的互动视为认知产生的必备条件。其中,前三种并没有推翻传统认知科学的表征主义框架,被称为“温和派”。唯有生成认知对表征全盘否定,因而被称为“激进的认知”。具体可参考Rowlands,The body in mind: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processes。
② LIS于1966年首次出现在临床文献中,通常由脑干中风引起,也有可能由于脑外伤或晚期肌萎缩性脊椎侧索硬化症(AIS)而发生。LIS分为三种状态:第一种是不完全状态,即患者除头部运动和手指运动外,全身瘫痪;第二种是经典状态(CLIS,意为经典锁定综合征),在这种状态下,患者的眼球垂直运动和眨眼的能力都会受到影响;第三种是完全锁闭状态(TLIS,代表完全锁闭综合征,在这种状态下,患者的身体完全瘫痪,甚至连眼球运动也无法进行。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存在这种障碍,LIS 患者仍被认为是完全清醒的,他们的认知能力普遍不受影响。因此,LIS的出现,特别是TLIS的出现,似乎动摇了具身认知和延展认知的根基。
参考文献:
[1] FENTON A. ALPERT S. Extending Our View on Using BCIs for Locked-in Syndrome[J]. Neuroethics, 2008, 1(2): 119-132.
[2] SUSAN SHERWIN. Foundations, frameworks, lenses: the role of theories in bioethics[J]. Bioethics, 1999, 3(4): 199-205.
[3] 肖峰. 脑机接口哲学研究的兴起: 国外BCI哲学述介及国内拓展的思考[J]. 河北学刊, 2023, 43(2): 43-55.
[4] SVEN WALTER. Locked-in Syndrome, BCI, and a Confusion about Embodied, Embedded, Extended, and Enacted Cogni⁃tion[J]. Neuroethics, 2010, 3(1): 61-72.
[5] 叶斌, 刘畅. 脑机接口的延展认知解释争议与表征机制[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22, 44(3): 25-31.
[6] CLARK A. Supersizing the Mind: Embodiment, Action and Cognitive Extensi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7] VIDUARRE CARMEN, BLANKERTZ BENJAMIN. Towards a cure for BCI illiteracy [J]. Brain topography, 2010, 23(2):194-198.
[8] MIRIAM KYSELO. Locked-in Syndrome and BCI-Towards an Enactive Approach to the Self [J]. Neuroethics, 2013, 6(3):579-591.
[9] 叶浩生, 曾红, 杨文登. 生成认知, 理论基础与实践走向[J]. 心理学报, 2019, 51(11): 1270-1280.
[10] DAVID A REID, JOYCE MGOMBELO. Survey of key concepts in enactivist theory and methodology[J]. ZDM, 2015, 47(2):171−183.
[11] EVAN THOMPSON. Mind in life: B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mind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2] 叶浩生, 苏佳佳, 苏得权. 身体的意义, 生成论视域下的情绪理论[J]. 心理学报, 2021, 53(12): 1393-1404.
[13] CASASANTO D. Embodiment of abstract concepts: Good and bad in right- and left-handers[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09, 138(3): 351-367.
[14] 周卓钊, 超越表征和计算: 生成认知范式理论研究[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8(4): 123-126.
【责任编辑:王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