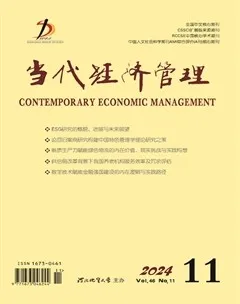论回归案例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之策
2024-11-07张志鑫王淑娟钱晨
[摘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案例研究是构建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路径。建构中国自主的管理案例研究要注重实证主义范式和诠释主义范式在管理案例中的合理运用。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时代意蕴包括中国企业的丰富实践是管理案例研究的富矿;中国管理案例研究是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工具;构建管理学的“中国话语”地位是管理案例研究的使命。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短板在于研究主体脱离管理实践,以及“问题意识”模糊难以生成有价值的案例研究结论。基于实践维度,研究主体应树立以“真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观,摒弃“唯论文”的错误认知,并且深度扎根现场;基于文化维度,管理案例研究要关注“人性”“和谐”“义利”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于价值维度,研究主体要重视管理案例研究的学理性和因果机制,避免盲目追求学术热度。
[关键词]管理案例;案例研究;自主知识体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24)11-0031-11
一、引言
作为管理学质性研究方法,案例研究因能在特殊情境中深入挖掘管理现象受到管理学者青睐,被推崇为构念开发和理论构建的有效方法。推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管理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中国企业发展和改革的难点和重点,借此以构建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为中国企业提供管理启发、学术借鉴和理论参考。为加强案例研究,助力中国管理学科整体水平提升,《管理世界》《经济研究》《管理科学学报》等26家国内知名学术期刊于2021年4月共同成立中国案例研究期刊联盟,鼓励管理案例研究者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挖掘出具有原创性、典型性和高价值的案例,促进管理研究范式持续深化转变,强化管理案例研究的学理价值和对策价值。因此,“植根企业实践,讲好中国故事”由此成为中国管理案例研究者的时代使命。本文首先阐述管理案例研究的实证主义范式和诠释主义范式,阐述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时代意蕴,随即剖析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现有问题,最后提出开展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因应之策。
二、管理案例研究的科学哲学
(一)实证主义范式与诠释主义范式
管理案例研究存在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m)和诠释主义范式(Interpretivism)两种类别[1]。实证主义案例研究范式哲学理念来源于现实主义的本体论,强调客观事物是真实存在的,事物间内在联系可被观测、洞察和揭示,是一种可复现和可拷贝的规律。采用实证主义范式进行管理案例研究旨在通过“自然规律性”赋予管理案例研究严谨性、科学性和合法性,试图揭示管理现象各要素之间的“恒常因果联系”,并以此复现其内在规律继而对其他管理或组织现象具有推测作用[2]。实证主义范式将管理现象视为相对独立的实验案例,在案例中进行数据收集和提炼,抽象出隐藏在“管理现象之外,浮于数据之上”的逻辑关系,最终构建相关管理理论。相比大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实证主义案例研究核心要点是“逻辑克隆”,取样规则并非是统计视角的正态分布随机抽样,也不以案例获取的便利性来选择案例,而是遵循“理论抽样”原则,即拟研究的管理案例是旨在建构理论或是进行理论升华[3]。理论抽样原则下,目标案例旨在彰显研究问题的独特性,最适合揭示内在的管理实践逻辑、因果关联等。如选择单案例要注重管理案例的极端性、独特性和启发性[3],其案例应具有“会说话的猪”的独特性而帮助案例研究者巡视独有的管理现象,从而对单个情境进行详实地解析和演绎。多案例研究则依赖跨案例数据分析,对不同案例中重复迭代的关系线索进行对比、总结和分析,排除其他解释的干扰并能进行更为精准的理论抽象。当前实证主义案例研究主流方法是艾森哈特教授(EisenhardtKM)的研究框架,主要步骤可划分为研究问题、数据收集和分析以及理论构建。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哲学理念来源于人文主义的批判实在论,其观点强调社会事物间的关联性并非存在恒常的规律联系,而是存在“半规律性”或者“近似规律性”[4]。诠释主义案例研究核心要点是“共情”,强调案例研究者应当深度嵌入组织情境之中,通过自身体验感受客观事物活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应互为“主体间性”。案例研究者凭借对研究对象的“共情”来挖掘管理现象潜在的思想。“共情”强调案例研究者贴近情境是至关重要的,要运用自身的感官经验与组织、个体互联互通,实现由局外人(Outsider)向局内人(Insider)的身份转变[5]。当前诠释主义案例研究采取GIOIA[6]案例研究方法论,访谈、会议等方式获取的一手数据成为重点环节,并将数据划分为运行数据(Operationaldata)和演示数据(Presentationaldata)[7],而过滤、清洗和分离两类数据是案例研究者所具备的基本能力。研究者一般需要运用扎根理论呈现数据结构,即将原始数据标签为一阶概念,通过合并总结为二阶主题,由此萃取出聚合构念,运用扎根理论表述来展示构念间的逻辑关系,再将数据结构转换为涌现理论,进行文献对话后,方能凸显理论贡献。由此可见,诠释主义案例研究关注构念的结构化编码流程,体现出从特殊到一般的共性归纳(Induction)过程。
(二)两种研究范式在管理案例中的合理化运用
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均遵循理论抽样的取样原则,依赖理论扎根于数据的指导思想,通过实地调研、半结构式访谈、会议座谈、查阅便签记事本等方式获取高质量一手数据,并依据对组织情境的持续深入适时调整数据收集过程,在数据与涌现理论之间进行反复对比,最终形成理论洞见和理论升华。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通过借鉴自然科学的实验思想推断构念之间的因果联系,案例研究设计严谨规范,借助相关数据精准定义和测度拟研究构念,便于相似的管理现象在多案例之间建立“理论互信”,提升研究结论的可比性和可移植性,构建出具有良好信效度数据支撑的新理论[8]。研究过程中兼具演绎和归纳两类研究逻辑思维。但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过度强调现象之间的“物化”关系,刻意提炼所谓的“纯事实”。事实上,组织惯例、隐性知识和个体行为特征等要素较难通过数据分析予以呈现,数据测量困难导致有意义和有趣味的管理现象无法被充分挖掘。诠释主义研究范式认为管理实践始终处于特定时空之中,受到历史背景、文化传承、群体信仰、个体情感等多重情境因素交织的影响,案例研究者要充分运用个人经验来“共情”组织个体所处的组织情境,观察、沉浸和理解组织情境所构成的“微世界”[9],成为“局内人”获取组织情境中的主观描述,确保管理案例研究作为一则“好故事”具备情境程度、抽象深度和描述厚度等基本特征。然而,诠释主义研究范式在构念定义及测量等方面过度宽松,研究设计更加依赖研究者经验阅历和思维方式等主观构想,以及缺乏案例间可比性的演绎逻辑性,难以对案例研究进行评价、掌握和学习。
当前实证主义范式成为我国管理案例研究的主流导向,在严谨规范和科学性方面推动管理案例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实证主义范式要求案例研究者完全保持“价值中立”,然而不带有任何预设的观念、假设和认知等主观因素而嵌入组织现场是难以完全实现的。若一味追求实验研究设计来控制一切因素,以期运用精确的数理思维进行管理案例研究,组织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在编译成数字时难免丧失其旨趣。事实上,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连同看似缜密的逻辑演绎,尽管有效地回答了案例研究变量之间因果效应是否存在的问题,但是因果关系潜在作用机制的“黑箱”仍未能充分被揭示。特别地,管理本身具有本土性、文化性和历史性,案例研究者要洞悉研究对象话语之外的知识黏性和规则默示性,理解组织中个体行为复杂和环境差异,由此强化对研究结论的经验性考察和整体性阐述。对于诠释主义研究范式而言,挖掘管理现象的因果关系应是研究者归纳提炼和理论抽象的重要任务,而因果关联会内生在相互嵌套、缠绕和耦合的隐蔽性逻辑中,案例研究者深嵌组织情境旨在擦拭蒙在隐蔽性逻辑上的重重迷雾,揭示因果关联“守得云开见月明”。需要注意的是,诠释主义案例研究范式依赖特定案例生成理论洞见,但若所揭示的因果关联仅适用某类案例,不具备可复现和可预期性,则会削弱其关联机制的普适性。因此,案例研究者不可因追求案例“故事性”而引致无约束的想象性,要关注目标案例与特定情境的关联程度,促使其表征一组而非某个特殊现象。
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诠释主义研究范式均为管理案例研究健康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案例研究者要全面深刻理解不同范式潜在的哲学基础、核心理念和适用情形,提炼具有属性深度的新概念、新观点和新理论,实现管理案例研究由“形似”到“UU8f0Dx/SzMviFeqV1qpKw==神似”的飞跃[10],最终完成“形神兼备”的嬗变。
三、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时代意蕴
当今处在“乌卡”时代,前瞻性技术持续涌现以及范式革命不断迭代发展,导致以往务实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思想遭遇挑战或是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加之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是对我国管理案例研究而言,反而迎来“讲好中国故事”的发展机遇。
(一)新时代下中国企业的丰富实践是管理案例研究的富矿
管理学作为实践导向的社会科学学科,构建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管理理论,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时代课题向来是理论创新的“策源”,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企业丰富实践是理论研究的“富矿”,为开展案例研究提供充沛动能和试验场域[11]。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世界一流企业构建,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均为研究中国管理问题提供了生动现实的典型场景[12],为“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素材和构件。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上半年,我国市场主体多达146亿户,比2012年的5500万户增加近16倍,年均净增长超过1000万户,活跃度总体稳定在70%。特别是以阿里、美团为代表的平台型组织,以及海尔、小米、腾讯等生态型组织的蓬勃发展,催生了鲜活的组织方式、协作模式和运营方式等微观管理实践,为我国管理案例研究开辟了“机器换人”“人单合一”等全新研究领地。“从思想世界降维至现实世界是困难的”,但这恰是我国管理案例研究的应有之义。因5o0YE6Dag3hRgO1pM8gPng==此,案例管理研究要立足我国管理实践并回应重大时代命题[13],聚焦中国企业发展改革进程的“沉疴痼疾”,深入企业观察独特现象,提出新颖观点,探索纾困之道,构建“解企业之渴,释思想之惑”的特色管理理论,为本土企业迈向世界一流行列提供管理启发、学术借鉴和理论参考。
(二)中国管理案例研究是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工具
滥觞于欧美管理实践及其体系之上的管理理论是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产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市场资源基础层面与西方存在差异,就如同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有效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简单地将西方管理理论移植过来难以有效解决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问题,发展“含摄本土情境”的中国管理理论才能有效解释和预测中国管理实践[14]。构建本土管理理论的基本路径是管理学者要聚焦企业情境问题,探索企业实践的具体内容和潜在动机,洞悉明察企业独特的实践活动,描述企业管理过程的新现象,萃取、提炼和揭示相关结论,最终生成管理理论。案例研究是基于现有理论对特定情境中一系列典型实践现象的背景和机制进行描绘、归纳、总结和分析,旨在生成富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结论的定性研究方法[15]。管理案例研究者通过扎根现场,以企业鲜活火热的真实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经过规范化研究过程,从中总结企业管理的普遍规律,最终抽象出概念化结论[16]。因此,管理学界普遍认为案例研究是管理理论构建的基本方法[17],其天然的“在管理实践中认识真理、发展真理和检验真理”的固有属性应成为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有效工具。
(三)构建管理学的“中国话语”地位是管理案例研究的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守正创新,努力实现从“跟跑追随”到部分领域的“领跑超越”[18]。2020年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数量达124家,首次超过美国企业数量(121家),实现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大跨越。然而,权力话语理论表明“话语权即为权力”,现代社会权力是建构在知识体系基础之上。我国管理学过度依赖西方学术体系,造成我国管理学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话语权较弱,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局面,话语权“失语失声”与我国综合国力和地位并不相称。管理案例研究具有从“真问题”出发,扎根“真现场”的天然属性,便于对中国企业具体实践、机制环境和创新路径深入剖析,打造被国际学术圈所理解的中国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因此,构建中国管理学体系在世界领域的话语地位成为管理案例研究的使命。值得注意的是,构建管理学体系的“中国话语”地位并不意味脱钩于国际学术体系,构建中国管理学体系不应成为管理知识全球化传播中的“休止符”,而应成为中国本土管理知识“再全球化”的“吹哨人”。借助极具中国特色的管理案例研究,凝练标识性新概念,讲好中国管理故事[19],与国际管理学术界“接头”,继而让世界认识和理解“伟大复兴中的中国”“管理学术中的中国”。
综上而言,开展中国管理案例研究,挖掘涵养中国情境的企业故事,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具有重要意义。作为管理案例而言,更应将根植于本土、面向世界的中国管理创新成果生产和传播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四、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现有问题
虽然我国管理案例研究取得蔚为大观的理论成果,但当前仍存在“主体间性”解耦和“问题意识”模糊等问题。
(一)中国管理案例研究“主体间性”解耦
“主体间性”强调自我不应是原子式个体,而是自我与外部要素共生共演,自我主体与目标客体的平等对话和亲密关系,特别是自我与社会环境的互动。管理案例研究的理想状态是研究主体与实践主体之间存在融洽的“主体间性”关系,研究过程应是双方彼此融合、双向接纳和共同理解的过程,研究主体对管理现象和实践问题的审视、洞察和认识,实现管理“在场”,并与实践主体互动、撕扯、缠绕和碰撞[20]。然而,研究主体与实践主体的“主体间性”解耦状态阻碍了中国案例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管理案例研究主体多数是从“课桌”到“讲台”的“象牙塔式”青年学术团体,其与实业工作者的学识背景、生活环境和工作状态相去甚远,加之现场实地调研较为匮乏,未能与企业管理者和一线员工进行深入交流,造成案例研究所用的访谈数据和对话纪录欠缺实用性和准确性。“主体间性”解耦导致管理案例研究主体(特别是西方求学归来的研究者)更迷恋于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去“挑捡”解决中国企业实践问题的答案,动辄“言必称西方”“生吞活剥谈外国”,淡忘了管理案例研究的实质是用来开发和构建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功能。管理案例研究主体对中国管理真实情境不作全面周详的洞察和感知,对新发展阶段下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面目“若明若暗”,抽象地、盲目地识别管理现象,不是为了解决中国企业实践问题而去创造理论,而是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去学理论。深入观察中国企业管理现状的“空气的不浓厚”,自然导致管理案例研究主体的“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
其次,管理案例研究并非是“现象到理论”的简单映射,并非对管理现象进行“照相”和“复印”,而是一项对管理实践再认识和再反思的“思维加工”过程。“思维加工”强调“去繁杂存简约”,在形形色色管理现象中,案例研究者不能充当反射管理现象的“平面镜”,而要挖掘呈现管理现象背后的因果联系,诸如转捩条件、动力来源、传导机制、边界条件和行为特征等。真实企业情境中,各类企业实践要素所发挥的实际功效并非等价,案例研究者要剔除浮于表面、外在肤浅和无关紧要的内容,敏锐嗅觉始终围绕着发挥核心作用的内容,将“埋”在无序的、重复的细节之中的关键要素、机制关联,经过规范化研究继而明晰阐述。由此可见,若将管理实践逻辑准确地摄取至管理理论上来,就离不开主体间的彼此缠绕和共生。然而,当前案例研究者为了做出“可信任”的案例研究文章,不是选择回归到原汁原味的企业实践中去感知理论结论的真理性,而是寻求所谓高质量“模板”展开案例研究写作[21]。事实上,管理案例研究的归纳逻辑特点难以制作出严格明确的流程指南。如当前推崇以斯坦福大学艾森哈特教授为代表的多重案例复制方法和以宾州州立大学乔亚教授为代表的基于扎根理论的方法作为研究“模板”,虽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管理案例研究的规范化水平,但是模式化、公式化的学术思考方式隔断了研究者对管理真实情境的审视和解析,其案例研究成果中充斥的纷繁芜杂的访谈概括表或者编码结构表仅是描述浮于表面的管理现象而已。与其说是凸显案例研究的“严谨规范性”,倒不如说此“精致性”试图掩饰文章固有缺陷,遮挡数据信息背后的管理思想和规律。
最后,案例研究通常是“事基于理,理蕴于事”,案例研究论文要揭示企业管理的客观事实和内在规律,即“文以载道”。就案例研究而言,设定科学研究步骤、研究的规范与严谨、案例研究范式与研究者限定性因素匹配度均是确保案例研究质量的关键[22],意味着案例研究者须真正扎根企业内部,掌握企业实践活动的客观事实与详实材料。然而,“主体间性”解耦造成研究者脱离企业实际,基于自身预设立场与价值观念,凭借主观阐述和归纳,以期解释企业运行的客观规律,反而异化为“道以载文”。进一步地,脱耦实践的案例研究者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依赖数据分析和编码工具,但是文章通常回避编码的方法论来源,只是用主题编码或者开放编码一带而过[23];或者数据来源依赖企业短期的集中调研,忽略访谈对象是否掌握拟研究问题的相关信息,未能有效使用其他原始纪录或者现场观摩等多源数据进行三角验证。撰写管理案例研究文章通常采用“列举文献”“描述故事”“推出结论”的三段式窠臼结构[24],普遍存在“文献”与“故事”的承接条理较为生硬,“故事”到“结论”的推导阐述欠缺缜密等问题,造成“文献对话无话可讲”和“数据无法支撑理论”等硬伤[25],所提管理建议更像是“管理遐想”,过度演绎理论价值和夸大指导作用,如此研究结论实属“无实事求是之意,却有哗众取宠之心”。
管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主体间关系的良好互动,研究者不能充当袖手旁观者,应是亲力亲为的实干家[26]。因此,研究者要“脚踏泥土、鞋挂露珠”,勤临企业基层“概查”,频进员工身旁“摸底”,洞见中国企业管理现象和关心其“成长的烦恼”,在饱含活力和真实生动的组织情境中做好案例研究。
(二)中国管理案例研究“问题意识”模糊
管理案例研究的“问题意识”是指将管理活动中某个特有现象置于管理学的学术语境中去解读,将管理问题或者现象提炼并萃取为具有学术内涵的命题,结合分析方法和合理运用相关数据资料并辅以学术语言论证推理,最终提升管理知识总量和理论含量。然而,研究者问题意识的模糊难以生成有价值的案例研究成果及理论。
首先,案例研究应秉承“真问题”导向而非技术导向。受实证主义范式的影响,案例和质性研究逐渐追求数理模型的统计特征,但是研究方法只是手段并非目的。缺乏问题导向会造成管理理论与现实管理世界背离,诱使案例研究论文过于推崇框架鲁棒、逻辑自洽和数据完美。学界批判管理研究对数理统计的痴迷宛如陷入《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兔子洞里,如管理案例研究在数据分析时过分依赖词条数目和词频等量化分析手段,而非关注问题本身。管理案例研究者应成为扎根企业以及反复思考后的“问题解决者”,忽略问题而偏重技术导向的管理案例研究生成的管理理论只能是象牙塔中的“堂前燕”,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外,多数管理案例研究都宣称自身的研究结论弥补某理论“空白”或者作出理论贡献,或许从学术视角而言,所研究问题的确是“无人研究”,但是“前无古人”并不是确定其为研究问题的理由,管理案例研究自然是以问题作为出发点,但并非任意一个管理问题都富含解决价值,也并非所有的“理论空白”都值得去弥补,凭空而来的问题意识往往是虚假问题。若盲目追求“学术时髦”,则会助长“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不良文风。研究者需要从管理现象中发现问题和感受问题,即从“无字之书”产生“问题意识”。
其次,管理案例研究应注释问题而非叙述问题。叙述问题关注“是什么”,仅强调直序、表述和陈述管理现象。管理案例研究文章离不开对案例研究对象或管理现象的描写和刻画,但是叙述性发挥的功能应是附属性,是为案例研究者解释管理现象和揭示管理真理发挥辅助效用和服务功能,若就管理现象进行纤毫俱足的讲解说明,管理案例研究就沦为“企业背景介绍”,案例研究者也就沦为“企业宣讲员”。注释问题强调“为什么”,是指对管理现象的前因后果进行剖析,以及对定义或构念的深度阐述。注释问题体现案例研究者智力活动,须以缜密逻辑推理对所占有的案例资料取舍、排列和推断,揭示关键影响和核心关系,即注释问题是对管理现象潜在因果机制的探索。当前案例研究者普遍感受是自身在企业沉浸时间相对较久,数据资料足够充分,但总是陷入无话可说的两难境地,并在提炼研究问题和案例材料之间形成“钟摆”。原因在于案例研究者将观察触角停留在企业表象,未能下沉至管理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层面。当前案例研究文章饱受诟病的缺陷恰好证实,案例研究文章仅仅关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的相关性,但是未能揭示变量间是通过何种影响机制发生关联,未能将潜在因果关系从繁杂管理现象中撷取出来,自然难以借助因果关系的影响机制提升管理案例论证的可信度。例如,以知识搜索视角来探索组织技术创新路径时,案例研究者不能仅聚焦知识搜索是否影响技术创新绩效[27],更要通过案例材料来诠释问题,从而深入揭示“知识-创新”之间存在何种特定的因果机制。再如,当前管理领域借鉴量子力学的粒子纠缠隐喻组织内外各要素的互动和演化,但研究者若无法通过管理现象来揭示潜在的作用机制和关联,那么“幽灵般的超距效应”就难免成为管理学的科幻玄学了[28]。因此,以寻求管理理论为要旨的管理案例研究,绝不是在娓娓道来一个个管理案例故事,而应在调研访谈、收集数据资料,以及后续思考进程中关注案例的事实发现和背后理论意义[12],这正是“思辨终止的地方,便是理论开始的地方”。
最后,管理案例研究应关注“中国问题”。“国之大者”的问题意识应是面向中国实际、正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29]。管理学及其理论是舶来品,西方管理理论通常是建立在其自身的文化理念和哲学思想等基础之上[30],多数管理学者对于中国管理理论的论述和解读主要借鉴西方管理哲学思想进行阐述和诠释,问题意识受到西方学术束缚。特别是以外国理论作为依据对中国管理现象展开论证,“留声机”功能自然无法解决中国管理问题。更糟糕的是,当前中国管理案例研究学者并非旨在解决中国问题而进行案例研究,而是把发表管理案例研究论文异化为期望体制权威的认可和尊重,证实自身学术水平符合体制权威的主流要求,这种“阿尔都塞式的承认”更加煽动案例研究者迷恋西方管理学术新定义、新概念和新方法,通过贩卖学术精致性讲述管理故事,试图成为“合格学者”。然而,受情境牵引的管理学,其背后思想基础和实践逻辑应折射出中国文化向度和历史意蕴,管理案例研究不注重中国问题,就难以做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管理“真研究”。从现实背景来看,当前我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启发研究者将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纳入国内和世界的双重场域中来识别、反思和提取。例如,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创新,正是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从而形成经济发展战略及相应的改革政策
,实现“洋火洋蜡”到“中国制造”的伟大跨越,缔造了国外经典理论无法诠释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由此成为中国特色理论创新的突破方向。同样地,伴随数字经济发展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必然涉及组织系统性变革和结构性演变,前所未有的问题在组织管理和生产生活中泛起涌现,组织中人的因素逐渐变得微妙,其思想洞见和价值观念变得多元复杂。因此,中国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参差交错,要求研究者在“时代坐标”指引下,聚焦中国企业现实诉求,面向中国管理问题,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在解决中国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寻立场,最终提升管理案例结论的情境性。
正如巴尔扎克所述“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毫无疑问的是问号”,中国管理案例研究者应唤起问题意识,不夹杂预设立场和固有观念进行案例研究,而是“怀揣”问题观察企业实践,对相关逻辑进行抽丝剥茧的演绎推理,继而回应问题并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正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的现实写照。
五、开展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因应之策
(一)实践维度:观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真山真水”
社会生活实践引致了以往理论难以解释的问题,形成了诸多理论空白,而任何理论都要在实践中发展,都要接受实践检验。对于管理实践的样貌、纹理和架构的案例表达,是管理理论蓬勃生命力的佐证,而基于管理理论对于管理实践中的张力、挣扎和反常的案例窥探,则为理论洞见提供契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企业实践为管理案例研究提供肥沃热土,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供给充沛动力和广袤空间。
首先,发展中国管理案例研究要树立以“真问题”为导向的实践观,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展开管理案例研究,讲请讲透中国企业管理的底层面貌。建议研究者围绕工商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及“十四五”发展规划的要求[31],洞悉中国问题,立足我国管理实践并回应重大时代命题,探索本土企业的管理和发展改革问题,聚焦具有中国现实意义和亟待突破的关键问题[32],如“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突破路径与组织管理”“大型企业组织数字化转型影响组织管理实践及理论创新”“双碳目标下的企业转型发展研究”等重点问题,以及关注数字经济下数字领导力提升路径和价值创造,员工数字能力对绩效影响等新问题。同时,高校可在实业界开展管理研究问询活动,邀请企业家“出卷命题”,指出当前实践领域亟待解决的“疑难杂症”,通过梳理和整合形成有价值的问题清单,由管理领域学者进行甄别和完善,形成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真问题”,由此展开有针对性的管理案例研究,这也是“企业之所忧、之所盼,研究者必念之、必行之”的真实写照。
其次,案例研究者应深度扎根现场。管理案例研究是一种在实际组织情境之中深入地研究当前现象的经验性考察,研究者只有置身鲜活火热的企业实践中,持续扎根现场并保持主体间紧密联系才能催生自身学术活力。建议研究者将中国独特情境的管理现象与理论相结合,在研究探索阶段,研究者躬身入局感受企业真实运作场景,观察和审视企业独特管理现象,将企业实践作为出发点并与现有理论进行对比和迭代,发现现有理论对新现象解释苍白或是有相抵之处,从而择取有价值、新颖的研究角度。研究者要科学设计结构化访谈、合理运用问卷调查,以及参与企业内部会议并做好各项调研纪录,寻找代表性样本回答相应的问题确保数据可靠性,同时将研究分析结果返回企业相关方进行准确性验证。此外,高校要鼓励研究者扎根企业内部丰富地描述管理现象的具体表现,激活在企业现场调查之上的问题感,探索具有时代特性的研究型案例。还可将学术研究基地设在当地企业内部,为管理案例研究者搭建产学研融通平台,帮助研究者以企业成员身份参与企业日常经营活动,并相抵部分校内工作量。
最后,以实践为导向要摒弃“唯论文”的错误认知。管理实践性表明有效管理是以管理结果而非学术奖励来度量的。一方面,高校应优化评价方式,重点考察管理案例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社会影响,若研究成果在实业界作出显著贡献的,在职称评审、人才申报等环节可适度向研究者倾斜。开展多元管理案例研究成果评价,建立针对企业决策、评估、咨询的案例报告评价体系。在拟定博士培养方案时将管理实践应用和社会影响作为重要考察维度,开设“管理科学哲学”“管理思想价值论”等思辨课程,帮助博士研究生认识到管理案例研究不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也不是试图刷新自身论文发表纪录,而是从中国之进、发展之果中萃取时代主题,提升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学术增量和对策价值。另一方面,国内管理学学术期刊是讲好中国管理故事的“喉舌”,期刊社应鼓励管理案例研究范式多元性以及行文风格差异性,为具有挑战性和“有悖常规”的管理案例研究文章开辟发展空间。期刊社可选取适当比例的优秀企业家纳入至外审专家库中,获取更加贴近管理实践内容的评审意见。为奖掖后学,期刊社可开辟青年学者或者博士生管理案例研究专栏,鼓励学术新秀以独立署名发表案例研究文章。
“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管理案例研究者要见证变sM2/Qwmv68XXXgRlF2iGN9UkCbOBSrsXqs6LngToP/E=局下的中国企业诸多变革和发展,案例研究要为中国企业实践服务,用求真求实勾勒出管理案例研究的最美模样。一味追求“龙门赋诗夺锦袍”所形成的管理案例研究及其理论看似“层楼巨厦,画栋雕梁”,但其背后实践价值言之无物。因此,管理案例研究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结合“国家所需”“实践所需”展开研究活动,促使蕴含丰富实践的“中国故事”及其管理案例研究赢得世界的接纳和认同。
(二)文化维度:显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真善真美”
多数研究者对于中国管理理论的论述和解读主要借鉴西方管理哲学思想进行诠释,西方管理理论是建立在其自身文化理念和哲学思想等基础之上,中国文化深层内核性导致中国管理模式不同于西方管理,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呈现鲜明的中国文化基因[33]。若缺乏对传统优秀文化真诚敬仰,中国管理案例研究及其理论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34]。
首先,管理案例研究要关注“人性”。中国优秀文化向来主张“以人为本,人为为人”,倡导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和谐关系,并强调个人发展性和再生产性,将人与泛在的物体进行明显区分,通过借用伦理、礼教和教育等教化措施,对人的情感、内心和思想进行善意劝导,用文化方式激发人性向善,推动个体生命成为自我管理的主体[35]。建议研究者应运用“共情”的态度对待人性,深入组织现场要观察人性,理解人性,站在人性立场思考管理现象,体恤人的喜怒哀乐,关心人的生存发展和情感需求,借助研究情怀的驱动,可以催生案例研究者更多建设性研究动力。研究者要克服以技术为导向的,或是独立于情感和态度之外对研究对象展开逻辑演绎,避免过分依赖理性工具将人置于相对封闭的工业车间环境来推测人的工作动机和心理预期。此外,研究者可主动发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活动,真实感受一线员工工作和生活状态,用情用力感受组织中的“人性”。
其次,管理案例研究要关注“和谐”。组织情境中充斥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对立,建议研究者学会用“有差别的统一”的观点去对待组织内部张力,在审视看似表面割裂的管理现象时,研究者要将组织现象各要素视为相互融洽、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状态,并在案例研究中体现“异种求同,和合共生”的“整体论”哲学,通过充满智慧的“和谐”思想展开案例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路径和新方法。例如,研究者在开展“机器与人”的原创案例中,不能将“人机关系”视为二元属性,应将“和谐”管理思想注入研究过程中,表明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要形成人机互补、协作、共融的良好互动关系,由此提出数字化时代下和谐管理理念,为智能化管理实践活动提供理论支撑。
最后,管理案例研究要关注“义利”。“义利”观因具有独特意蕴和文化取向成为我国基本的商业道德准则[36]。在探索以组织归因与行为关系为重点的社会责任案例研究中,建议研究者借助“义利”观来审视中国企业所遵循的“公共之利”与“经营之利”相融合的制度伦理观,意识到“义利”思想是追求经济利益和践行伦理行为之间的动态平衡,其历史逻辑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现实逻辑是一以贯之的,据此开展案例研究工作,从而预测和解释企业行为动因。研究者应避免照搬西方理论将企业视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以及“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组织”,片面强调组织行为“目的”有效性以及“手段”效率性。一旦脱离“义利”思想试图解读本土企业履责行为,研究者也就难以培养问题意识、发现核心问题,自然无法真正揭示中国企业履责的动因,相关结论也就难以提炼具有场景意识的理论框架。
高质量中国管理案例研究是富含家国情怀研究者的涵养之功,更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养育之功。若急于求成的“务实”促使研究者只顾“低头拉车”,适当“务虚”反而帮助其反思和沉静。基于历史所沉淀的优秀文化来推动中国管理案例研究,才能真正彰显“通古今指点江山,说未来经纬天地”的学术气派。
(三)价值维度:探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真知真相”
管理案例研究是将管理实践问题理论化、系统化的重要工具[37],既要做到文通句顺,又要追求文理俱美。案例研究者要揭示有学理性的管理理论,总结有规律性的因果机制,推动管理案例研究与创新“融盐于水”。
首先,管理案例研究者应关注管理案例研究的学理性。理论总是要对现象做出某种程度的抽象,然而管理案例所构建的理论绝非“管理术语互相交织的迷宫”。当前研究者过度追求研究工具的先进和精致,以此标榜其案例研究的合法性和科学性,将案例研究等价为撰写完美文章,反而忽略案例研究的学理分析。建议案例研究者要熟知不同案例研究范式的哲学基础,培育自身概括归纳、逻辑演绎的学理性分析能力,运用批判性思维观察组织客观事实,科学合理地使用案例研究相关工具,将繁杂的管理现象提炼为贴近现实的、有启发性的观点和理论。在理论演绎和逻辑推理阶段,管理案例研究者要摆脱过多的主观经验干扰,遵循科学的研究流程和合理的范式进行思维严密的推理活动。在构建理论外推过程中,讲究理论解释区域和范围界限,不可盲目膨胀和无限扩大解释边界。同时,案例研究者要持续加大案例研究的规范性训练,减少自身在研究过程中的任情随性,特别在研究设计阶段表明案例研究使用的方法及相应根据,详实地披露数据收集过程、阐述分析策略和交代处理流程,并解释多元数据实施三角验证的过程。在分析阶段,研究者要在原始证据的基础上呈现完整证据链条,从而为演绎推理提供事实佐证和逻辑支持,提升相关结论的合理可靠性。在研究启示方面,研究者要善于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出所构建理论的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并与现有理论对话对思,形成理论创新与研究缺口的学理“闭环”[38]。
其次,管理案例研究者应关注案例研究的因果机制。“讲好故事”要阐述其管理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并借助因果机制提升案例研究普适性。建议管理案例研究者关注样本属性,在关注目标企业的行业类型、发展周期的基础上,特别要运用外推逻辑对目标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实践现象和研究过程等信息进行深度描述,凝练概念、提出命题和建构理论,并通过反绎推理将相关管理理论与现象经验印证对照,即“现场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从而夯实其因果机制的“理论-实践”的价值性。进一步地,研究者利用案例现象背后的因果关联将案例本身与一般性知识建立联系来提升案例研究结论的普适性[39],所构建的理论不但解释当前案例,而且具有可移植可预测其他类似的管理实践。建议研究者将因组织情境不同所展现的管理现象差异化形式置于所构建理论之下,针对表面看似无关联的现象进行识别、对比和分析,判断在案例情境下的解释作用与其他情境下的重合度,推断所构建理论的可移植和可复现性,最终产生预测效用。需要明确的是,研究者应挖掘不同案例的关键性特征,考察各要素关联以及解释机理的相似性等“形而上的道”,而并不是纠结案例材料本身或者具体的人与事的相仿和雷同等“形而下的器”。
最后,案例研究者不应盲目追求学术热度。管理案例研究的学术热点贮藏高价值理论含量,所体现的现实问题通常处于伊始状态,例如,“基于数字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不同层面及跨层互动的公司创业导向下多主体价值共创与分享机制”“平台型、生态型组织中的管理伦理问题”等广大精微议题均值得研究者持续耕耘。当前国内26家核心期刊成立“中国案例研究期刊联盟”,旨在为高水平案例研究发表提供渠道,为研究者发表高质量的案例文章提供良好平台;与此同时,多数期刊在官网列出最新选题指南以便为案例研究者指明方向。然而,案例研究者若因期刊开设案例研究专栏便投入研究热情,一拥而上的、盲目跟风的“大跃进式”管理案例研究则会“爱之太殷,忧之太勤”,反倒是“爱之、害之,忧之、仇之”[40]。建议研究者应冷静对待管理案例研究热点,将案例研究视为细火慢熬的学术志业,保持研究定力和耐心,要以合情、合理、合用的学术作风对待研究热点,切勿将实践富矿滥采成贫矿。
六、结语
“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匠心是心的修为。在国家卓然发展的时空场域中,案例研究者要聚焦管理前沿,服务现实需求,研究中国管理问题,向世界讲述中国管理故事,用案例研究来诠释中国企业实践,建立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学理论,才是学术创造使命光荣的时代表达。
[参考文献]
[1]毛基业,苏芳.质性研究的科学哲学基础与若干常见缺陷——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8)综述[J].管理世界,2019,35(2):115-120.
[2]井润田,孙璇.实证主义vs诠释主义:两种经典案例研究范式的比较与启示[J].管理世界,2021,37(3):198-216.
[3]EISENHARDTKM,GRAEBNERE.Theorybuildingfromcases: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2007,50(1):25-32.
[4]吕力.后实证主义视角下的管理理论、实践与观念[J].管理学报,2015,12(4):469-476.
[5]GEHMANJ,GLASERVL,EISENHARDTKM,etal.Findingtheorymethodfit:acomparisonofthreequalitativeapproachestotheorybuilding[J].Socialscienceelectronicpublishing,2018,27(3):284-300.
[6]GIOIADA,CORLEYKG,HAMILTONAL.Seekingqualitativerigorininductiveresearch:notesontheGioiamethodology[J].Organizationalresearchmethods,2013,16(1):15-31.
[7]VANMJ.Thefactoffictioninorganizationalethnography[J].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1979,24(4):539-550.
[8]苏勇,段雅婧.当西方遇见东方:东方管理理论研究综述[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41(12):3-18.
[9]黄光国.“主/客对立”与“天人合一”:管理学研究中的后现代智慧[J].管理学报,2013,10(7):937-948.
[10]苏敬勤,贾依帛.我国工商管理案例研究现状、应用前景及情境化深度[J].管理学报,2018,15(6):791-802.
[11]黄群慧.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情境、历程、经验与使命[J].管理世界,2018,34(10):86-94.
[12]毛蕴诗,郑英隆.立足中国企业成长,创建管理前沿理论——毛蕴诗教授学术访谈[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0(5):1-8.
[13]吴照云,张兵红.中国管理科学体系的未来构建[J].经济管理,2018,40(9):5-17.
[14]井润田,程生强,袁丹瑶.本土管理研究何以重要?对质疑观点的回应及对未来研究的建议[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8):3-16.
[15]王梦浛,方卫华.案例研究方法及其在管理学领域的应用[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9,36(5):33-39.
[16]欧阳桃花.试论工商管理学科的案例研究方法[J].南开管理评论,2004(2):100-105.
[17]EISENHARDTKM.Buildingtheoriesfromcasestudyresearch[J].The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1989,14(4):532-550.
[18]张志鑫,闫世玲.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中国企业技术创新[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8(1):113-122.
[19]刘军,朱征,李增鑫.讲好“中国故事”——管理学者的责任与行动方向[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2(8):36-49.
[20]陈春花,马胜辉.中国本土管理研究路径探索——基于实践理论的视角[J].管理世界,2017(11):158-169.
[21]周小豪,朱晓林.做可信任的质性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20)综述[J].管理世界,2021,37(3):217-225.
[22]唐权,杨振华.案例研究的5种范式及其选择[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2):18-24.
[23]DETERDINGNM,WATERSMC.Flexiblecodingofindepthinterviews:atwentyfirstcenturyapproach[J].Sociologicalmethods&research,2021,50(2):708-739.
[24]毛基业,李高勇.案例研究的“术”与“道”的反思——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3)综述[J].管理世界,2014(2):111-117.
[25]王冰,齐海伦,李立望.如何做高质量的质性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案例与质性研究论坛(2017)综述[J].管理世界,2018,34(4):140-145.
[26]盛昭瀚.话语体系:讲好管理学术创新的“中国话”[J].管理科学学报,2019,22(6):1-14.
[27]张志鑫,梁阜.知识搜索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知识基础的曲线调节作用[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9(8):108-117.
[28]白长虹.管理研究与隐喻方法[J].南开管理评论,2020,23(3):1-2.
[29]侯志阳,张翔.作为方法的“中国”:构建中国情境的公共管理案例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1,18(4):126-136.
[30]程少川.管理学价值认知的东西方哲学观察:形式与原则[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0(1):77-87.
[31]杨俊,赵新元,冉伦.如何提升工商管理研究科学问题的需求属性?——以工商管理学科发展战略及十四五发展规划研究为例[J].管理评论,2021,33(4):12-23.
[32]井润田,贾良定,张玉利.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及其关键科学问题[J].管理科学学报,2021,24(8):76-83.
[33]段锦云,徐悦,郁林瀚.中国儒家传统中的自我修为思想:对交换范式的审视与补充[J].心理科学进展,2018,26(10):1890-1900.
[34]黄光国.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由文化“复建”到文化“复兴”[J].心理学探新,2019,39(5):387-392.
[35]张志鑫,钱晨.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J].当代经济管理,2024,46(2):41-54.
[36]张志鑫,郑晓明.赤子心峥嵘路:张謇精神对中国式管理现代化的启示[J].清华管理评论,2022(12):15-23.
[37]郭文臣,代容,孙韶声.中国管理案例研究的现状与趋势刍议[J].管理学报,2016,13(5):664-670.
[38]苏敬勤,张雅洁,贾依帛.我国工商管理探索性案例研究的发展现状及规范性评估[J].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2022,15(1):99-114.
[39]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J].中国社会科学,2018(8):126-142.
[40]赵涛.对学术热点的“冷思考”[N].光明日报,2022-01-07(11).
OntheConstructionStrategiesofManagementTheoryResearch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roughCaseStudies
—ChineseStoriesRootedintheChineseContext
ZhangZhixin1,WangShujuan2,QianChen3
(1ResearchCenterofGeneralAdministrationofCustoms,Beijing100730,China;
2ShandongAcademyofMacroeconomicResearch,Jinan250002,China;
3SchoolofEconomies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Developingmanagementcasestudies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isacrucialpathtoconstructinganautonomousknowledgesystemforChinesemanagementstudies.TobuildanindependentChinesemanagementcasestudyapproach,itisimportanttofocusontherationalapplicationofboththepositivistparadigmandtheinterpretiveparadigminmanagementcaseresearch.ThecontemporarysignificanceofChinesemanagementcasestudiesincludestherichpracticeofChineseenterpr731f5afcaaa4003872f584085a7b6a1dcba214d6e136fbce48b3ae3834bdd2feises,whichservesasavaluableresourceforcasestudies;ChinesemanagementcasestudiesactasatoolforconstructingindigenousChinesemanagementtheories;andestablishinga“Chinesevoice”inmanagementstudiesisthemissionofcaseresearch.TheshortcomingsinChinesemanagementcasestudiesincludethedisconnectionofresearchsubjectsfrommanagementpractice,andthevague“problemawareness”thathindersthegenerationofvaluablecasestudyconclusions.Basedonthepracticaldimension,researchersshouldadoptapracticeorientedperspectivefocusedon“genuineproblems”discardtheerroneousnotionof“publishorperish,”andimmersedeeplyinthefield.Fromaculturaldimension,managementcasestudiesshouldattendto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alelementssuchas“humannature”,“harmony”,and“righteousprofit”.Fromavaluedimension,researchersshouldemphasizethetheoreticalrigorandcausalmechanismsofmanagementcasestudies,avoidingablindpursuitofacademictrends.
Keywords:managementcase;casestudy;autonomousknowledgesystem;excellen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
(责任编辑:李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