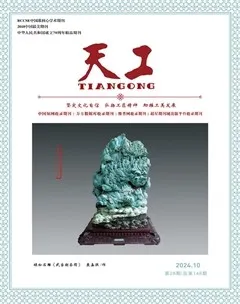先秦时期青铜器纹样的组织形式及美学特征
2024-11-04王路路
[摘 要]先秦时期工艺美术以青铜器见长,青铜器纹样作为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组织形式和美学特征充分展示了古代工艺美术的艺术美和技术美。先秦青铜器纹样在形式构成上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纹样的组成形式为对称,包含成双成对的纹样和同一图案一分为二的纹样;第二类是连续纹样,包括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形式;第三类是带状分割的组合纹样形式。从青铜器纹样及其组织形式可以窥见古人的审美风尚、工艺水平、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对当今的图案设计也有所启发。青铜器纹样的组织形式一方面与政治结构、古人的宗教信仰和审美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与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有关。旨在研究纹样组织形式及美学特征,为理解先秦文化的整体面貌提供新的视角。
[关 键 词]先秦时期;青铜器纹样;组织形式;成因;美学特征
[中图分类号]J5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556(2024)28-0094-03
文献著录格式:王路路.先秦时期青铜器纹样的组织形式及美学特征[J].天工,2024(28):94-96.
先秦一般指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先秦时代的青铜器在类别上有饮酒器、烹饪器、乐器、兵器;在造型上有仿生形态、几何形态和综合形态;在纹样上以神兽纹、仿生动物纹、几何纹、人物纹为主。这些装饰纹样都按照特定的方式进行排列组合,也可以说具有特定的规律或原则。青铜器的纹样与铸造工艺之间有着极大的关联,其呈现出来的线条、图案、形式都是古人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重要符号,凝结着古人的智慧。因此,深入探讨先秦青铜器纹样的组织形式、成因及审美特征,对理解先秦文化的整体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一、青铜器纹样的组织形式
组织形式一般指画面的布局、结构、组合方式等。先秦时期青铜器纹样的组织形式指的是纹样的布局排列、组合构成、层次结构。布局排列指纹样在青铜器上的位置、分布和排列方式;组合构成指的是不同纹样之间如何组合成整体图案;层次结构指的是纹样的层次感和结构感,即纹样的穿插重叠关系。
先秦时期青铜器纹样的组织形式多样,既有对称、均衡的布局,也有动态、变化的构图。其中,带状纹样、独立纹样和组合纹样是三种常见的组织形式。带状纹样以连续不断的纹样环绕器身或局部,形成强烈的节奏感;独立纹样则以独立的单元形式出现,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组合纹样则是由多种纹样组合而成的复杂图案,展现了古人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一)对称排列的动物纹样
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纹样组织形式以对称居多,包括独立纹样剖分为二、以呈中间对称和成双成对的纹样左右对称。对称排列的纹样以动物纹为主,包括写实动物纹和想象动物纹两类。写实动物纹如牛、虎、象等,形象生动、线条流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细致观察和模仿能力。想象动物纹则更加神秘莫测,如饕餮纹、夔龙纹、凤鸟纹等,这些纹样往往融合了多种动物的特征,创造出独特的形象。饕餮纹作为想象动物纹中的典型代表,其形象神秘而威严,象征着古人对自然力量的敬畏和崇拜。
这样的纹样组织形式与青铜器的器型有关,龙宗鑫先生总结了其组织形式的特点:划分器物的主体为两面、三面或四面(因便于等分主体,尤其是鼎多为三足、四足,这样划分可以使装饰花纹与造型紧密结合),在每一个等分面里安置一个单位样(如兽面纹),每个等分面的中心轴同时是装饰纹样的中心点,花纹由左右向中心聚集,呈对称直立状。[1]例如方形器,以洛阳北窑出土的兽面纹铜方鼎为例,取鼎的四个边棱为对称轴,左右和前后两面分别对称,且兽面又以中间凸起位置对称,恰似鼻梁。这在饕餮纹、兽面纹、龙纹、龟纹、鸟纹等中常见。又如圆形鼎,以出土于河南辉县的子龙鼎为例,圆形鼎在设计纹样时,一般将器物表面按照二、三或四份平分,再取每一等份的中线为对称轴。
从这些纹样可以看出这些动物大部分为脊椎动物,而且动物颜面自然对称。有学者认为,商周时代青铜器纹样之所以呈现轴对称是由于“任何民族对动物和人类的颜面都有深刻的印象,而凡属脊椎动物,其颜面部分均自然对称,左右平均,对一些庄严礼器装饰的处理,自觉有均齐与安足的必要,所以礼器取以颜面为主体是很自然的表现”。对称的形式不仅用于纹样,也用于青铜器造型,给人平衡、权威、稳重、安定的感觉,由此可看出青铜器装饰非常注重与器型相结合。
商周时代青铜器纹样常以成双成对的形式出现,组织形式表现为对称,如对龙纹、对凤纹等。以龙纹为例,在《楚辞》和《山海经》中数次出现“二龙”一词,如“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等。历史上关于这种对称的组织形式也有几种解释。张光直认为这和殷礼中的二分制度有关,并指出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与王室之内分为昭穆两组似乎有很密切的关系。[2]他认为,青铜器作为政治和宗教的象征,其器型和装饰必然也是商代文明现象的缩影,在王室分为两组的情况下,祭祀的器具、动物必然也要成双成对。
脱离时代背景来看,将纹样进行对称排列也与当时的制作工艺、工匠的审美有关。在青铜器的制作与成型技术中,翻制外模需要分块进行。当以两块接缝处为对称中心时,整个工作变得准确而易行。这种制作工艺上的需求促使工匠在设计纹饰时倾向于采用对称的格式,以便更好地完成制作。中国传统的宫殿、庙宇都是对称的布局,给人威严、庄重的感受。商周青铜器更是阶级的象征,将神秘、威严、庄重的图案以对称的形式呈现在青铜器上,会产生极强的稳定感和庄严的秩序感。
(二)连续呈现的动植物纹样
西周青铜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运用了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纹样。连续性纹样是用一个母题,围绕青铜器外壁,组成连续反复的图案,其中包括单一图案连续和多种图案连续。二方连续纹样是青铜器纹样中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指的是将一组纹样(单独纹样或两三种纹样组合为一个整体)沿着器物外壁左右或上下循环排列,整体图案简洁美观并富有节奏感。这种纹样组织方式使得青铜器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如窃曲纹、环带纹、垂鳞纹、云雷纹、方格纹、菱形纹等,常见于铜鼎、尊、壶、卣、罐等器物。窃曲纹的每个图案都是由卷曲的条纹构成,两个卷曲条纹以中心原点旋转对称,呈连续排列。四方连续纹样属于连续纹样的一种,指同一组纹样向上下左右四周重复连续地扩展,一般常见于器物的腹部。图案纹样以变形动物纹和植物纹为主,常见蟠螭纹、蟠虺纹。纹样的组织形式与铸造工艺有关,青铜器在制范时采用小块方格印纹法,即只雕刻一次纹样,在器物表面上下左右连续压印,这样便形成了连续纹样。
这种反复连续的组织形式常见于《诗经》,《诗经》多运用“一唱三叹”的反复形式,以强化所表达内容,也产生一种韵律感。而青铜器的纹样则用反复连续来表达有条不紊的秩序和规律。例如,《王风·采葛》中的“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通过“一日不见”的重复来表达思念之情。诗书画同源,诗中的重章叠句传情,这种处理手法增加了诗歌的节奏和韵律感。青铜器纹样不仅传达了一种秩序和规律,而且这种秩序和周代的礼治要求有一种间接的联系。[3]周代的青铜器是适应政治的需要,服从礼的规矩,在纹样组织形式上反映着礼的秩序。从纹样的组织方式看,图案纹样多运用了二方连续的带状纹样。正是在礼制的制约下,装饰纹样体现了严谨的秩序感。这种纹样的组织方式也反映了古代图案艺术的形式法则是用以恰当表现思想意识的。[4]
周代的礼治体系和青铜器的纹样有着深刻的关联,二者共同构成了周代社会的文化特征。青铜器传达了社会等级、权力象征和宗教信仰,而青铜器的纹样则通过题材、布局和工艺体现礼治的核心理念和规范。青铜器作为周代礼治的重要物质载体,不仅在祭祀和礼仪中发挥重要作用,也通过其精美的纹样传递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信息。
连续性的纹样体现了青铜器制作工艺的精湛和艺术设计的巧思,在美学特征上,给人以秩序与变化之美、节奏与韵律之美。连续纹样通过纹样单位的规律性重复和扩展,形成了有序的图案结构。这种秩序感给人带来了一种和谐、稳定的美感。同时连续的组织形式也具有寓意之美,代表着周代的制度,是古代社会的信仰、观念或文化价值观,不仅具有审美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三)带状分割的组合纹样
随着铸铜工艺的成熟、铁器的普遍使用以及装饰技术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呈现出更精彩的内容。在内容上增加了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制作工艺也更加多样,有焊接、镶嵌、刻划、镂空、金银错等。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画像故事类题材,青铜器的纹样组织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装饰纹样常以组合纹样的形式呈现。组合纹样包括主纹地纹结合和多种纹样的组合,主纹、地纹结合的纹样在商周时期十分常见,主纹和地纹的位置安排、面积大小都有很大的区别,目的是突出主纹,但又不显得单一。一般以回纹作为地纹,饕餮纹作为主纹,如团龙纹簋,簋腹饰团龙纹,龙身饰麟纹,地纹则衬以细密的雷纹。又如勾连雷纹大鼎,口沿下六个饕餮纹作为主纹,以螺旋形卷云纹衬底。多种纹样的组织方式在商朝之后十分常见,如:乳钉纹+兽面纹、弦纹+联珠纹+兽面纹、窃曲纹+瓦纹、蟠虺纹+云纹+其他等多样性组合。这种组合方式对工艺美术的影响十分深远,包括后期的汉锦、漆器、瓷器、家具等。如战国时期的采桑宴乐射猎攻占纹铜壶,以三角形的卷云纹组成连续性花边纹样,环绕器物四周对画面进行分割,分成三层六组,画面中既有丰富变化但又不失整体的协调。这种组织形式打破了程序化的图案样式,使构图自然而生动。又如金银错鸟耳壶,以条带状的绳纹将画面分为四部分,设计十分独特。带状分割的组织形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绘画式纹样装饰中十分常见。
先秦青铜器中带状分割的组合纹样形式的出现主要与青铜器的加工方法和制作技艺的多样性有关。带状分割的组合纹样呈现出节奏与韵律之美,在条理清晰中富于变化,尤其以采桑宴乐射猎攻占纹铜壶为主,有激烈战争的场面、有惬意的采桑画面、有欢庆的演艺场面,动静之间使人置身于画面中。
二、先秦时期青铜器纹样的美学特征及意义
先秦时期的青铜器纹样主要为动物纹和几何纹,动物纹形态多样、表情各异、线条流畅,趋近于写意、神似。在艺术表现上,通过抽象与变形的手法对动物形象进行夸张和重组,呈现出神秘、狞厉、怪诞、恐怖的形态。在铸造技术上,动物纹的线条流畅且富有变化,无论是飞翔的凤鸟还是狰狞的兽面纹,通过线条的巧妙运用表现得栩栩如生,赋予青铜器灵魂。在组织形式上,对称的格式能够最直观地表达出这种审美追求。它给人一种稳定、平衡的感觉,增强了青铜器的视觉冲击力,使其显得更加庄重和威严。青铜器动物纹的对称构图还具有一定的寓意和象征意义。例如,饕餮纹对称的构图可能寓意着平衡与和谐的重要性,即贪婪与满足之间的平衡。而龙纹作为力量和尊贵的象征,其对称的构图则可能强化了这种象征意义,使其更加鲜明和突出。
青铜器上的植物纹以自然界中的植物为原型,通过艺术加工和提炼,将植物的形态、结构和美感展现在青铜器上。这种表现方式不仅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界的细致观察和深刻理解,也展示了他们高超的艺术创造力和审美情趣。植物纹的线条流畅、形态逼真,给人以自然、生动、和谐的美感。青铜器植物纹的构图和布局往往非常精致和考究。工匠在设计植物纹时,会根据青铜器的形状、大小和用途等进行综合考虑,使纹饰与器物相得益彰。同时,在植物纹的组织形式上运用对称、均衡、重复等构图原则,使植物纹在视觉上呈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
三、结束语
如今,我们已经无法与当时的工匠艺人直接对话,只能通过史书资料去探索青铜纹样排列组合形式的内涵,并试图对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及体现的社会制度、哲学观点进行分析。先秦时期的工匠不仅追求技艺的精湛和纹饰的精美,还注重艺术创新和个性化表达。这种艺术追求不仅使得先秦青铜器纹饰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为后世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研究先秦时期青铜器纹样的组织形式和美学特征有助于对中国传统图案的形成和风格进行探源。
参考文献:
[1]龙宗鑫.古代铜器上的纹饰结构[J].文物参考资料,1958(11):23-27.
[2]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97-219.
[3]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58.
[4]杨远.透物见人:夏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218.
(编辑:王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