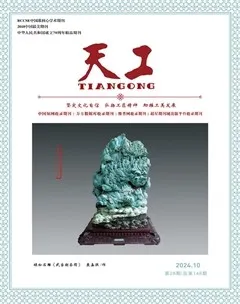唐代金银器中的屏风图样考析
2024-11-04鲍子仪
[摘 要]从设计学和艺术史的角度对唐代金银器中的屏风图样进行分析,溯源了屏风界框的产生与金银器器型的转折、时代审美风尚与绘画潮流之间的关系,指出唐代金银器中屏风界框的两种形式,同时又从空间性、叙事性、装饰功能等角度对界框功能进行对比与总结,并将金银器中出现的屏风图样内容与绘画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唐代绘画精神体系。
[关 键 词]金银器;屏风;界框;绘画;唐代
[中图分类号]K87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556(2024)28-0088-03
文献著录格式:鲍子仪.唐代金银器中的屏风图样考析[J].天工,2024(28):88-90.
屏风画作为绘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与壁画、卷轴画等共同构成了唐代绘画的重心。[1]杜牧的“屏风周昉画纤腰”[2],李白的“疑是天边十二峰,飞入君家彩屏里”[3],《历代名画记》中有“董伯仁……综步多端,尤精位置,屏障一种,亡愧前贤”等文史资料中皆记录了屏风的意涵。[4]屏风作为一种具有隔断性质的家具和装饰物,其空间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释宫》中是这样描述的:“门屏之间,谓之宁,屏,谓之树。”[5]天子视朝时,立屏风于门前,屏与门之间所形成的宁立之处,即可屏蔽。《说文解字》中载:“屏,屏蔽也。”即遮挡和阻隔之意,暗含屏风对空间分割和空间再造的功能。[6]本文将从唐代金银器中屏风界框的溯源、形式与功能、装饰图像等方面进行研究与论述。
一、唐代金银器“屏风界框”形成的原因考察
(一)器型与转折
金银器装饰中屏风界框的产生原因之一是框界对金银器器型转折的适应,这种适应离不开工匠的设计思维。屏风框架形式与媒介的相适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石制床屏以石料拼接而成为媒介,每屏画面之间相互独立,拼接的形式促使了屏风框架的形成。魏晋时期绘于单块砖面内的宴饮图,将饮酒、出行等故事内容排布于一块块狭小的砖面上,这是屏风界框适应媒介的另一个案例。出现在唐代墓室壁画中的屏风则多受制于装饰位置与墓室功能。如西安羊头镇李爽墓室北壁壁画,平视观察为实线屏风框架,视角上移则会注意到仿木建筑的融入。画中人物被均匀排布于每个仿木建筑柱间的同时,又巧妙地融入整幅建筑场景,这是屏风框架形式对建筑构造的一种适应。
当屏风框架出现在金银器这一媒介中时,需与金银器本身的形体相适应。例如,狩猎纹高足银杯的杯体装饰面无棱线分割,工匠便根据题材内容,采用植物纹样进行分隔处理。再看唐代八棱杯,杯体自身的多个转折面给金银器工匠提供了灵感来源,于是屏风的界框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转折导致面与面之间不能进行流畅地顺延,这一点和屏风本身的分隔作用相同,于是金银器工匠便巧妙地化器型转折为屏风框架,再于屏面内填充装饰内容,工匠的设计意识在这一环节发挥了重要作用。转折本身还是归因于多样的器型,不同形式的转折也为工匠在框架设计的过程中提供了理想的图样与更多的可能,因此可推断金银器器型的转折是影响其屏风框架形式的关键因素。
(二)审美与绘画
金银器中植物屏风界框的产生是受南北朝时期审美风尚和绘画潮流的影响。在研究唐代金银器屏风界框的过程中,首先联想到的是粟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唐代金银器的器型与纹样受粟特银器的影响十分深远,但以树木花卉作间隔的装饰手法在粟特地区出土的金银器中极少出现。其中少数具备分隔功能的纹样题材内容、装饰特征等均与唐代金银器中的植物屏风界框大不相同,因此这一分隔装饰手法出自粟特金银器的可能性较低。[7]同时期一并传入中原的还有外来织物,如唐代的花树对鹿织锦,此类具有外域特色的织物纹样以树为对称轴,左右各饰侧身相对的动物或人物形象,联珠纹以此为基础在织物上进行四方连续的延伸。将织物中的植物形象和金银器中的分隔植物进行对比,发现此类织物纹样内容单一,无连贯性和叙事性,且对称的视觉效果远大于间隔所产生的观感。由此推出唐代金银器中以树为间隔表现出屏风意象的装饰手法并非来源于唐代织锦纹样。
植物形式的屏风界框可以在壁画中找到更清晰的发展脉络,如南朝时期的南京西善桥墓室的模印砖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见图1),可初见与唐代金银器屏风式装饰界框的联系。再观北凉、北魏、西魏时期的莫高窟壁画,其中并没有出现植物花卉间隔人物的做法,直到北周时期,树木间隔人物的狩猎场景开始在莫高窟壁画中出现。如第428窟中出现的《策马报信图》(见图2),错落的山水空间表现了单情节的狩猎故事,其中“树”传达了空间透视的视觉效果,在画面布局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林中狩猎主题壁画在唐代还有延续,如陕西乾县唐代章怀太子墓道东壁的《狩猎出行图》、武周时期的莫高窟第321窟《宝雨经变图》局部。[8]以上列举的南北朝、唐代时期的壁画构图手法,与“狩猎乔木纹高足银杯”“架鹰狩猎纹高足银杯”近乎完全贴合,唐代金银器中的植物屏风框架发展脉络到这里便已清晰。
学者张建宇曾指出,北魏晚期的中原艺术发生了显著变革:它从平面的、概念化的图像转变为具有纵深感的立体图像。大约在20至30年之后,敦煌佛教艺术在“形式词汇”与“视觉语法”上也同样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北朝时期新兴的审美理念极大地推动了敦煌壁画的高速发展,其中“山林图式”的显著成就便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标志。[9]金银器在唐代常常被视作“画媒”的补充,以此来丰富绘画的载体。[10]“时有宇文肃,善小画、金玉镌刻之样、禽兽葩叶之能”,《历代名画记》记载了字文肃擅长金银器与玉器之设计,并绘制花草禽兽的图样之事。[4]可见在唐代人的视角中,被视为“工艺美术”范畴的金银器装饰同样构成了绘画艺术的一部分,这种潮流被复制转移到金银器、墙壁、石面等不同媒介的过程是绘画的传移与摹写。因此唐代金银器屏风图样中的以植物为分割框架的装饰手法可能是基于南北朝时期的审美风尚和绘画潮流。

二、唐代金银器“屏风界框”的形式与功能
(一)几何类界框
封闭式几何图形的屏风界框较为传统,主要是以实线组合来作为分隔的基础,对平面图样进行明确且具体的划分。此类框架的外形又可细分为U形、花瓣形、扇形、梯形等多种,界框外形不同,观感亦有差别。以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收藏的“狩猎纹六瓣银脚杯”为例,杯腹由杯棱均匀划分为六瓣,每一屏画面中均描绘了一位骑马狩猎人物奔走于狐兔间的场景。这种以矩形边框相隔的构图方式能够有效区分装饰题材与情景,在金银器表面塑造出明确的空间单元。以沙坡村出土的“鸿雁衔绶带九曲莲瓣纹银碗”为例,碗身的莲花形特殊框架被环绕一周的突棱分为上下两个区间,花瓣整体被均分为多个形状相同的U形屏面,内容题材紧凑。再观何家村出土的“唐代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当审视此类唐代金银器所采用的装饰手法与配置时,依然可见金银器转折处所发挥的装饰作用。在封闭式几何屏风格局中,由于画面题材之间互不相关,屏风内的叙事联系难以在金银器中建立,因此几何界框在同一个金银器内装饰不同的题材方面更具优势。具体且明确的矩形屏风框架线条清晰明朗、对比鲜明,密闭的图形在唐代金银器中传递出稳定感和秩序感。花瓣形、U形、扇形等屏风框架则少了一些拘谨,更多了自然与生动之感。
(二)植物类界框
金银器表面以连续的树木花卉作屏风界框,这种空间分割手法在空间营造方面更自然。西安市西郊出土的“八曲忍冬纹葵形银碗”所采用的屏风分割框架较特殊。此杯的棱线不仅是整件器型的界框,同时充当着折枝花叶的茎秆,花卉纹样以金银器棱线为轴,呈左右对称,这是金银器器型结构与植物纹饰巧妙结合的屏风式装饰手法的特殊案例。例如,西安沙坡出土的“狩猎乔木纹高足银杯”,杯身整体被乔木花束等图样均匀分为几个单元,填饰为驰马扬鞭的狩猎者形象。[11]此种以树木花卉作为金银器表面分隔的装饰手法在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狩猎纹高足银杯”中也有出现。连续的植物纹可在有限的金银器器壁空间内不断地重复与延展,在打破传统实线界框限制的同时,又巧妙地建立了与人物、动物之间的叙事联系。从欣赏者的角度看,以树木花卉所营造的屏风框架并未使观者感到突兀,反而更有效地引导他们沉浸其中。对比上述金银器中出现的有着明确界限的屏风框架,以植物纹样来隐喻界框的装饰手法更具空间感。
三、唐代金银器“屏风界框”的装饰图像
金银器中的屏风图像反映了唐朝人向往自然的审美潮流和佛道结合的绘画精神风尚。魏晋南北朝以来,绘画的功能由教谕功能向审美功能转变,受多重因素影响,士人群体普遍将文艺活动作为精神寄托,在工艺美术上体现为大量高士的形象与自然意象的涌现,如《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树下人物图》等传统绘画中的仕女、高士等形象的固定题材。[12]此类人物形象同样延续到唐代金银器上,如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银杯杯型呈现出外凸的多曲状,一幅幅定格的图像在金银器物表面生动还原了当时的狩猎、宴饮、伎乐等世俗化的生活场景,相同的还有西安未央区大明宫乡马旗寨出土的“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单柄银杯”[11]。到了宋代,仍有前朝“竹林七贤”和“树下人物”的图样留存于金银器中,如鎏金“高士图”簪花银把杯和嵌松石簪花八棱金杯,同样保留了唐代屏风式装饰手法的特征。[13]两件八棱杯以旧时的风貌延续到后世,反映出绘画流传的滞后性。器中人物如同在屏风前,展现出质朴、自然的美感,人物的写实风格契合了唐代人向往自然的心理需求。
绘画在唐代经历了一场破旧立新的变革,它兼容并蓄了本土的黄老学说、魏晋玄学与佛学,其中佛道思想相融合的“禅宗”精神是唐代绘画的整体概括。[14]钱正坤先生针对禅宗与文人画之间的关系描述到,禅宗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深入且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而山水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佛、道思想融合而成的禅宗之兴盛。[15]这场风格转变的核心,实质上是通过艺术性的画面构图手法,对外来的佛教主题图像进行了改造并融入道教元素。[16]唐代绘画的时代精神转移到金银器中则表现为杧果系树木、菩提树、忍冬纹等佛教装饰题材与竹林七贤、树下人物等道教题材的混用。唐代金银器中的屏风图像反映出佛教美术在汉地所经历的“视觉形式”的革新,这是外来信仰与中国既有美术传统相结合的证明,也是唐代绘画精神体系的证明。
四、结束语
唐代金银器中几何形界框的产生源于对器型转折的适应,植物界框的产生则是受南北朝时期的审美风尚和绘画潮流的影响,二者都离不开金银器工匠精妙的设计思维。前者能够有效区分装饰题材与情景,叙事功能较弱;而后者在空间分隔的处理上更隐晦和自然,叙事联系与空间感强。金银器属绘画艺术的一部分,唐代自然的审美潮流和佛道结合的绘画精神风尚也被金银器所记录。
参考文献:
[1]刘婕.唐代花鸟画研究[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17.
[2]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2003:5975.
[3]李白,杜甫.李太白集 杜工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218.
[4]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
[5]阮元校.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鲍里斯·艾里克·马尔沙克.粟特银器[M].李梅田,付承章,吴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8]段文杰,樊锦诗.中国敦煌壁画全集5:敦煌初唐[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86.
[9]张建宇.样式背后:省思北朝晚期风格之变[J].美术研究,2018(2):53-58.
[10]刘婕.唐代花鸟画研究的新视野:墓葬材料引发的思考[J].文艺研究,2011(1):100-107.
[11]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2]汪小洋.中国墓室壁画史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44-146.
[13]张景明.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135.
[14]姜澄清.中国绘画精神体系[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22.
[15]钱正坤.禅宗与艺术[J].美术研究,1986(3):10-15.
[16]张建宇.敦煌净土变与汉画传统[J].民族艺术,2014(1):131-137.
(编辑:王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