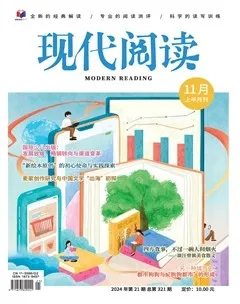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
2024-11-01明光暗影


翻阅完汪曾祺的四十余篇饮食文化散文,深感汪老实乃现当代文坛中为数不多能媲美梁实秋的大美食家—名副其实的吃货老饕!按他的话来说,除了那令人望而生畏的贵州鱼腥草招架不了,就没有什么吃不了的。在《豆汁儿》中他就幽默地自嘲道:“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可见其食之杂、食之广,得意之情之溢于言表。他甚至还为在江阴读书时未能吃上“有剧毒却美味”的河豚而引以为憾—“六十年来余一恨,不曾拼死吃河豚!”这般对美食的执着与热爱,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各方各地的美食,汪曾祺通过如叙家常般的白描式文字娓娓道来,像清澈的河流缓缓流淌于心田,让人在品读的过程中不禁馋涎欲滴、猛咽口水,灵魂仿佛也得到了滋润,从寻常质朴中感受到一丝丝温情与暖意。
在大家熟知的名篇《端午的鸭蛋》中,汪老相当自豪地介绍自己家乡的咸鸭蛋—“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并说他走过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他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他实在瞧不上!他还老顽童般不无揶揄地举了个例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对家乡5ee54a90ecc621b187a7544fcd9e4655的深深眷恋,更彰显了他作为一位资深吃货对食物品质与口味的极致追求。
如今,生吃鱼片、生蚝已是极为寻常之事,而数十年前的汪老如此热衷此味,怎么都算是先锋前卫了。在《四方食事·切脍》中,他从《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说起,文章涉足古今中外,引经据典,如数家珍地谈了“生吃”的种种,并亲自品尝过醋鱼带把、呛虾、醉蟹、醉泥螺、醉蚶子、醉蛏鼻、作料都不搁的鲜蚌……其中,汪老认为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有一次,他特地取出家乡人赠送的醉蟹款待天津客人,客人却只尝了一小块,疑惑地问:“这是生的?”便不敢再动筷。汪老对此颇为不解,“生的”为什么就不敢吃呢?还说法国人、俄罗斯人吃牡蛎,都是生食。还有一次是吃“羊贝子”,一刀切下去,会有血水滋出来,同去的人有的望而生畏,有的浅尝即止,“鄙人则吃了个不亦乐乎”。凡此种种,均可见作为资深老餮的汪老,在吃的方面是走在了时代的前端。无论多么生猛、活蹦乱跳的,他都敢直接放入嘴里,好的就是“极鲜美”那一口!
汪老对于美食可以说是痴迷,甚至见到古书古文中但凡涉及食物的内容都追根究底,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格物致知精神。比如他小时候看京剧《金玉奴》,别人关注的是剧情的跌宕、表演的精湛、服化道的华丽,汪老倒好,长大后惦记的居然是剧中出现的“豆汁儿”。又如在《葵·薤》一文里提到汉乐府《十五从军征》中的“采葵持作羹”,他不明白葵是如何可以为羹的,并逐一验证了向日葵、秋葵、蜀葵、戎葵等。直至后来读到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以及实地考察过南方省份,他才知道《十五从军征》中的“葵”是冬苋菜!这种锲而不舍、寻根刨底的精神,已不能用吃货来形容了,此乃“食神”是也!
有意思的是,汪老一生对古今中外的美食“执迷不悟”、上下求索,而如今,在他家乡高邮,有餐馆根据对其美食的考索,推出了别具一格的“汪氏家宴”,还原汪氏推崇的本真内味,深受游客喜爱,已成为当地的一张亮丽旅游名片。我最想尝尝汪曾祺自称可申请专利的一道独创菜—塞肉回锅油条,据说是酥脆香溢,“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汪曾祺的饮食文化散文,洋溢着对美好食物的热忱。但又并非普通记食散文,更非泛泛而谈的美食指南,而是蕴含着浓郁的烟火气息与深刻的人文内涵,浸润着对世事洞察的独特人生感悟。所谓“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汪老笔下的美食背后,正是那些接地气的风土人情,人生百态,柴米油盐尽在不言中,如一幅幅生动的民间生活画卷徐徐展开。蔬菜汤羹,都透着淡然和温暖;字里行间,都表达着怡然自得的豁达人生观。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每每读之,总会让人心生感慨: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正如汪老每到一处新地,不逛百货公司不逛书店,反而更喜欢流连于菜市之中,“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即便他后来身在偏远荒凉之地,也能淡然处之,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吃马铃薯都吃出了新花样,甚至还绘制了详尽的马铃薯大全图谱。
汪老写美食、谈吃喝,总归想要表达他对文艺创作和世间百态的一些看法。在《吃食和文学》一文中,他认为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兼容并蓄,方显大智。与此同时,汪老给年轻人也有类似的寄语:“第一,我希望年轻人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古人说诗的作用: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还可以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第二,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吃一点。一个一年到头吃大白菜的人是没有口福的。”
由此可见汪曾祺文如其人,温文尔雅,从容散淡,不愧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怀有一颗宽容的心及大度的容人之量。从接受不同口味的食物到接纳不同习俗的文化,鼓励世间万事万物要多尝试、多样化、多元性,或许,这就是他写美食随笔的主旨与用意所在吧—以食为引,道尽人生百态及文艺之精髓。